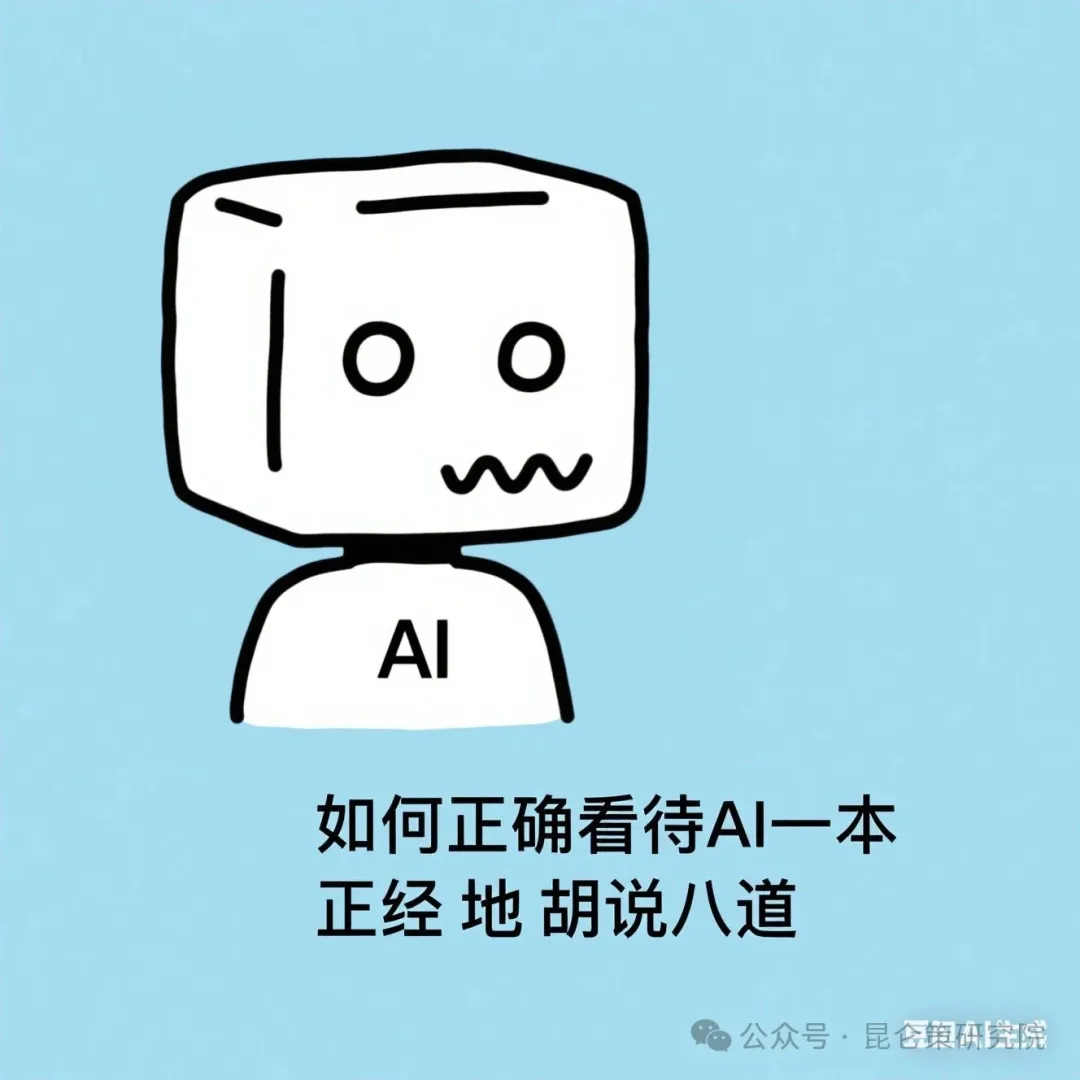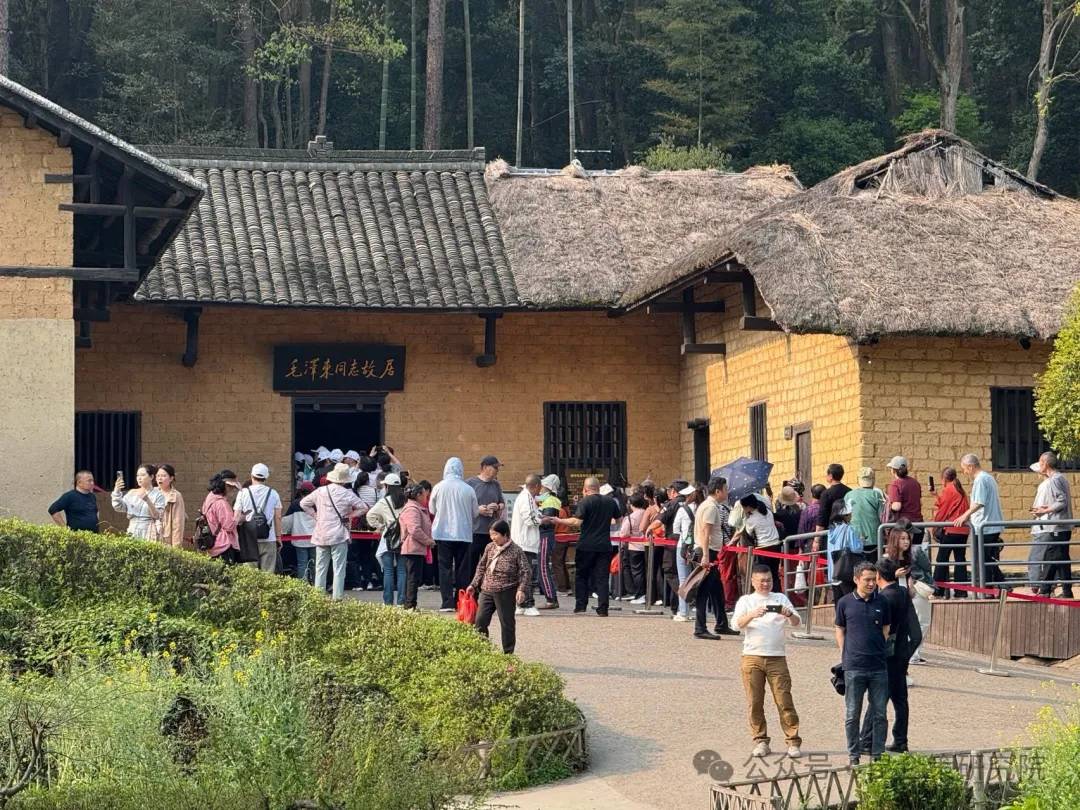刘继明:中国视野下的米兰.昆德拉
![[s]1.jpg](http://img.wyzxwk.com/p/2021/11/e33694459714a04b9de4916dda165403.jpg)
据说米兰.昆德拉的作品正在中国掀起一股新的热潮,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某家出版社经昆德拉亲自授权,出版了一套完整的米兰.昆德拉作品集却是事实,且销售业绩颇为可观,前不久刚刚结束的上海书市一天就卖出去上千册,包括网络在内的各类媒体谈论昆德拉俨然也成了一个颇为热门的话题。有人言辞凿凿地撰文说,这股悄然兴起的“昆德拉热”已经从文学界、知识界,延伸和扩展到白领阶层乃至“城市小资”等时尚读书消费群体,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品味和身份的标志,就像余秋雨的散文那样。
但这是否就是新一轮“昆德拉热”业已形成的佐证?抑或仅仅是出版商们操纵的一种广告攻势?目前尚不得而知。不过这倒勾起了我心底的一番感慨。毕竟,所谓的第一轮“昆德拉热”,据今一晃都十多年了,以至让人想起来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不是吗,当我从书架上取出那套1990年代初期作家版的昆德拉作品时,发现上面落了不少灰尘,书页都有些泛黄了。这使我不由想起最初购买和读到昆德拉作品时那种异常惊异和欣喜的心情。从韩少功和韩刚合译的那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开始,作家出版社以“作家参考丛书”陆续出版的《生活在别处》、《玩笑》、《为了告别的集会》、《不朽》以及《被背叛的遗嘱》和文论集《小说的艺术》等,我差不多每一本都有,用现在的话说,算得上一个狂热的米兰.昆德拉的“发烧友”了。这当然决非我一个人的喜好,而是当时的一种“文化现象”,说是时尚也未尝不可。在那个时候,你如果是一个写作者,没读过一两本昆德拉的小说或者对他说不出一点所以然来,那简直就会被人当作文学门外汉被人嗤之以鼻的吧。
1990年代初叶风靡中国大陆的那股“昆德拉热”,显然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境遇有着密切的关联。作为从激进主义政治环境下走出来的中国人,与曾经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捷克人,在生存体验和精神遭遇上,都存在许多近似孪生兄弟和胎记式的历史记忆。尤其是那些长时间沉溺在对文革伤痛的自怨自怜般的控诉和抚摸中难以自拔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他们读到昆德拉作品中捷克知识分子在集权体制下种种触目惊心的人性变异和荒谬处境,产生的那种感同身受显然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昆德拉以对小说艺术驾轻就熟和游刃有余的高超把握,的确比中国作家们技高一筹,把政治小说从单纯的意识形态话语提升到了一种哲理和“纯文学”的层次,并在西方世界爆得大名,成为了“为数不多的”几位在世的文学大师之一。这肯定让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模式下徘徊,一直在向西方寻求思想和艺术资源而又苦于找不到出路的不少中国作家眼睛为之一亮,从昆德拉身上看到了令人振奋的希望和启示。用韩少功先生在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前言中的话说,“中国作家写过不少批判‘文革’的‘伤痕文学’,如果以为昆德拉也只是写写他们的‘伤痕’……那当然是误解了他的创作意图,在他那里,被迫害者与迫害者同样晃动着灰色的发浪用长长的食指威胁听众。于是,萨宾娜对德国反共人士们愤怒地喊出:‘我不是反对共产主义,我是反对媚俗!’……什么是媚俗呢?昆德拉同样借萨宾娜的思索表达了他的看法:只要流行公众的存在,就免不了媚俗。不管我们鄙视与否,媚俗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
媚俗。这可是贯穿于昆德拉作品并让许多人耳熟能详的一个关键词。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和文人嘴里一不小心就会冒出这个字眼来,到今天,差不多作为一个日常用语频繁出现在大众媒体上,甚至变成人们的口头禅了。当然,其含义也许与当初的丰富内涵发生了不小的变异。事实上,在对昆德拉的最初接受和理解上,身兼中国新时期文学重要实践者的作家和译者双重身份的韩少功先生的某些观点,今天看来仍然不失为一种相当准确的解读:“昆德拉由政治走向了哲学,由强权批判走向了人性批判,从捷克走向了人类,从现时走向了永恒。面对这一个超政治超时空的而又无法最终消灭的敌人,面对着像玫瑰花一样开放的癌细胞,面对着像白花花一样升起的抽水马桶,面对着善与恶两极的同位合一。这种沉重的抗击在有所着落的同时就无所着落,变成了不能承受的轻。”
这显然敏锐地切中了昆德拉与他的中国同行和读者产生深深契合的要害,也是昆德拉在“后伤痕文学”时代的中国新一代作家和知识分子群体中获得广泛青睐的原因所在。昆德拉在其作品中反复揭示的诸如“媚俗”、“轻”与“重”、“存在的被遗忘”、“快与慢”、“忠诚”、“背叛”等等充满悖谬意味的生存命题,以及托马斯、萨宾娜、弗兰克、卢德雅克等一系列富于张力的捷克知识分子形象,大面积地进入了当代中国的文化视野,并且在不断的阅读和阐释过程中,获得了某种普遍性的意义,从而为陷入困顿和迷茫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认知框架和思想制动阀。值得一提的是,昆德拉穿越意识形态的小说叙事由于其艺术形式上的不拘一格和探索姿态,比如他对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的大胆借鉴,对博尔赫斯的情有独钟(众所周知,后者是中国先锋派作家们争相效仿倍受推崇的一位“作家中的作家”),这在不少新进作家和知识分子的眼中,显然具有一种特别的魅力与亲和感,因此对他们来说,昆德拉不仅是一个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反叛者”,还是一个艺术上的先锋派。凡此种种,都使昆德拉在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众多外国作家中,显得鹤立鸡群,占据了无人能比的地位,因此如果说昆德拉为当时的中国文学和思想史进程做出了一份特殊的贡献,如同萨特、加缪之于1980年代的中国文化界那样,堪称一位引人注目的“文化英雄”的话,丝毫也不夸张的。
只可惜好景不长。1990年代的中国文化思潮,像三四月份的天气那样波诡云谲、一夕三变,很快将昆德拉远远地抛到了后面,在文学市场上,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几乎一夜之间抢滩登陆,他那部行销全世界的小说《挪威的森林》更是赢得了日益成为一个庞大的文化消费主体的中国白领和小资们的垂青,并成为了这些新新人类的文学偶像,其发行量大概比当年昆德拉所有作品的总和还要多。在这种诱惑下,也使不少“70年代以后出生作家”跃跃欲试,催生了做一个国际性畅销作家的文学雄心。而在思想界,取而代之的是曾经与昆德拉一起被视为捷克批判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哈维尔以及其他一些鼓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如哈耶克等西方学者。90年代的中国是自由主义市场理论大行其道的时代。在全球化的召唤下,迫切与国际接轨的冲动与幻觉,使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一边借重哈耶克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国家资本化寻求理论支持,一边加大了清算和颠覆传统政治话语结构的力度,后一种努力的结果,就是哈维尔在90年代中后期的闪亮登场。在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批判和清算上,在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执著程度上,哈维尔显然是一个更坚定彻底、更符合自由知识分子理想的“标准”斗士,相形之下,作为“前流亡作家”的昆德拉就黯然失色许多了。昆德拉后来在意识形态上的刻意后撤,在“重大问题”上的闪烁其辞,以及他的个人主义艺术趣味和立场,都必然导致他像一个吃了裁判红牌的球员那样被中途罚下了场。而在中国思想界接踵而至充满火药味的那场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当中,昆德拉则沦落到了几乎被人遗忘的境地,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新左派,都根本不提他的名字。
自由主义者们不提昆德拉,自然有他们充足的理由,而新左派的“不提”,也许同样有其充足的理由。因为尽管在1990年代末,全球化的声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声势浩大,并且覆盖和渗透到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但文化环境的日渐多元化,使“西方”显然已经不再是一个君临天下的超级话语,而受到了来自“新左派”的强烈阻击和质疑。这当然不仅仅是知识分子阵营在争夺话语权,而是在推行经济市场化近十年之后,日益暴露出的严峻社会问题,迫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那种超级发展主义模式的“唯一有效性”,并且在“现代性”和“中国问题”这两大核心命题之下,试图从本土问题和特殊历史语境出发,寻找一条更加符合中国关切的发展道路,其中也包括怎样理性、全面地审视和继承现代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那场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轰轰烈烈的红色革命遗产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也许要首推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等几篇文章和对话。汪晖等人的努力显然不在于他们是否能够像许多人期许的那样,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所谓一揽子方案,而在于使人们的目光从狂热的“市场神话”下摆脱出来,将捆绑在西方发展模式上的匆匆步伐落实到日益矛盾重重布满危机的中国现实中来,并试图给予一种重新的诠释与解答。这种努力当然不会为自由主义者们所接受,随后便演变成了继1980年代之后中国思想界最具影响力的一场理论交锋。因此也成为中国迈入21世纪时刻一道最引人注目的文化风景线。
在这道风景线上,为中国知识界提供理论资源的无疑是柏克、哈维尔、哈耶克和杰姆逊以及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昆德拉似乎已经从中国视野下全然“引退”,成了一个仅仅被少数作家推崇的“专业人士”,面孔模糊、暧昧不清,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微乎其微,以至几乎荡然无存了。
那么,此时的昆德拉在干什么呢?这位早已跻身于西方主流文化,过早地赢得了“大师”头衔的前流亡作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二臣逆子”,彻头彻尾的欧洲中心主义者,像一个标准的法国中产阶级绅士,仍然在巴黎这座世界文化之都埋头著述,萦绕在他心头的早已不再是他曾经在作品中反复揭示的捷克处境。恰恰相反,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他一直在努力学会遗忘,忘掉自己的捷克身份,甚至忘掉自己的母语,将祖国的地理位置悄悄从“东欧”移向“中欧”,以便使他内心深处那种根深蒂固的“欧洲人”的身份诉求变得合法化,为此,他甚至在创作最新两部作品《慢》和《身份》时干脆使用法语,就像后来以法国作家的身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位中国“流亡作家”一样,并且获得了预期的成功,被誉为“最精粹的法语散文”。
对于这种选择,昆德拉是这样解释的:“没有人能够在两个国家、两种文化中充分地生活,虽然我同妻子只说捷克语,但是我处在法国书籍的包围之中,必须对法语世界、法国词句作出反应。有一天我必须对写作的语言有所抉择。”而且,他还以特有昆德拉式的幽默说道:“……我和法语的关系,就像一个14岁少年跟他爱得发狂的嘉宝的关系……少年对嘉宝颤声说:‘我要跟您亲热,只跟您一人亲热,您不能也爱我一点点吗?’嘉宝听了疯笑不止,说:‘跟你?哦!不,不,真的不行。’爱遭到拒绝只会更加激奋,法语愈不爱我,愈叫我爱。”这真是有点撒娇和煽情了!但如果我们知道昆德拉的妻子曾经说过,他做梦都想成为一个法国人,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诚然,昆德拉的选择是无可非议的。其实,别说与欧洲只有一墙之隔的东欧,就是在中国,不是也有不少精神上的“流亡”或准流亡作家,都在做着与昆德拉相同的“欧洲梦”或“西方梦”么?
只是,曾经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参与到中国思想进程的的昆德拉,这么快就变成了一张褪色的旧照片,徒使许多曾经热爱过他的人暗自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但在这种情形下说一说昆德拉的意义也并非仅此而已。透过他,如果能够一窥199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风云流转、起起伏伏的嬗变过程,不是也颇值得细细玩味吗?
其实,变化的不是昆德拉,而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己;或者说,昆德拉的变化完全是他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无关。事实上,从一开始,昆德拉就是作为一个“他者”被中国视野过分热心地阅读和塑造着。仿佛一个顾客在柜台上的一大排琳琅满目的工具面前选购,用完了这件工具后重新选购另一件工具,全凭他随心所欲使然,顾客无可指责,工具本身也是无可指责的。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市场上可能刮起新一轮的“昆德拉热”,我也完全相信。只是这个昆德拉已经不再是十年前的那个昆德拉了。千万别再将他跟“知识分子的文化诉求”这类深奥的题目联系在一起。明摆着,此次昆德拉的重返中国,完全是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出现在图书市场上的。是购买与被购买、消费与被消费的关系,而不是选择与被选择的关系。所以说昆德拉会更多地被中国城市小资和白领们接受与青睐,倒是一种符合逻辑的推断。这除了中国日渐成熟健全和“国际化”的文化市场,当然还缘于昆德拉作品具备的“可消费性”有关。尤其像他的新作《慢》、《身份》,那种对中产阶级生活情状的机智表达,将心灵深处的存在焦虑转换为不同国家和身份的文化大众都容易接受的软性话语等等,都使人们不难看到那个充满幽默感的机智过人的昆德拉的影子。比如他在《慢》中讨论性,说做爱要品味,生活也要品味。不宜太快:“……太激奋就不够细腻,好事前的种种妙处不及品味就匆匆奔向欢乐。太快是个宿命的不可避免的错误。十八世纪的T夫人就知道当着人可以买弄风情,却要躲着人寻欢作乐的道理。事情发展太快时,她会降速,设计小屋插曲,使得她与骑士幽会的最后阶段,在新的背景下绸缪缱绻,享受慢的极致……”
还是那个昆德拉,那个喜欢“耍嘴皮子”,擅长从日常生活中寻求微言大义、举重若轻的昆德拉。句句都能撩拨起城市小资和白领们的心理期待。就这个意义上说,昆德拉堪称一个“煽情高手”了。但昆德拉真的会像村上春树等人那样毫无裂痕地将自己融化到后现代消费大潮的文化快餐当中去吗?或者说,作为法国人的昆德拉真的能够完全“删除”曾经弥漫在他的许多作品中的“捷克记忆”吗?对此,我倒有点儿心存疑虑。
昆德拉在《魔论》一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他在捷克见到廉租公寓时,高音喇叭随时随刻灌输一个意图,觉得缺乏以人为本的居住理念,让人感到有些可怕,可当他到了法国才知道:
“到处横行同样的官僚主义。大企业对使用者的蛮横代替了阶级斗争。手工艺技艺日益衰落。讨好青年的官场演说愚不可及,假期旅行类似牲畜放牧,农民手工劳动逐渐消失,使田野变得丑陋。这些公约数中最糟糕的一点是对个人和私生活的不尊重。这里有人挥舞神圣的‘知情权’为此辩护……不论什么制度,我们大家在这里和那里,都是生活在一个被同样深刻的倾向控制的世界……而这里面对这些荒谬现象,却有心把它们看做是神圣民主制度下一件无辜的常事或者一个必要的属性。”
哦,这是我曾经熟悉和喜欢过的那个昆德拉,那个热衷于不断向存在发问,锋芒毕露、富于批判精神的昆德拉。但今日中国的城市小资和白领们不一定喜欢。置身于文化超市的昆德拉现在可是属于他们,而不属于我了。
写到这儿。我恍然意识到,昆德拉已经是年逾七旬的老人了。对于这样一个老人,我们还能够指望他走多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