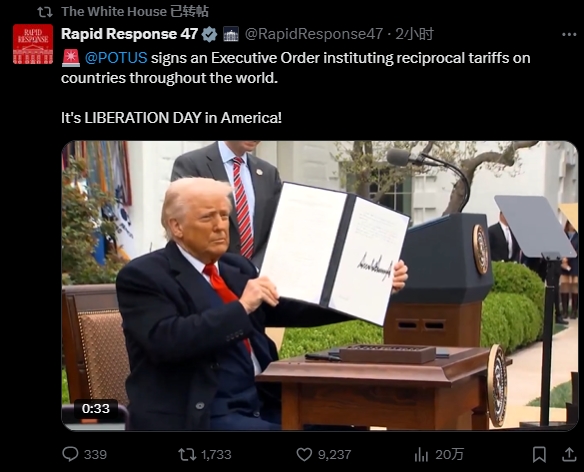欧洲金靴| 李泽厚:一直亡命着的旧制士大夫
11月3日,根据赵士林消息,“哲学家”李泽厚先生在美国科罗拉多时间昨日清晨7时逝世,亡岁91。
李泽厚生于1930年,湖南宁乡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学热”与“‘美’学热”中,李泽厚曾被青年人尊为“精神导师”,是右翼自由主义文人的代表人物之一。
昨日亡讯一出,一干南方系媒体旋即倾巢而动、哭天喊地地披麻戴孝,其中以“噗通”一声跪叩不起的凤凰网为首,集体鬼哭狼嚎,泪淹中文社媒……

1
李泽厚的名声很多人其实还是知道特别是他的那本《美的历程》,辐射范围确实过广。
但宣布死讯的这位赵士林先生,今天许多年轻人恐怕知之甚少。
事实上,通过了解赵士林这个李泽厚的得意门生,就可以一窥李先生的政治风貌——赵士林,一个坚定的反共反华分子,1992年(也就是李泽厚逃往美国的那一年)曾主编过一本奇书《防“左”备忘录》,书中罗织了李泽厚、沙叶新、胡绩伟、张显扬等反共亲美学者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
数年前,赵士林还曾与戴旭公开撕逼,吃相极为难看,此处不便多述。
还是说回李泽厚。
李泽厚少年时曾就读于宁乡四中和湖南省第一师范,是毛泽东主席的校友,甚至他还(曾)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全班就我一个人倾向进步,后来被学校拉进黑名单,还突击检查我,不过我事先把书藏好了。”
“我还一直想加入共产党,当时湖南大学就有地下党,后来因为母亲死了要奔丧,等回来以后再找这个人,就找不到了。可能他们也不会接收我,我当时太高调了,周围人都以为我是共产党,连我弟弟都这么以为。”
“我当时也是不要命的。去送毛泽东的一个文稿,街道上真是军警林立,我把文稿藏在鞋垫下面。所以我对一些学生说,不怕死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怕死过,但那不解决问题。”
上述这番表达,乍一看仿佛是一位优秀的青年赤色才俊……然而命运始终为历史的行程所左右。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蛰伏了二十年的他一口气拿出《批判哲学的批判》(1979)、《中国思想史论》(近代1979、古代1985、现代1987)、《美的历程》(1981)、《华夏美学》(1988)、《美学四讲》(1989),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了所谓“青年偶像”。
有人这样概括:在80年代,邓丽君是爱情的启蒙老师,李泽厚是思想的启蒙老师。

1986年,“解脱禁锢”、放飞自我的《人民日报》都忍不住刊登一篇雄文:《请听北京街头书摊小贩吆喝声:李泽厚、弗洛伊德、托夫勒……》…
而通过李泽厚的作品和言论,我们倒也可以清晰地梳理出这位李先生对待历史、特别是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的诸多看法,以及由此引申的他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制度的评判纠结。
2
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等人炮制了一本《告别革命》,书名就很言简意赅。
在这本书里,李泽厚把马克思主义污蔑曲解为“吃饭哲学”、“经济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
关于经济决定论,早在1975年,一位后来坐镇头把交椅的同志在任职中科院时,毛主席就用两个字概述过他的经济决定论:“放屁!”
那位同志到底放了什么屁,让毛主席勃然大怒呢?
主席他老人家当时已82岁,但是思路依然非常清晰:“他就是放屁!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是放屁是什么?科学技术是渗透到生产力各个要素之中的,是通过提高各个要素的质量来发挥作用的,并不是与生产力其他要素相并列的独立要素,并不能独立存在,所以不能与其他要素去并列排行第一第二。”
二十年后,李泽厚先生却还在咀嚼陈年旧粪……
李先生本人实际是不差钱的,他的不差钱体现的正是新中国对知识、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后世的后来者多以1992年李泽厚出走美利坚而蝇营狗苟,但没有人会去探究新中国曾在一穷二白搞建设的背景下给予了像李泽厚的学者怎样的呵护。
1956年时,李泽厚就拿过每千字20元的稿酬,这是当时的最高标准,业内一般为10元左右。他还买过一个电动唱片机,不用手摇,这在当时是绝对的奢侈品,他就是这样在小资情调里搞创作。
即使是在被下放的60年代,他被开除了公职,但依旧巨额的稿费支撑,约有2000元,相当于现在的二三十万元。
1960年从乡下回京,李泽厚到高级饭馆去吃了好多次,点肥肉不看价格。这都是李先生的自述。
在那个全中国人民为了工业化、为了国防现代化、为了两弹一星、为了巩固政权主权而勒紧裤腰带大干特干的年代,李泽厚则直言:“我没有饿到那种程度。”
因而不难理解,为什么“没有饿过”的李先生会大力主张“阶级合作而非阶级斗争才是历史主流”,在他的思维里,当代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满足中国人的生理需要,为了吃饭、为了发展经济、为了性交,中国人应该告别革命。”
马克思主义,就这样被篡改为“生产力哲学”与“兽性哲学”,并被成功灌输给此时春潮涌动、春心萌动的中国人。
荼毒之下,随着经商下海、黄赌毒复活、假冒伪劣蔓延、诈骗偷窃兴起……中国社会开始变成私欲膨胀的自由主义兽性社会。
3
在80年代中后期,李泽厚大力鼓动经受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青年应当变成“野兽”,并主张“多元的情爱”。
在李先生的认知中,中国人不仅要有夫妇之爱,还要有情人之爱,只要不得艾滋病、不怀孕即可,这和李银河的观点一模一样。
根据后续在1995年出炉的《李泽厚与刘再复对谈:理念与爱欲-论情爱的多元》的披露,可以看到李先生的言论有多么炸裂:
“夫妇的爱和情人的爱,不能相互替代。中国只讲夫妇的爱,认为此外均邪门……其实,可以有各种不同层次、不同比例、不同种类、不同程度、不同关系的性爱。我们不必为性爱这种多样性、多元性感到害羞,而应当感到珍贵。”
90年代中后期,正是在李泽厚等“美学”学者的隔岸吹风下,伴随着自由化大潮由于南巡讲话的再度涌起,文学创作中的“欲望化”叙事逐渐成为新风尚,文人们开始迫切追求利用人体器官来表现自己的卓尔不群。
一夜之间,本是个个自称文学家的人,通通成了生物老师。
“躯体语言”书写和“下半身”写作在90年代末的兴起,使得一部分人关于人性的解读,走向了一种极端。
《2000年中国新诗年鉴》曾刊载一奇文《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宣称:
“我们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传统、文化、知识等外在之物异化了,污染了,已经不纯粹了。太多的人,他们没有肉体,只有一具绵软的文化躯体,他们没有作为动物性存在的下半身,只有一具可怜的叫做‘人’的东西的上半身。”
“我们只要下半身,它真实、具体、可把握、有意思、野蛮、性感、无遮拦。”
“只有肉体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艺术以第一次的推动。这种推动是惟一的、最后的、永远崭新的、不会重复和陈旧的。因为它干脆回到了本质。”
这在当时被一帮早就憋着淫欲的臭笔杆,欣喜若狂地奉为圭臬:“这是21实际中国民间文学的‘启蒙宣言’!”
同年7月,这篇文章的作者沈浩波创办《下半身》诗刊,并收录了那篇惊为天人的《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
当闸门被放开,饥渴难耐的“文学家”们就立刻撒开了欢,“三陪”题材日渐火热,如巴乔《一起走过的日子》、张者《朝着鲜花去》等。
个个张着血盆大口、流着瘟臭的哈喇子,用键盘飞速敲击着对“下半身”极其病态的描摹与欣赏。
你敢对这样的作品评论一句“恶心”?马上就有乌央乌央的“学者”、“文学专家”们蜂拥而至,一边擦着口水,一边怒目圆睁得诘难你是“土掉渣”、“老保守”、“不开化”、“不懂潮流与艺术”………
2006年,李泽厚在《情本体和两种道德》一文中大谈特谈动物性情欲的合法性:“中国讲的是理性融入感情,人之所以爱人是由生物性自然情绪提升而来,是一种理性化了的自然情感。我讲‘情本体’并非专指中国传统,它有人类普遍性……它就来自这个‘道始于情’……而情欲的相联相异,错综复杂,对人的生存具有本体意义,在今天和今后更将成为生活的核心部分。”
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被抬上天,鲁迅退居了二线。
4
当李泽厚在捌玖十年代大张旗鼓地为中国新兴的精英阶层和死灰复燃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大唱艺术赞歌和美学魅力时,不知道他会否还记得,自己青年时曾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
马克思曾多次谈到:“非常操心的穷困的人对最美好的戏剧是没有感觉的,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
马克思还有过一段更辛辣的点评:“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一个方法可缩短、简化和集中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
所以呀,不难奇怪李泽厚会提出“告别革命”,且会在世纪之交说出这样的话:“我是坚决支持加入WTO的,小平的改革将中国从毛时代解放出来,加入WTO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殊不知“世界工厂”之中,无数血汗工人的生命和青山绿水的环境为GDP做了嫁衣。
可是在彼时之年代,远在大洋彼岸指点江山的李泽厚就是国内一众学者和媒体奉为圭臬的大拿。
他说“一个吃掉另一个是单向思维,双向思维是对话,而且要平等对话、协商。世界上没有什么问题不可以协商解决,要有这信念。”
身位的转移、阶级的堕落,可以让他忘记青年时挂在嘴边的“消灭私有制”。
“改良不是投降,不是顺从,改良也是斗争,而且可能是非常尖锐的斗争。”这恰是李泽厚引以为傲的“告别革命”理论的真实写照。
但是恩格斯说得好:“矛盾绝不能长期掩饰起来,它们是以斗争来解决的。”
由此可见,让李泽厚在改革开放历程的前二十年中飞上枝头成凤凰的,并非什么美学,实际就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学。
对于四五运动的看法,李泽厚是“救亡压倒启蒙”这番胡适式理论的评论鼻祖,即“反抗压倒下跪”,中国人应当向西方下跪,而五四运动耽误了伟大的下跪进程。
李泽厚之流理解不透的地方是,中国人其实早就被“启蒙”了,正是西方人对我们的循循启蒙,让中国人抽起了大烟,让中国诞生了买办,让中国迸发出了“割据合理论”与“曲线救国论”。
这都是“启蒙”的成果。
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斩断了这一条滴着血的启蒙利益链。换句话说,拿起枪炮,暴力革命,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启蒙——真正的启蒙。
从历史来看,李泽厚的“呼唤启蒙”行为,确实成功让“启蒙”一词成为中国HeShang一代的圣词,造就了大批流毒难去的公知群体。
直至今日,仍旧迷乱舆论场。

至于如何启蒙,李泽厚给出的方子是法治:“启蒙要走向真正的建设,首先是法治的建设,这方面要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和步骤。”
但配合着李泽厚对一党执政与群众路线的排斥,所谓“法治”背后的资产阶级法权思维,或许才是李先生真正青睐的路数。
5
1995年,李泽厚提出著名的现代化“四顺序论”: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这是其经济决定论的延续,也为后来在中国进入新时期、新航道时他再次出来大放厥词,埋下了理论铺垫。
2013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授权新华社刊发《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党的新领导班子献给中国人民的一份大礼,其时震动全球。

对于《决定》,八年前的李泽厚不安寂寞,或者说表现出了某种“担忧”和“不安全感”,他立即针对《决定》大声呼吁:“中国的国企集团必须改掉,这样民主宪政就不是问题了!”
何为“民主宪政”?不过就是要中国共产党让出执政权罢了。
在私有化和市场化早已大行其道三十年的历史当口,竟然还要求将国有企业这个党和人民最后的一块堡垒肢解,称李泽厚为“舆论打手”已经不足以描绘其能量了。
汇合那一年《南方周末》那篇肆无忌惮的《新年献词》,李泽厚也成功站上了舆论战线的前三排。
“经改的阻力非常大,相对而言,政改很容易”——相信吗?这就是李泽厚先生在那时的原话。
你不由不想起二十余年前他声名鹊起时,当时的世界头号政治明星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手术方案,同样是“要经改,先政改!”
甚至,连如何毁灭媒体业和意识形态领域,李泽厚都仿佛照着戈尔巴乔夫的葫芦画瓢:“今天中国只要一声令下开放报禁,第二天就可以实现(政改)!”
那一阶段,李泽厚留下的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我讲过,我们应该明确‘中国不要走哪条路’,比如重庆唱红打黑的那条路!”
………无需多言…李先生经年累月呐喊的“西体中用”也便充满了逻辑性。
跋
在李泽厚的世界里,主张天下大同、政治归一,这在长久以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依旧对抗激烈且地球资源日益枯竭的现实面前,无异于是一种“圣母政治”的异想天开。
他没有对疫情给出过建议,否则我相信以李泽厚的调性,他会很赞赏“与病毒共存”说。
李泽厚并不过分推崇美国文化,相反,他不止一次批评过西方精神文明的匮乏。
但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文明,李泽厚同样没有探索出一个立体化的认知——尤其是,他经历过1978年为界的前后两种态势,却仍然无法给出一句公允的评论,这不失为一个巨大的遗憾。
他反对极端自由化,他认同中央集权的效率,却又时时刻刻以一种被裹脚布束缚的姿态对所谓“新威权主义”指手画脚。
他很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的问题是“封建主义”,而非“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才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也是阻碍中国崛起的最大抗力——但是,他寻求药方的路径却是否定整个党的制度,而试图去从儒家千古、民族性格的框架里探索答案。
这显然是走回到了一百年前的老路,并否定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合法性、合理性。
一方面,李泽厚始终无法“放下身段”让自己成为群众一员(他只想做精英、做艺术大咖);另一方面,他又在整个九十年生命里所看到的“人民伟力动天地”的现实中陷入彷徨,这让他自始至终处在左右两不是的境地里。
他肯定毛主席,他不止一次地认为拿蒋和毛相提并论是对主席的折辱;但同时,他对毛主席时代的人民本位,又向来表现得万分惊恐、害怕、排斥……
对李泽厚这样的人,毛主席倒曾给出一个鲜明的揭露:“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告别革命,就是告别自己。
李泽厚之流,属于他们的身份永远只能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被专政对象。
“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
【文/欧洲金靴,188金宝搏体育官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