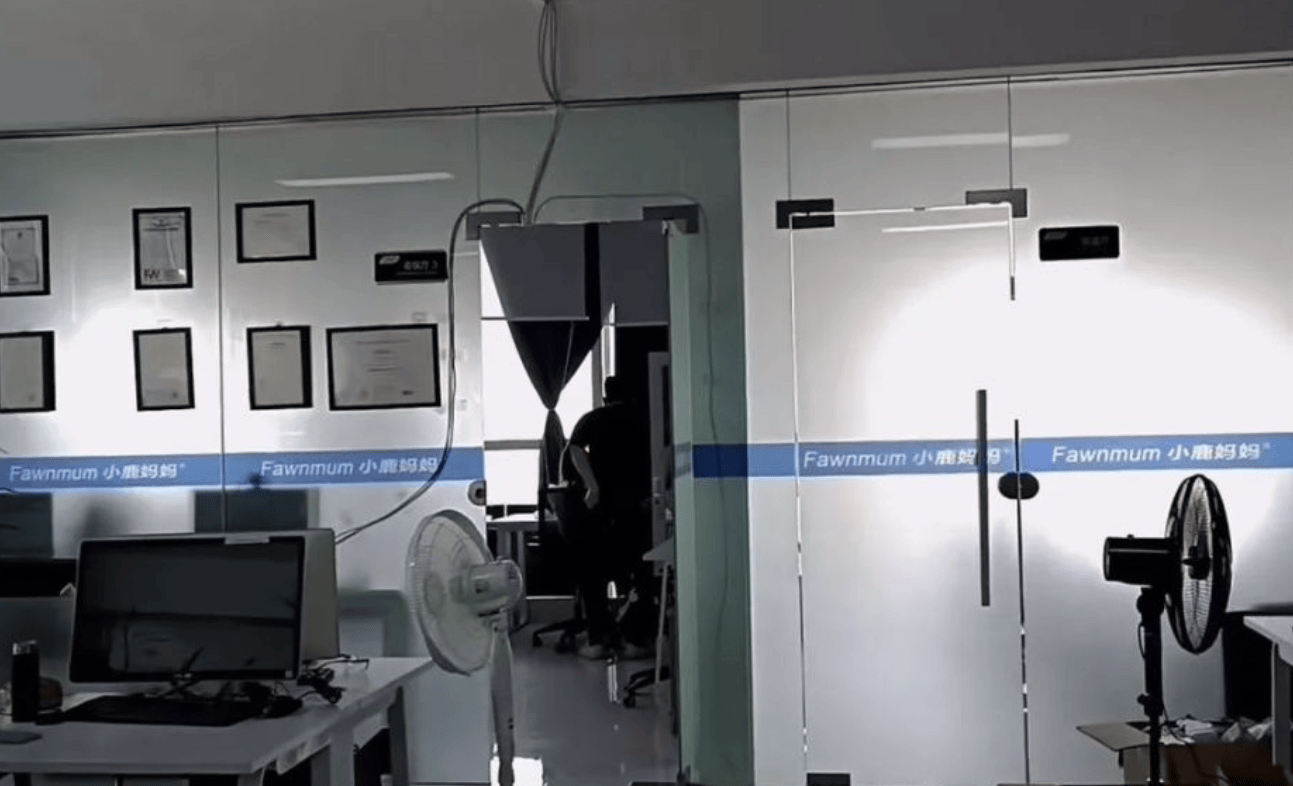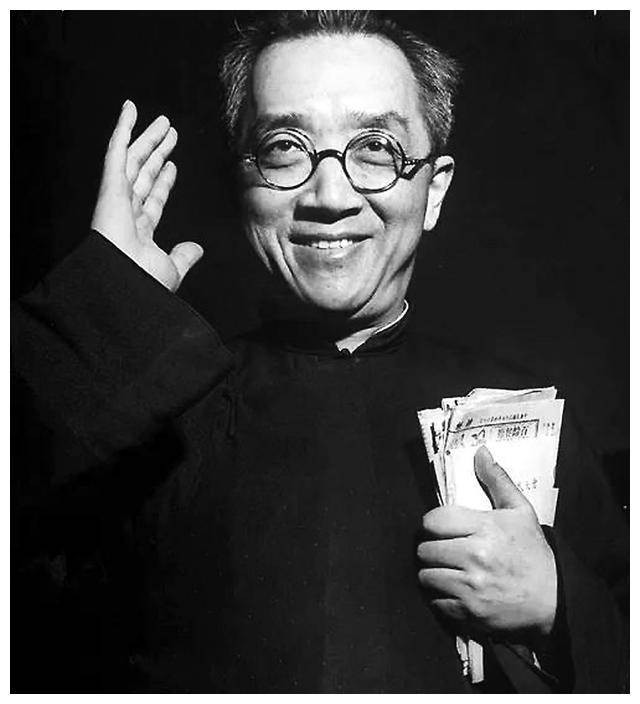大规模资本下乡,如今付不起地租,怎么办?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离开田地,以及小农经营的低回报问题,土地流转逐渐成了释放乡村振兴潜能的新思路,也在全国多地开始摸索、尝试。
而结合多地的调查研究,笔者发现这条道路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当下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少资本下乡搞规模经营,但如今出现付不起地租的情况。

资料图来源:新华网
一、“先进经验”被告上法庭
G村是位于东部地区的一个“明星村”,从人口规模和耕地面积来看,G村的体量不算小,全村有33个村民小组,5000多户籍人口,1.8万亩耕地。
因地处东部地区,相比于广大中西部地区,G村具有一定的地理区位优势,且G村每亩土地的租金也普遍较高,所以地方政府也有较强的动力推动土地流转。
G村33个村民组,以增减挂钩的方式拆迁了28个(2022年的价格:瓦房480元/㎡,石砖房500元/㎡,楼房680元/㎡),并建立了一个集中居住小区和两个集中安置点。如今,G村1.8万亩耕地已全部流转出去。其中,R公司是G村最大的土地流入方,流转了G村近七成约1.2万亩的耕地。
R公司主要经营风景苗木和特色花卉(如樱花、紫薇等经济苗木)。自2013年入驻G村以来,R公司便被地方政府宣传打造为“高效农业产业的样板”、“现代农业示范园”等荣誉模范,并被树立为带动共同富裕和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先进经验”。
然而,今年八月中旬的一天,笔者到G村调研,却了解到这一“先进经验”被G村告上了法庭。
通过对村干部的访谈得知,G村将R公司告上法庭的原因很简单,就是R公司没有向G村支付去年600多万的土地租金。
G村的干部表示,R公司自入驻以来,一直能够及时支付土地租金,与村里相处得也比较和谐,但由于2022年苗木市场不景气,加上企业部门之间的合并纠纷,R公司的资金运转出现了问题,便无法支付去年的地租,村里拿不到地租,也就无法给村民交待。
在入户访谈期间,许多村民向笔者表示,如今G村的老人几乎不再种地了,自己的土地也都流转给村委会了,每年的土地租金便成了在村老人的“养老指望”,虽然地租的钱款不算多,却是一项重要的生计来源,一旦拿不到,那日子也过不下去了。许多老人谈到此事时神情激动,有的老人甚至潸然泪下。
今年,G村为此事上访、讨说法的情况十分普遍,村、镇、县也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二、“我们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一)R公司的经营风险
针对这个问题,笔者访谈了R公司负责农林部门的齐经理。齐经理介绍道,R公司于2013年通过县政府的招商引资来到G村,分两期进行土地流转,一期流转了耕地5000亩,二期流转了7000亩;土地流转费为550元/亩,包括给农户的520元地租费和给村委会的30元管理费。
R公司所种景观树的销售渠道主要为房地产公司和市政工程,但市场范围比较局限,主要集中在华中地区。齐经理表示,景观树产业面临着诸多风险,“一旦上游销路不好,我们下游就不行了。这两年房地产不景气,所以整个下游包括建材和苗木全都快完蛋了。”
根据对齐经理的访谈,笔者将R公司苗木产业的经营环节及各个环节所承受的风险进行了粗略地归纳,详见下图:

苗木产业经营环节与所受风险简图
根据简图可看出,苗木产业存在着较大的经营风险,这种风险具有关联性、贯通性与沉积性,上游的风险容易积累到下游环节。由此看来,R公司生产经营的确面临诸多挑战,一旦苗木市场不景气,R公司便很容易受到冲击,冲击进而波及村庄和农民,容易造成治理困境和社会隐患。
(二)地租危机:R公司不是特例
在G村今年爆发的“地租危机”中,R公司不是特例。除了R公司之外,Q公司、S公司、P公司也因无法支付地租,而被G村告上了法庭。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G村土地流转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偏重,即86%的土地都流转给了种植经济苗木的公司,只有不到两成的土地流转给家庭农场进行粮食作物的生产。由于种树的市场风险往往大于种粮的风险,因此树价的波动便直接影响到G村的农民是否可以如期拿到地租。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Q、S、P三个公司的老板并不是实际管理者,这三个包地公司实际上采用了“老板投资-村民组长代理”的模式,也就是说,三个公司的实际管理者都是G村的村民组长。
笔者也对这三位负责管理的村民组长进行了访谈,其中张组长十分健谈,说到了很多关键信息。
张组长今年68岁,是G村的老村民组长,群众基础好,农业生产的经验也十分丰富。张组长对笔者坦诚聊道:“Q公司在我们G村种树,其实老板是见不到人的,也不管什么事儿。种树育苗的事情几乎全权委托给了我们村民组长,我们等于是受雇于他们,每个月给2500元的工资。”
笔者也跟随张组长来到了卖树的现场。在谈到今年普遍爆发的地租矛盾时,张组长表示:
“去年还300多元的一棵树,现在降到100块钱还不好卖。前几年不愁销路,而今年都卖不出去。像三角枫和栾树,以前都不愁卖,今年就不行了,这么大一卡车,最后才卖了这么点钱,找谁说理去?老板赚不到钱,村里也就得不到地租,眼下这是燃眉之急。”

身价下跌的风景树
“当初老板刚刚准备来包地的时候,我就有这个顾虑。按照我多年的经验,老板包我们一个小组的地种树,就足够我们一个县的需求了。G村33个村民小组,29个小组都在种树,哪有那么大的市场销路?只不过前几年还不错,算是比较幸运,没有出事罢了;一旦出事,积累已久的风险就会集中爆发,而且往往也都是大事儿。”
“一句话,我们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三)“今年少亏一百万,就是进步”
齐经理表示,实际上,R公司一直以来就从未真正实现过盈利。
R公司是一家综合性控股集团旗下的子公司,之所以能够维持至今,就是依托集团雄厚资金的“不断输血”。齐经理告知,R公司的生存成本(纯支出)为700~800万/年,包括地租、用工支出、苗木养护成本等。自2014年迁入之后,2014~2017三年育苗期内是没有任何收入的,期间主要靠集团的力量支撑,当然政府也会给予一定的补贴;真正开始有收入是在2018年,但每年的收入也只有300~400万,根本入不敷出。
“集团对我们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期待,最大的目标就是让我们能够‘实现自保’。比如去年亏了300万,今年只亏了200万,少亏了100万,这就是很大的进步了!”
除了经营苗木,R公司也承包了近1000亩耕地用来种植粮食作物,其中包括320亩水田、600亩旱地。齐经理表示,目前公司“以苗木为主,以粮食为辅”,但随着房地产行业的不景气,公司可能进一步提高粮食作物生产的比重。
此外,R公司还启动了特色民宿的规划,准备打造综合性生态旅游运动观光园区。但是,“宣传的确说得很好,然而我们目前并没有开园。因为‘接待能力’跟不上,那还不如不开,盲目开张不仅会亏损大量资金,也容易砸了自己的招牌。”至于以后会怎样,齐经理也不知道,目前的主要矛盾还是地租问题。
三、“资本下乡”“规模经营”冷思考
(一)“规模”是把双刃剑
按照地方政府的设计,土地流转之后,便可以推进规模经营,这样既容易打造出亮点和政绩,也能更向“现代农业”的方向发展,农民还可以从土地中解脱出来又拿到地租,村集体经济也能收点管理费以实现壮大——这实在是一步多方受益的好棋。
设想很丰满,现实情况却往往大相径庭。
“规模经营”不是神话,不是有了种植规模就一定会有等比例的收入。应该看到规模往往伴随着风险,而且规模越大,风险也越高。比如,规模经营并不能明显降低农业投入的成本,但往往还要承担更多的高额地租;同时,规模经营对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更为敏感,一旦遭遇极端天气或面临不景气的行情,往往规模越大损失越多。
所以,规模经营绝不能被视作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富人带动、政府支持”、“集中资源、政府造点”这两种方式都需要充分考虑风险与收益的比较,不能为了追求集体经济规模而盲目跟进。
此外,我们也应进一步发掘隐匿于社会事实背后的逻辑,即不仅仅要看到规模经营存在的问题,也应该发问: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起了这个“规模”?又是什么力量一直维持着这个“规模”?另外,这种力量是可持续的吗?即便能够持续,又是否具有合理性?
总之,“规模经营”应是一个中性词,对“规模经营”的盲目崇拜是要不得的。
(二)规模越大,社会风险可能越高
而对于“资本下乡”热潮带来的规模经营,我们的顾虑范畴显然不能局限于经营盈亏。
G村的罗书记表示,“我们也不怕这公司不给地租。法院目前冻结了R公司大概600万元的资金,至于这笔钱会不会转到村里还要再协商。但是现在老百姓的意见太大了,大家的情绪很难平复。”
“当前他们付不起地租倒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矛盾其实在后面,就是这些公司一旦倒闭了,土地怎么办?指望他们按照合同将土地恢复是不现实的,而将如此大规模的林地重新变为耕地,这个成本又该由谁来承担?”

不给地租钱,就“住”到村委会
G村的土地已进行大规模的流转,老年人基本退出了农业生产领域,流转出去的土地租金成了一笔重要的生活保障。但这一生活模式显然并没有绝对的保障。
简单来看,R、Q、S、P四个公司,与G村大致经历了“蜜月期-平静期-累积期-爆发期”四个阶段,但隐患和风险其实自始至终都潜伏着。而且这种集中爆发的风险,具有持续性和不稳定性,短时间内无法解决,而且未来也不能保证不再爆发。
换言之,土地对农民生计的保障,由之前的生产供给转变为资本方的地租供给,在这个过程中,实则将不确定的市场性风险与经营性风险悄然转嫁给了小农户。
农业领域中很难有超额利润,高额地租作为生产成本,让公司和家庭农场几乎没有盈利空间,而这些经营主体为了避免运营失败,就必须依赖当地政府的政策优惠和专项项目补贴;地方政府的政绩导向也顺应了其需求,并有动力继续推动“资本下乡”的热潮——这是一种“立竿见影”的政绩体现。
但是,资本下乡不是做慈善,因此地方政府不能总想着把工商资本“请进来”,把广大分散的小农户从土地上“请出去”——这些被请进来的工商资本往往是想着来“分蛋糕”的,而不是真正要发展农业。况且,农业的剩余是有限的,以逐利为目的的工商资本还会挤压适度规模经营的本土性农业生产经营者,即广大在村的“中坚农民群体”,而这部分群体对于村庄的农业生产和社会治理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推动农村土地规模流转,不能一厢情愿、盲目乐观,而应实事求是,综合考虑多方位的社会风险。若激进推动土地流转,对基层社会治理而言,反倒可能是增添新的不稳定因素。
当然,需一再强调的是,资本本身并不是洪水猛兽,只是希望各地在吸引工商资本下乡、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时能进行更慎重、长远的考虑。或者,至少先想好一个问题:大规模资本下乡后,一旦付不起地租,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