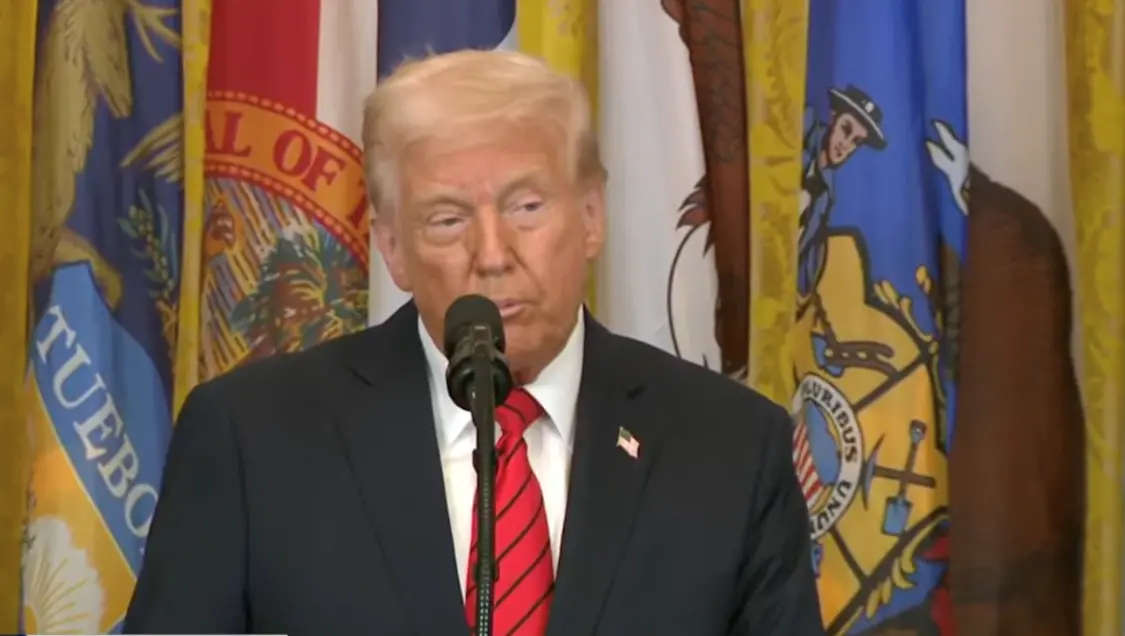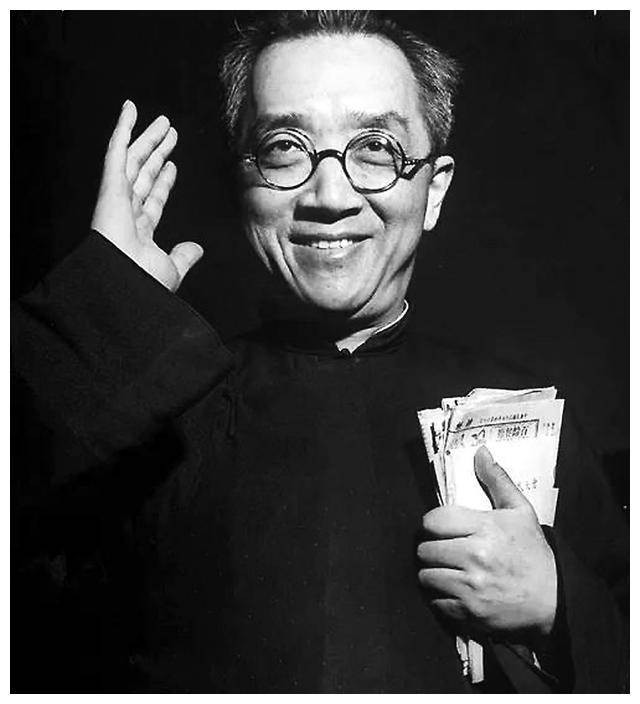惊动莫迪的“三大突变”:执政十年的隐患爆了?
【导读】印度大选落下帷幕,莫迪“虽胜犹败”,印度人民党爆出冷门,甚至没能赢得足以单独组阁的席位。这场对“莫迪十年”的全民公决背后,是埋藏在“莫迪十年”发展成就背后的隐患的一次集中爆发。今日推送的毛克疾、石雅风的特约稿件,系统性梳理了莫迪政府十年来如何获得成功,又埋下了哪些隐患,为我们理解印度大选和印度未来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文章指出,本次印度大选,莫迪率领的印人党能够拿下第三届任期,本身就证明过去十年执政成果可圈可点。之所以选票远低于预期,最大客观原因仍是“莫迪十年”强势推进的改革透支了印人党积累的政治资本,同时树立过多政治对手,导致他们抱团阻击莫迪政府。从大选过程分析,尽管北印超50摄氏度极端高温天气、选民确信印人党优势导致投票积极性下滑、部分议席临阵换将等因素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国大党领衔的“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展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团结性,也是本次印人党丢失席位的重要原因。
莫迪之所以能够三度连任,关键还是在于走出了一条新路线。社会文化上,印人党通过印度教民族主义有效凝聚了社会,激活了占印度人口85%的印度教群体,但也严重积压了穆斯林、基督徒等群体的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空间。政治治理方面,印人党特别强化了中央集权、改善国家能力,重点推动了党内组织改革,强化了组织动员优势。经济上,模仿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扩大投资”“发展制造业”“促进出口”。外交上,抓住地缘政治剧变的机遇期,既在主要大国之间摇摆获益,加紧经略南亚周边地区,还将“外交胜利”转化为“内政红利”。
这些执政策略也埋下了隐患。社会文化上,莫迪政府的策略有可能激化其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团家族与印人党的矛盾,对外可能激化印度教同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政治上,印人党激进改革打破了长期存在于印度政治体系中的政治平衡,动摇了自身的组织基础,推动了包括国大党在内的其他政党的“抱团反抗”,以及内部的组织能力、央地关系问题,都带来了隐患。经济方面, 印度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发展利益的妥善分配都还受到制约,经济发展既包括印度国内的挑战,也包括当前的国际环境是否能够支撑起一个印度量级的出口导向型“发展型国家”;利益分配上,印度国内尖锐的阶级、宗教、地域和族群矛盾都体现出其结构性问题。外交上,印人党的外交政策在事关内政的问题上缺乏灵活性,无关内政时则缺乏原则性,外交风险明显。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专栏特稿,由作者授权发布。标题为编者自拟,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辨析。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4年第19期 总第191期
印度大选与莫迪十年的成就与隐患
6月4日,长达47天的印度人民院选举宣告结束,莫迪领衔的印度人民党(以下简称“印人党”)大选“爆出冷门”,呈现“虽胜犹败”的局面。印人党不仅未能实现选前许下的400席宏愿,甚至没能拿下半数单独执政,需要获得泰卢固之乡党(TDP)、人民党联合派(JDU)等全国民主联盟(以下简称“NDA”)盟友支持,才能够获得超过272席的组阁权。如果莫迪成功组阁,这将使其成为印度独立以来除建国总理尼赫鲁外唯一成功实现三度连任的领导人。虽然各方均对莫迪赢得第三任期并不意外,但大选过程中仍出现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印人党胜选幅度之小出乎意料、印人党在北方选情恶化之甚出乎意料、反对党联盟反攻势头之猛也出乎意料。
然而,这些看似出乎意料的情况,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印度本次大选某种程度上也对“莫迪十年”的全民公决。在本次大选中,印人党之所以“先扬后抑”“虽胜犹败”,只能艰难赢下第三任期,本质上是因为印人党虽然探索出一条发展新路,却并未很好顾及传统利益集团的诉求,也未能兼顾劳工、农民、部落民等遭受改革冲击群体的利益,更完全无视甚至肆意侵害穆斯林等群体的利益。面对印人党变本加厉的施压,原本一盘散沙的反对者重新集结在国大党周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本次大选“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以下简称“INDIA”)才能攻城略地,一举推动把印人党拉下神坛,推动印度政治向分散化方向大幅回摆。
但是,印人党拿下第三任期毕竟还是创造了历史,能够固守执政地位也表明印人党此前十年执政确实可圈可点。在莫迪引领下,印人党政府不仅告别了国大党延用数十年的治国理政方略,还走出一条从社会文化、政治治理到经济发展,再到外交战略都截然不同的全新道路,并在各个环节之间形成互相促进、正向反馈的闭环。莫迪治下的印度如此不同,甚至可称之为“印度第二共和国”。
鉴于此,莫迪艰难赢下第三任期组阁权不仅需面对前期有利因素演变,还需要面对累积而来的各项风险挑战,包括印度教民族主义狂热的宗教反噬、印人党的政治堕落、印人党莫迪的接班人“赤字”、印度财阀主导发展恶化经济社会两极分化等,更需在盟友掣肘、地方分权、“悬浮议会”的背景下,艰难摸索出一条有别于前两任期,并取得各方妥协的全新发展道路。这可能才是莫迪政府在第三任期有所作为,乃至在更远的未来继续开辟印度式发展道路的关键所在。
2024年印度大选的“意料之外”和“意料之中”
印人党胜选实属预料之中,但胜选过程之艰难却在预料之外。尽管在大选之前和大选过程中的很多迹象都表明,印人党能够再次胜选取得连任,各方直至出口民调结果公布仍对印人党压倒性胜利寄予厚望,但计票结果却“重大爆冷”:印人党及其所在联盟所获选票远低于预期。据印度选举委员会公布数据显示,印人党主导的NDA赢得了292个席位,其中印人党单独赢得239个席位,不仅远低于2019年大选的303席,还低于2014年的282席。印人党丢失了单独执政地位,需要至少三个盟友才能组阁,甚至就算在盟友支持下组阁,面对反对党也仅能保持微弱优势。分析本次大选过程不难看出,尽管北印超50摄氏度的极端高温天气、选民确信印人党优势导致投票积极性下滑、部分议席临阵换将等超预期不利因素的确对大选结果产生显著影响,但印人党“虽胜犹败”的最大客观原因仍是“莫迪十年”强势推进的改革透支了印人党积累的政治资本,树立了过多政治对手,导致他们抱团阻击莫迪政府。
印人党赢下印地语核心地带在预料之中,选情恶化之甚却在预料之外。在本次大选中,印人党虽然保住了其位于北印、西印的“基本盘”,但选票争夺之惨烈、选情波动之剧烈令人瞠目,印人党反而在这些地区选票丢失最多。在传统势力范围内,印人党不仅在北方邦狂丢29席(从62席降至33席)、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丢掉13席(从23席降至10席),在莫迪老家古吉拉特邦也丧失了完胜战绩,被国大党狙击得手1席,仅在中央邦拿下全部29个议席。更令人震惊的是,仅在两年前的2022年北方邦立法会选举中,印人党还以狂斩北方邦403个议席中的255席、选举联盟273席的辉煌成绩赢得选举。尽管地方选举和全国性选举存在显著区别,但由于这种差别过于剧烈,还是严重冲击了印人党作为“印地语核心地带强势代表”的选举人设。
尽管极端天气、选民懈怠等超预期因素削弱了印人党的选举优势,但选情如此恶化的直接原因在于:北印民众对于莫迪政府在损害许多既有利益的同时,却迟迟未能兑现新的增量发展红利而心怀不满。例如,莫迪政府第二任期推进农业法案等改革严重损害北印农民群体利益,因此这一群体自然无法满足印人党“国族整合”“国家崛起”等宏大叙事,而是要求更为直接、更为集中的政治关注与经济资源。相较之下,在选前被认为“事关印人党优势地位”的南印、东印地区,印人党反而确实有所斩获:印人党在安得拉邦、喀拉拉邦等南印邦地取得零议席突破,同时保住在阿萨姆邦等印东北邦的优势地位。然而,在北印“爆冷”的背景下,印人党取得的“外线”成就不仅显得微不足道,甚至反向佐证其选举策略有些舍本逐末。
反对党联盟执政无望在意料之中,反攻势头之猛却在预料之外。由国大党牵头组建的INDIA本次大选狂取232席,其中仅国大党就实现议席翻倍的目标,获得99席。但是,选前从媒体到学者均高度质疑这个“大杂烩联盟”的竞选能力——毕竟除“反对印人党”外,INDIA几乎拿不出任何实质性、可执行的政治目标和施政方针,更不用说围绕“共同参选”问题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或共识——各党均无意愿支持联盟内任何人在“印人党组阁失败”的情况下上台执政。
尽管如此,INDIA却精准把握了印人党前两次大选暴露的致命弱点——印人党之所以能够连选连胜,并不是因为印人党能够在单一选区内赢得绝对多数选票,而是因为印人党利用了其他政党选票碎片化的特点,仅以相对优势就能赢得选区的胜利。显然,这种策略只有在印人党将反对党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功,但如果反对党选择团结一致,那印人党将大概率无法取胜。本次大选,反对党之所以冰释前嫌、抱团反抗,一个关键动因就是因为印人党近年来频繁破坏印度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肆意打压国大党、平民党。这类倒行逆施的“公害行为”不仅严重冲击普通选民对于印人党的观感,还把很多原本游移不定的中小党派推向INDIA麾下。因此,这样一个以“搅局”为目标的竞选联盟居然拿下232席,几乎追平印人党席位,也足以迫使印人党向其盟友和反对党做出让步或妥协,这势必有力阻击印人党宣扬在第三任期推动“重磅改革”政治抱负。
莫迪能够三度连任,关键在于走出了一条新路线
尽管在本次选举中遭遇逆风,但莫迪能够三度连任,成为唯一比肩尼赫鲁的印度当代领导人也充分说明“莫迪十年”绝非一无是处。能在印度这样一个国情极端复杂、规模极其庞大、利益极为多元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取得连选连胜的成绩,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纵观“莫迪十年”,印人党不仅告别了国大党延用数十年的治国理政方略,还初步探索出一条从社会文化、政治治理到经济发展,再到外交战略的执政新路,并争取在各个环节之间形成互相促进、正向反馈的闭环,呈现出一种隐约可见的“印度第二共和国”气象。
首先,在社会文化方面,印人党通过完成印度教民族主义目标有效提高了印度社会文化凝聚力,增强了印人党的组织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为莫迪推动政经等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正是在印人党引领下,印度教民族主义不仅摆脱被世俗政治所不齿的边缘身份,还一举迈入印度政治生活的舞台中央。例如,“莫迪十年”期间,印人党强势推进复建罗摩神庙、废除宪法第370条克什米尔特殊自治地位、出台《公民身份修正案》、通过《统一民法典》等一系列标志性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并取得突破性进展。正是因为这些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活动,印人党进一步激活了占印度人口达85%的印度教徒群体,特别是将这一庞大群体的政治注意力从种姓、阶层、民族等零散议程中拉回到整齐划一的宗教议程。也正是因为利用了印度教这个跨越种姓、阶层、民族的“最大公约数”,印人党才进化为足以颠覆社会文化议程,并成为塑造社会文化新范式的主导性力量。这种议程挤压穆斯林、基督徒等群体的政治活动空间甚至社会生存空间,他们被用来当作维护印度教徒团结而树立的“假想敌”。
正是在这样一套社会文化话语之下,印人党通过自身及其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以下简称“RSS”)的庞大基层组织全面开展文化、教育、卫生基层运动与志愿服务,并辅以“清洁卫生运动”(Swachh Bharat Mission)“直接福利转账计划”(Direct Benefit Transfer)等财政拨款或转移支付手段,使民众更加切实感受到“罗摩盛世”的到来,以此增强印人党的精神感召力和社会动员力,巩固并扩大印人党的政治基础。
其次,在政治治理方面,印人党政府不仅履行执政功能,还特别强化中央集权、改善国家能力,重点推动党内组织改革,强化印人党的组织动员优势。莫迪强势推动以“财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改革,将印度中央面对地方的权威提到空前高度。莫迪政府2014年上台以来就紧抓中央财政权力建设,不仅在2015年就撤销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一涉及预算内投资和财政资源分配的重要中介部门,将其职能分归莫迪个人直接管辖的总理办公室、财政部和其他职能部委,还连续推动预算改革、税制改革等涉及财政汲取能力和财政分配关系的重磅改革。其中,商品及服务税(Goods and Services Tax)改革更是有印度版“分税制改革”之称,以中央直接征收并统一分配的方式代替各邦分头征收,在较短时间内就极大提升了中央政府面对地方政府的政治议价能力。
作为执政党,印人党同时“刀刃向内”大力推动党内组织人事改革。一方面,印人党中央通过组织手段不断平衡党内种姓势力,试图最大化扩张党员基本盘。为平衡印人党扩张带来的低种姓群体势力崛起、协调地方主导种姓间群体矛盾、保护党内高种姓群体的传统利益,印人党中央着力塑造高种姓干部的“政治中立性”,大量任用上层种姓担任领导角色,同时在必要时也会吸收低种姓代表担任要职,达到平衡派系利益的目的。另一方面,印人党中央也不断强化党内组织纪律。例如,在中央邦2023年邦立法机构选举中,印人党中央“边缘化”任该邦首席部长超16年的乔汗(Shivraj Singh Chouhan),转而推出缺乏邦内基础而只能仰仗莫迪提携的莫汉·亚达夫(Mohan Yadav)。再如,在2024联邦院选举中,印人党16名候选人中仅有1名“老面孔”,而在其余15位“新秀”中,甚至多达10人均为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基层人员。
此外,印人党在各级选举中也不吝“公器私用”,不但惯于直接操纵行政工具直接打压政治对手,更善于“俘获”本应保持政治中立的国家机器。一方面,印人党加速从国家官僚体系中搜罗、捕获人才,包括外长苏杰生、前国防参谋长拉瓦特等均由印人党在技术官僚中“二次发掘”。其中,苏杰生更是在2019年就在莫迪的强势提携下,赢得古吉拉特邦联邦院议席,完成从事务官到政务官的转型。另一方面,印人党也充分发挥立法和行政双重优势,推动带有鲜明党派特征的法律法规,以更加机制化的方式破坏政治传统。例如,2021年、2023年印人党分别推动“允许选举登记机构识别选民身份”“允许政府加强管控选举委员会和选举过程”的法案。再如,2023年莫迪政府推出“社会勇士计划(Social Warrior Scheme)”,由本应严守党派中立的军方“建议”印军士兵在休假期间协助“清洁印度运动”等莫迪政府推出的政策。
第三,在经济方面,莫迪政府凭借稳固执政地位强势推进了不少深层次经济改革,重点是引领印度走上“扩大投资”“发展制造业”“促进出口”的经济方针,模仿东亚国家的“发展型国家模式”。经济发展不仅是莫迪政府“印度崛起”叙事的核心支柱,其中蕴含的“绩效合法性”也是印人党赢得选举的关键支撑。“莫迪经济学”很大程度上直接背离印度长期以来奉行的“跨越工业化”传统发展道路,并努力推动印度脱离“轻制造业、重服务业”“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重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模式。
在招商引资上,莫迪政府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线,大力推动电力、港口、公路、铁路等印度长期缺乏的关键基础设施,同时定向降低外资准入门槛、优化国内营商环境,希望更多依靠投资而非消费带动印度经济发展。在产业发展上,莫迪政府抓住中美博弈引发的全球产供链重组机遇,以消费电子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切口希望替代中国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地位,提振青年人口就业率,以缓和社会压力,并提高底层群体收入。
同时,莫迪政府高强度投入财政资金、外交资源、政治资本连续推出“分阶段制造计划”(PMP)、“制造业激励计划”(PLI)等产业政策,同时继续扩大“以工代赈”项目规模满足底层民众对于福利政策的依赖,增强经济的造血能力。
第四,外交方面,莫迪政府抓住国际地缘政治剧变的机遇期,不仅在主要大国之间摇摆获益、加紧经略南亚周边地区,将“外交胜利”内销转化为“内政红利”。边境安全方面,印自2017年以来对华挑起的边境争端乃至冲突是印调整对华立场的标志性事件,但印军的战略、战术劣势却使莫迪政府只能借边境议题挑动国内民族主义情感、加强边境军备及基建建设,但只能在双边现实层面选择“冷处理”。经贸方面,莫迪政府一方面大批封禁中资APP、锁控自华赴印签证发放、加大对在印中企的勒索迫害力度,另一方面客观依赖中国产业体系与出口产品支撑印本土制造业发展,持续扩大自华中间品、制成品进口规模。
面对美西方,印贴靠美国程度达到空前水平,甚至可以说抛弃了长期以来的“不结盟”立场。为迎合美西方抛出的“印太战略”,填补美西方对华“脱钩”“断链”后的生态位空白,印积极与美西方缔结“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等双边产业技术框架,积极参加“四方机制”(QUAD)、印太经济框架等小多边机制,通过坚定“反华”立场自美西方获取大量资金、技术、市场、政策及军事情报支持。面对俄罗斯,印在美西方接受的限度上最大保持印俄合作,在维持自身“中立”形象的同时从中攫取实质利益。印一方面在俄乌冲突的大背景下大规模购买低价俄油,在填补自身能源需求之外,还对外“低买高卖”获取高额经济收益,另一方面表态拒绝在俄与美西方之间选边站队,在维护自身“中立”形象的同时保留对双方发展关系、攫取利益的渠道。
对南亚周边地区方面,印加速推进对孟加拉、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的互联互通建设,以此在加强对周边国家的控制能力的同时,对内体现“印度崛起”的地区强国地位。此外,在对巴基斯坦的事务上,印人党政府更倾向于“降格处理”,以此显示印巴实力的差异与印巴关系的不对等,满足国内民族主义群体诉求。对全球南方方面,印通过积极参加“全球南方”事务、加大对外援助、打出“数字化”发展大旗等方式与中国竞争,提升对美西方议价地位,迎合印人党“印度崛起”叙事。
莫迪政府强势改革的“得”与“失”
“莫迪十年”在各方面的强势改革虽然在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强化印度国家能力、提升印度国际地位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成就,但其极端的改革目标、过激的改革节奏、偏激的改革手段使其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为印度国家与社会埋下了众多隐患,反而推高了印度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这次大选印人党选情出现超预期削弱,很大程度上就是“改革阵痛”遭遇民主选举“释放应力”的结果。
社会文化方面,莫迪政府推进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执政成就和执政长期化趋势,从内部来说对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在印度教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权威地位构成事实挑战,对内可能激化RSS、团家族与印人党的矛盾,对外可能会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进一步极端化,表现更加激进“排他”。对内方面,莫迪强大的个人权威将RSS与印人党事实上变为建设“印度教特性社会”总体目标的两个职能机构,但印人党逐渐侵蚀RSS的母体地位。这种党团地位的扭转可能和印人党与团家族间的历史矛盾叠加共振,在“后莫迪时代”引发党团双方基于路线、权力、甚至莫迪“衣钵”传承正统性的全方位对抗。对外方面,“莫迪十年”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议程以“矫枉过正”的姿态抹除了独立以来印度穆斯林群体拥有的几乎所有“特权”。目前RSS和印人党均陷入了短暂的“议程空白”期。但是,这也给在大选中遭遇超预期挫折的印人党受激迎合RSS极端派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激化、极化。穆斯林虽可选择投向国大党联盟,但一旦爆发类似2002古邦危机的事件,就可能成为印人党启动紧急状态的导火索,导致社会矛盾向不可预料的方向演化。
政治方面,印人党激进改革打破了长期存在于印度政治体系之中的政治平衡,动摇了印人党自身的组织基础,使印度政坛整体处于“非稳态”的风险状态之中。从党政关系看,印人党的组织形态与教派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内核将进一步侵蚀印度政治体制,强化印度政治体制与实际政治运行之间的张力。从党际关系看,竞选博弈的白热化将导致印人党变本加厉打压在野党,而双方意识形态的极端化甚至可能重新激起印度“政治刺杀”的政治传统。从党团关系看,印人党1.8亿之巨的党员规模与RSS500万的成员之间可能已触及某个足以扭转党团关系的临界点,而“政治强人”莫迪的出现与其说是缓和,不如说是掩盖了其中的矛盾。“后莫迪时代”印人党能否继承、如何继承莫迪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目标十分值得怀疑,不排除因“路线之争”爆发矛盾的可能。从党内关系看,由数十万发展而来的印人党自身很难说拥有独立维持、管理、动员1.8亿党员群体的能力。在缺乏莫迪之后,印人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间如何形成新的平衡也仍未解决。
经济方面,印人党政府虽在发展经济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这种发展是否有可持续性,以及发展利益能否得到妥善分配尚不能断言。经济发展方面,印人党政府虽成功将原先“跨工业化”的发展路径转为更加合理可行的“发展性国家”模式,但仍面临诸多问题挑战。首先,印人党目前采取的“发展型国家”模式本质上是对于上世纪末“东亚奇迹”而产生的描述性理论,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国内政治基础,并非保证直接、持续推动经济发展的“万能灵药”。一方面,这意味着印度仍需根据自身经济实际进行相应调整,若无法解决诸如根除市场对于成熟服务业的路径依赖、克服联邦制民主国家对政府能力的多重限制、打破大多数民众无力参与市场经济的体制障碍,那么印度在“发展型国家”模式下的经济发展潜力就会大打折扣。另一方面,这也可能意味着“发展型国家”模式已不再适应当今的国际环境,或者说世界上的空白市场已不足以支撑一个印度如此量级出口导向型“发展型国家”的兴起,而印度需要自行探索一条适合印度发展的新路径。其次,关于经济发展“蛋糕”的分配问题也是印人党头疼的一大难题,印度国内错综复杂的阶级、地域、宗教、族群矛盾使印人党在利益分配时极易引发社会冲突,严重时甚至可能干扰打断印度经济发展进程。从横向的阶级矛盾来看,当前印人党政府是一个依靠极少数财阀与大量贫民的民粹主义政权,这种分配模式不可持续:向财阀的分配增加了财阀的独立性,向贫民的分配则推高了贫民的边际效应,进而走向“持续增长加剧贫富极化”“无力增长导致支持联盟内爆”的死路,更不用说在这一分配过程中被边缘化的中产阶级及少数群体了。从纵向的社会矛盾看,宗教矛盾自不必说,以印穆矛盾为代表的宗教矛盾是印度全面社会冲突的导火索,一旦爆发将严重干扰甚至打断印经济发展进程。地域和族群矛盾尽管不会如此激烈、如此有破坏性的经济后果,但各方在资源倾斜、产业分布等问题上的博弈倾轧也会部分扭曲纯经济条件下的“最优解”,积少成多可能构成印度又一个难以根治的结构性问题。
外交方面,印人党的外交政策在事关内政的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在无关内政的情况下则缺乏原则性,使其外交日益陷入窘境,一招不慎就会倒灌回流,冲击印人党内政布局。保守外交方面,从对外经贸合作角度来看,印经济现代化程度低、财阀垄断程度高、面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强,这些特性共同决定印无法得罪内部利益群体与外部经济体建立深层次经贸沟通合作,锁死了印对外经济合作的上限。从全球南方合作角度看,印度自身战略资源匮乏,不会自掏腰包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又与南方国家经济结构高度相似,本质上是全球南方国家最大、最具威胁的零和博弈对手,这锁死了印领导全球南方合作的上限。投机外交方面,印在中美、美俄之间拉扯摇摆,在攫取短期收益的同时长期形象严重受损,危及各方对印战略信任、降低与印合作意愿。印一味争夺全球南方领导权,但投入微薄、拒绝担责,只想借此抬升对美西方议价能力,持续损害印独立以来积累的国际声望。不仅如此,印人党长期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实行霸权主义,妄称建立“大婆罗多”国家。在这一构想下推行的南亚“互联互通”只会进一步激发周边国家的提防心理,事实上阻碍南亚地区一体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