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摘自台版新译本《失序的心灵 : 美国个人主义传统的困境》一九九六年版作者序
「我们该怎么生活?……作为美国人,我们是谁?」自从十多年前我们在本书卷首提出这些问题,它们如今已显现一种严重的急迫性。它们的意义自建国起就不停地被争辩,但从来不曾辩得像眼前有人呼吁「恢复美国」或克服「道德危机」的这一刻那么不可开交。
我们美国人总是想要闯出点名堂。我们追求当个有自信和活力的人,相信只要吃苦耐劳,品行端正,就能在开放社会中成为自重又正直的人。然而,环视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四处都能看到对社会健全性的不安,以及对未来的担忧。我们当中有愈来愈多人不确定能不能信任我们的国家制度、我们选出来的官员、我们的街坊邻居,甚至开始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实现自己对人生的期待。焦虑的情绪一触即发,社会可能出了差错的恐惧萦绕心头。对很多美国人而言,这些恐惧在对犯罪、道德败坏,以及日益扩大的收入与机会分歧的担忧之中达到临界点。折磨人的不确定性笼罩著我们的工作、合理收入,以及家庭生活的未来,尤其是下一代的福祉。
这些恐惧浮现是因为人们发现全球经济成长,对多数美国人而言,不再意味著机会,而是代表「缩编」、「再造」工作,以及资遣单。然而,尽管荣景遭受如此巨大的威胁,民众却耐人寻味地鲜少公开抗议经济游戏规则的改变。有人说,我们因种族、文化、信念、国家认同的不同观点而彼此分歧。但事实證明,我们起码在某个核心信仰上是团结一致的,超越肤色、宗教、区域和职业:美国人相信经济的成功与不幸是个人责任,完全与他人无关。
我们该如何解释如此压倒性的价值共识,它似乎和美国社会总是争论不休、严重分歧的常态截然不同?当我们发现,不论欧洲或东亚任何工业国家的人民都不同意这个普遍的美国信仰时,事实就更加令人匪夷所思了。欧洲和东亚的工业国家也正经历新兴全球经济令人迷惘的震撼。然而,美国最富裕与最贫穷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远远大过他们所有国家,而且美国持续容忍比他们高很多的经济剥夺率。为什么美国社会为经济改变付出较高的代价?这个巨大的代价,和信任与信心的衰退有关吗?会不会这些发展其实有同样的成因,源自我们对个人及其责任从不动摇的一些看法?换句话说,这道难题是不是根植于被美国人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几乎看不见的文化价值里。
个人主义又来了
在本书中,我们尝试理解这个文化态度。我们沿袭托克维尔的传统,称之为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美国人倾向用来思索人生的第一语言,它最注重的是独立和自力更生(self-reliance)。这些特质被期待能在争强好胜的社会中赢得成功奖赏,同时也被当作一种美德而受到重视。基于这个原因,即使美国社会的开放本质提供人民获得丰厚奖赏的诱人机会,个人主义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很沉重的负担。
美国的个人主义要求个人付出,并激励人们实现目标的热情,然而它几乎不鼓励养成,对道德成长及经济成功采取一种浮沉靠个人的态度。它欣赏坚韧与强壮,惧怕柔软与虚弱。它谄媚赢家,同时轻蔑输家,这种轻蔑可能如泰山压顶,无情地粉碎那些被他人或自己视为社会败类或窝囊废的人。
我们在本书中探索了这样的美国个人主义。我们追问它来自何处,试图描述其结构。我们发现,它既有「冷硬的」功利线条,又有「柔软的」表现形式。一个注重底线,另一个聚焦感受(通常是从心理治疗的观点看待)。最重要的是,我们质疑这两种形式的个人主义对整体社会是否有任何助益,甚至质疑它们对美国社会中最成功的人(也就是受过教育的中上阶级)是否有任何助益,传统上,这些人向来最忠于个人主义的许多价值。我们的答案是强而有力的否定。我们主张(再次感谢托克维尔的启发)个人主义在美国能持续不断地发展,完全是因为它一直以来受到更宽宏大度的其他道德条件的支持与控制。
经济繁荣时,美国人将个人主义视为一种自给自足的道德和政治指引。在当前这样的社会逆境中,他们倾向主张,自己的利益自己顾。然而,很多人都觉得不论在盛世或灾难中,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缺少了某些东西,光是透过个人主义无法让人理解生活中的某些基本现实,特别是人与人的相互依赖。当个人的努力本身被證明无法满足生活的要求,这些事实就变得更加醒目。过去每当遭逢类似处境,美国人总是求助于其他的文化传统,尤其是被我们称为对生活的圣经传统诠释和公民共和传统诠释。每当有人呼吁以团结行动解决共同问题时,这两个传统总是能挺身报效国家。
圣经传统是多数美国人透过各式各样宗教社群而熟悉的第二语言,它教导人们基于自己和超验的关系而学著关注个人的固有价值。它坚持我们有义务尊重与承认众生的尊严。自共和国建立以来,圣经传统藉由坚持国家应当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一直在政治领域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诸如美国内战的国家危机与重建时刻。在这种时候,信仰圣经的各股势力,和指引开国元勋的公民共和主义有了共同的目标,它们都强调美国实验是一项具有普遍道德意义的计划,它把谋求国人同胞的福祉及共善的责任交付给公民。
让这两个传统产生连结的关键,也是它们截然不同于激进个人主义的原因,是它们对人类作为社会动物的理解。这些声音辩称个人主义把青春期的典型美德,也就是主动和独立,错误地等同于个体性(individuality),也质疑伴随而来的媚谄成功与轻蔑弱势是不可取的态度。公民共和主义和圣经信仰提醒我们,作为一个个体(自己作主的人)不意味著我们跟他人没有连结,拒绝人类的社会天性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我们只是需要以带有批判性的成熟忠诚去实现这份天性,因为我们知道为更大的社会国家贡献是每个人共同的责任。笔者们想在公共对话中加强的正是这些声音,可是我们担心美国的国家论述正逐渐被强硬的、具有破坏性的个人主义单声道变得贫乏。
出版本书时,我们大力强调个人主义的重要性,可能对它和圣经及共和传统关系的模棱两可著力不够,这两个传统在某些方面缓和了个人主义,但在其他方面却是个人主义的重要推手。诚如恩斯特.特尔慈(Ernst Troeltsch)所言,苦行的新教主义拥有强烈反政治,甚至反公民的一面,但它是美国人养成时期最普遍接触,而且至今仍有高度影响力的圣经信仰形式。1国家和外在社会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因为得救的信徒会照顾自己。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一派的新教徒倾向把被他们认为道德不及格的人彻底从社会主体中排除,这里的不及格通常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不成功(例如不值得帮助的穷人)。这种态度受到其他新教徒的抵制,天主教传统更是大加挞伐之。在天主教的传统中,对共善的强调防止了任何人被排除在社会的关怀与照顾之外。相对于将工作视为自我證明之道的新教流派,这个对立的观点把工作看成对一项共同志业的贡献,每个人都尽其所能,但没有人会因能力不足而被排斥。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忘记有一个在美国影响力极大的圣经信仰流派,鼓励人们退出公共生活,而不是鼓励公民参与,甚至想要谴责最脆弱的人在道德上不值得同情。
除此之外,有一种我们继承自十八世纪的重要的共和主义(美国版的英国辉格党传统),既反国家、又反城市,把自耕农的独立想得太过浪漫,它最广为人知的形式是早期的「反联邦主义」。汤玛斯.杰佛逊坚持把国家的首都放在沼泽中绝非偶然。杰佛逊─麦迪逊(Jefferson-Madison)的共和主义不仅敌视城市,而且对税收乃至为国家服务的所有政府职能都怀有敌意。对国家偏执的恐惧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自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存在的事实。2
笔者们还低估了被我们称为功利个人主义的个人主义在道德上的意义。至少在某一种功利个人主义中,真正的焦点是道德的自律和自助,而不是首重外在的奖励。世俗奖励不过是品行良好的征兆 ── 这是从喀尔文主义传统内部逐渐发展出来的一个观念。个人主义对青少年独立的重视,始终惧怕一个爱干预的、强大的父亲,因为他可能把孩子推回幼稚的依赖关系,而这种恐惧很容易被转移到一个家父长作风的国家身上,认为它将迫使自由公民沦为无助的老百姓。3这种道德功利主义可以用阶级的术语来理解:有钱人就像独立的成年人,而穷人是受抚养的孩子,他们的成功与失败都是自己一手促成。美国的个人主义抗拒比较成熟的美德,像是照顾和传承,智慧就更别提了,因为争取独立的奋斗占据了所有心思。
比起已经变得复杂、相互依赖的今日社会,这个复合式的个人主义文化比较适合未开发的边疆(虽然它在边疆当然也有破坏性的后果)。如果有些本书的读者认为我们是在怀念一个被理想化的过去,我们现在想除掉这个想法。我们仍然相信在许多方面,圣经及共和两大传统都比功利和表现个人主义更可取,但它们的任何形式都不能被不加批判地采纳,抑或是毫无保留地予以肯定。
公民的身分危机
相较于十年前本书出版时,激进个人主义的后果在今日更为显著。在本书中,当我们谈起承诺,谈起社区(community,按:根据前后文脉络,书中译法有社区、社群、共同体),谈起公民权,是把它们当作与疏离社会的个人主义做对照的实用术语。若有适当的理解,这些术语对我们目前的理解仍然很重要。不过,今天我们认为「公民的身分」这个说法,能呈现出其他术语捕捉不到的内涵。尽管我们批评各种扭曲变形的个人主义,但我们从来不打算忽略每一个个体的核心重要性,而且发自内心地同情个人在美国社会上面对的种种困难。「公民的身分」指向个人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关键交叉点。假使我们面对一场公民认同的危机,那不只是一场社会危机,也是一场个人危机。
我们所谓的公民的身分危机是指,在各个美国生活的层级和各个重要的团体中,都出现了脱离整体社会的种种诱惑与压力。这会产生两个后果:社会资本(我们将在下一节定义这个术语)被耗尽,以及个人认同受到威胁。受到公民身分危机威胁的东西,就是成为我们相信的社会的一员,所带来的「自信独特感」,在这个环境中,我们既能够信任别人,也感觉被人信任,而且对这份归属感没有怀疑。这种威胁不单单是政治幻灭的问题而已,虽然政治幻灭也够糟糕了。它是一种更激进的撤退(disengagement),比起只是疏远政治的领域,对社会凝聚有更大的威胁。
由于我们认为公民的身分危机在不同社会阶级呈现出的样貌不尽相同,关心美国阶级体系日益扩大的差距是厘清危机的必要步骤。美国人在谈论阶级时往往感到不自在。总的来说,难道美国社会不是一个无阶级社会吗?当然不是。对阶级因素的考量在本书中大抵是含蓄的,因为书中的焦点是多数美国人所属的中产阶级身分的文化理想。但过去十年,美国阶级结构发生了引发严重道德问题的变化。直截了当地处理阶级如今已变得无可避免。
全球性市场经济的压力正冲击著世界各地的社会。这些压力造成的主要结果是全球市场赢家与输家间的悬殊差距持续扩大。我们不仅看到收入两极化,富人愈富,穷人愈穷,还看到一个持续萎缩的中产阶级对未来愈发焦虑。让我们看看这些全球性压力在世界各地创造出的一些趋势,但主要以美国为深入焦点。首先是由罗伯特.赖希(Robert Reich)所谓「符号分析师」(symbolic analysts)组成的一群孤立精英的诞生,也就是懂得使用正在改变全球经济的新技术和资讯系统的人。4这些人在邻里社区的根基不如在专业圈人际网络中牢固,后者弹性而短暂地将他们与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其他「符号分析师」连结起来。这样的人在顶尖大学即研究所的高度竞争氛围下完成教育,他们学会不要太投入家庭、教会、地方、乃至国家。正是在这群人身上,但不限于这群人,我们清楚看到本书研究的个体化所呈现出的文化轮廓。
这群精英强者的公民的身分危机,表现在丧失公民意识、丧失对社会上其他人的义务感之中,这导致他们从社会退缩,躲进大门出入管制森严的住宅飞地,与超现代办公室、研究中心及大学里。这个精英阶级对社会公约(social covenant)、众人皆属同一主体的观念,感受异常的薄弱。
比这些知识/权力精英脱离社会更令人不安的是,他们对社会其他成员的掠食者态度,以及他们愿意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不顾任何人。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已经谈过统治集团(establishment)与寡头统治集团(oligarchy)之间的区别。5他主张,日本拥有一个统治集团,而多数拉丁美洲地区则因寡头统治集团而饱受摧残。两者都是特权精英。根本差别在于统治集团透过为整体社会谋福祉寻求自身的利益(又称作贵族义务〔noblesse oblige〕),而寡头统治集团藉由剥削整体社会照顾自己的利益。换言之,统治集团的公民的身分感很强,寡头统治集团则欠缺这个感受。两者的其中一个主要区别在于征税:寡头统治集团对自己收最少的税,统治集团对自己课最重的税。在美国历史上,我们有统治集团(最著名的出自建国世代和二战后的时期),不过我们也有寡头统治集团。不难看出今天的美国是前者或后者。
瑟罗最近指出,当寡头统治集团取代统治集团,国家的收入差距会愈来愈悬殊:「多数美国劳工从不曾在人均国内生产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遭遇实质的薪资缩减。」在一九七三和一九九三年间,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成长了百分之二十九。尽管增长率低于前二十年,不过仍是相当显著的增长。然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并没有平均分配:百分之八十的劳工不是落入窘境,就是勉强维持原地踏步。「在男性中,前百分之二十的劳动力拿走了国家所有的薪资成长。」这并不是每个高科技经济体都能看到的特征。其他能与美国相比的国家,譬如日本和德国,其GDP增长是由全体社会共享。6如果只看美国前百分之二十的劳工,我们会发现超乎合理限度的差异。收获最大的是前百分之五,其中又以前百分之一最有斩获。
与这批知识/权力精英同步成长的是一个贫穷的底层阶级(underclass),也就是精英阶层最渴望与之分割的一群人。四十年前,住在都市贫民窟的人们可以不上门锁就安心入睡。他们很穷,而且被隔离,可是他们当中失业的人并不多,未婚生子的情况也比较少见。他们不被称为「底层阶级」 ── 这是瑞典社会分析家冈纳.米尔达(Gunnar Myrdal)于一九六三年发明的用语,专门指涉受贫穷与隔离伤害最大的那群人。7他谨慎地为用语加上引号。起初它是少数政策专家才知道的说法,等到一九七○年代后期时,已成为受社会大众广泛认可的用语及社会问题,就连贫民窟的居民本身都认可。(尽管一开始是社会科学分析使用的中性用语,它最终变得带有贬义,是一种指责穷人贫穷的方式。我们要澄清,我们在使用这个用语时,只取其分析意义。)
在种族语言变得敏感的时期,作为一个用语,底层阶级有不分肤色的巨大优势。然而,在多数美国人之间,底层阶级主要被用来指称黑人,事实上是专指仍住在人口外流的贫民窟的那些黑人。这些贫民窟曾经是蓬勃发展的社区,但如今就像是被轰炸后面目全非的遗迹。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穷人有六分之五是白人,此外贫困在滋生毒品、暴力和不稳定家庭时是不分种族的。
这一切怎么会发生?我们怎么会让它发生?答案有一部分来自美国城市的去工业化。过去三十年,美国主要城市已流失了数十万份蓝领工作和数千份白领工作。教育程度足以踏进专业或准专业技术劳动力的非裔美国人,纷纷搬离旧贫民窟,但并不是搬到种族融合的住宅(多数地区的居住隔离情况在过去三十年并没有改变),而是搬到新兴的黑人邻里与市郊,拥有与相同收入水准的白人社区一样的便利设施。贫民窟的人口因此减少,很多贫民窟现在只有全盛时期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人口。8
留下来的人于是面临公共与私人制度性支持的系统性撤除。中产阶级非裔美国人在离开时,也带走许多他们一直以来参与的教会和俱乐部。财政压力日增的城市关闭了贫民区的学校、图书馆和诊所,甚至连警察局和消防局都裁撤掉。留下来的最弱势的群体,必须在一个通常连果腹都是大问题的霍布斯式世界自生自灭。如今贫民窟完全不会助长依赖,因为想在这里生活必须拥有最迫切的那种自力谋生能力。和某些精英阶层不同,底层阶级为公民的身分危机所苦不是因为它的成员选择退出,而是因为他们被经济及政治部门赶走了(拒绝给予其公民身分),因为对经济及政治部门而言,底层阶级完全是多馀的。其他不那么受个人主义文化蒙蔽的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存在比我们更为敏感。譬如在法国,失业的人开始被称为「被排除者」(les exclus),因而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9
这可不是精英阶级想听见的故事,于是有些记者,甚至有些社会科学家,用另一个故事帮助他们,这个故事因为我们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而好像说得通。按照这个替代故事的逻辑,底层阶级不是(国家)系统性撤除最贫困且最孤立的社会成员的经济与政治支持所造成的。底层阶级的成员只能怪自己:造成问题的是他们对一切帮助的抗拒。又或者,在底层阶级故事另一个广受支持的阐述中,底层阶级恰恰是社会在帮助这些人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尤其是「大社会」福利计划(Great Society),它导致了自我延续的永久性福利依赖(welfare dependency)。讲述这个故事的人略而未提的事实是,包括「对单亲家庭补助」(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在内的福利金支付,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系统性地减少了,而且光是一九八○年代期间就下降了一半,而且有超过七成接受社会补助的人不会拿超过两年,超过九成的人,八年内就能脱离救济。
底层阶级的故事指责受害者,而不是承认美国社会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失败得一塌糊涂,其用意是为了安慰富人的良心,甚至让他们在赤字不断扩大的时候,还能对社会福利成本表现得更加愤愤不平。不过,更重要的是,底层阶级的故事有吓唬和警告所有不那么富裕的人的效果,他们当中有些已看到自己的财产被侵蚀,有些则是倾全力也只能勉强打平。底层阶级使人有依据去定义自己不想成为的样子;有了底层阶级,他们才知道自己还不算太糟;有了底层阶级,他们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才是最可怕的。此外,底层阶级让他们有个对象可以责怪。日益萎缩的中产阶级因为全球竞争的压力丧失战后的工作安全感,变得很容易瞧不起穷困潦倒的人,将他们视为国家问题的源头。若说成功和失败是个人努力的结果,我们不可能去指责处于社会顶端的人 ── 当然啦,除非他们是政客。
赖希详细阐述了当前社会经济生活的三阶级分类学。他把美国的三个阶级区分为:生活在菁英郊区的安全中的「上层阶级」(overclass)、「被隔离在黯淡且暴力频仍环境中的底层阶级」,以及被困在「保持现有地位的狂热」中的新兴「焦虑阶级」(anxious class)。愈来愈多的家庭试图将两份、有时甚至是两份以上的薪水凑起来,以弥补不断扩大的收入、健保与养老金的差距。这些差距正刺激著传统定义的中产阶级的「瓦解」。10公民的身分危机在焦虑阶级间表现为对政治的幻灭,以及对经济前途的不确定感,这种不确定感㳽漫社会,导致对个人生存的担忧可能取代社会团结。11
在经济成长几乎由所有人利益均沾长达二十五年之后,美国于一九七○年达到了近代史上收入平等的高峰,并且拥有强健的公民文化。一九六○年代的挑战令人非常不安,但也激励人心,对公民的身分的理解持续刻划整个社会的样貌。在经济成长的利益彻底流向前百分之二十人口长达二十五年之后,美国于一九九五年来到近代史上收入不平等的高点,而且我们的公民生活一团糟。我们看到了麦可.林德(Michael Lind)所说的富人革命,以及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所说的对穷人的战争。12当一个社会的多数人口原地踩水,底层不断下沉,上层正在崛起,这个社会显然在各个层级都陷入了公民的身分危机。13
正在衰退的社会资本
谈论衰退的社会资本,是描绘社会生活与公民参与实践变弱(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公民的身分危机)的一个方法。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最近让公众注意到这个用语,他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如下:「若以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1]和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2]的概念做类比(增进个体生产率的工具和训练),社会资本指的是能促进协调和合作以实现互惠的社会组织特征,譬如网络、规范和信任。」14社会资本有许多潜在指标。普特南使用最广泛的两个指标分别是社团会员数和公众信任。
普特南以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作为最近一篇文章的标题。「独自打保龄球:美国正在衰退的社会资本。」15他调查发现在一九八○到一九九三年间,美国的保龄球友总数增加了百分之十,可是保龄球联盟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他指出这可不是微不足道的事:近八千万美国人在一九九三年至少打了一次保龄球,比一九九四年国会选举的投票人数高出将近三分之一,与声称定期上教堂的人数则大致相同。但普特南只是利用保龄球的例子象徵美国社团生活的衰退,自从一八三○年代托克维尔访美以来,社团生活的活力一直被视为美国公民文化的核心。
诸如家长教师联谊会(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和妇女选民联盟(League of Women Voters)等典型妇女组织在一九七○年代开始面临会员锐减的情况,而这通常被解释为妇女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结果。传统上属于男性的社团,譬如狮子会、麋鹿会、共济会和圣地兄弟会,则在一九八○年代遇到会员流失的问题。工会自一九五○年代中期达到顶峰以后,会员数已减少了一半。我们都知道合法选民中真正有去投票的人,人数持续地减少,但普特南提醒我们,当被问及过去一年是否曾参加城镇或学校事务的公开会议时,回答「是」的美国人,和一九七三年相比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
罗伯特.伍斯诺(Robert Wuthnow)最近研究的支持性团体,像是十二步骤团体(twelve-step groups),几乎是唯一正在成长的团体。这些团体对成员的要求很基本,而且主要是针对每个个人的需求。事实上,伍斯诺形容这些团体是让个人「在他人的面前专注自己」,我们不妨称之为「在一起孤单」。16普特南认为只要求会员做纸本登记的团体,像是已发展得极为庞大的美国退休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几乎没有公民重要性,因为他们的成员也许有共同利益,可是却没有有意义的互动。普特南还担心网际网路、城镇电子会议和其他被大肆吹擂的新技术装置,大概不具任何公民意义,因为它们无法维系公民的参与。举例来说,谈话性广播鼓动的是私人意见,而不是公共舆论,而且不怀好意地利用人们的焦虑、愤怒和不信任,这一切对公民文化都是致命伤害。宗教似乎是唯一正在抵抗这个总体趋势的领域。自一九五○年代宗教热潮消退以来,宗教成员人数和教堂出席率一直保持得相当稳定,不过自一九六○年代以来,与教会相关的团体会员数下降了约六分之一。
与社团参与度衰退并行的是公众信任的下降。听说美国人当中偶尔相信或几乎从不相信华府的人数稳定增加,已从一九六六年的百分之三十成长到一九九二年的百分之七十五,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意外。但当我们听说,美国人认为社会上多数人能被信任的占比,在一九六○到一九九三年间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认同的人从百分之五十八降至百分之三十七),是否还能同样镇定?
社会资本衰退不是我们当初在本书提出的论点。本书根本上是一种文化分析,重点放在语言上,而不是行为。我们担心个人主义语言可能动摇公民承诺,但我们点出美国人加入社团的比例向来很高,以及相较于其他先进工业国家,美国有较强的社团会员力量。究竟这样的衰退是否属实目前仍有争议,不过我们倾向认为,在一九八○年代初撰写本书时还不太清晰的一些趋势,如今已显露无遗,令人感到不安。17
我们相信个人主义的文化和语言影响了这些趋势,不过它们的出现也有结构性原因,其中许多源自我们已经提到的经济变化。社会资本的衰退在不同阶级中以不同的方式显现。譬如退缩到门禁森严的封闭社区,是上层阶级公民参与度下降的标记。这也与许多公司在合并分家的过程中不断迁移有关。萝莎贝丝.康特(Rosabeth Kanter)最近提出了这些迁移的一些后果:
对于社区和员工而言,反覆的公司认同重组令人困惑,而且影响深远。大城小镇仰赖私部门增加公共服务,以及支持社区理念。这样的社会回馈有强烈的「总部偏差」(headquarters bias):总部设在城市的公司往往为此付出更多,多过其他规模相当但总部不设在城市的公司,平均每年比在地的联合劝募(United Way)多贡献七万五千美元。18
康特指出,一个公司总部从中型城市出走,可能会破坏该城市的社会结构。城市不仅失去了数千个职缺,也失去了企业高管的公民领导力。当地慈善机构不仅失去金钱赞助,也失去董事会成员。
企业的变动无常可能在金字塔顶端导致一种「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与社会脱离后,富人可以不带罪恶感和责任感地扮演他自己选择的角色,」麦可.路易士(Michael Lewis)指出,「他成为美国神话的伟大人物 ── 四处漫游的拓荒者。这年头,发迹致富的人可能会花更多的钱在代步工具,而不是他的住宅,例如私人飞机是最能够让他鹤立鸡群的资产。……昔日贵族对地方抱有的自负感,已被光荣的无地方性取代。」19过去富人世家的豪宅无疑是炫耀性消费的表现,但它们也促使富人对自己居住的特定地方(城市、州、地区)有种责任感。温德尔.贝瑞(Wendell Berry)谈到「漂泊不定的习惯性破坏者」(itinerant professional vandals)20,这些人和赖希的「符号分析师」(孤立的精英)可能没有太大区别,他们不对任何地方产生感情,因此往往表现得比较像寡头统治集团,而不是统治集团。
移动到收入光谱的另一端,李.伦沃特(Lee Rainwater)的经典著作《钱的用处》(What Money Buys)證明,贫穷(指收入不足以维持可接受的生活水准)不仅剥夺了穷人的物质资本,也剥夺了他们的社会资本。在传统的阶级社会中,低度的物质福祉与提供侍从制度各项待遇的明确社会地位相关。在美国这样的社会中,由于根本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对个人自立的重视,社会地位(乃至个人认同)主要是由一个人跟经济体的关系所赋予,由一个人的工作及源于工作的收入所赋予。若是收入低于社会可接受的标准,或没有获得符合社会期待收入的机会,对一个人日后可能成为的人,以及可能拥有的生活都会有长期的影响。诚如伦沃特所言:
人们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不断地暗自评估自己有多大机会获得维持某种正当身分所必须的管道与资源。人们对未来机会的预估,特别是在儿童期、青春期和青年时期等阶段,明显地影响了他们与他人交流的方式,以及他们利用身边资源的方式。一旦个人评估他未来参与受社会认可的活动的可能性很低,尤其是当这个看法被生活周遭的其他人(老师、警察或父母)一再强化时,他便有可能在追寻另一种获得认可的可能性时出现偏差行为。一旦认定自己的人生已经「没什么好损失」时,人们对街坊邻里和官方社会管理机构施展的非正式与正式社会控制就会显得无动于衷。21
长期贫穷藉由减少社会资本挡住穷人的经济与政治参与,连带削弱了培养道德品格(moral character)及延续家庭生活的能力。
当我们把居住隔离的结果累加到贫穷的结果之上,情况变得惨不忍睹。我们要记住尽管国家已制定了《公平住房法案》,但过去三十年,对黑人的居住隔离在大型城市始终未变。22确定改变的是贫穷率最高的地理区,失去了零售贸易出口、政府服务、政治影响力,最糟糕的是,失去了能提供像样生活的就业机会。那些被剥夺社会资本的人,已经被关在实际上与周遭社会无关的「保护区」。
甘斯在《中产阶级美国的个人主义》(Middle American Individualism)描绘美国社会中产范围的生活样貌,有助于我们了解焦虑阶层的社会资本状况。23甘斯批评本书对中产阶级美国的个人主义太过吹毛求疵。甘斯说,毕竟住在中下及劳动阶级郊区,对家人朋友比对公民生活更尽心的这些居民,自移民祖先从事体力劳动的赤贫状态或在原居国从事小农耕作的繁重粗活脱离才不过一两个世代。这些不那么遥远的祖先,过去在社会上属于任人摆布的从属地位,受到命令他们做事的人的欺负。拥有自己的房屋,到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度假,在离开工作场所后可以自由决定去找谁或买什么 ── 全都是不曾享有这些自由之人的后代特别爱护的自由。简朴的郊区不是开放边疆,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它成了一个合理的边疆复制品。
然而,对一批为数可观的中产阶级美国人而言,生活中的诸多讽刺之一是工会身分对他们实现相对富裕及随之而来的独立有很大的帮助;可是对他们许多人而言,工会已成为他们想摆脱的另一个相斥机构。在甘斯看来,中产阶级美国人不仅怀疑政府,也根本不喜欢任何形式的组织。相对于中上阶级(也就是我们所谓「上层阶级」的下层),他们不是加入许多俱乐部或社团的那种人,至多只属于一到两个社团,其中最多人加入的就是教会。尽管持续保有强烈的国家认同,他们对政治的感受是困惑与不安,愈来愈无法相信政治。他们的政治参与逐步衰退。
由于这些(甘斯完全有理由要求我们理解的)趋势,中产阶级美国人如今渐渐失去当初让他们得以实现宝贵独立性的社会资本。最重要的是,劳工运动的衰退也是如此。工运衰退源自过去二十年的修法剥夺了工会的大部分权力和影响力,以及国会自一九九一年以来一直拒绝将最低工资从每小时四.二五美元提高。不过,诚如我们在仍忠于工会的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所见,这种攻击是可以被扭转的。在美国,即使有工会的地方,工会会议至多也只有百分之五的成员出席。由于欠缺工会身分能提供的社会资本,焦虑阶级的美国人以新的方式受制于他们本以为已经摆脱的独断支配。一个人如果被裁员,可能甚至会失去房屋和旅行车,而唯一的替代就业机会只提供最低工资。
若考虑美国政治参与发生的变化,我们的社会资本衰退就更令人苦恼。悉尼.韦尔巴(Sydney Verba)及同僚们最近在《声音与平等》(Voice and Equality)中提出了关于美国政治参与的全面评估。24尽管有关长期趋势的数据并不明确,但它们确实暗示了某些趋势。过去三十年期间,美国公众的平均教育程度稳定上升,可是通常与教育相关联的政治参与程度却没有跟著上升。这一事实可被看作政治参与有所下降的标志。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改变的性质。政党认同和党员人数下降了,给国会议员的捐献与信件却增加了。开支票或写信这两种持续成长中的活动,通常都是在人们的家中私下进行的。韦尔巴及同僚们指出,两种活动都无法产生比较社交性质的政治参与给人的个人满足。
此外,捐献与收入有高度相关性,是我们社会中最不公平的政治参与形式。捐献作为一种政治参与形式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以及政治参与和收入、教育与职业产生关联的普遍趋势,使《声音与平等》提出以下结论:
有意义的民主参与,需要公民在政治中的声音清晰、响亮且平等:清晰,以便公职人员知道公民的想要与需求;响亮,以便促使公职人员认真看待他们所听到的内容;平等,以便公平回应众人喜好与利益的民主理想不受侵犯。我们对主动参与美国政治的分析显示公众的声音通常响亮,有时清晰,但鲜少平等。25
尽管教育、职业和收入的不平等,有利于本来就有优势的人获得政治参与的资源,但有个例外却不容忽视。韦尔巴及同僚们注意到:
唯有宗教机构能抗衡此等资源累积过程。藉由提供本来资源匮乏的人培养公民技能的机会,宗教机构在美国的参与式系统扮演非同寻常的角色。常见的说法把美国政治的特殊性格归因于工会孱弱,还有缺乏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党,因此无法动员下层社会(特别是劳动阶级)从事政治活动。而另一个美国社会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国人上教堂的频率很高,其结果是在其他地方通常由工会和劳工党或社会民主党执行的动员,在美国更可能是由宗教机构执行。26
为概述社会资本衰退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我们可以看看这种关系在几个社会阶层的样子。总体而言,除了围绕宗教机构的活动,政治参与已从需要公民投入的形式转变为基本上私密的形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捐款。韦尔巴及同僚们指出的不平等声音显示焦虑阶级的民意严重被忽视,而底层阶级的民意几乎完全没得发声。即使在上层阶级之间,政治参与也从比较活跃的投入形式,转变为单独的开支票与写信行为。最后,韦尔巴及其同僚指出金钱在政治生活中日益提高的重要性,导致公众变得愤世嫉俗:「简言之,一个比较看重金钱的参与式系统,不太可能使社运分子或全体公民对政治观感更佳。」27
个人主义和美国危机
多数美国人都同意我们的社会出了大问题,就如同民意调查问题常说的,我们没有「朝正确的方向前进」,但他们对于为什么会这样,以及该如何应对却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在被我们称为公民的身分危机和社会资本衰退的结构性问题中寻求解答。此外还有哪些不一样的解释呢?把问题源头定位在家庭危机,大概是最广为接受的替代解释。我们千万别把主张美国社会亟需「家庭价值」的呼吁不当一回事。前文中描述的所有趋势几乎都威胁到家庭生活,而且往往在家庭中感受最为深切。由于失业而无法结婚成家,还有被裁员或沦为打工族而没有足够收入养家,连同这些情况造成的紧绷情绪,绝对可以被看作家庭危机。不过,为什么危机的实际表现是欠缺家庭价值呢?
除非再次把个人主义文化纳入考量,否则我们不太可能了解这其中出了什么事。若把人力缩编造成的失业或收入减少视为纯粹的个人问题,而不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将试图理解每个失业或未充分就业的人出了什么问题。如果我们还发现这些人有未婚生子、离婚或无力支付抚养费的倾向,可能就会判定问题的根源是被削弱的家庭价值。在本书中,我们大力肯定了家庭的价值;而在本书和《美好社会》(The Good Society)中,我们都主张对婚姻和家庭责任重新做出承诺。但把美国政经结构中的故障所衍生的种种问题,主要归咎在欠缺家庭价值的个人的缺点上,在我们看来是个可悲的错误。这不仅增加了个人的内疚感,也将焦点从更大的集体责任衰退转移开来。
个人主义文化与重视家庭价值之间的连结还带来另一个结果。传统上,家庭由从事有偿劳动的男人供养,不能养家糊口有可能被视为男子气概不足的标志。因此人们很容易妄下结论地认为:如果美国的男人能像个男人一样,家庭生活就会得到改善,社会问题也将得到解决。毫无疑问,这样的想法多少支撑了「基督教守约者」[3]运动,和一九九五年的「百万人大游行」[4]。尽管我们认同这些运动的许多价值,但我们不认为增加男性责任就能充分解决美国经济与政治的深层结构问题,我们甚至怀疑这么做顶多能微不足道地减轻美国家庭承受的巨大压力。要是男人尽到男人的本分,社会上所有人就都会好起来的观念,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可悲的文化幻想。
对于我们面临的种种困难,另一个常见的替代解释是把它视为社区的失灵。我们相信,这说法的确有理,但前提是我们对社区的理解够广够深。然而,在许多当前的用法中,社区是指由个体自愿组成的面对面接触团体。若是做此用法,那把社区失灵视为问题根源就可以被诠释为,要是有更多人自愿到「慈善厨房」(Soup Kitchen)、「仁园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或「送餐到府」(Meals on Wheels)做爱心,我们的社会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了。诚如家庭价值的例子,本书大力肯定面对面接触社区及义工团体能为社会做出的宝贵贡献,但我们不认为美国社会的深层结构性问题,可以从增加投入狭义的社区而得到有效缓解。我们同意若自愿投入社会服务的个人愈来愈多,长远来看可以增加社会资本,从而丰富我们用来解决问题的资源。但如果想要根除我们的问题,就必须利用这些资源去克服无法单凭志愿性行动(voluntary action)直接解决的制度性困难。
强调社区的小规模与自主性为问题解决之道,还会遇到另一个困难。诚如在讨论韦尔巴及其同僚们的作品时所指出的,志愿活动往往与收入、教育和职业相关。比起底层阶级或焦虑阶级,我们更容易在上层阶级找到「参加很多俱乐部与社团的人」,唯有宗教团体的成员是不分阶层的。这代表志愿活动往往是为富人的利益服务,胜过为帮助最贫困的人(但我们不否定还是有真正在帮助困顿者的志愿活动)。政治的志愿主义(political voluntarism)尤其如此,韦尔巴及同僚们的研究不容置疑地證明了这点。因此,拆除给最贫困者的公共供给(public provision)结构,期望志愿部门(voluntary sector)[5]出面接管,是在三个重要的方面受到误导。首先,志愿部门绝没有资源帮忙擦屁股,诚如教会、慈善机构和基金会近年来再三强调的。第二个造成误解的原因是,富裕的公民觉得他们透过志愿活动付出时间与金钱「改变世界」,已履行了对社会的义务,却完全无视一个事实,也就是他们几乎没有减轻多数人面临的实际困难。第三个原因是,我们注意到,有钱有势的公民不成比例地主掌了志愿部门,而且有不少的志愿活动给富人的保护胜过需要帮助的人。
假使认为解决之道在于振兴社区,那么还有一种对社区的理解也会带来困难:把社区理解为邻里或特定地点(locality)的概念。本书鼓励邻里团结,支持大城小镇的公民参与。但居住隔离是当代美国无从改变的现实。即使不谈城市贫民窟的高度隔离,住房成本差异导致的阶级隔离在美国郊区也愈来愈明显。因此,一个人很可能就算「参与」邻里、乃至郊区小镇的公共事务,也永远不会遇到来自不同种族或阶级的人。人们不会接触到处境与自己不同的人的生活现实,甚至可能屈服于自然的人性诱惑,把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尤其是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看作不如自己的人。例如焦虑阶级就不希望自己被跟底层阶级搞混在一起。上层阶级(包括受过教育的中上阶级的下层族群)最不友善的一个特征是,他们不想跟中产阶级美国人有瓜葛,不想跟「普通人」和其他文化特质不够体面的人往来。即使在底层阶级中,没有领社会救济金的人,也会看不起长期依赖社会救助的人。28在这种情况下,单独强调邻里社区的团结,实际上可能导致更大的社会问题,而不是解决这些问题。
强调美国社会问题是欠缺家庭价值或社区失灵所致的解释,其共同之处在于把我们的问题当作个人的问题,或仅是最狭义的社会问题(即关于家庭和地方社区),而不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问题。上述对美国困境的常见解释都对政府或国家的角色抱持敌意。如果我们能照顾好自己,也许偶尔从朋友家人那边接受一点帮助,谁需要国家?实际上,国家常被看作爱管闲事的父亲,不承认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大,不再需要他。29他没办法帮忙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创造这些问题的人就是他。
根据这种思维逻辑,市场相较之下显得无害,大抵是个中立的竞争场所,奖励有成就的人,惩罚无能的人。然而,有些人意识到市场并不中立,他们意识到某些人与组织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能做出不利于许多公民的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大企业也和大政府一样,是问题的根源,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尽管如此,与多数类似的社会相比,认为市场比国家公平的倾向在美国社会中比较强烈。
个人主义和新资本主义
因此,在本书第十章中被我们称为新资本主义(neocapitalism)的意识形态,其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拜个人主义文化所赐。我们当初在第十章勾勒的美国政治局势样貌,如今看来并不完全到位。我们那时认为福利自由主义(welfare liberalism)及其反制运动「新资本主义」之间的僵局即将结束,而且管理社会(administered society)和经济民主(economic democracy)这两种替代方案即将登场。这一双刚发轫的替代方案如今看来并未成为现实,起码正处于漫长的等待之中。倒是新资本主义对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控制愈来愈强大。对「大政府」和「量入为出自由主义」(tax-and-spend liberalism)的批评不断加剧,尽管许多特定选区(加总后等于绝大多数的公民)赞成使他们受益的各种公共供给,却同时反对他们得不到的补助。
我们相信,我们十年前没有误看新资本主义方案正在为国家带来的严重伤害。这些伤害在今天变得空前显著。不过,我们显然低估了新资本主义立场所能利用的意识形态狂热 ── 这个失算对我们而言有点讽刺,因为这里所说的狂热很大一部分是源自本书关注的焦点:个人主义。新资本主义的愿景唯有在被视为吾人主流意识形态个人主义的表现时(甚至是一种道德表现),才有可能实现,它不由自主地强调独立、轻蔑弱点、吹捧成功。狂热的程度会在经济困境中加剧,因为在这种时候,「努力工作,按规矩办事」的人,得不到他们自觉应得的奖励。
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新资本主义一直都能成功将它的政策失败,转化为意识形态的成功。它说服了许多美国人相信它所造成的问题,譬如一九八○年以来国债暴增为四倍,其实是福利自由主义的后果,尽管福利自由主义已经二十多年没影响美国政策的议程了。因为给穷人的公共供给大幅减少而产生的种种问题,被新资本主义将责任推得一乾二净,一口咬定这些问题都要怪经过数十年删减仍阴魂不散的福利制度成效不彰。新资本主义认为切断穷人对国家的「依赖」,其实是对他们的仁慈。
从新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透过私有化增加经济竞争力几乎可以解决所有的难题。健康保险「产业」最近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是新资本主义面对公共问题的典型解决之道。在健保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政府从事投资与再分配以便照顾所有人并控制成本的积极作为遭到拒绝,取而代之的是营利性医疗保健组织的大规模成长。医疗服务仍然由同一群人以相同的方式提供,只不过低薪的医生变少了,而且这群医疗从业人员训练有素地不断设法削减成本,愈来愈无心照顾病患的福祉。非营利医院被连锁企业和健康保险公司收购,为管理阶层和投资者创造最大利润。这些大集团的首席执行长获得八位数、甚至九位数的年薪,而能够使医疗保险更有生产力、更有效,或是(老天保佑,万万不可)更公正的新投资则被搁置。随著保险公司提高保费,雇主要求劳工负担更多健保给付,更多人被彻底赶出私人医疗体系。即便还没关闭,不堪负荷的公立医院在危险的条件下营运,将使纳税人为就医求治付出巨大代价。从新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角度来看,跌进完全没有医疗保险深渊的那些人,只能怪自己,在顶端抽取了系统资源的富人则有权强取豪夺。
新资本主义思想的目标,是说服民众相信政府的一切社会计划都失败得一塌糊涂。尽管有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数百万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和社会安全福利(Social Security)的受益者认为这样的立场难以服人。于是这些计划不再被抨击为本质上邪恶的,而是被抨击为太过昂贵,等于为了年长的上一代抵押我们儿孙的未来。于是民众根本不清楚这些社会计划实际上多么的成功。
六十五岁以上的美国人,主要因为受联邦医疗保险的照顾,是世界上同龄人口中最健康的。要不是有社会安全福利,六十五岁以上的美国公民将有半数处于贫穷线以下,就像一九四○年以前的美国社会,而不是像现在只有百分之十的贫穷老人。因此,社会安全福利使百分之四十的老年人不致陷入贫困。总体而言,我们「对贫穷宣战」[6]遭遇惨败,并不是如新资本主义思想家所说的,因为我们为穷人做了太多,而是因为我们几乎什么都没做,所以甘斯才会把这情况称为「对贫穷的争执」(skirmish on poverty)。30提供教育基础建设与经济机会给长期贫穷者所需的资金,从来都只是空头支票。(把钱确实花在这方面的西欧,扫贫战争一般是有成果的。)支出方面的最大例外是社会安全福利。要不是今天国家和公共供给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攻击,有关「世代正义」的辩论就会被更严肃地对待,不过应得福利(entitlements,按:指现行法律承诺给予公民的福利)增加将导致破产的最糟糕预测,没有把预期生产力成长可能填补福利增加的预算缺口纳入考量。在我们确实使多数老年人远离贫穷之际,贫穷的儿童人数却不断增加。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删减联邦医疗保险和社会安全福利所得,不会被用来帮助有需要的美国年轻人,只会被拿去填补富人减税留下的洞。
二战结束后的头几十年,大幅的社会支出带来了大幅的经济成长。过去二十年,随著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加深,社会支出急剧下降。诚如我们所见,随著物质与社会基础建设支出的减少,经济成长率开始下降,经济不平等迅速恶化。我们会以为任何读过基础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一个国家如果不投资未来,前途必定萧瑟黯淡。不过,在新资本主义思想的拥护下,美国经济选择了较高的短期收益率(不管多么投机),而不是会带来长期成长的投资。尽管结果显而易见,选择背后的意识形态理由,却被比最为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更能忍受失验[7]的新资本主义思想遮蔽了。
近几十年,美国的政经变化与西欧极为相似(却和东亚并不相像,这点很有趣),但这些变化在美国比任何地方都更极端。这当中肯定有结构性的原因,其中有些原因还有待理解。然而,我们深信在收入不平等和对公共供给的攻击等问题上,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极端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主义文化所致,因为它不理解政府的职能与责任。
接下来何去何从?
我们认为新资本主义的政治议程存在致命缺陷。它自称强烈反对国家,却无情地利用国家执行「市场纪律」。它创造出来的问题只会被市场恶化,需要有效的政府干预和一个强壮的独立部门才能解决。当初撰写本书时,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按:强调个人与群体之间的联系)一词尚未流行,关心公民社会也还没蔚为风尚。激发对公民社会关注的是康米主义的垮台,以及对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民主基础的担忧。本书以出乎我们意料的方式被捲入辩论中。诚如我们在《美好社会》序言中指出的,如果社群主义等于反对新资本主义议程,以及反对几乎只有自主这项优点的理论自由主义,我们就是社群主义者。可是如果社群主义意味著,首重加强以十九世纪小镇为模范的小规模与面对面接触的人际关系,我们就不是社群主义者。31就像我们在《美好社会》主张并在此重申的,唯有有效的制度,即经济的、政治的与社会的制度,能使复杂的现代社会变得宜居。
倘若单凭小规模社区无法解决我们的问题,到哪寻找解决方案的压力仍然存在。在当代共和主义、甚至国族主义中,国家共识和国家行动被认为是克服我们目前困难必不可少的条件,这观点以林德的《下一个美国》(The Next American Nation)为代表作。站在反方的是复杂的社群主义或结社主义(associationism),它们主张头号重点是把职能下放给较低层级的社团(但不是避免承担国家责任),代表作有强纳森.波斯韦尔(Jonathan Boswell)的《社区与经济》(Community and the Economy)32或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的《联合式民主》(Associative Democracy)。33然而,我们拒绝将上述两方视为对立的观点,因为我们认为唯有国家达成共识,才能将责任下放给各种社团而不至于削弱公共供给。
尽管其政策影响尚无定论,公民社会讨论的活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34我们赞同以波斯韦尔和赫斯特的提议为代表的民主社群主义和民主结社主义,是因为他们没有把公民社会想像成和国家与经济彻底隔绝,而是将社区和社团生活看作和国家与经济相互渗透的。他们愿意给予社团在国家与经济方面的治理功能。赫斯特预言社团将承担起社会福利供给的职能,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发生在美国社会中。他们都希望看到民主的治理职能在经济中运作。他们认定国家和经济应该为人民服务,而不是颠倒过来,诚如今天常见的实际情况。我们肯定波斯韦尔的经济观点:
若想要追求平衡的、持续的经济表现,为了求表现而渴望经济表现是不明智的,甚至会弄巧成拙,更不用说在道德上是不健全的。如果我们真心想要经济表现,我们似乎应该更积极地追求另一个目标,也就是一种延伸至、但不限于经济体系本身的社会变迁。这么一来,我们将会认为企业唯有属于社区,和社区共生,而且为社区著想,才能在实务意义与道德意义上成立。我们将会承认经济健康与一场社区复兴密不可分,而且两者之中比较重要的是社区复兴。35
我们在本书的末尾以社会生态学的概念,想像由形形色色的小社区所组成的一个整体大社区,每个小社区都有独立的议程和需求,但是每个小社区也会影响整体,而且前途取决于整体大社区的健康。社会关系的形式在每个层级都不同。每个层级应该有自己的权利与责任,而且不断透过公共辩论修订其性质。在探讨社会制度、作为本书续集的专著里,我们没有把社区变成书中的核心用语,而是代之以《美好社会》。我们强调一个美好社会在尊重每个成员的尊严之际,务必在各个社会层级谋求共善。我们相信这个取径可以为社群主义与公民社会理论家,提供一个有用的思考框架。
只要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维持霸权地位,上述一切可能都是纸上谈兵。决定论是新资本主义观点的危险之一。它意味著制度性的选择不存在,因为市场会决定一切。事实上,当代个人主义最复杂难解的一个难题,就是它可以把对个人选择自由的绝对信念与市场决定论相结合。但我们相信,这个决定论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错觉,无论全球经济、股市、边际利润,谁都不能决定我们的制度性选择,除非我们以公民的身分同意他们这么做。公民做制度性选择的能力靠的是文化资源,但我们的文化资源,还有物质与社会资源,都极度枯竭。本书呼吁重新填补这些资源,作为将美国社会朝新方向推进的基础。根据这篇序言谈到的许多议题,我们认为该论点值得再次重申。
公民身分的意义及其延续
虽然说社区的观念如果仅指涉邻居朋友,还不能满足我们当前的需求,我们想肯定作为一种文化主旨(cultural theme)的社区,将我们的忠诚圈不断向外扩大,最终拥抱理查.尼布尔(H. Richard Niebuhr)口中属于众生的普世社区(universal community)。36我们应该记住,当耶稣被问到,「我的邻居是谁?」他以「好撒马利亚人」(《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九至三十七节)的寓言作答,故事诉说真正出手相助的好邻居是一名撒马利亚人,尽管撒马利亚人是以色列境内被鄙视的族群。耶稣认为住在隔壁的人、同村庄的人,或同族裔的人可以是邻居。不过,当被直接问及时,耶稣却把邻居形容是一个陌生人、一个外族人、一个被仇视的族裔团体的成员。任何称不上普世社区的社区,都不是备受爱戴的社区。
美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许多改变,正从各个层级破坏著我们的社区感(sense of community)。我们当前正在面对的种种趋势,威胁著我们与他人的基本团结感:与生活周遭往来密切的人的团结(忠于街坊邻居、工作同事、镇民同胞),还有与住得离我们很远的人的团结,与经济处境和我们截然不同的人的团结,与其他国家的人的团结。然而,这份团结,这种人与人相连、命运与共、人人有责、四海一家的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使人类社会能应付威胁与利用机会的,正是团结、信任、人人有责。我们要如何强化这些濒危的能力,这能力说穿了就是以特定方式思考的文化力?
思考如何在美国社会三个阶级中再生其社区与团结文化力时,我们最好能记得前文提及的一些东西:在美国社会,宗教社团对成员的影响最大,而且几乎单凭己力就能触及各个阶级中的个人。我们可以把以社区与团结为目标的根本重新定位的需要,构想成某种改宗,某种意识与意图的转向。在圣经传统中,改宗意味著远离罪恶,面向上帝。远离自私自利,面向某个超越个人的身分认同,是多数伟大人类宗教信仰与哲学思想的特徵。改宗不能单单出于意志力,但若要实现改宗,我们务必找回使它有意义的故事和符号。
先谈谈上层阶级,对欧美白人男性支配社会长达三十年的严厉攻击,并未大幅削弱他们实际上的支配地位,而是被用来合理化有权势者衰退的公民责任感,以及自私地专注于增加金钱财富。在开放社会中,我们可以努力创造更具包容性的领导阶层,而不用贬低昔日精英的贡献。若要处理美国社会巨大的问题,至少有一部分上层阶级得表现得像个真正的统治集团。假如上层阶级的成员能克服自己的焦虑,他们会意识到属于统治集团能获得的自尊,远比属于寡头统治集团更多。他们可能会发现公民参与(是种对共善的关怀,对所有人皆属于同一主体的信仰),不仅对整体社会的福祉有贡献,也能有助于他们的灵魂救赎。唯有更大规模的公民参与能改善目前美国上层阶级的毁灭性文化与心理自恋。上层阶级重拾公民的身分,恢复对社区和团结的承诺,对社会整体及个别社会成员都是有益的。
我们应该特别说明,绝大多数本书的受访者属于上层阶级的下层,即所谓的中上阶级,无论他们(及属于同个阶级的我们)多么不喜欢被称为中上阶级。当然,这些人不是做重大决策的人,也不是目前美国经济的最大受益者。甚至可以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一针见血的「支配阶级中的被支配成员」(dominated fraction of the dominant class)来称呼他们。37但诚如我们在本书中提出的主张,他们是美国社会的象征中心,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多数美国人立志追求的,而且他们的确比百分之八十的同胞更富有。他们的资源远远超过其他阶级,他们具有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以及能够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公民技能。但问题是,他们能否找回前后连贯的世界观,进而利用这些资源创造共善,而不是创造自身的财富增长呢?
焦虑阶级也面临同样严峻的挑战,因为它的问题不仅止于文化和心理层面,还有很明显的物质问题。白人男性的平均收入已从一九七三年的历史最高点三万四千二百三十一美元,缓慢下降到一九九二年的三万一千零一十二美元。38但比收入衰退更可怕的是经济不确定性的连带上升,毕竟收入的衰退在很大程度上被愈来愈多女性进入职场抵消了(尽管女性就业也有它的诸多问题)。我们正逐渐成为所谓的「高度不安全」(advanced insecurity)社会。人力缩编、兼职工作,以及失去保险给付,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生活。
严重经济焦虑引起的愤怒和恐惧,很容易转移到「福利女王」[8]和非法移民身上。这些感觉也导致投票率衰退和社团会员减少,甚至工会会员的减少,还有离婚人数的增加。尽管经济上的焦虑是真实的,而且最终必须从结构上进行处理,但它所导致的焦虑阶层公民参与度下降,只会加剧他们的愤世嫉俗和绝望。恢复社会参与,是最有机会解决焦虑阶级所面对的问题,而对许多人而言,排序最优先的管道是教会、工会,然后是透过公民组织。除了物质问题之外,焦虑阶级和上层阶级有不少共同的心理与文化问题,而最好的解药就是为团结与社区的观念注入前后连贯性的意义更新。
处理底层阶级的问题,试图将其成员重新融入整体社会,是最艰巨的任务。问题的症结来自经济发展,它使底层阶级的两千或三千万成员变得多馀(别忘了,它也使焦虑阶级的很多人仅剩下些微重要性)。唯有公共政策的根本性改变才能扭转情况,而在目前的政治氛围下,这种改变几乎是毫无指望的。
不过,即便必要的公共政策改变也无法单独应付这情况。当社会信任有限且士气委靡不振,最紧迫的需求之一就是恢复人的自尊和能动意识(sense of agency),而这只能来自使民众得以属于整体社会并为社会贡献己力的参与。参与式正义要求每个人付出一切是实现社会共善所必须的。而反过来说,它迫使社会在安排其制度时,让每个人都可以用有尊严且延续其自由的方式,为公众的福利做出贡献。39光靠转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9]或社工的恻隐之心,绝对不可能解决底层阶级的问题。
在处理底层阶级的问题时,也许我们需要求助从天主教社会教诲衍生而来的「辅助原则」(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辅助原则主张最靠近问题的那些群体应该出面处理,在必要时接受社会层级较高的群体支持,但在可能的情况下,不会被社会层级较高的群体取代。这项原则代表尊重那些与需要帮助之人关系最靠近的群体,但不让这些群体变得独断,或是凌驾于适用所有层级的道德标准之上。底层阶级社会重建的过程将需要大量的公共资源,不过这些资源应由第三部门机构提供,可能的话,最好是地方的机构。在今天,辅助原则被拿来辩护政府削减支出,违背它的基本用意。事实上,辅助并不是公共供给的替代品,而且唯有在公共供给充分时才显得有意义。
归根究柢,底层阶级的需求和上层阶级或焦虑阶级的需求,并没有什么不同。底层阶级的社会资本更加枯竭,士气崩塌得更彻底,可是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底层阶级成员最需要的是明确的团结感与社区感,以及和社会上其他人同属于一个未来的感觉。
分裂之家
把眼前的情况和两段美国早期历史做对照,或许能对我们有所帮助。首先是导致后来美国内战的黑暗时期:一八五○年代的共和国危机。大卫.格林史东(David Greenstone)认为当时美国政治分成以林肯(Abraham Lincoln)为代表的改革自由主义(reform liberalism),和以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为代表的功利自由主义(Utilitarian liberalism)。40一八五八年伊利诺州参议员竞选期间登场的林肯─道格拉斯辩论,是美国历史的决定性时刻。辩论主题是奴隶制该不该扩展到位于西部的领土。道格拉斯走人民主权路线:如果人民想要奴隶制,就让他们拥有奴隶制。换句话说,在这个例子中,随心所欲的自由,就是随多数白人所欲的自由。支撑道格拉斯立场的基础是功利自由主义,它只求总和所有偏好,而不在乎偏好符不符合道德。
可是林肯说奴隶制是不对的,奴隶制与国家最基本的原则抵触,无论西部的多数人想要什么,都不应将奴隶制延伸到这些领土。换句话说,自由是只能做符合道德之事的权利。支撑林肯立场的基础是改革自由主义,源于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主义。它仰仗的是圣经文献,以及拥护共和的文献,不仅相信有客观道德秩序(「自然法和自然之造物主的意旨」),而且深信人人都住在一个共同利益超越个人利益总和的社会。就是这种道德政治使林肯在一八五八年六月十六日于伊利诺州春田市(Springfield)发表了精采的「分裂之家」(House Divided)演说。「『闹内讧的分裂之家不会成功』41,」林肯说,「我相信这个政府不能忍受,永久的半奴隶半自由制度。」42
将林肯的话套用到我们的处境之上,我们可以说,美国这个家今天不是因奴隶制而分裂,而是愈来愈深化的阶级分歧。道格拉斯完全不认为家的分裂是个问题,因为社会在他的眼中不过是个人选择及其后果的加总。然而,林肯认为某些情况在客观上是错的,并要求社会负起改变这些情况的责任。从历史上看,我们今天的情况与林肯当初所言有关,尽管奴隶制已被废除,但非裔美国人还没得到平等的对待。不过我们认为,尽管种族歧视的问题一直很严重,问题其实不在于种族歧视,真正的问题是社会阶级等级制度的种族化── 林德称之为「美国的巴西化」(Brazilianization of America)。43
种族差异在美国社会中真实存在,但我们不该让差异模糊我们的共同点。珍妮佛.霍柴尔德(Jennifer Hochschild)最近在《面对美国梦》(Facing Up to the American Dream)中,分析了美国人因种族而不同之处。44她證明美国黑人和白人共享美国梦的大部分意识形态(她所谓的美国梦不单指物质方面的渴望,还包括道德方面的抱负),但非裔美国人实现梦想的程度就是种族分歧之处了。单单关注种族差异会模糊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真理 ── 种族差异的根是阶级差异。阶级差异超越种族,分裂所有的美国人。
我们认为,今天的阶级差异程度是错的,就像林肯认为奴隶制是错的:阶级差异剥夺了数百万人充分参与社会,以及以个人身分实现自我的能力。这是美国人不愿面对的可怕秘密。许多国家在分裂成一个奢华的小精英圈和一个生活在不同程度的不安全与苦难中的广大群众,却还是屹立不摇,可是美国这个国家,带著过去二百二十年的理想和希望,不可能这样长此以往。
这带领我们看向第二个历史参照: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在一六三○年于麻萨诸塞湾殖民者下船前发表的布道「基督徒慈善的典范」(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温斯罗普讲道时警告说,如果我们追求「一己之乐与一己之利」,必将在这片美好的土地上灭亡。温斯罗普解释,使徒保罗的话是想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以兄弟情谊对待彼此,我们必须愿意为了供应他人的必需,节制自己不要物质过剩……我们必须以彼此的陪伴为乐,对别人设身处地得著想,一同欢乐,一同哀悼,一起劳动与受苦,一刻不能忘记……我们的社区,我们属于同一个主体。」45
在美国今日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忽略温斯罗普的忠告,很容易忘记我们团结的义务和我们的社区,很容易铁石心肠地只顾自己。在希伯来圣经中,上帝透过先知以西结对以色列人说:「我要从你的血肉身躯取出石头的心,给你一颗血肉的心。」(《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我们能否祈祷上帝为今天的美国人做同样的事呢?
[1]译注:投入生产过程中的耐久财或资本财,指实体的生产设备等商品。生产要素中的资本,主要指的就是物质资本。物质资本是一种固定资本,可以因为劳动而增加,在运作过程中产生的损耗为折旧。
[2]译注:指人的知识、经验、制度与习惯等。人力资本分成个人与社会两个方面,具备这些资本的劳工,拥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可以将这些资本转换成经济价值。人力资本可以经过教育等投资手段来增长。
[3]译注:基督教守约者运动(Promise Keepers)源自一九九○年代,是美国男性基督徒发起的一场全国性运动。时常藉大型集会、小型团体、媒体传播,鼓励男性过虔敬的生活,谨守对上帝、对家庭、对属灵夥伴的七个承诺,特别是对家庭要负起全责。
[4]译注:非裔美国人领袖路易斯.法拉堪.穆罕默德(Louis Farrakhan Muhammad)一九九五年十月在华盛顿特区组织与领导了「百万人大游行」,呼吁黑人男性重新认识他们对家庭和社区的责任。
[5]译注:也称为第三部门,第一、第二部门分别是公部门和私部门。
[6]编按:一九六○年代詹森总统提出的「大社会」计划,其中就有「对贫穷宣战」(War on Poverty),致力于解决美国底层阶级的贫困、饥饿问题。
[7]译注:失验(disconfirmation)是指期望与绩效相比较所得的结果。当实际绩效等于期望时,则无失验产生;当实际绩效大于期望时,会产生正面的失验;当实际绩效小于期望时,则产生负面的失验(Anderson, 1973)。
[8]编按:福利女王(welfare queens)是用来形容为提高生活水平而滥用福利制度的妇女,是带有污名化的标签。
[9]译注:透过政府无偿支出实现社会收入和财富再分配的一种手段。生活中常见实例有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以及政府对特定企业的补贴等。
1在《基督教社会思想史》(The Social Teaching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1 (1911))卷二的页八百一○,特尔慈写道苦行的新教「从纯粹功利的角度看待国家」,并否认「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合乎道德的目的,这点在古代世界(Ancient World)不言而喻,而且在现代世界再度被看见。」这是「把所有真正的人生价值转移到宗教领域很自然的结果,意味著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其馀的人生价值也只被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虽然这是一个「普遍的基督教观念,……喀尔文教派比路德教派或天主教信仰更是如此。」
2Stanley Elkins and Eric McKitrick, The Age of Federalism: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1788-180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各处,但主要是第四章。
3George Lakoff, Moral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4Robert B. Reich, The Work 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 Century Capitalism (New York: Knopf, 1991), part 3, “The Rise of the Symbolic Analyst.”
5Lester Thurow, Head to Head: 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 Europe, and America (New York: Warner, 1992), pp. 266-67.
6Lester C. Thurow, “Companies Merge; Families Break Up,”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 1995, p. E11.
7Gunnar Myrdal, Challenge to Affluence (New York: Pantheon, 1963).
8威廉.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是研究这些问题最可靠的学者。参见他的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 Urban Racial Tensions,” American Economist, 39, I (Spring 1995); “The ‘New Poverty’ Social Policy and the Growing Inequality in Industrial Democracies,” forthcoming; and other forthcoming works.
9参见Hans Koning, “A French Mirror,” Atlantic Monthly, December 1995, p. 100。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污名化失业者,透过提供他们足够的收入,让他们不会失去社会成员的资格。天主教在法国的地位更重要,再加上拥有另一种类型的共和主义,这两点部分地说明了美国和法国的差异。
10As reported in “Labor Chief Decries Middle-class Squeeze,” San Francisco Examiner, September 25, 1994, p. A2.
11约翰.格雷(John Gray)最近把我们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特有的「主流自由个人主义美国文化」描述为一种「个人选择和自我实现是唯一无可争议的价值」的文化,将「集体忠诚」和「公民参与描绘为个人选择和市场交换固定菜单上的非必选额外附加项目」。这个文化的影响有好有坏。诚如格雷所言,「在巨大的社会混乱、城市废墟和中产阶级贫穷背景下,它产生了非凡的科技和经济活力。」格雷实际上所说的是,对自由的错误信念,即认为自由是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的自由,而不是做道德上合理的事情的自由,其后果正在从根本上破坏我们的社会凝聚力。参见John Gray, “Does Democracy Have a Futur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anuary 22, 1995, p. 25.
12参见Herbert J. Gans, The War Against the Poor: The Underclass and Antipoverty Polic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在谈论对穷人的成见和污名化穷人方面尤其值得一读。另参见Michael Lind, The Next American Nation: The New Nationalism and the Fourth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chapter 5, “The Revolution of the Rich.”
13对美国不平等当前最佳的探讨是Claude S. Fischer, Michael Hout, Martin Sanchez Jankowski, Samuel R. Lucas, Ann Swidler, and Kim Voss, Inequality by Design: Cracking the Bell Curve My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14参见Robert D. Putnam,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American Prospect, 13 (Spring 1993): 35。普特南这概念是衍生自James S. Coleman,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300-321,柯尔曼又把介绍这个概念的功劳归给格伦.洛瑞(Glenn Loury)。
15In Journal of democracy, January, 1995, pp. 65-78.
16Robert Wuthnow, Sharing the Journey: Support Groups and America’s New Quest for Commun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p. 3.
17西摩.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对普特南有关美国人减少参与志愿组织的论点及相关数据的审慎评估中,推论表示这个论点「没有得到證实,但很有可能是对的」。参见他的文章“Malaise and Resiliency in America,” Journal of Democracy, July, 1995, p. 15.
18Rosabeth Moss Kanter, “Upsize, Downsiz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7, 1995, p. A23。另参见Rosabeth Moss Kanter, World Class: Thriving Locally in the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5).
19Michael Lewis,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November 19, 1995, p. 69.
20在《家庭经济学》(Home Economics, San Francisco: North Point Press, 1987)页五○,贝瑞写道:「一个强大的漂泊不定的习惯性破坏者阶级如今正在搜刮国家,彻底破坏国家。他们的破坏行为并没有被称为破坏,是因为它(对某些人)的庞大收益以及它规模的宏大。」
21Lee Rainwater, What Money Buys: Inequality and the Social Meanings of Incom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p. 31.
22Douglas S. Massey and Nancy A. Denton, American Apartheid: Segreg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dercla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3Herbert J. Gans, Middle American Individualism: The Future of Liberal Democra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8)。我们应该指出甘斯在谈论美国中产阶级时,大致是指收入分配的中间百分之四十,而我们把焦虑阶级定义在大约中间百分之六十。
24Sydney Verba, Kay Lehman Schlozman, and Henry E. Brady, Voice and Equal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5Verba, Voice and Equality, back cover.
26Verba, Voice and Equality, pp. 18-19.
27Verba, Voice and Equality, p. 531.
28Loic J. D. Wacquant in “Inside the ‘Zone’: The Social Art of the Hustler in the Dark Ghetto,”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Working Papers, 1994.写道:「『那些人比起我更是最糟』,贫民区的居民经常这样说,包括他们当中最一无所有的人,彷佛是自我安慰般,创造一个文法错误的双重最高级,充分说明社会最底层精密的微观等级制度。」
29Lakoff, Moral Politics.
30Gans, The War Against the Poor, p. 178 n. 1.
31我们相信这个退化的社群主义概念主要是其批评者的产物;那些自称社群主义者的人不是出于怀旧或对现代世界的恐惧。参见Amitai Etzioni, The Spirit of Community (New York: Touchstone, 1993).
32Jonathan Boswell, Community and the Economy: The Theory of Public Coope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33Paul Hirst, Associative Democracy: New Form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Governanc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4).
34谈论公民社会的新兴文献量很大。重要的理论声明包括:Ernst Gellner, Conditions of Liberty: Civil Society and Its Rivals (New York: Penguin, 1994); John Keane,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New York: Verso, 1988); Adam B. Seligman, 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and Jean Cohen and Andrew Arato,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2)。有一个明确的宗教观点,请参阅German Protestant Academies、Vesper Society、Ecumenical Foundation of Southern Africa和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等机构发起的Corresponding Academy on Civil Society出版品。
35Boswell, Community and the Economy, p. 201.
36H. Richard Niebuhr, The Responsible Self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8 [1963]), p. 88。考虑到我们的论点,从理查.尼布尔的儿子那里得知,「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我感觉到父亲对在我们不幸国家发生的他所说的「阶级受难」(class crucifixion)愈来愈担心,虽然我不太明白」,出自Richard R. Niebuhr to H. Richard Niebuhr, Theology, History and Culture: Major Unpublished Writing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as reported in Harvard Divinity Bulletin, 25, 1 (1995): 8,阶级受难是普世社区的对立面。
37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979]).
38Thurow, “Companies Merge; Families Break Up,” p. E11.
39关于这个立场特别有说服力的一个陈述可见于Economic Justice for All: Pastoral Letter on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and the US. Econom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 1986)。天主教徒当然没有独占这个立场。它植根于可以追溯到希伯来圣经的圣约传统,而且也显现在喀尔文社团主义里,诚如后文引用的温斯罗普布道「基督徒慈善的典范」。但天主教社会教育的现代传统已经相当有活力地肯定这点。
40J. David Greenstone, The Lincoln Persuasion: Remaking American Liber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我们应该指出格林史东自己的术语有些不同。他相对于改革自由主义的反面术语是人文自由主义(humanist liberalism),称为人文主义是因为它没有超验的指涉(transcendent reference)。编辑使用格林史东自己的话来定义人文自由主义如下:「人文自由主义指的是一整套看法,主要强调『公正地满足个人的欲望和偏好』,以及实现『每个人所定义的福祉』」。我们认为这是对功利自由主义的准确描述。考虑到格林史东将改革自由主义描述为「人道主义的」(humanitarian),人文主义似乎是对这个立场一种非常不适当的描述。
41「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Mark 3:25, King James Version.
42Abraham Lincoln, Speeches and Writings, 1832-1858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89), p. 426.
43「我所说的巴西化不是指按种族的文化划分,而是按阶级划分种族。就像在巴西,一个共同的美国文化可以无限期地与一个模糊的、非正式的种姓制度兼容,在这个制度中,社会等级最顶端的多数人是白人,而多数棕色和黑人美国人则永远处于最底层。」Lind, The Next American Nation, p. 216.
44Jennifer L. Hochschild, Facing Up to the American Dream: Race, Class, and the Soul of the N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45John Winthrop, “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in Conrad Cherry, ed., God’s New Israel: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s of American Destiny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71), p. 42. Spelling has been moderniz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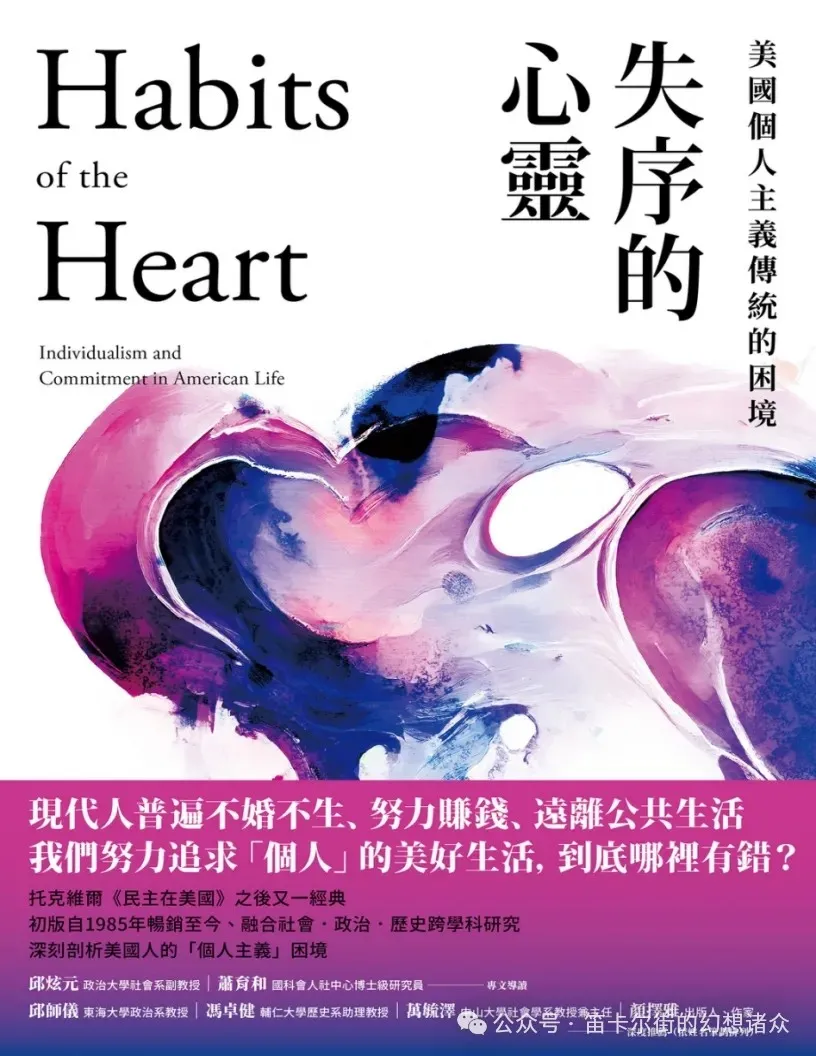

 188金宝搏体育官网 SZHGH.COM
188金宝搏体育官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