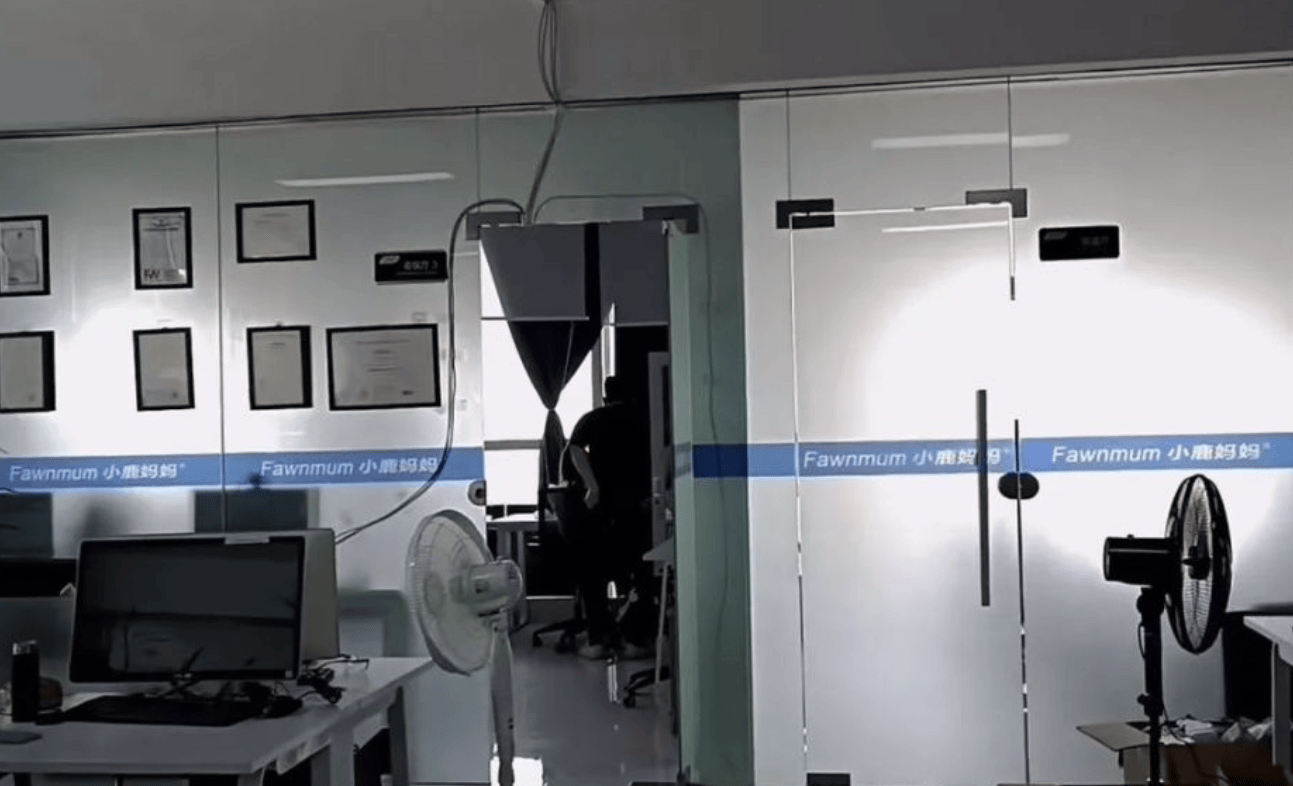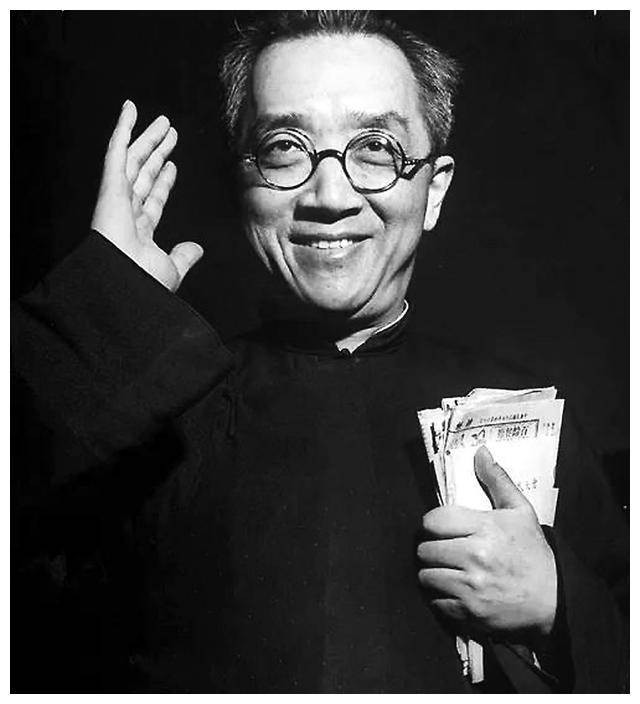作为时代象征的“孩子剧团” ——硝烟中的文艺轻骑队及其“小先生”

陈志昂同志最近修改完成了一部五幕歌舞剧《红色孩子剧团》。该剧以胶东孩子剧团的历史人物为原型,通过戏中戏的形式,塑造了一批在暴风雨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少年儿童群像。
从内容看,《红色孩子剧团》是一出以历史真实人物的对话、行动和作者的亲身经历编创而成的“文献剧”。剧作依托了抗战时期胶东文化组织的史料文献,透过孩子剧团这“一滴水”,带我们回望胶东解放区文艺那片被遗忘的海域并展现了敌后抗战的“黎明风景”。
在五四运动的“新青年”们的影响下,革命文艺的思潮在胶东大地萌发。王统照报告“山雨”欲来,臧克家呼吁奴隶们举起“黑手”。胶东的党组织自发动游击队时期开始,便十分重视“精神”的“武装”。所谓的“精神武装”的过程,就是“文化革命”的实践。早在1937年,在“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的旗帜下,革命的巨浪迅速席卷齐鲁大地。1938年秋天,胶东半岛的第一个综合性文艺杂志《海涛》在掖县创刊。这个同人刊物发表有时论、诗歌、报告文学等等。期刊的封面,画面的下部是汹涌澎湃的蓝色大海,象征着渤海的风浪;上部是几只白色的海燕,呼唤着暴风雨的来临。该刊的发刊词这样写道:
在这伟大的浪潮里,不是前进的,就要后退,我们的力量虽然薄弱,但也要在“海涛”里吐一个泡沫。鲁迅先生说过:“世上本来没有路,人走得多了,就成了一条路”。在胶东,我们希望能展开猛烈的思想斗争,建立新的基础,荡尽了旧的渣滓,向着正确的大路迈进。
《海涛》的创办者之一罗竹风回忆抗战时期胶东的文化工作时曾说:
古今中外,恐怕没有一个军队像八路军、新四军这样重视文化工作的……要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需要不断提高部队和群众的文化水平,使他们开扩眼界,懂得抗战和革命的道理,了解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加强民族意识和阶级观念,因此除武装斗争之外,还必须从精神上把农民和广大劳动人民武装起来。
正是在这“海涛”中,以硝烟为背景的胶东大地上,妇女儿童不甘落后、争先登场。
假设“少年中国”的“革命儿童”是古老的中华民族蜕变为“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国家”的象征形式,那么“孩子剧团”就是一支以声诗革命为“装备”的“轻骑队”。“孩子剧团”的前身,是1938年中共胶东特委(后为区党委)青年部组建的少先队,队员大多数为十多岁的青少年,他们之中,有的是追随父兄,脱离小家庭,背井离乡,加入革命队伍;有的是部队在行军过程中沿途收纳的孤儿。从开始的二三十人形成了一支一百多人的少年队伍,跟随部队西进,活跃在黄、掖两县一带。1940年,《大众日报》曾刊载过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鲁迅宣传大队的戏剧教员贾霁创作的长诗《儿童们》,为硝烟中成长的儿童画了素描:
当我过他们的战场时,他们喊,“欢迎前线打鬼子!”这应谱成庄严而喜悦的歌曲——这些孩子们的认真的跳跃,将把这古城,带到光明的国土去!”
这一支由少先队员组成的文艺“轻骑队”,不似《海涛》封面上部的白色海燕,更像是封面下部蓝色渤海中的朵朵浪花。在革命的海洋中,“浪花”们冲破了战争的阴霾,在朝阳下,他们跳跃着,“轻匀的步法,活泼的身姿,木刀当做马,驰骋在寂静的山埠。”那是些因为战争而抛家别舍或无家可归的孩子,在国破家亡的危机中向往光明,在血雨腥风中接过革命的火炬,成为少先队员和革命儿童。在共产党这位“保姆”的养育下,在革命大家庭中,这些各自母亲的“孩子”成长为祖国大家庭的“小先生”。据陈志昂回忆,这些在抗日战争和群众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小先生”脸上总是洋溢着革命的朝气和力量,他们顶着夏天的烈日酷暑,冒着冬天的寒风飞雪,一行三四个孩子,翻山涉水,跑五六里,甚至十几里的山路,到附近的村庄,给当地的小学生讲着他们在报纸上以及队长和指导员口中了解到的抗战救国的道理,教他们唱抗战歌曲,帮他们建立儿童团组织,布置儿童团的任务:站岗、放哨、拥军优属等等,完成这一切后,他们才会返回驻地。尽管他们偶尔也会因为顽皮捣蛋而被罚多站一班岗,以及在生活检讨会上做自我批评,可天真、稚嫩的孩子身上却总是能够迸发出一种难得的革命浪漫主义热情,并用歌声传递给身边的革命战友。在“声诗革命”的初期,孩子们大唱抗战歌曲,其中有《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十杯茶》;还有一些外国革命歌曲,如《国际歌》,苏联的《工人歌》、《光明赞》以及《我们勇敢地走向战斗》;还曾将吕骥的《武装保卫山西》改成了《武装保卫山东》。孩子们最爱唱的还是苏联诗人倍泽敏斯基根据由德国青年带到苏联的《德国工人之歌》的旋律(原曲为奥地利民歌),重新填词,由李求实翻译的《少年先锋队歌》,每当开会集合或者行军的路上,孩子们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声唱着:
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勇敢向前,稳着脚步,要高举我们的旗帜!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在那个到处都是抗日歌声,遍地都是救亡战歌的时代,这些孩童从“野孩子”“放牛娃”成为舞台上的主人翁。1939年的夏秋之交,胶东青联开始筹备孩子剧团的组建工作,几个月后,孩子剧团以原来少先队为基础,吸收了文登抗战话剧社和牟平青年话剧团的部分成员,在掖县山村夫子石正式宣告成立。女孩子们亲手为剧团做了一面红色的团旗,上面写着“胶东青年抗日救国会孩子剧团”。同年12月8日,他们在夫子石迎来建团的首演,由包干夫创作的独幕话剧《夜里》,在那个只能用几张灰军毯做幕布,用棉花卷成的粗芯,放在花生油里燃烧的自制灯具的舞台上,革命新人完成了“亮相”。随后,他们遭遇了日寇对胶东抗日根据地的第一次“扫荡”。他们一边随部队转移,一边演出宣传。除此之外,他们还被组织送去胶东鲁艺和抗大胶东分校进修学习,一天天不断成长。1942年1月,胶东区党委决定将孩子剧团改为大众剧团,尽管这一年,日寇对根据地进行了更频繁更残酷的“扫荡”,可剧团的孩子们仍组织起了反响强烈的演出。时年15岁的陈志昂指挥剧团演出了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那时没有大幅的画布,负责舞美的王广汉就将波涛汹涌、气势磅礴的黄河万里图绘制在一张一张的报纸上,然后再拼贴在天幕上。陈志昂、王广汉都只有十五六岁,通过勤学苦练和观演实践自学成才。他们虽未受过正统学院式艺术训练,却成为革命文艺的“小先生”。1942年,根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组织之间关系的决定》精神指示,这些孩子所在的大众剧团解散,一部分干部回胶东青联做青年和儿童工作,少数艺术骨干调往文协工作团,一些年纪小的孩子送去公立学校或回家继续求学。此后,他们在广阔的革命天地中“经风雨、见世面”,继续将革命火种播撒在新中国的四面八方。实际上,在全国各地,各种称谓的“孩子剧团”为数不少,这些团体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文化革命的骨干力量。胶东的孩子剧团是其中的一个典型。遗憾的是,在山东地区,这些文化活动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图片资料,只有零散的口述、剧本、歌谱存世。“孩子剧团”的革命形象、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也在“去政治化”的历史解构中逐渐褪色……
所幸的是,这部歌舞剧和相关史料弥补了这个遗憾,抢救了那段历史。《红色孩子剧团》这出戏,一方面,展开了尘封已久的、三四十年代的抗战画卷;通过歌舞剧的写作和口述史料的整理,为地方革命文化研究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由陈志昂在剧中连缀起来的、胶东孩子剧团的观演现场,也向今天的历史研究者揭示了解放区的战地“轻骑队”们如何自觉地利用民族形式和各种民间形式。
从形式看,《红色孩子剧团》称得上是一部新的、以儿童为主角的“音乐舞蹈史诗”。同上世纪六十年代诞生的《东方红》一样,这部载歌载舞的舞台作品充分利用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中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革命小戏、革命歌曲,超越了传统西式舞台上的再现体系,将胶东革命的“史诗性”“地方性”建立于该地区文化宣传中广为流传的短小“声诗”“杂剧”之上。
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经由中共海上交通线运来的专业书籍,如饥似渴地吸收各种门类艺术的专门技艺,并在蓬勃发展的群众运动中完成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可以说,他们是切实贯彻了毛泽东在延安倡导的“普及和提高”的辩证法;也可以说,在这一支支“轻骑队”的身上,文化革命的自觉自下而上,早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开端和民族形式的正式提出之前,声诗革命、旧剧革命的“轻骑队”就以胶东大地和全中国为其广阔远景,将原有的民间形式(民歌、劳动号子、秧歌、快板、对口等等)、民族形式(京剧)和西洋形式(交响、合唱、小说、新诗)融为一体并搬上舞台。
据罗竹风回忆,胶东话剧演出的流变,是从移植外来作品到自编自演歌颂军民鱼水情的独幕剧,继而广受群众欢迎。同时,由于话剧不适于露天演出,一种有音乐伴奏,以唱为主,又间道白的“小调剧”诞生了。“小调剧”主题鲜明,音乐生动,也很受群众欢迎。与此同时,同延安一样,胶东半岛也进行着一场旧剧革命。1939年,原龙口天宫戏院的演员朱瑞祥、李云、鲁诰(鲁继诰)、鲁继训(铁军)、张青、李云、徐永凯、刘春,在日军入侵前夕焚毁了演旧戏的天宫舞台,加入抗战剧团,演出京剧现代戏《唐宫屯》、《张家店》等,而后成为了胶东地区旧剧革命的主力,在解放后他们并入了山东京剧团,即后来编创《奇袭白虎团》的样板团。“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提出之后,胶东的演剧活动更为自觉地发展民族形式,在生产劳动中吸取更多民间形式的要素。例如,由马少波创作的新编历史剧《闯王进京》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中的政论为主题,全剧长达四个小时,也收到很好的效果。同时,农村群众文艺活动蓬勃展开,到1945年6月,胶东解放区共有一万两千五百多个农村俱乐部,文协会员两万三千多人,教师抗日救国会会员两万六千多人,民间艺人(盲人)抗日救国会会员三千七百多人,医生抗日救国会会员两千四百多人。1946年,胶东文协全体深入农村,一边演出,一边发动群众,有五千以上的农村剧团演出过《白毛女》。属于部队系统的国防剧社这支文艺“轻骑队”为迎接春季大生产运动,采用了胶东秧歌、小调,创作了以改造二流子为内容的五场秧歌剧《改邪归正》,并于三八节在莱阳城首演。此外,在《白毛女》《兄妹开荒》影响下,国防剧团还组织了大型秧歌队,包括打花棍、头子戏、打花鼓、跑旱船、跑驴等民间歌舞形式,还有时事活报、滑稽演说、双簧、快板等。秧歌队演出作品大多是部队练兵和农村生产劳动,广受欢迎。解放战争中,配合部队的阶级教育,《瞎老妈》《三世仇》《解放》等歌剧发挥了巨大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依据马少波小说改编、由张波执笔、陈志昂作曲的新歌剧《农公泊》中,为表达女主人公的悲剧情感,陈志昂将梅兰芳、姜妙香合作的《贩马记》中的哭腔与胶东妇女哭丧的调门结合起来,并吸收各种民间音乐素材,采取非传统的和声手法,将剧情推向高潮,其演出产生了轰动。当时,于会泳是陈志昂领导的胶东文协文工团音乐组的骨干之一。陈志昂在歌剧《农公泊》中采取的、令当地群众印象深刻的创腔手法,在六十年代中期由于会泳主导的京剧现代戏创腔中发扬光大。
历史地看,革命文化于胶东半岛掀起的“海涛”中,作为“海燕”的罗竹风、陈迈千、马少波、虞棘等人,对作为“后浪”的陈志昂、于会泳等人的文艺活动产生过重要影响。胶东解放区文艺曾开创的声诗革命和旧剧革命直接或间接地通向了六七十年代新中国创作革命礼乐的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集体创作而成的样板戏,正是这一枝文艺奇葩上结成的硕果。
孩子剧团在四十年代初期曾由王文俗编导演出过一部“影剧”《铁流两万五千里》,采用投影的方式,配以画外音,表现“红军不怕远征”的伟大精神。原剧早已失传。《红色孩子剧团》最后一幕《雪山之梦》是陈志昂在70年代初期的创意,如今最后成型。这场戏之所以放在全剧的末尾,因其内涵超越了抗日战争的民族话题,抒发了革命战士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红色初心,并且其象征形式超越了前面几个场次的轻骑队文艺,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双重升华。在这场戏中,陈志昂,这位少年时就参军入党的革命者、大海潮起时的“浪花”和革命退潮时的“海燕”,塑造了一位在长征途中因为受了毛委员的启迪,而在片刻假寐中梦见了胜利、看到了未来的红军小战士。《雪山之梦》不仅仅是一场戏,而且是在冰天雪地中凌寒绽放的革命理想主义的璀璨花朵,也可以说是活着的革命者用歌舞形式做出的祭祀,用以缅怀千千万万个像王广汉那样过早牺牲在革命道路上、没有机会目睹新中国的“小先生”。他们生前怀揣的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在舞台上化作了用胜利腰鼓作伴奏音型、以《国际歌》旋律为母题发展而成的壮丽交响。这场革命礼乐的诞生、成型和出版,印证了作者近一个世纪来“地坼天崩不变心”的思想立场。
雪山的这场“梦醒之梦”从未有过公演。希望《红色孩子剧团》的出版能够让读者尽快在剧场中看到这场戏。诞生于20世纪的“孩子剧团”又被时代的洪流冲上21世纪的海岸。这个剧本仿佛一支沉甸甸的海螺,令观者听见半个世纪前革命的回音。在“海涛”的冲刷下,台上和台下、历史与现实之间不再有明确的界限。在革命礼乐的天幕上,一个伟大、坚强的祖国再次成为“海燕”“浪花”们登台亮相的舞台布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