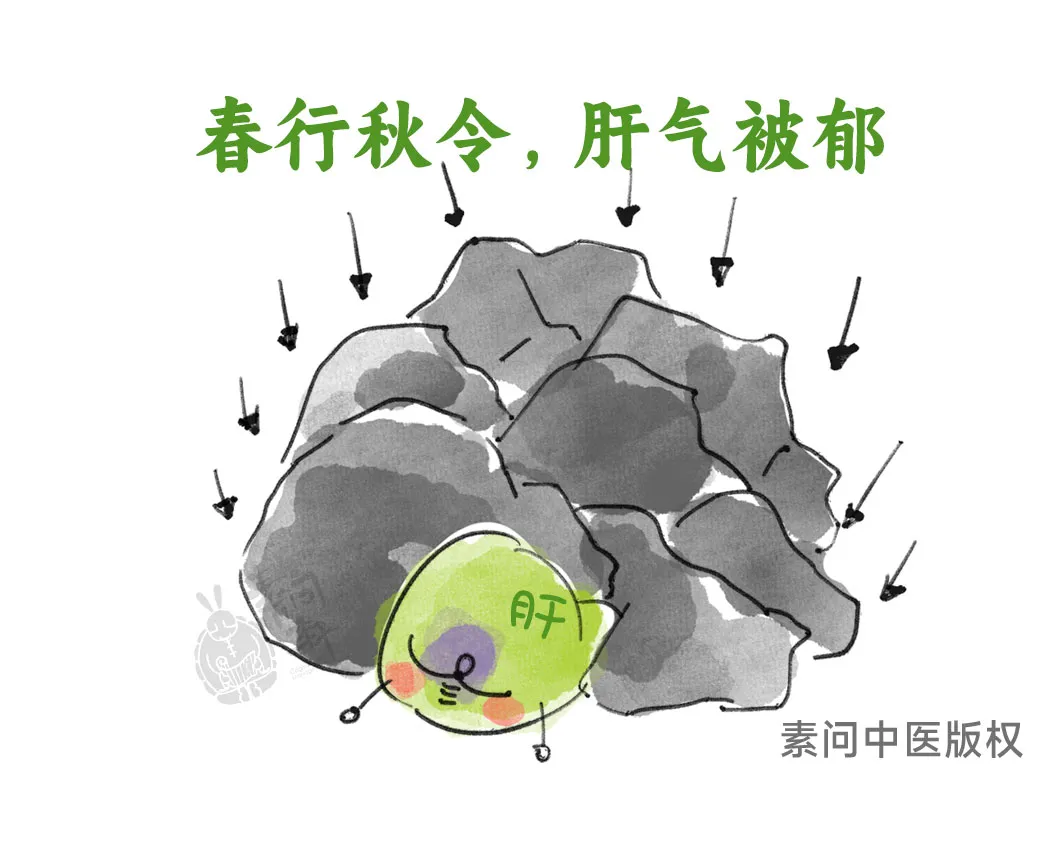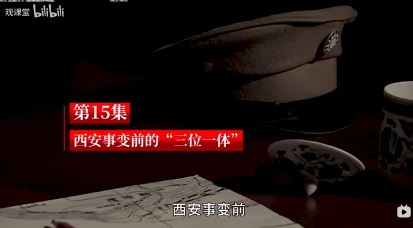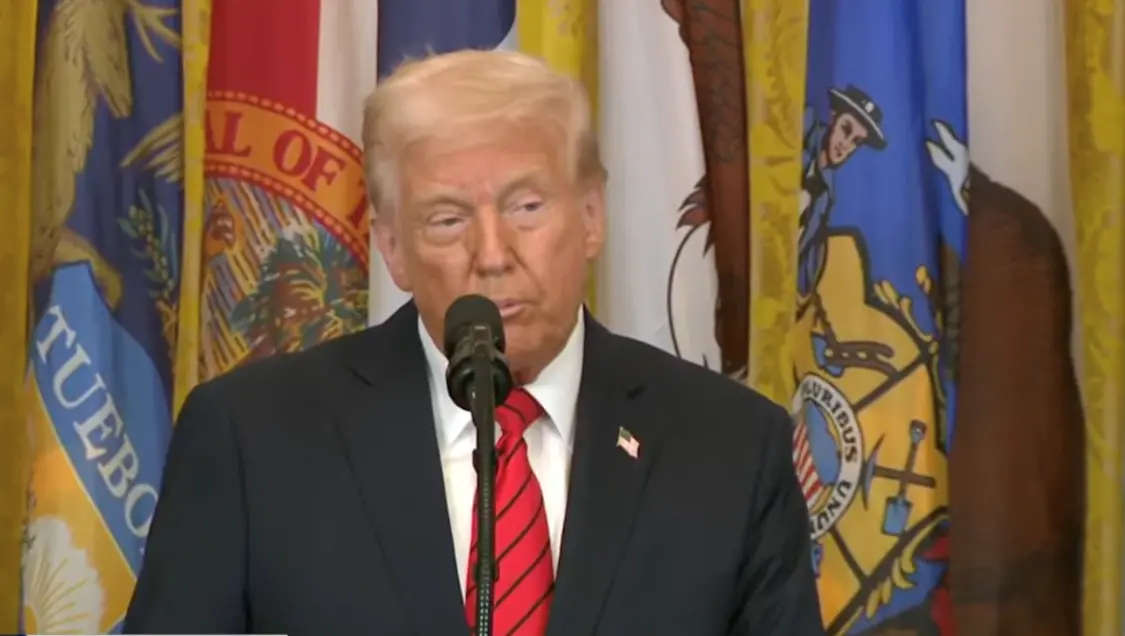中情局也读法国理论:冷战时期CIA瓦解文化左翼的知识劳动
人们通常会认为知识分子仅仅能够掌握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政治权力。栖身于养尊处优的象牙塔内、为了细枝末节的专业问题而卷入毫无意义的学术争论当中、或是徜徉在高玄的理论的云端……知识分子常被刻画成既和现实政治毫无瓜葛,同时又无力对现实施加影响的形象,但美国中央情报局可不这么认为。
事实上,策划过政变、暗杀以及秘密操纵外国政权的中情局不仅相信学术理论的力量,他们还组织了专门的特工小组钻研这些被认为是最为深奥复杂的学说。根据《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公布的资料,一份写于1985年的报告表明,中情局一直派人学习复杂而又引领风潮的法国理论,包括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等人的著作。
美国特工们聚集在巴黎大大小小的咖啡馆里头,埋头苦读法国理论和意见领袖们的著作,并认真做着笔记,这样的画面大概会震惊不少人,比如把知识分子奉为伟人、并认为他们的“空想”可使其免遭世俗叨扰的人们;而把知识分子看做卖弄修辞话术、且无力影响现实的江湖骗子的人们,同样也会对此感到惊讶。然而,一些人对此则丝毫不觉得意外,他们熟知中情局对文化战争持之以恒的投入,包括对先锋艺术的支持等,这些都被弗兰西斯·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吉尔·斯科特-史密斯(Giles Scott-Smith)和休·威尔福德(Hugh Wilford)等研究者很好地整理并记录了下来。
托马斯·W·布雷登(Thomas W. Braden),前中情局文化事务主管,在一份刊载于1967年的坦诚的内部人员陈述中说明了中情局的“文化攻击”所具有的威力:“在欧洲,当(中情局支持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比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的演讲赢得更多的欢呼时,我感到莫大的喜悦。”这绝不是什么小范围的行动。事实上,威尔福德就曾指出,总部位于巴黎、后被发现是中情局在文化冷战期间掩护机构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堪称历史上最重要的赞助人,这一机构支持了范围惊人的艺术和知识活动。该机构在35个国家设有办公室、出版了大量极具声望的杂志、渗透进图书行业之中、组织过引人注目的国际会议和艺术展、安排演出和音乐会,还为各种文化奖项、奖学金和法弗德基金会在内的掩护机构提供了充裕的资金。

巴黎的“地下组织”:中情局特工及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主席迈克尔·乔塞尔森(Michael Josselson)(中)同约翰·克林顿·亨特(John Clinton Hunt)和梅尔文·拉斯基(Melvin Lasky)(右)共进午餐。
中情局文化斗士的“双向运动”:
引导知识分子从批判美国转向批判苏联
中情局相信,在他们为保障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所部署的武器库中,文化和学术理论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一份写于1985年、题为《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倒戈》(France: Defection of the Leftist Intellectuals)的研究报告最近被公布出来,该报告考察了——无疑也是为了把持操纵——法国知识界及其在塑造足以影响政策制定的知识潮流时所发挥的基础作用。虽说在法国历史上,左翼和右翼在知识界相对而言保持着意识形态上的平衡,但该报告强调,由于共产党人在对抗法西斯及二战的胜利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因而在战后左翼很快就赢得了垄断地位,而如我们所知,这正是为中情局所深恶痛绝的。尽管右翼由于直接参与了纳粹集中营的暴行、全面的排外主张、反平等主义以及(按中情局所描述的)法西斯式的行为动机,从而在声誉上遭到沉痛损失,但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右翼重新抬头,对此,也不难察觉出秘密特工们在起草研究大纲时的喜悦。
更具体地说,这些暗中工作着的文化斗士们为他们眼中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欢呼呐喊,因为这一双向运动使得知识分子们的批判矛头从美国转向了苏联。就左翼而言,他们对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渐生不满,激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远离了公共讨论,而在理论上他们也开始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分道扬镳。至于右翼,随着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机会主义者在媒体上高调地发起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造谣诽谤运动,他们也荣获“新哲学家”和“新右翼”知识分子的称号。
当世界各地的特工组织开始把魔掌伸向推翻民选领导人、为法西斯独裁者提供情报和资助以及支持右翼敢死队等活动时,巴黎知识界的特工分队则收集起了资料,以了解理论界的“右转”将如何使美国的外交政策直接受益。战后,左倾知识分子公开谴责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作为一位直言不讳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他作为《解放报》(Libération)的创办者而地位显赫,在媒体上也拥有极大的影响力。萨特揭露了当时中情局安排在巴黎的办公人员及大量秘密行动,这一切都被中情局密切监视着,并被视为眼中钉。
与之相对,日渐崛起的新自由主义时代所营造出的反苏、反马克思主义氛围,转移了对中情局发动的这场肮脏战争的公共监管,并为其提供了绝佳的掩护,包括使得“知识精英们难以动员起来,以表达对美国在中美洲所施行政策的强而有力的反对,”格雷格·加尔丁(Greg Grandin),这位拉丁美洲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在其著作《最后的殖民地大屠杀》(The Last Colonial Massacre)中将这一情形完美地概括了出来,“除了由于插手1954年的危地马拉、1965年的多米尼加共和国、1973年的智利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萨尔瓦多与尼加拉瓜等国的事务,从而招致灾难性且致命的损失外,美国暗中为这些恐怖国家残忍的平叛行动提供了稳定的经济、物质及精神支持。但斯大林犯下的罪行却又保证了,无论上述这段卑劣的历史有多么明显、彻底且罪孽深重,都无法动摇世人观念的根基,即认为美国在保卫所谓民主方面具备典范作用。”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潜伏着的情报官僚们对新一代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如伯纳德-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evy)、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和让-弗朗索瓦·勒维尔(Jean-François Revel)等人对“最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圈”[”the last clique of Communist savants”,按匿名特工所说,由萨特、巴特、拉康和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等组成]不间断的攻讦,表露出极大的赞许和支持。考虑到这些反马克思主义者在年轻时的左倾思想,他们给出了一套完美的话语模式,为的是建构一种把个人政治抱负同时代潮流结合起来的虚伪说辞,仿佛个人生活和历史都不过是“成长过程”的简单组成,同时他们还认为平等社会的深刻转型从个人层面和历史层面上讲,都已是属于过去的事物。这一自诩全知全能的失败主义不仅致力于诋毁新兴的,尤其是青年人发动的社会运动,而且也错把反革命镇压的部分成果当作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

反马克思主义的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左一)同妻子苏珊在度假中,左三为中情局卧底人员迈克尔·乔塞尔森,右一为哲学家丹尼斯·德·鲁日蒙(Denis de Rougemont)
诱导左翼理论右转:
“后马克思主义”如何清扫左翼的影响力
就算没有这批反动知识分子那么反对马克思主义,一些理论家们也参与造就了这样的社会环境:平等主义变革幻灭,脱离社会动员以及缺乏激进政治的“批判探索”。这对理解中情局的总体策略,及其如何通过其广泛且影响深远的举措瓦解欧洲及各地的文化左翼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意识到不可能完全摧毁文化左翼之后,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特工组织开始谋求把坚定地反资本主义并提倡政治变革的激进左翼,与较少公开批评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中间偏左群体分离开来。实际上,如桑德斯所详细论证的,中情局战后一直紧随麦卡锡所把持的国会,为的是能直接一直支持并促进某些“左翼计划”,以驱使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远离坚定的平等主义左翼份子。在分裂及诋毁后者时,中情局还致力于粉碎普遍意义上的一切左翼,只留下中间偏左的保守群体,赋予其最低限度的权力及公共支持(中左势力仍可能遭到抹黑,这是由于中情局与右翼政治势力相互勾结所造成的:他们将继续折磨当今早已体制化了的左翼政党)。
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需要明白中情局所热衷的偷梁换柱式叙事,以及他们对“改良马克思主义者”的赏识,这是贯穿在这份关于法国理论的中情局报告始终的主题。“在摧毁马克思主义方面更具影响力的,”匿名特工们写道,“是那些起初深信马克思主义可以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但最终却对这一理论传统加以反思批判甚至拒斥的知识分子们。”他们着重提到了年鉴史学和结构主义学派,尤其是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和福柯对“扫除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力”所发挥的影响。被称为“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的福柯提醒哲学家们,所谓“血的教训”正是“源自18世纪启蒙运动和革命年代理性主义者们所主张的社会理论”,这被认为是对新右翼知识分子的褒扬而为福柯本人赢得喝彩。或许,把一个人的政治主张和影响概括成单一的立场主张会有失偏颇,但福柯反对革命的左翼主张,以及他认为古拉格式劳改营将一直存续(即声称,旨在推进更深层次社会文化变革的过度激进运动,将只能使得最危险的传统复苏)的观点,恰好完美契合了中情局在哲学战线上的总体策略。
中情局对法国理论的学习可以让我们停下来重新看待法国理论在英语学界传播时所披着的激进且华丽的外衣。根据阶级主义者所持的进步史观(通常会对自身绝对且固执的目的论熟视无睹),福柯、德里达和其他法国前沿理论家的著作,通常天生就呈现为意味深长且复杂的批评形式,而这也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或是无政府主义传统中的任何主张都望尘莫及的。而正如约翰·麦坎伯(John McCumber)所准确指出的,英语学界接受法国理论,并将用于抵抗错误的政治中立、保险的逻辑和语言术语,以及麦卡锡主义和英美哲学传统影响下因循守旧的意识形态主张,这一点是值得强调和肯定的。然而,一些理论家拒斥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所说的激进批判传统(即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他们的理论实践无疑推动了远离政治变革的意识形态转向。按照中情局的说法,后马克思主义的法国理论直接参与到了中情局诱导左翼向右转的企划当中,中情局一边诋毁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理论,并打造了这样一个舆论环境:在那里,他们的帝国主义图谋可以免遭来自知识界严厉的批评监管,从而为所欲为。
大学、出版社和媒体:
中情局如何改造文化生产、分配的组织机构
从关于中情局心理战计划的研究中可以得知,这个情报机构不仅追踪并胁迫个人,还一直热衷于了解并改造负责文化生产、分配的组织机构。实际上,中情局对法国理论的研究,表明了大学、出版社和媒体在构建及巩固社会总体的政治氛围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说到这一点,就像这份报告其他章节所描述的,我们都应该更好地批判思考英语世界里的学术现状。除此之外,报告的作者强调了学术工作这个铁饭碗如何在激进左翼的垮台中发挥作用。如果强烈的左倾思想无法给予我们足够的物质保障,无法让我们继续工作下去,又或者我们多少在不知不觉中为了工作、发表著作和赢得观众而妥协,那么原本坚固的左翼共同体根基就已经开始动摇了。高等教育的职业化趋势是用以瓦解左翼的又一工具,这一举措的目的是把人们变成资本主义生产机器中的一环,而不是能够参与社会批判的独立自主的公民。正因如此,中情局的理论官僚们十分欣赏法国政府“把学生送到商科和技术课程去”的政策。他们也指出了像格拉塞这样的大出版社,大型媒体机构及美国流行文化在推动其后社会主义、反平等主义平台发展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针对当前的政治环境,以及情报机构持之以恒的对批判型知识分子的叨扰,我们应该从这份报告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首先,它给我们提了一个醒:要是还有人以为知识分子是没有力量的,又或者以为我们的政治立场是无足轻重的,那么中情局,这个当今世界政治舞台上最强有力的权力掮客肯定第一个摇头。中央情报局,就像这个讽刺的名头一样,深信情报和理论的力量,这也是我们需要警惕的。错误地以为知识分子和他们的著作对“现实世界”几无影响,不仅使得我们误解了理论工作者的努力,同时也让我们承担着风险,即对政治阴谋视而不见的同时,在不知不觉中为阴谋家们所操纵,成为他们的“文化”代言人。虽说法国政府和文化部门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比世界其他地方远为广阔的平台,但中情局抢占先机,并图谋瓦解海外理论与文化成果的事实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其次,现在这些作为权力掮客的情报部门,为了既定利益而培养着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热情和笔锋或已被消磨侵蚀,或不见踪影,因为有关部门正着力扶植以商科和理工科为主的教育机构,把左翼政治跟反科学划上等号,把科学和玄之又玄但明显是错误的政治中立联系起来,支持发展听话的媒体,把有影响力的左翼分子排挤出主要的高校或降低其曝光率,以及抹黑任何对激进平等主义和环保运动的呼吁。按照设想,他们所要培养的是这样一种(左翼)知识分子文化:中立、固化、死气沉沉并且满足于失败主义,又或是不痛不痒地批判激进左翼。反对激进左翼这一政治立场,作为当前的美国学术界的主流,之所以被我们认为是危险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岂不是正好迎合了中情局在全世界范围内所展开帝国主义阴谋?
再者,反对情报机构对左翼分子的干预与攻击,必然也要反对教育界存在着的一劳永逸与职业化倾向。为真诚的社会批判创造公共空间,并为那些相信另一种世界图景并非可能、而且也是必须的人们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对我们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我们还需要团结起来,支持发展独立媒体、不同的教育模式、反体制的激进政治共同体。
【文章原载于小镇读书会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