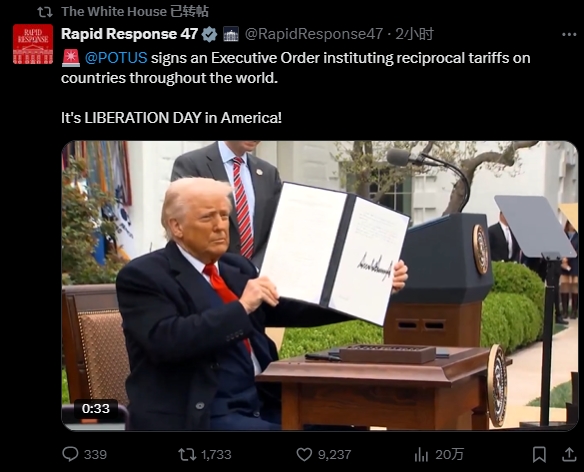林之辛:与外国元首的交往中彰显伟人的品格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与许多外国政要会谈过,都给他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在与这些外国政要的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待人接物的风格是反映他为人和品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已经从大量的文献看到毛泽东如何对待那些大国、强国的元首,特别是当年的两个超级大国。他一贯的态度是:不卑不亢,既不屈从强势,也不唯我独尊。若是能平等待我,毛泽东也乐意平等交往;如果以强国自居,以势压人,毛泽东就会坚决地顶回去。苏联的赫鲁晓夫在他所写的《最后的遗言》中记下了当年苏方向中方提出要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管的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潜艇舰队时毛泽东拍案而起的怒斥:“你们怎么敢提出这样的建议!这种建议是对我们民族尊严和主权的侮辱!”事隔十几年,赫鲁晓夫还清楚地记得,毛泽东说:“我们正在建设自己的潜艇舰队。如果苏联潜艇可以进出我国港口,那不成了侵犯我国主权了吗?” 当赫鲁晓夫提出中国可以在苏联的北冰洋沿岸建立潜水艇基地作为苏联有权使用我国的太平洋港口的交换条件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行,也不能同意。每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只应驻扎在自己本国领土,而不能驻扎到任何别的国家中去。”赫鲁晓夫没有料到,一贯待人彬彬有礼的毛泽东在涉及国家主权问题时如此警觉和强硬,会毫不留情地当面发火以致于使他尴尬得下不来台。美国的头目历来敌视中共,在朝鲜战争时曾经用甩原子弹来威胁恫吓中国。可这一套对毛泽东根本不管用,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而当美国面临苏联的威胁,愿意放下架子,与中国平等对话时,毛泽东也就相应地调整了政策和态度。即便如此,在台湾问题这样关系国家主权的事情上,毛泽东一点也不让步,在《中美联合公报》即将发表之际,美方有些人叽叽咕咕,节外生枝,毛泽东立即给予严厉警告:“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毛泽东的这种态度无疑给美国总统尼克松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以致几十年后,尼克松在他所写的《领袖们》一书中仍然不无敬佩地评论说:“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尽管他承认与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有着“共同信念和原则”,“与北京之间的和解对我个人说来是个很痛苦的过程”,但他在比较蒋介石与毛泽东时,还是不得不承认:“蒋介石的智慧乃是小智,是一种为个人生存意志而忙的不自由的智慧,而毛泽东的智慧则是大智,是一种超然于个人生存意志之外的自由的智慧。”
如果说如何对待比自己强势的对手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意志和品格,那么如何对待比自己弱小的伙伴同样反映一个人的为人。在某种意义上说,由于在与比自己弱小的伙伴相处时,没有外在的压力,往往更自然地流露出内心的情感,更容易显现出真实的人品。
西哈努克曾经是中国人相当熟悉的一个名字。他是一个小国 — 柬埔寨王国的首脑,又是一个与毛泽东交往最多的外国政要。(柬埔寨的面积只相当于中国一个广东省的大小,长期处于不发达状态,直到2016年才被世界银行宣布脱离最不发达国家之列。) 由西哈努克口述、美国记者伯纳德·克里歇尔执笔写的一篇题为《西哈努克眼中的毛泽东》的文章,发表在《海内与海外》(中国侨联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1997年第8期,为我们提供了从一个从小国元首的视角观察毛泽东的窗口。
西哈努克在文中这样描述了他与毛泽东第一次会面的情况:“195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与来自中国的周恩来首次见面。第二年我到了北京,在周恩来的陪同下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当我的汽车驶入毛主席寓所院子的时候,毛已经站到门口等候我了。见我的车驶近,毛亲自走上前来迎住了我。这对我是个很大的意外,也是种殊荣。在我们结束长时间热烈的讨论之后,毛又亲自送我上了车。直驶到出了他的视线,他才折回到他那幢传统中国样式的简朴房中。”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礼节啊!不仅是平等相待,而且是对待一个尊贵的客人所持的高度尊重的态度。这对西哈努克来说“是个很大的意外”,他没有想到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泱泱大国的领袖会如此礼待他这样一个来自小国的客人。事实上,相当多的发达国家的领导人看不起第三世界国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上不稳定,经济上贫穷落后,把“贫穷落后”看成是“第三世界”的代名词。1960年,一向被称为最讲礼仪的英国邀请西哈努克访问,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口称女王陛下“将会很高兴地接见你”,可是第二天,西哈努克收到的书面邀请上却注明是“非正式”的,这使他非常气愤:我不是来旅游的,怎么能把我们国家的时间和金钱浪费在皇家花园的宴会上。一气之下,他取消了那次访问计划。1965年应邀出访莫斯科也使他感到羞辱。当西哈努克按照原先排定的连续几个国家的出访计划,访问了中国、朝鲜,准备前往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时,苏联突然通知他“推迟”出访苏联的时间,理由只是苏联领导人“很忙”,这使得西哈努克进退不得,颇为难堪。感受屈辱的西哈努克取消了其余的访问,直接飞回金边。西哈努克每提起这些事,把这些大国领导人对他的轻视态度同毛泽东的态度稍加对比就来气。这种对比使他更加觉得毛泽东对他的平等和尊重的态度无比真诚与可贵。
其实,毛泽东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要都是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相待,从来不以大国自居。毛泽东很带感情地说:“我们见到三个地方的朋友最亲,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同你们见面,我们就感到平等。”正因为这样,广大亚非拉国家对毛泽东和中国怀有特殊的感情,他们把中国视为同呼吸、共命运的患难之交和可以信赖的朋友,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关键问题上以及重大国际事务上与中国站在一起,不仅使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票数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且多次挫败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出的反华提案以及台独势力的外交阴谋。
西哈努克与毛泽东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之所以享有这种“殊荣”,与他一生都致力于维护柬埔寨的独立与主权相关。柬埔寨原是法国的殖民地,但西哈努克不甘心当法国的“儿皇帝”,经过长期的斗争,他于1952年6月发布了《告柬埔寨人民书》,誓言在两年内实现完全独立。柬埔寨民众在西哈努克的感召下,争取国家独立的情绪空前高涨,迫使法国人不得不作出退让。1953年11月9日,法国和柬埔寨签署新的《法柬条约》,柬埔寨获得了完全独立。此时,西哈努克年仅31岁,却已成为柬埔寨万民景仰的“独立之父”。为了确保中立,他在1955年出席万隆会议,并在1956年和铁托、纳赛尔、尼赫鲁等共同发起了不结盟运动。1956年,西哈努克首次访华,毛泽东非常亲切地接见他,在短短九天里,同他进行了三次长时间的单独谈话。交谈中毛泽东说,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真正拥有独立,不受别的国家摆布。国家不论大小,都应该是平等互利的。柬埔寨是小国,而中国是大国,但没有理由不在平等的基础上成为朋友,也没有理由不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国家关系。毛泽东还表明,柬埔寨坚守中立政策很好,中国将永远支持这个政策。正是对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执着追求奠定了两人友谊的基础。西哈努克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的第一印象是,我正面对人群中的一位巨人。”“我在见面之后马上就喜欢毛主席,那是互相的。随着时间的发展,我觉得他对我也有一种感情,正如我对他的感情一样。”
两个政治制度及信仰完全不同、幅员和人口差距极大的国家,却能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这是毛泽东平等待人而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的结果。西哈努克亲王在他的回忆录中十分感慨地写道:“中国领导人从不打算指挥我们。从来不要求我们的独立是‘红色’独立,不要求中立是‘左倾’的中立。”“毛主席和周总理从未向我训示、告诫、警告或‘友好进言’等等,而这正是我在西方领导人和他们的卫星国那里所必须忍受的。”西哈努克讲起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当中国人使用经济援助的办法给予协助时,他们总是很谦虚的,经常讲这样的话:‘我们希望它质量更好一些,可是我们还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希望数量更多一些,可是我们的产量还有限。我们希望,等我们的工业发达起来之后,才可能给我们的朋友以更加有效的帮助。’”这种态度与西方某些大国总是在所谓的“援助”上附加种种条件形成鲜明对比,那种“援助”不仅使被援助国感到屈辱,而且带有控制别国的企图。
在《海内与海外》上发表的这篇文章里,西哈努克很真诚地写道:“我同毛的家庭背景差异巨大:他来自农村,我则是地道的王族,但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开始,我们之间的相处便十分随和融洽。我们两人之间,既不需要做作地同情,也没有相互反感之处,直到毛去世,连接我们的一直是一种自然流露的相互尊重和友谊。”
文章记录了西哈努克最后一次见毛泽东的情形:“我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75年9月”,“毛的身体那时候已经十分虚弱,言谈也不那么流畅了。他每说几个字都要费很大的力气,起身走动必须有两位护士的搀护。”“当他费好大劲向我作出微笑的时候,他的头却偏向一旁。看到这种情形,我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就在这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毛泽东告诫同去向毛辞行的乔森潘等红色高棉的领导人“不得虐待莫尼克(西哈努克夫人)和我的两个儿子西哈莫尼和纳林卡朋,也不得强迫他们干重体力劳动。”“然后他要求我不要辞去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元首职位。”
西哈努克在这篇文章中客观地评论道,毛泽东那时候“不可能预见到我一回到柬埔寨,我和我的一家立即就被置于软禁之中,被完全隔断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当然更不可能预见到波尔布特及其追随者后来的所作所为。在毛泽东逝世时,“我曾经三次向红色高棉领导人提出,请他们准许我参加毛泽东主席的葬礼,至少让我到金边的中国大使馆,在悼念簿上签上我的名字。可是我的每个要求都遭到了拒绝。”为此,西哈努克无比内疚而深感痛苦。
很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还披露了毛泽东曾经劝说西哈努克学习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谈话。西哈努克是这样写的:“朗诺政变两个月后,即1970年5月,毛很认真地向我建议,我应当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当时是这么说的:‘你有资格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从现在起,请考虑做一个共产党人吧!’我回答说:‘主席先生,我并不懂什么共产主义,也不懂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我只读过您的小红书,仅此而已。我同意您小红书里的思想观点,但是我并不懂共产主义。我成不了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者。’可是他并没有放弃对我的劝说。通过他那位杰出的法语翻译,再度劝说我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浅显易懂的精选摘要著作。可是最后我还是对他说:‘主席先生,肯定地说,我接受不了— 我到如此年纪,已经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哲学观念了。我是个笃信佛教的人。请您原谅我吧。’”
西哈努克称自己是一个“资产阶级亲王”,毛泽东会认为这样的人也可能“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这确实出人意外。毛泽东这样想,也许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相关:他也不是一开始就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不止一次地向别人坦陈自己的思想变化和成长过程:小时候信过佛,也接受过孔夫子的教育,开始并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后经过反复比较才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际探索各种救国救亡的道路的实践考察中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西哈努克这时正处于政治生涯的危难之中,他的祖国也正处在分裂与动乱的危难之中,朗诺政变迫使他流亡于国外,如他自己所说,他的“情绪非常低落”,若不是中国等“朋友们的鼓励”,他“可能早就无力支撑下去了”。毛泽东从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也会想到,处于困境与绝望中的西哈努克,为了寻求救国之路,会不会也像他当年那样,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希望。毛泽东是一个在认定自己掌握了真理之后就热情希望与自己的朋友和同事共享真理的人,年轻时组织《新民学会》就是这样。在这一点上,他很愿意担当一个诲人不倦的角色。对于西哈努克这样可视为朋友的人,他同样抱着这样的态度。毛泽东历来相信,社会的改造离不开人们思想的改造;人人都需要改造,包括他自己。同时,他也相信,人的思想是可以改造的。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能够改造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把同样的希望放在他认为聪明、好学而又爱国的西哈努克身上。
然而,西哈努克以诚实而坦率的态度做出了回应:他“接受不了”,“到如此年纪,已经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哲学观念了”。这时,毛泽东也不强人所难,更不会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西哈努克的文章这样记录这次谈话的结尾:毛泽东对他说:“没关系的。我仍然喜欢你这个人。” “几个星期之后,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一个规模盛大的活动,毛主席在上百万人面前热情地称赞我”。
【文/林之辛,本文为作者投稿188金宝搏体育官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