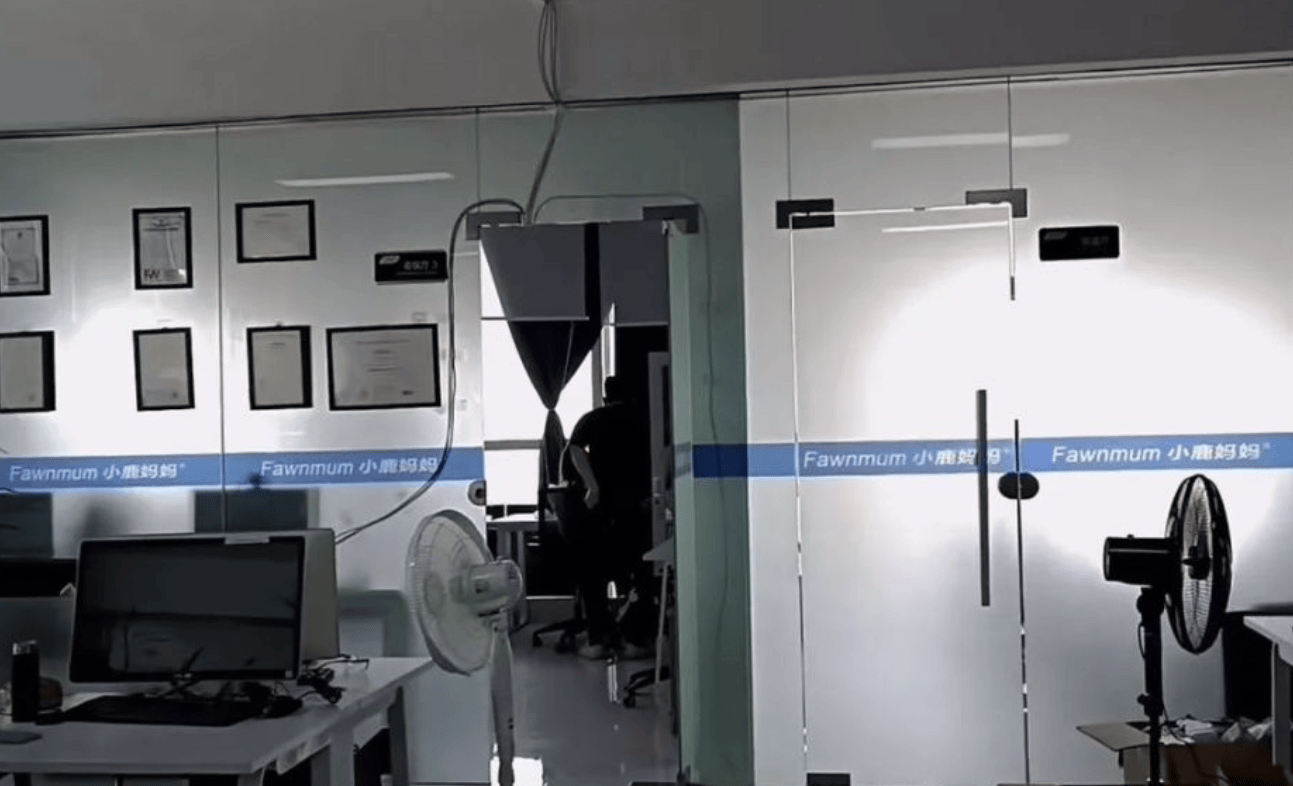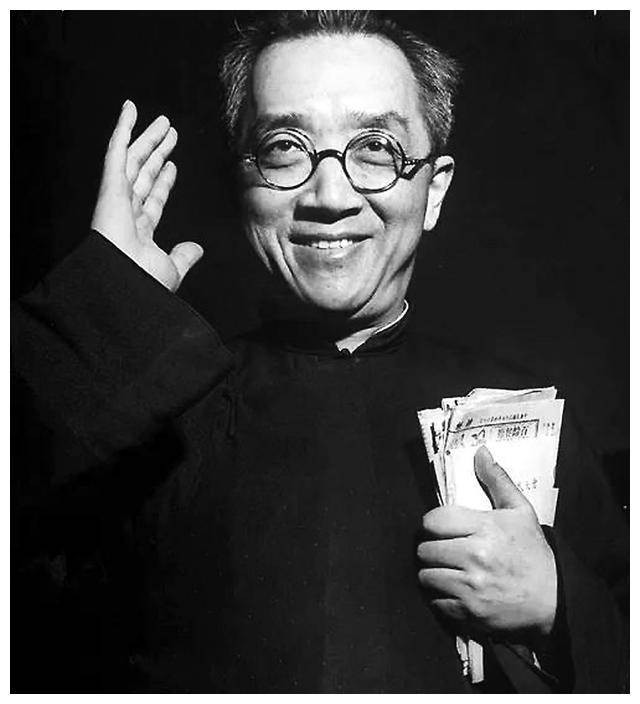我们应该关心美国中期选举吗?
“亲爱的,我们来选举建立一个民主和谐的家庭吧”,新婚的妻子也说,“要让我们今后的生活甜甜蜜蜜,以后所有的大事都由你来决定,而所有的小事都听我的安排,怎么样?”
看上去很美妙,丈夫问:“那么,具体讲哪些小事听你的安排呢?”
妻子:“我决定应该申请什么样的工作,应该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应该买什么样的家具,应该到哪里度假,以及诸如此类的事。”
丈夫:“那么哪些大事由我来决定呢?”
妻子:“你决定谁来当总统,我国是否应该增加对贫穷国家的援助,我们对原子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等等。”
显然,很多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就是那位丈夫拥有的伟大的民主。至于那些鸡毛蒜皮的家事,是读书人不屑一顾的。他们一向就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匹夫每天所面对的村干部、打卡机或者暂住证,是很该为总统选举这种大事让路的。
然而,我们每天面对的鸡毛蒜皮小事,才是民主的本质。
知识分子们所梦想或者假装梦想着的普选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历史上,真正的民主只可能存在于古希腊城邦中——是否真的存在,还得两说。现在没有城邦国家,都是民族国家,而且,国家还在超越民族的界限,变得愈来愈大了。在这样区域辽阔的国家里,选举都是在人们彼此互不了解的范围内进行,因而全是虚假选举。就如现在的美国已经不可逆的失去了工业能力,这点不是特朗普,奥马巴也同样发现了问题,但无力回天,美国社会的撕裂,只会越来越严重,造成不可调和的社会问题,并让国家失去基本的支撑。
代议制,尽管不失为历史的进步,但本质上还是虚假选举。议会,即使是经过普选产生的议会,它本身仍然是间接的代议民主机构,因而也就是对劳苦大众和人民管理自己事务的能力极不信任的表现。
在间接的代议民主制度下,“公民”是分散的、互不联系的个人,他们不仅容易屈服于资产阶级思想的种种压力,而且更主要的是容易屈服于劳动和消费的形式的压力;因为那种劳动和消费的形式是由资本决定的,主宰着他们的全部生存条件。这样的“公民”不能担当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甚至连配角也不能担任,而只能举举旗帜,喊喊口号而已。
由于“公民”并没有监督的权力,因此根据投票人的意志而经常更换的议会,在选举之后,就不会受到市井小民经常不断的压力了。因此无论竞选时说得天花乱坠,到头来总是背弃他们的诺言,为维护资产阶级秩序而立法。
真正的民主必须回归本义,即人民当家作主,因此就必须把所有选举都限制在互相了解的范围内。例如,一条村里的农民,或者一个生产班组的工人是相互了解的。一个车间的班组长之间配合生产,磋商事务,工作上的横向联系使他们也相互了解。议员彼此可能相距很远,但他们要讨论国家大事,相互协作,他们拥有的通讯手段和信息保证他们可以像朝夕见面那样互相了解。
在此小范围内的选举,才能让选举随时随地举行,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才会让社会权力从私有制变为公有。
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即使是一个生产队,或者一个生产班组也会有藏龙卧虎之人,他的才能无疑高于同班组伙伴许多,他当选是无疑的。当上了班组长,他就进入下一个选举层次。同车间其它班组长以前可能不熟悉他,但这个新的选举范围很小,很容易互相了解,又有朝夕共事的表现机会。用不了多久,其它班组长就能认识到他的过人才能,他就会被选为车间主任。
这样一级一级向上,不管哪个层次,原理都是一样的。只要他的才能和综合素质总是超过同层次其它人,他就能不停地被选拔上去,一直到达他的能力极限与职位的平衡点。如果那个平衡点是国家元首,他就一定能沿着这个途径从最底层一直登到顶峰。
有人说既然美国人直接选举总统还没打破权力私有,人民民主制度只让人民选举头顶的芝麻官,怎么倒成了权力公有?
问题就在这:美国社会让人民选举他们根本不知其然的总统,却不让他们选举最切身的头顶芝麻官,因为那一来整个社会就得翻个个儿,难道不说明芝麻官比总统还重要吗?
专制社会的独裁者只任命直接下级,如各省省长,但并不因此失去对浩瀚如海的基层官员的约束,反而产生放大效应,上面哼一声,下面变成一片雷。
人民民主制度颠倒了以往的任免顺序,让人民用任免芝麻官控制整个社会直到最高统治者。这种以多控制少的权力结构比独裁社会以少控制多的结构应当更有效。
在最基层的选举中,人们决定选举谁或罢免谁的标准是每个人物质的或精神的切身利益。每个人都希望自身利益得到最大满足。那么以三分之二多数当选的领导者就是这个互相了解的范围内多数人认为最能代表自身利益的人。他在随时可以被罢免的状态下,必须时刻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集体利益为根本原则才能保持当选。那么他在参加上一级选举时,他的选举和罢免标准就会是自己所代表的那个集体的利益,谁最有利于自己的集体就选谁。那么三分之二多数选出的那一级领导者就将是最能代表那个选举范围内多数下属集体利益的人。往上每一级选举都与此相同。
这就是直接民主制度的集中过程。乌合之众的个人利益和意志这样一级一级集中上去,越来越明朗﹑准确。当最高领袖向n个大区的首脑负责,受他们约束时,就等于正在向全社会负责,受全社会约束。当他在追随自己的n个选举者的时候,实际上他也就是在追随着全体人民。这个世界才真正由民作主。
一旦群众(而非“公民”)自己组织起来,一旦各个直接民主机构建立起来,群众就不再处于分散状态,互不联系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减少。他通过大家的力量,意识到了个人的力量;通过参加制定集体决议,而消除了个人的偏见。他不只是满足于仅仅把一张小纸片投进选票箱,而且还要参与决议的制定,参与这些决议的实施,检查这些决议的实施情况,看它们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他不再是跑龙套的人,而是政治舞台上的真正角色,并且是主角。这是在民主方面迈出的一大步。
群众的直接发动和直接行动越多,群众动员越广泛,那么,群众的自我组织和直接民主的主动性就会在各个领域中越充分地表现出来--从工人管理工厂,到组织“人民市场”;从接管公共服务行业到建立文化机构和“非官方”的托儿所。但是,直接民主扩大的范围越大,与国家机构的冲突也就越大,越不可调和。这并不单纯是与镇压机器本身和“国家机器”的最高机构发生冲突的问题,也是因为间接民主的代议机构拼命地维护它对“统治权”的垄断,维护它的最终决定权以及由它赋予的政府的“权威”,反对由动员起来的群众行使的新的大多数人的权威和新的人民大众的统治权。
那些否定人民民主的人(包括顾准)认为,“权力真正掌握在人民手里”是想入非非的事情,而且是一种骗局。不错,直接民主是有可能被独裁者利用的,但什么东西是不会被利用的呢?他们却因噎废食,一方面主张必须“扩大群众的福利”,另一方面又反对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要求“加强和扩大代议机构的权力和威信”,企图使水火相融。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办到的。一旦社会紧张局势和阶级矛盾引起了人民斗志的高涨,并因而引起了资本家的国家与群众的自由和行动这两者之间真正不可调和的冲突时,他们就会最终选择支持资本家的国家,而反对群众的自由和行动。
他们喋喋不休地指责“专政”,实际上无产阶级专政就其本来意义来说和人民民主是同一回事。马克思和列宁说:假如工人要对旧统治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残余实施专政,一个新的国家就是必要的。但这个新的军队、警察和法律系统要由工农控制,不与他们的利益相悖,它就必须建立在跟资产阶级国家完全不同的原则之上。它必须是作为多数的工农阶级对社会其余部份实行统治的工具,而不是用来对付工农阶级多数的专政。
士兵和警察可以由普通工人担任,他们与工人伙伴们自由相处,享有同样的观点并过着同样的生活。当然,要确保士兵和警察不会发展到脱离工农大众,“士兵”和“警察”就要由普通工农大众轮流担任,按同样的制度值班,担负职责。武装力量和警察不再由一小撮军官来管理,他们将直接由工农大众当中选出的代表来管理。
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代表通过法律,但只能将它留给全职的官僚、警察局长和法官去执行。这意味着议员们总能找到大把藉口来给自己开脱。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代表以其高薪与选民们相隔绝。在工人国家里,代表的报酬不得高于工农大众的平均工资。那些在重要岗位上执行工农代表的决策的全职人员也是如此(等同于今天的公务员)。
工农代表将不再像议员那样能在五年内免于撤职(或像某些高级公务员那样终身任职)。他们将至少要每年选举一次,如果选民认为他不能贯彻他们的意愿,可随时将之撤换。
直接民主的核心不是某个领袖,而是工农大众的自治团队(委员会),建立在工厂、矿山、船坞、大机关,以及像家庭主妇、领取退休金的人、在校学生之类团体的基础上,学生将拥有自己的代表。
通过这种方式,工农大众的每一部份都将有自己的代表,能够直接判断他或她是否遵从他们的利益。通过这些方式,新的国家无法形成一个脱离和违背多数工农大众的的那种势力。
同时,委员会制度提供了一个工具,让工农大众能够利用它,依照民主决定的国家计划来协同管理工厂,而非彼此竞争。很容易就能看出,现代的电脑技术将使全体工人能够得到向社会公开的、有关经济选择的大量信息,并且命令他们的代表选择多数工人所认为的一套最佳方案。
由于国家权力不再脱离多数工农大众,它的强制性要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少得多。当旧社会的残余随着革命的胜利而放弃了反抗,当外国统治阶级被根除,强制的必要性就不断减少,直到最后工农大众无需再从工作中抽出部份时间来充当“警察”和“军队”。
这就是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国家将会消亡的意思。国家不再是对抗人民的强制力量,而变成了只是负责决定如何生产和分配产品的工农大众委员会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