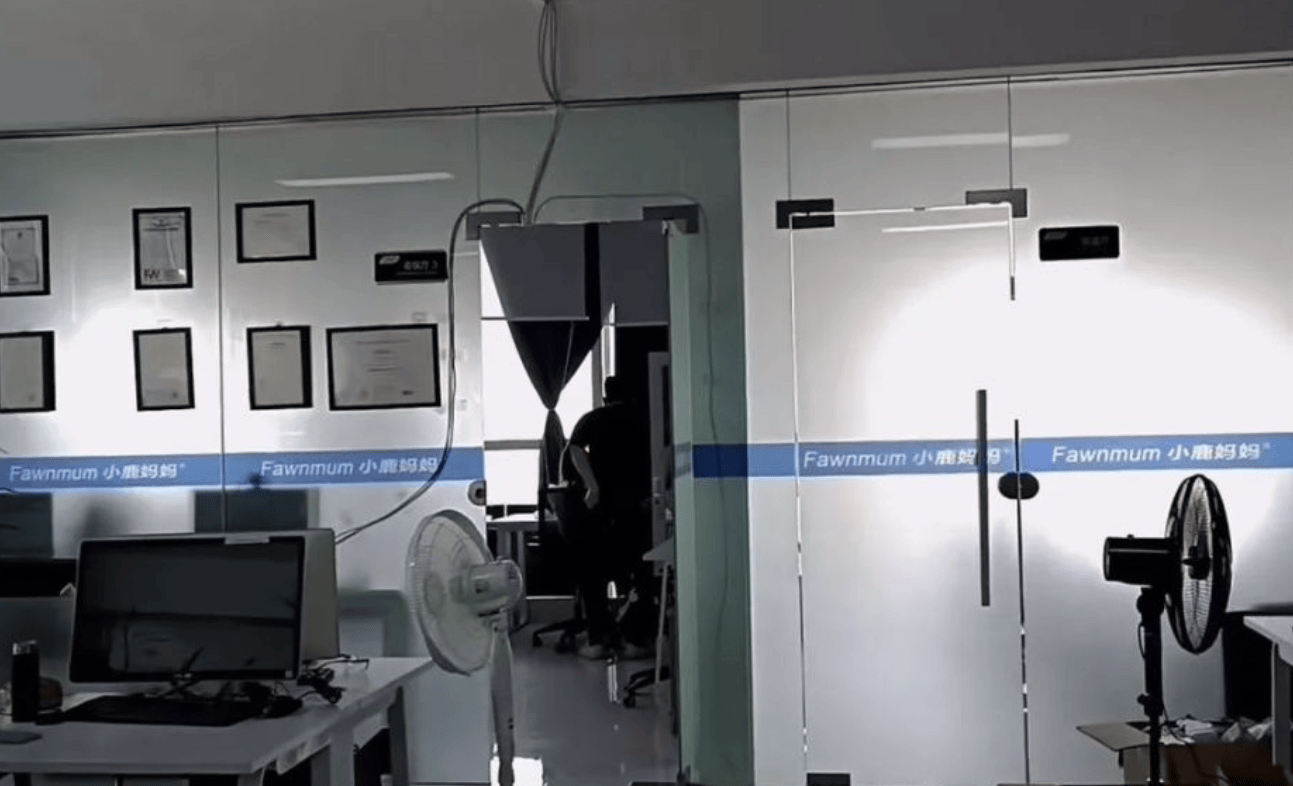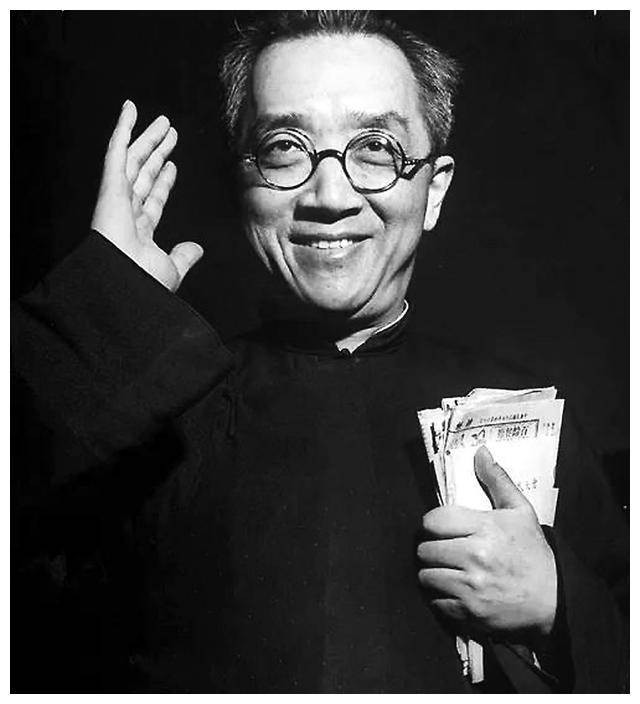告诉你一个秘密:司马南老师不像是“歌颂派”
告诉你一个秘密,别传人:司马南老师不是“歌颂派”,至少他以前不这样的。
写稿子《“文学”的过于神圣化要改变――由“莫言粉丝的一句反问”而联想》,上网查些资料,也顺便看看大家对这件事的看法,忽地发觉大家一致公推司马南为“歌颂派”,莫言为“暴露派”,最近文坛这些事儿据说就是“歌颂派”与“暴露派”PK。
我不懂文学,壮年后也不再看小说,因此也就不进去,但“歌颂”与“暴露”这俩词儿还是明白的,你说莫言为“暴露派”,我没读过他东西,没法说,也就人云亦云,你说司马南为“歌颂派”,我到有些疑虑。
大家有记忆的话一定还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有过那么一段时间,中国的媒体界和舆论界――管他纸媒质还是电子媒质,管他电视媒体还是其他,弥漫着一股“指鹿为马”的横气,甚至可以说整个中国被这股横气所笼罩,目的只有一个,试探社会谁顺从,谁不顺从;直到一个人的出场,对媒体界和舆论界的这股横气迎面撞击,几乎以一人之力,几乎以同归于尽的勇气迎面撞击,才踩刹住了这股横气。没有他的出场,许多人的气被活活憋死都有可能。
这个人是谁?这儿先卖个关子吧,很少有机会卖关子的!
以“指鹿为马”的方式试探社会的顺从程度,其中一个典型事例就是“特异功能”热,比如耳朵认字,腋窝认字,屁眼认字。
对这件事,有些人是相信的,其中不乏科学巨匠,比如我们敬爱的钱学森。就我们现在判断,钱老是确实真诚相信的,相信人体有某些超能量是可以开发的,他年轻时就相信。他是有功于我们民族的,他对我们民族的忠诚是无可怀疑的;某些国家政府或军方也有支持这项研究的――据传以色列军方就专门有研究人体“特异功能”的。他的成功与否,确证与否不谈,其存在和研究价值仍应得到肯定;
然而这些都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建立在科学理性之上的,容不得哗众取宠,对我们绝大部分普通大众,只不过娱乐、魔术、表演、找乐子,增加一点生活情趣而已,这是全世界人儿找乐子的方式,几千年了,中国有几处挖掘的石碑石刻,表现了三千年前中国人就懂得“魔术”找乐子;或有道具遮掩,或有小巧门,智力再平平的人都明白这道理。
可九十年代的“特异功能”热完全变了味,哗众取宠,来势凶猛,是一场“全民热”,与1949年以来多场“全民热”(比如“打鸡血针”热、“红茶菌”热、“香功”热)如出一辙,因为他又打着“科学”的神圣旗帜,一些重量级人物出场,道貌岸然、“国家拟人化”方式来背书这场“科学+神圣”【注】。
今天大家都已释然,平常心看待那件事,对于“特异功能”,都抱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心态,对相信他的人,那就让他们去研究,没碍着你,管他干嘛:对普通大众,那就本着“魔术”找乐子心态。两根平行轨道让他们永远平行下去,谁也不碍谁。
可当初为何演变成一场全民热,成了一项“科学”和“神圣”的全民事业?
自那以后我一直关注这件事,关注中国的意识形态,关注中国意识形态对这件事的态度和解释;据我所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似乎仍在集体沉默,假装没发生过这件事。可这件事发生过,没法假装下去的,十多亿中国人曾经紧盯屏幕,正在发生“耳朵认字”、“腋窝认字”、“屁眼认字”,他们全都神圣的接受过这件事。北方游牧民族没文字,我们汉族人代他们书写历史,今天土耳其人要找他们爸妈的历史,就要到中国历史档案馆来;九十年代我们发生的那件大事,我们不书写,外国人是有记载的,我们的后代要追问的话,那时他们肯定也得到外国的历史档案馆中去查的。
为什么会发生那件事?为什么至今仍然假装没发生过?
我今天分析一下可能与三个有关:与1949年以来诸场“全民热”有关;与时尚和商业化大势有关;与某些“权威”的流失而又心有不甘有关。
1949年以来诸场“全民热”:我以为50岁以上者大都还记得些,比如“打鸡血针”热、“红茶菌”热、“香功”热,他反映了我们民族的整体精神特质,某些事物哪怕匪夷所思,一旦“引导”就会演变为“全民热”;说句大笑话,你把机枪架那儿,也禁不住全民狂热。我们民族屡战屡胜的“国家威权”在他面前居然败下阵来,这时管得住的只有老天爷了――只能由他去,经过几个月自然冷却下来。
记得“香功”热那会儿我在机关上班,那会儿一到“香功”时间,科室干部全都开始串门做香功了,记得上午10点一次,下午3点一次,我印象中有几个平时非常矜持的女干部,那会儿也非常张扬兴奋,我们几个小赤佬就逮住机会对她们“下手”――你好香噢!你比他还香噢!你这儿比那儿香噢!记得没过几天,办公室紧张兮兮,发文劝大家别太过分了,后来又发文以“科学”的口吻解释“香功”没用,后来又发文,语气越来越重,反正我记忆中类似“12道金牌”那种味道;可是“国家威权”已然失效――虽然他曾屡战屡胜,这时没人会服从,这时唯一的权威来自“天”,必得几个月由他自然冷却――我记得这样折腾了大概三个月。国家机关可是我们民族智商最高的所在啊!我这里没半句假话,假话招雷劈呐!
关于时尚和商业化大势:大家一定不陌生“超距发功”、“空盆变蛇”、“徒手折钢”、“飞车过身”、“三五变六”,其实一连串有好几十个,我念不下来,其中有些与商业追求有关,有些与科学追求有关,有些与好奇探究有关,有些纯粹噱头招徕……,他们谁是谁,究竟冲何而来?我们庸众大白痴一个,你分得清?小子们推出这些,为了商业追求哪怕有些噱头招徕,老天爷也会原谅些个,姑娘打扮漂亮些好嫁郎,过分些,老天爷也不会过分为难姑娘的。
于是有小子推出“耳朵认字”,就是魔术,直奔找乐子而来,原本商业追求,满足探究,搞些噱头招徕,借“特异功能”增加一点神秘性,吸引更多眼球而已,就象今天的流量,谁会过分在意追究?
某些“权威”的流失而又心有不甘:当时的一些权威把“特异功能”当了真,他们手中资源有的是,于是将他放大,以至“科学”,再至“神圣”。小子们一看机会来了,原本假借“魔术”糊弄一下,也就商业得利,可现在变成一项神圣事业,那种流量带来的效益,一不做二不休,假戏真做,借“威权”将“特异功能”做成“科学+神圣”的事业。这种事情绝非我们今天人手一机可以媲美想像。你想像一下欧洲那时,马丁·路德对“一个子儿叮咚一响,灵魂升天”的怒不可遏,以至发动军队,对教会痛下杀手,就明白了。
权威们后来也明白了全部,所谓“特异功能”也就魔术,但已来不及了,“14亿人追科学”已被他们从无到有凭空造了出来,整个世界都关注华人这件事。这时摆在他们面前正确选择应该是:认错、懊悔、反思、检讨、寻求原谅、下不为例……,当然这样一来无论哪一项,都面临着“权威”流失,贻笑大方;他们却豁出去了,一不做二不休,假戏真做,与小子们联合起来将“魔术”朝“骗局”方向发展。
原本一场商业闹剧,如果这事发生在今天,好办,简单得不得了,因为人手一机,只要几个人朝他吐吐沫,全民就会清醒,闹剧三天就会结束,可当时“权威”把持全部媒体,因应这“三个有关”,于是这场闹剧必然朝向政治事件发展,必得有天人出世来制止。这就是我今天对这事的看法。
闹剧就是闹剧,总得结束,有些“权威”会来事却断不了事;这时的司马南进入了历史,进入了中国当代史,后面发生的事大家全知道了,司马南手撕“耳朵认字”之类。我对这件事的评价确实很高,一直评价很高,把他列入中国当代大事件,列入历史,后代必在课堂了解这个历史――正如他们学习基督教在西亚发生时与群巫斗争的波澜壮阔史。
为何评价这么高?
因为在中国“媒体权威”神圣不可侵犯,这个权威始终被少数人垄断,小子们在“三个有关”背景下,为了一点商业上的蝇头小利而加以利用,他是我们今天“流量狂”们永远无法企及,也难以想像的;而司马南在此撕开了一道口子,在中国的媒体界和舆论界撕开了一道口子,自那以后他们道貌岸然、神圣不可侵犯的形象不再,权威开始流失。
这个难道还不重要?
我们今天人手一机,并且历史又演进了二十多年,很可能感觉不到他的重要意义。我们今天谁还在意“媒体威权”?真还存在的话,也许已被压缩到很小一片地区――比如党报党刊之类,一般媒体哪怕“CCTV-1”、“CCTV-2”…人们也不当回事,哪怕再来一次“特异功能”,人们也就茶余饭后笑谈一下,谁会去搞事搞出司马南那样的动静来呢?
今天人手一机,都可方便发表自己见解,只要言语不太出格,普通人心声表达渠道还是畅通的;可当时“媒体权威”,没人蔑视和撕开他威权,能有今天这个局面吗?这个太重要了,应该载入历史。
×××××××××××××××××××××××××××××××××××××××
就这则故事看,司马南老师可不像是“歌颂派”呦。以我所知,当时有不少人还要司马南的命呢,更有人假借“老干部”名义写信造势“查那个小子”。以我的认知,“歌颂派”无论如何难以承受其重的。
或以为世事会变,司马南不会例外,也许吧?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今儿不谈哲学,就事论事――谁见过“暴露”苹果、鸭梨、蔬菜的呢?谁见过“歌颂”蟑螂、蚂蚁、臭虫的呢?谁见过“暴露派”永远暴露下去的?谁见过“歌颂派”永远歌颂下去的?事态总是有赞有讽,见解不同,立场对立而已;司与莫也就不同道而已,把谁标识为“暴露派”或“歌颂派”都有偏颇的。
如果大家已淡忘了九十年代那件事,我今天重提,也算透露一个“小秘密”吧!另外我还透漏一个秘密:那些人现在站我面前,我还会扇他一嘴巴,以解当初之恨。九十年代他们握有媒体资源,以“特异功能”来愚弄嘲笑人们的智力,以“指鹿为马”来试探社会服帖顺从的程度,没有司马南的以身撞击,他们差点得逞了!扇他还是轻的。
当然不免琢磨,其中有些人今天可能八、九十岁了,扇他可要小心点,不然我就赔大了。
【注】
1949年甚至前溯几十年以来,“科学”在中国是一项非常神圣的事业,他的神圣性在我们今天已很难感受,90以后各代越来越难感受何谓“神圣”,我给90后们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吧:三十万血性男儿为一个心念准备赴死冲入敌阵,军旗列列、军号声声,哪怕一个不剩、同归于尽,这个心念就是救出他们的爸妈、弟弟姐姐妹妹们――就是那样一种神圣;90后你们敢吗?不敢!或者不愿这种场景再现的话,就得始终保存某种“敬畏”和“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