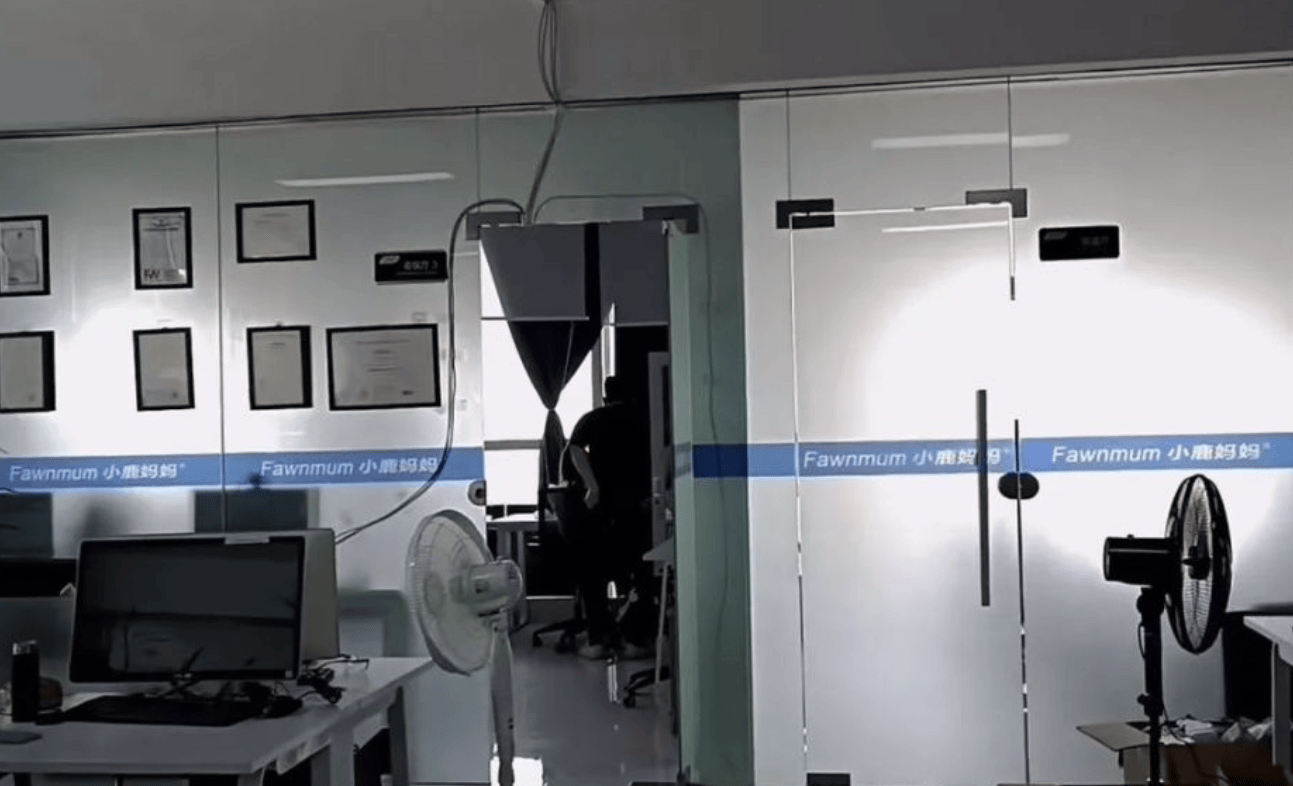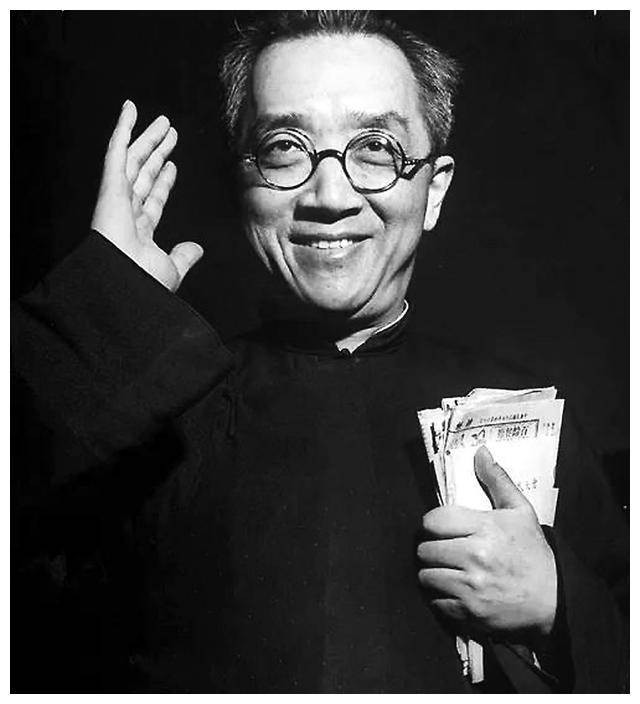不理解政治,就难以理解命运
01
人生的岔路口
1999年9月,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乘坐姑父的小车,进入了我的大学。差不多同一时间,以两分之差落榜的同桌兄弟搭上了南下深圳的火车,在那里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那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以至于我忘掉了日期。
在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那是我人生的一个岔路口。在那一天,我和同桌兄弟一起告别了农村,不同的是,我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而他的户口还留在原地。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和同桌兄弟保持着密切联系。我跟他讲述大学里的逸闻趣事,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他跟我诉说工厂劳动的酸甜苦辣,在那里,再没有人欣赏他漂亮的钢笔字,再没有人崇拜他丰富的历史知识,才华在忙碌的流水线上找不到位置。
尤其让他感到挫败的是,高中毕业的他不得不接受一个初中毕业生的管理。我们的生活大相径庭,唯一的共同点是我们都会抱怨食堂的糟糕伙食。
大约一年以后,随着他工作地点的频繁变动,随着我们共同话题的日益减少,我们渐渐失去了联系。
直到2009年的春节,我们在老家的街头不期而遇。他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孩子,他的妻子牵着一个背书包的小女孩。他们夫妇现在东莞打工,哺乳期的小儿子跟在身边,上学的女儿交由老家的父母照看。
我们激动地寒暄着,多数时候都是我在发问,而他最关心的问题是我一个月赚多少钱,穷追不舍,让我不知所措。临别握手的时候,我才发现他的右手失去了两根手指!我猛然想起,在多年前通电话的时候,他曾经告诉我,一个工友不小心轧断了手指,这让他忧心忡忡:有一天我的手指会不会也被机器轧断?
他留给我一个手机号码,几天后我打过去却是空号。
在那一天,我忍不住热泪盈眶,我想起十年前的九月,从那时起,我们便分道扬镳了,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只是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十年以后,我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一名政治学者,而他和他的孩子则成为我的研究对象——农民工及其子女。命运让我们看起来如此不同,而我知道,我们曾经多么地相似。
02
命定的博士论文
现在想起来,我的博士论文以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与政治社会化为主题,似乎是命中注定的。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一个叫做《心里话》的诗朗诵,在一瞬间击倒了我。
要问我是谁
过去我总羞于回答
因为我怕
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
他们的爸爸妈妈
送他们上学
不是开着本田
就是开着捷达
而我坐的三轮大板车
甚至没有装马达……
孩子们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久久萦绕,挥之不去。三个月后,我终于下定决心,放弃已经执行了一年的博士论文计划,重新选题,写这样一群“城市化的孩子”。当时,我和身边的朋友一样,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决绝,那么冒险。直到写博士论文后记的时候,我才逐渐理解自己的选择。
倾听和叙述他们的故事,其实也是在体验我自己的生命。我的命运曾经与他们如此接近:我出生在一个亦工亦农的家庭,父亲是国企职工,母亲在家务农,而我自幼随外公外婆居住在县城边上;在农村念完小学后,我转入质量较好的城镇中学寄读。
为了让每学期一百元的寄读费有所减免,外婆不得不托教育局的亲戚帮忙,然后拿着领导的条子去敲开校长的办公室,这曾经深深刺痛我的心灵;我这个农村小学的尖子生、班长,在那里成绩一落千丈,上课犹如梦游,直到多年以后我依然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突然间变得懵懂;
但我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农村孩子,我没有成为农民工的一员,纯属偶然。念高中那年,母亲携弟弟妹妹进城,一家五口蜗居在父亲厂里的单身宿舍,母亲在厂里做临时工补贴家用,现在想起来,原来自己也是农民工子女!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多年以后,我会选择这样一个博士论文题目。
我不只是在书写他们,我也是在寻找自己。一个从中部农村走进大上海的青年,虽然只是一介穷书生,每月拿着微薄的津贴,不得不四处兼课以求温饱,为什么却会与这些孩子及其父辈有着完全不同的生命体验?这就是阶级政治与身份政治的奥秘。不管我与底层有多么亲近,我还是逐渐地脱离了这个阶级。
我走上了一条通往城市中产阶级的康庄大道(尽管只是“慢车道”),而通过博士论文的研究,我试图回到那个决定我命运的岔路口,去看看,如果我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我的人生将会怎样。
03
城市化的孩子
当我把新出版的博士论文《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送给一位朋友时,她脱口而出:“城市化的孩子?应该是城市化的私生子吧?”这句犀利的玩笑话让我在错愕之余倍感贴切。
我之所以将进城农民工子女称为“城市化的孩子”,是因为:首先,他们都是在当代中国高歌猛进的城市化浪潮中出生和成长的,如此多的“放牛娃”涌入城市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
其次,他们自身也在经历一个城市化的过程,乡土性逐渐地从他们的心性中剥离,与此同时城市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塑造他们心智、观念、气质和认同,李强称之为“日常生活的城市化”;最后,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彷徨、迷失是由城市化——更准确地说,是经济上吸纳、政治上排斥的“半城市化”——带来的,最终也必须通过城市化来得到解决。
要研究这样一个群体,就必须把他们放到城市化的时间脉络与城市的空间格局当中来思考,而不是把他们悬置在一个空洞的、无差别的、没有质感的时空之中。
“城市化的私生子”这个说法虽然刻薄,却也道出了部分的真相。一方面,我们的城市化离不开农民工及其子女,他们不仅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强大的价格优势,也是城市化率中的光鲜亮丽的数字;
另一方面,他们却存在于一个半合法的灰色空间里,仿佛私生子一般见不得光,他们不是官方承认的移民或市民,常常被视为挤占城市公共资源的“搭便车者”,甚或潜在的犯罪者和不稳定因素,就如同私生子构成家产和家庭团结的威胁一样。
这一群体同时兼具三个特征:第一,跨越城乡边界,城乡二元结构深深嵌入其心智结构和生活历程当中;第二,生活在城市,但缺乏地方性公民身份 / 市民资格;第三,绝大多数生活在城市底层。
在他们身上,地域政治、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交汇在一起。城乡对立、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三者相混合,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这样一个群体对于当代中国政治而言,意味着什么?
而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又在于:其一,农民工子女如何定位其自身(我是谁),即身份认同的问题;其二,农民工子女在与政治系统的互动中,形成了什么样的政治倾向,他们的独特经历将会造就什么样的政治心理和政治人格?也即政治社会化的问题。
我的博士论文试图解决这样一系列问题:首先,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是通过什么方式形成的?不同的政治社会化媒介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农民工子女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与他们的身份认同是什么关系?最后,如果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会对他们政治观念与行为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围绕身份差异而形成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的分化究竟有多大?
农民工子女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者,抑或形成了一套相对自主的底层文化?如此一来,看似后现代的“认同政治”就与政治学的传统议题——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阶级再生产——紧密地勾连在一起。
这些农民工子女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命运。一方面,他们是“回不去的一代”。他们大多生于城市,长于城市,没有务农经历,与乡土社会缺乏文化纽带和情感联系,他们不可能像父辈那样往返于城乡之间,而倾向于定居城市,不可能将农村的土地作为最后的退路或“社会保障”;
另一方面,虽然他们在事实上构成了第二代移民,然而在政策上却仍然被界定为流动人口。在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下,农民工子女无法像城市的同龄人那样享有各种权利和福利。
长期以来,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只能就读于校舍简陋、师资薄弱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而这些学校不仅无法提供优质的教育,而且时刻面临城市教育行政部门的取缔。
现行的教育制度、高考制度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导致农民工子女在初中毕业时进退失据,处于就学就业的两难境地:如果选择在上海升学,目前只能进入中专、技校或职高。
如果回到家乡念高中,一方面,农民工子女将不得不与父母分离,寄居于亲戚朋友家,不仅需要付出极大的经济成本,而且需要承受因分离而带来情感代价;另一方面,家乡的教材和教学方式与上海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学生回去之后也存在学业不适应的问题。由于升学困难,大部分农民工子女在初中毕业之后选择直接打工,一部分人甚至成为街头混混。
04
学术马拉松
在选择了有趣或重要的问题之后,学术研究还需要你持续地投入你的热情、忍耐和想象力。
一个好的研究者,往往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疯魔”,一旦发现新的资料或解释,会两眼发光,手舞足蹈,兴奋不已;一个好的研究者,往往有一颗赤子之心,研究带给他的快乐就如同玩具带给孩子的快乐,这是一种不含杂质的幸福;
一个好的研究者,未必是一个优秀的“短跑选手”,但一定是一个合格的“马拉松选手”;一个好的研究者,未必是人群中最聪明的那一个,但一定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人。
我记得有一回,我的同事唐世平教授在短短的十五分钟内,连续三次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满脸喜悦,因为他突然想通了一个问题,自己十年前建立的理论模型终于可以在经验上得到证明,所以他激动不已,跟我们两个年轻人兴奋地讨论自己的新发现。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一个好的学者必定有一颗孩子的心,只有纯净的、充满好奇的心灵才能透视纷繁复杂的表象世界。
有了热情,我们才能持之以恒地投入精力;有了忍耐,我们才能克服研究中的障碍;有了想象力,我们才能发现与众不同的另类解释——在通衢大道和通幽曲径之间,我永远选择后者。
这三者缺一不可,没有人可以仅凭聪明和灵感就写出伟大的学术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坚持是学者最大的美德,想象力是学者最大的财富。
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我曾经有8个月的时间写不出一个字,尽管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兼课,到农民工子女家里走访,到NGO做志愿者,却完全没有理论上的进展,当时距离预答辩仅仅只有两个月了,以至于我怀疑自己的选题是不是一个错误。
2008年7月,我对一个刚刚初中毕业的小女孩做了一个访谈。这个来自四川的15岁女孩杨洋梦想成为一个街舞高手,与世界各国的街舞高手同台竞技。
然而,现实与梦想之间总是存在距离,不久以后,杨洋将进入上海市某职业技术学校就读酒店管理专业,在她看来,这是无可选择的选择,因为一共只有三个专业可供农民工子女选择,除此之外就是数控车床和烹饪。
这三个专业与杨洋父辈们的职业——饭店服务员、工人、厨师——何其相近,可是,不管杨洋们有多么不情愿,还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他们推上与父辈相似的生活轨道——杨洋的父母称之为“命运”,而学者们称之为“阶级再生产”。
杨洋还跟我讲述了她所在公办学校里老师与学生、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同龄人之间的互动故事,这些看起来琐碎的故事就像火种一样,让我眼前一亮,醍醐灌顶,突然间以前收集的碎片化信息被串成一个整体,当天我一口气写了一万多字,套用一句广告词,“根本停不下来”。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很顺利地完成了论文初稿写作。学术研究的美妙之处就在于,你不知道你的终点在哪里,你不是搭乘一列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而是骑着一匹不羁的烈马,奔驰在广阔无垠的草原上,等待你的有危险,也有风景,有苦行僧的时刻,但也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05
命运的共同体
长久以来,命运一直是文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青睐的主题。在主流政治学的分析框架里,我们找不到命运二字。也许是“命运”这个词太抽象,太模糊,太过于情绪化,与社会科学所强调的精确性和价值中立格格不入。
人们以为命运就像手心的掌纹一样专属于自己,其实不然,我们的命运或多或少具有外部性:我们的好运气或许会给别人带来坏运气;反之亦然。正因为如此,政治共同体同时也是命运共同体,我们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分享 / 分担着彼此的命运。
不理解政治,我们就难以真正理解命运;不关注命运,政治学就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
如果说个体的命运带有太多的偶然性和随机性,那么,群体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权力结构设定的。国家、市场、社会与家庭是命运的主要塑造者:
第一,国家通过制度和政策来塑造我们的命运。国家不仅对有形的资源进行再分配,也在对无形的机会进行再分配。
从上山下乡到恢复高考、从“WG”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化改革、从统招统分到教育产业化,国家行为对我们命运的影响何其巨大。国家对机会的再分配不是以个体为单位,而是以群体或社会类属(social category)为单位,譬如阶级敌人、流动人口、高收入群体。国家的再分配必须避免制度性歧视,即对特定社会群体的不公正待遇。
第二,市场包括物质市场和地位市场,前者通过产权、后者通过社会流动渠道为我们的行为提供激励,从而影响我们的命运。唐世平指出,在地位市场中,个人为社会地位而竞争。
和物质市场中的情况相比,地位市场中的竞争是纵向的、零和的,而且地位性商品的供应是内在有限的。简言之,我们通过物质市场获得财富,通过地位市场获得社会地位和外部承认。
第三,社会通过自由结社、社会运动、公共舆论、社会资本、关系网络来影响人们的命运。这对于一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尤其重要,显而易见,劳工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工人、黑人、女性的地位和命运。
第四,家庭是阶级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我们每个个体的人生轨迹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
以上四种力量与个人能动性的互动过程共同决定着我们的命运,每一种力量都不是绝对的。家庭是相对保守的力量,而市场、社会和国家都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有保守的一面,也有变革的一面。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系统中,这四种力量应当是相对平衡的,在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平、社会流动与阶级再生产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让社会成员各得其所,从而避免社会的过度僵化或无序。
而在农民工身上,我们却看到这四种力量惊人地一致:从国家的角度看,他们是“非市民”,无法在城市获得权利资格和公共服务;
从市场的角度看,他们被限制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同工不同酬;从社会的角度看,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缺乏社会支持网;
从家庭的角度看,他们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都相对匮乏。这四种力量的叠加效应,使农民工面临比常人更大的重力加速度,重重地跌落在城市底层。
06
正义的成本
为什么我要讨论命运的问题,是因为它关乎正义。命运的政治学追问的是一个最基本的正义问题——如果我们的命运具有某种外部性,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桑德尔在《正义——该如何做是好?》一书中讲述了一个叫欧麦拉的城市。这是一个拥有幸福感和公民荣誉感的城市,没有国王和奴隶,没有广告和股票交易,也没有原子弹。
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只有一个人例外。“在欧麦拉的一栋漂亮的公共建筑的地下室里,或者是在那些宽敞的私人住宅的地窖里,有一扇房间,它有一个锁着的门,没有窗户。”房间里坐着一个孩子,有些弱智,营养不良,并且被人们所忽视。
他在极度痛苦中勉强维生。所有的欧麦拉人都知道,他就在那里;他们都知道,他得待在那里。他们明白,整座城市的幸福和美好都是因为这个孩子所遭受的痛苦。因此,没有人来拯救他,他们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幸福。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其一,命运是有外部性的。在一个社会当中,每个人或每个群体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高度相关的,正如欧麦拉市民的幸福生活便是地下室孤儿痛苦的“溢出效应”;
其二,正义是需要成本的。如果不愿意分担正义的成本,那么对于正义的呼吁就是叶公好龙;
其三,我们不能用一个人(或多数人)的快乐去抵消另一个人(或少数人)的痛苦。
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处境类似于欧麦拉的地下室孤儿。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没有他们的付出,城市的繁荣便不可想象;没有他们作为廉价劳动力,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便无从实现;没有他们,就没有所谓的“中国奇迹”。
“中国奇迹”不是魔法师的作品,毋宁说一场超大型魔术,人们只看到舞台上潇洒自如的魔术师,却看不到后台紧张忙碌的农民工。
改革开放三十年,就这样同时创造着财富与贫穷。我们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深圳速度,却没有看到因赶超进度而缺乏劳动保护的风钻工,他们因此而罹患尘肺病。
2009年,有两条关于农民工的新闻格外引人瞩目。一条是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证明自己得了“尘肺病”而非肺结核;另一条是中国农民工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亚军。
表面上看,这两则消息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在第一个故事里,农民工扮演了一个凄惨无助的受害者角色,张海超胸前的绷带是最有力也最无力的控诉;
而在后一个故事里,中国农民工则成了对抗金融危机的平民英雄,6张青春快乐的面孔,成了美国版“劳动光荣”的最佳注脚。
其实,这不过一枚硬币的两面。长期以来,农民工为中国奇迹和世界工厂承担了过多的代价,现在,他们开始为权利和正义而斗争,他们开始主动地提出权利诉求,上访、罢工、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我们不能像欧麦拉的人们那样,对农民工的苦难和维权行动无动于衷。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唤善待农民工,但这不能掩饰我们内心的害怕:
我们害怕开放户籍,会让他们涌入城市,挤占我们的工作岗位,增加我们的财政负担,危及我们的美好生活;我们害怕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会让资本外流到其他城市或者国家,阻碍我们的GDP增长。
所以,我们更愿意让农民工作为弱者接受我们的帮助,而不愿意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一份子。而事实上,他们不是弱者,他们只是缺少基本的权利。
命运的外部性一方面使我们连为一体,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的社会陷入分裂,既得利益蒙住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对他者的苦难视而不见。不要将责任完全推给不公正的体制,也要反思我们自身,因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体制的受益者。
衡量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要看它的穷人过得怎么样;衡量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要看它的富人做得怎么样。如果一个社会的穷人尚且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那么这一定是一个富裕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的富人乐善好施、知书达理,那么这一定是个礼仪之邦。
相反,不管一个社会的GDP总量如何之大,只要有一部分民众仍然衣食无着、低人一等,这个社会在本质上还是贫困的,只不过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已;
不管一个社会的文化产业多么发达,高等教育如何普及,只要大多数富人过着醉生梦死、为富不仁的生活,那么,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必然是低下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命运,是摆在我们全社会面前的一道考题,它考验着我们对于正义的看法和道德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