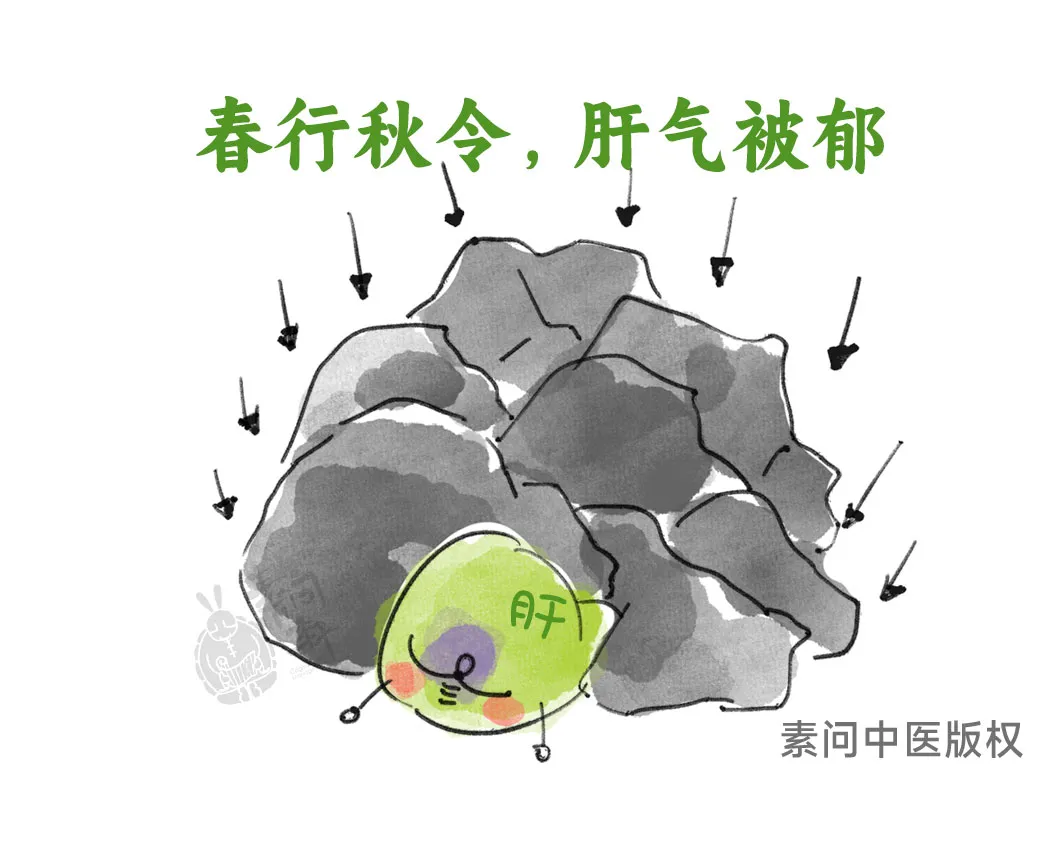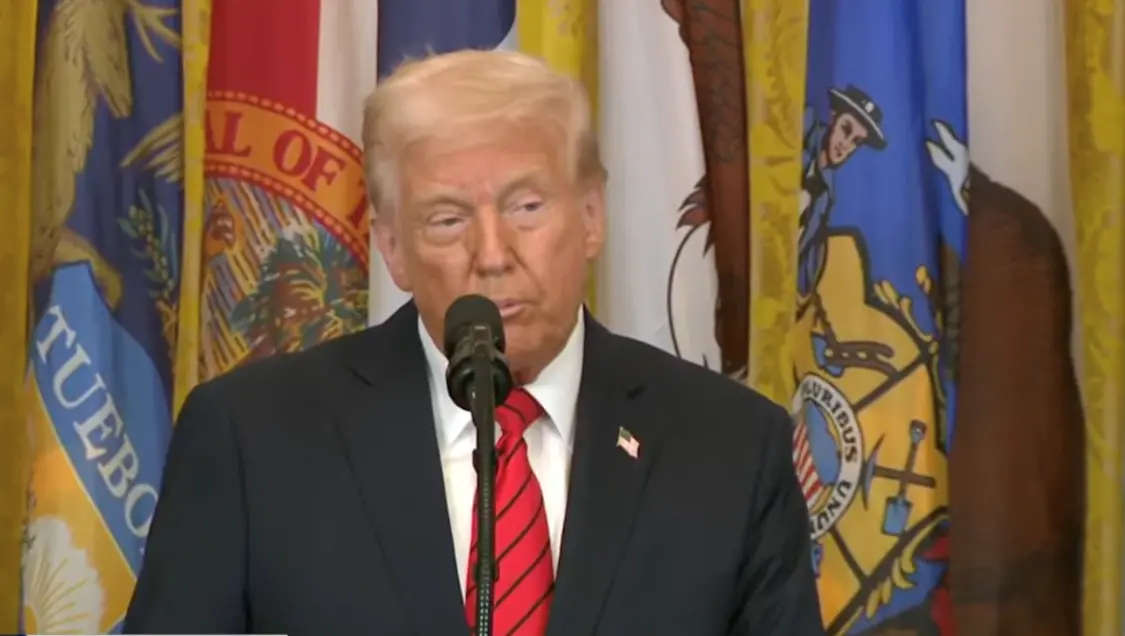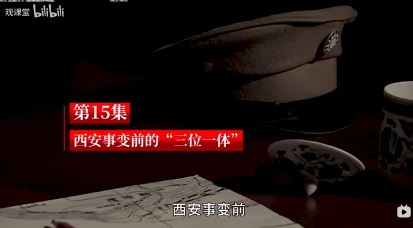黄纪苏:中国工人阶级变迁记
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因此,究名实往往是第一步的工作。本文要讨论的“工人阶级”究竟说的是谁,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近代产业工人么?我读中共早期文件时,发现他们面对“工人阶级”时,也是闪烁不定。一方面是能与欧洲工人运动接轨的“铁路工会”“冶金工会”“海员工会”,另一方面是从工不工农不农的“手工业工人”。前者虽然条条达标,但规模可怜——中国当时的海轮就没几艘,海员工会又能凑多少人?后者按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虽然缺斤短两,但毕竟人多势众。当代的“工人阶级”也会让人产生类似的纠结。例如农民工,农闲在城里,农忙回乡下,今天盖楼,明天看门,后天流浪,实在是游移不定。所以,在很多年人的心目中,他们算不算“工人”是成问题的。因此,在讨论“中国当代的工人阶级”时,需要有道墙,只是墙别太高了,以方便腿儿长的进进出出。
近代中国产业工人的崛起
中国古代的商业经济相对发达,有些产业具有相当的规模。例如盐业就可以说是个支柱产业。200多年前,据当时一位县太爷的观察,在盐场运水的挑夫就数以万计。不过,关于这些工场的工人生活,历代似乎并未留下太多的记录。即使是在毛时代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相当繁荣,工人阶级状况也不在聚光灯下。吸引学者尤其是大众兴趣的,还是资本家阶级的“徽商”“晋商”之流,即这个时代人人都想成为的那类人的鼻祖。
西方资本主义从19世纪开始向中国的扩张,不但造就了中国革命,也造就了近代产业工人阶级。近代产业工人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很有意思。在中国革命的初期,“工人阶级”基本上就像苏联飞机撒下的一张传单,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拿着传单上的画像按图索骥,寻找据说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这个阶级中国确实有,但由于规模太小,在中国近代的大舞台上基本上属于那种没两句台词的演员。但既然苏俄道路上“工人阶级”一马当先走在头里,中国革命也只好将工人阶级奉为领导阶级。中共早期的骨干或实干人物如毛泽东、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等人于是跑铁路的跑铁路,下煤矿的下煤矿,又是组织工会,又是发动罢工。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他们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但在随后的“四一二政变”中,蒋介石的部队轻易解除了工人的武装,还砍了许多共产党员的脑袋。这是中共的第一次重大挫败。挫败之后,一些中共领袖紧紧攥着那张俄国传单不放,对工业化的城市恋恋不舍,继续在大城市里开会、串联,撒传单,贴标语,组织罢工,发动起义,以及东躲西藏。而另一些中共领袖如毛泽东等则转变了思路,虽然他们嘴上须臾不离“工人阶级”,但脚却走向了广阔无际的农村,把农民当成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实事求是地说,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或主要依靠的力量并非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的壮大
虽然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不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真正壮大却靠的是中国革命的成功。这个革命启动了大规模的工业化,作为现代化核心内容的工业化的主体,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中地位显赫。显赫的地位落实在以下方面。第一,在物质利益上,国营企业职工享受了和官僚群体差不多的保障,也就是说工厂不会倒闭,工人不会失业,看病有本,理发有票⋯⋯虽然名义上“工农”像连体婴似的形影不离,农民就享受不到这些。第二,在生产关系中,由于企业的国家或集体所有制,职工和管理者之间并不存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都是给国家干”的感觉缩短了二者在等级制中的距离。工人和管理者收入上的差距有,但跟今天一比,几乎就是没有。第三,中国的文化馆系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向工人普及文化艺术,经常组织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辅导工人中的文艺爱好者。可以想象,当一个工人哼着《卡门》中的咏叹调换工作服时,他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第四,工人的身份在入团、入党、升学、就业等人生重要关口,都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例如入伍这个毛时代社会流动的黄金渠道,“出身不好”的子女是进不去的。最后,符号上,毛时代可谓钩以工人,凿以工人,一切宣传机器,都给予工人阶级最高的礼遇。符号上的最高礼遇,肯定是可以兑换其他实际好处的。不过有个兑换率,肯定是以多换少。举个例子,那个年代的女子嫁人——我一直把女性的择偶标准看做社会实际价值观的最便捷指标——工人并不是首选,而是排在大学生、军人、干部之后。
文革中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听着很唬人,好像国家大事真由他们说了算。其实在毛时代,除了官僚阶级,文革前的旧官僚也好,文革中的新官僚也罢,中国没有任何别的阶级是领导阶级。可以说,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地位,真的比现在高,但真的不如现在一些人想得那么高。
品尝改革的苦涩
后毛时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在最初岁月里,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是相当不错的。他们的心情也比较轻松。最初改革所释放的自由,他们尝到了甜头。
当时的改革在“增量”上做文章,即让一些人更富而不是让任何人更穷,让一些人上去而不是让任何人下去。但社会关系也是相对的,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相对于迅速蹿升的知识阶级在下跌。我上世纪80年代中结婚,妻子在企业工作。她的收入差不多是我在社科院收入的两倍。她曾笑问我是否感觉不适。我真的没感到任何不适,因为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我的经济地位虽是她的一半,社会地位很可能是她的两倍。当时挣钱最多的,多是被人看不起的个体户即最初的民间资产阶级。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排行榜上,“科学”这时成了“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升格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次提升又满意又不满意:共产党的好意他们当然明白,但“工人阶级”的“前进帽”谁还稀罕戴呢?总之,他们是觉得,把自己搁工人阶级里面,太让工人阶级占便宜了。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部分工人开始尝到改革的苦涩。纺织行业最先沦为“夕阳产业”,大面积经历了关停并转。我的在袜厂工作了二十年、将近四十岁的大姐也在“下岗”之列。她很快就被亲戚介绍给从前的徒弟,在人家开的一个私人小公司里做雇员,收入比原来要多。然而,成为亲戚的徒弟的下属,这在她多少有点社会地位上的难堪。最早的下岗工人有相当比例不愿到私营部门再就业,想必与毛时代的企业职工身份以及自尊感有一定关系。我们家人,具体说也就是我和父亲这两位知识分子,当时虽然都为她的下岗感到难过,但同时又觉得这是中国改革需要付出的正当代价。
上世纪90年代到两千年初,中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企业重组”的喧嚣声中,企业大规模倒闭,工人大规模下岗。往往一个国营企业倒闭的同时,一个生产同类产品的私营企业便转世灵童般诞生,而老板则不是原来的书记厂长就是销售科长。可以说,书记变老板,是中国改革的根本机制和主要动力之一。
在书记变老板的过程中,主流知识精英提供了一系列不但生动还特别生理的理论支持。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张维迎教授的“吐痰”理论,其灵感来自饭馆里的一种乞讨行为:好好一桌酒席,被乞丐吐了口痰,败兴的客人离席而去,乞丐便成了接收大员。国有企业就相当于这样一桌酒席,书记厂长先要想办法把它搞得声誉扫地,资不抵债(这事谁都会),然后政府便依照张教授的另一个“冰棍理论”——反正吃也化,不吃放那儿也得化,还不如送个人情——把企业几乎白送给书记厂长们去慢慢嘬。
书记厂长出身的老板把设备、厂房、土地嘬进肚里,几口就把自己嘬到了中国财富金字塔的塔尖上;他们把工人吐了出来,吐向刚刚开工的社会保障体系。我曾创作过一部表现主义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描画了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各类人群命运的起伏升沉,对这一时期的工人有段描述:
工人一:咱也闹不清国外是不是真那样:四十不到就让回家,咱也闹不清铁饭碗是不是真该砸,反正我跟小孩他妈二十年来就没请过事假。
工人二:咱也闹不清那什么“现代企业制度”到底啥意思,厂子被他们几个搞垮,一转脸儿又成他们几个的啦!
工人三:这一辈子的饭碗说砸就砸了,这一万来块钱儿工龄买断费说光就光了,这一身毛病说来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