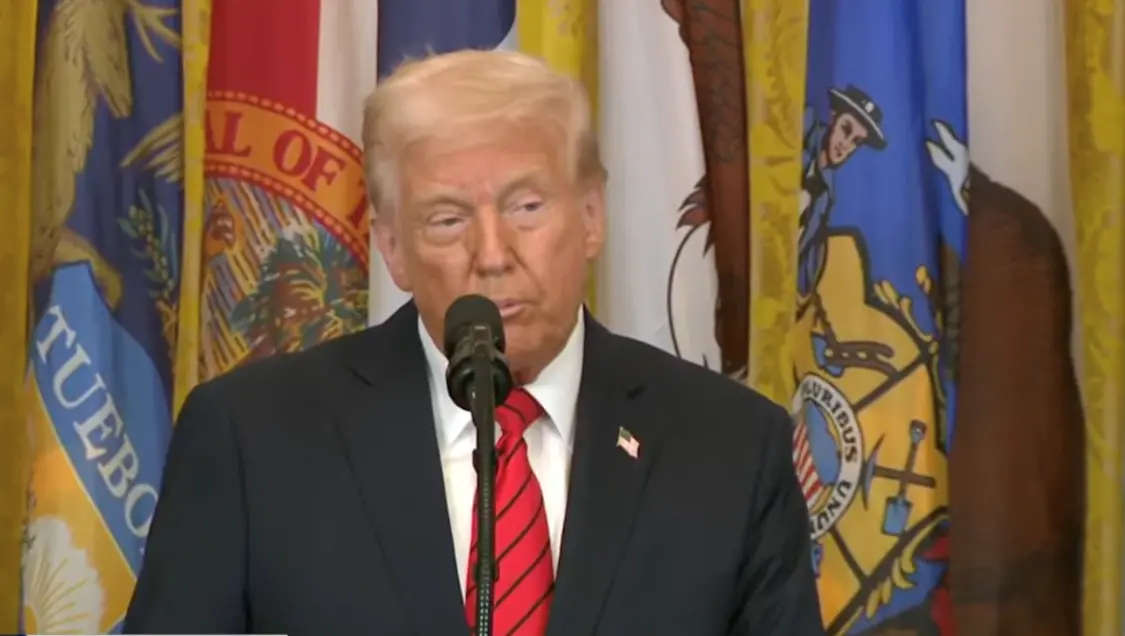拉美左翼“再下一城”之际, 如何理解对美国霸权的依附与反抗
【导读】当地时间2022年10月30日,巴西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击败有着“巴西特朗普”之称的右翼政客博纳索罗,当选巴西总统,标志着拉美左翼力量“再下一城”。美国一直以来视拉美为自己的后院,历史上倾向于扶持拉美国家的右翼力量,对左翼政党则比较警惕。虽然有分析称近年来拉美政坛新兴起的左翼力量反美色彩远不如以往激进,但仍可以视为拉美国家对自主性的一种探索。那么,如何理解在地理上直面美国霸权的拉美的主体性?拉美对主体性的探寻,对中国有何启发?
本文从拉美依附和反抗美国霸权的历史着手,尝试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的西半球霸权在一个多世纪中从未动摇过,但拉美与西方的关系非常复杂:拉美的前西方文明已基本被毁,现存的拉美文明主要是殖民之后的发展;在拉美许多国家,欧洲移民、美洲原住民和非洲裔居民的混血程度较高;拉美的主要语言与主导性宗教都来自西方;拉美的经济受美国经济乃至经济政策的影响非常深。这些都是拉美反抗美国霸权的艰巨挑战。但作者认为,无须期待拉美摆脱“西方性”,真正重要的是,拉美能否在政治经济上摆脱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支配和压迫,为自身多元因素混合而成的传统获取自由舒展和生长的空间。事实上,在思想层面,拉美知识分子始终坚持剖析霸权的构成,思索如何反抗霸权以及如何塑造自身的主体性,由此产生了丰厚的思想成果。而这些对另一个可能世界的深刻思考,恰恰可以和中国的思想者形成“接力”关系。
作者指出,无论我们通过美国还是拉美,认识世界和自我都是可能的。从美国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或许可以直观地认识到支配的快感,让认识者或认同既有的支配结构,或生长出“彼可取而代之”的雄心。然而,以中国的巨大体量,一厢情愿地认同和寻求“融入”既有的支配结构,并不会被霸权接纳;而如果寻求对霸权力量的简单替代,不仅会遭遇反击,更无法得到既有支配结构下被支配者的认同。因此,作者建议,中国更应该取道拉美而认识世界和自我: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最为坚实的基础在于“第三世界”;只有当中国与全世界大多数民众站在一起的时候,才有可能凝聚起足够的力量,突破支配体系的“薄弱环节”。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8期,原题为《霸权、依附与反抗:拉丁美洲的主体性》,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参考。
霸权、依附与反抗:拉丁美洲的主体性
如果不是因为写作“门罗主义”全球史著作《此疆尔界》的机缘,我也许很难真正从心灵上“重逢”拉丁美洲。17年前,我曾经在洛杉矶的“小哈瓦那”回声公园(Echo Park)居住一年,每天穿过熙熙攘攘的讲西班牙语的人群。我知道那些古巴流亡者可以与美国的“历史终结论”者发生什么样的共鸣。但对于“门罗主义”话语和实践的思考,让我意识到,拉丁美洲的谚语“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背后有着多么痛切的历史体验。
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的西半球霸权在一个多世纪中从未动摇过。美国的军事霸权、金融霸权、技术霸权牢牢钳制着西半球。不仅如此,用一位拉美国家高级外交官的话说:“美国更像是梵蒂冈,你很难被其接纳,你必须遵守很多规则,而且还要去忏悔,但你仍有可能会受到诅咒,而不是去往天堂。”这显然是一个充满天主教色彩的类比,美国绝不仅仅是一个世俗权威,它经常祭出自己的正当性原则,不断质问拉美国家,并要求其“忏悔”。
要理解被殖民者长期称为“西印度”的拉丁美洲的处境,不妨将其与殖民者眼中的“东印度”即东南亚地区做一个对比。西班牙和葡萄牙16世纪就在这两个区域建立起稳固的殖民统治,后来又有荷兰、英国、法国等殖民者加入。在两个区域的不少地方,发展出了类似的社会经济特征,如大庄园、大地主和天主教的强大影响力。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比东南亚要早一个世纪,但两者的历史境遇大大不同。由于地处冷战前沿,不少东南亚国家独立后得到美国的扶持,同时也获得日韩制造业的带动。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后,东南亚国家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和产业合作,经济发展进一步加速。在地缘政治上,很多东南亚国家也是“左右逢源”获取资源。
而19世纪以来,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独立后经济上先依附于英国,后依附于美国。二战后,随着美国霸权的进一步巩固,拉美各国受其影响程度也逐渐加深。如巴西在1960—80年代一度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实行贸易保护,吸引外资在国内建立工厂,然后补贴中产阶层购买国产工业制成品,以期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19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的影响,美国开始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国际借贷利率较低的情况下,巴西大幅举债,扩大公共开支。然而美联储从1979年开始加息,国际资本大量流出巴西,导致债务危机爆发。至1990年代,巴西走上新自由主义道路,还处于保护期的许多本国工业企业在进口商品的冲击下纷纷垮掉,大量国有工业企业被私有化,公共服务大幅削减,贫富差距急剧拉大。21世纪重新上台的左翼政权走上了依靠出口农产品和矿产资源等大宗商品、补贴穷人以拉动消费市场(同时也保证选票)的道路,但这样就缺乏资源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与制造业,尝到社会福利甜头的劳动者也很难再安于枯燥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岗位。由于拉美政权无法避免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波动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巨大影响,一旦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外资撤离,财政收入暴跌,政治动荡也就接踵而至。而政党轮替通常意味着经济政策的大幅震荡。最近拉美的政治钟摆再次向左偏移,但只要经济基础没有改变,恐怕拉美就很难摆脱这种充满动荡的政治周期。
拉丁美洲没有成为“世界工厂”,更谈不上进一步升级为“世界实验室”。与东南亚相比,它的制造业要更加薄弱,在互联网等新兴领域,拉丁美洲更是美国跨国企业的天下。即便部分拉美国家开始在大国之间搞平衡,也没有东南亚那样的地缘政治条件。美国在拉美的霸权是相当稳固的,缺乏扶植拉美经济的动力。拉美国家如果触动美国资本的利益,其结果或是政党轮替、经济政策转向,或是像古巴和委内瑞拉那样被长期制裁,经济外向发展空间严重受限。
尽管如此,拉丁美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秩序的本来面目,进而更好地理解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的主体性所在。以西方殖民者为中介,中国在明代就与拉丁美洲发生经济关联——大量美洲白银的流入对于中国内部经济的运行产生了深刻影响,美洲农作物的传入更是影响深远。但中国与拉美的直接交往要等到19世纪。废除奴隶制后,一些拉美国家偷运华工填补劳动力缺口,而中国与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往往从华工问题开始。如1874年,中国与秘鲁就华工问题展开磋商,签订《中秘友好通商条约》,但由于两国围绕在秘华工保护存在分歧,直到1909年才完成换约。甲午战争之后,在对中国被列强“瓜分”的恐惧之中,像康有为这样的精英人士还产生了华人大规模移民巴西、再造一个中国的想法。同时,由于美国“排华”的影响,很多在美国的华工也转往拉美,而他们劳作的种植园有许多是完全掌握在西方资本家手里。正因如此,在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华工往往和拉美本地底层民众并肩作战,共同争取政治经济独立和自主。
接下来,中国人对拉美的认识进入政治制度层面。1906年,康有为曾经在墨西哥的托雷翁设立华墨银行,投资有轨电车,并一度想前往巴西考察。1911年,墨西哥先于中国发生革命,反政府武装攻入托雷翁,洗劫了华墨银行,并杀死大量华人,其中包括康有为的族人康同惠。而这为康有为对于共和制的负面看法增添了新的材料。在民国初年,康有为不断撰文论证共和制会造成种种不稳定和动荡。为此,他不得不将美国处理为一个例外,即认为它能行共和制而保持稳定,只是因为存在一些特殊条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共和制在欧亚大陆的传播,康有为的这些批评意见就很少有人追随了。但可以说,由于康有为的介入,在美国与拉美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方面,中国的起步丝毫不晚,尽管此后缺乏持续跟进。
一战之后,随着“觉醒年代”的到来,中国的进步人士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框架里,认识拉美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的历史,并产生深刻的共情。1949年之后,中国更是大力支持全球的反帝反殖革命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1960年周恩来总理接见智利文化教育界人士时提出:“美国有门罗主义,而你们拉丁美洲应该有个新的拉丁美洲门罗主义,不让人家干涉,自己团结起来,完全组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力量。”周恩来总理建议的“拉丁美洲门罗主义”,其重点就在于拉美国家建立一个共同的经济体系,自主地与其他国家展开经济交往,摆脱美国的控制。19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1980年代以来,中美经贸关系日益紧密。但与此同时,中国与拉美交流中的经贸分量,也在不断加重,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双边经济合作更是有了长足进展。
这些历史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当代中国主体性的构成。中国有着非常完整和系统的、从未中断过的古代文明,在近代是少数未完全沦为殖民地的非西方国家之一。中国通过深刻的社会革命,重新获得独立自主,走出了一条“自主性开放”的道路。而拉美的前西方文明已经基本上被毁灭了,现存的拉美文明主要是殖民之后的发展。在拉美许多国家,欧洲移民、美洲原住民和非洲裔居民的混血程度较高。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强调的,在殖民地时期,欧洲移民的后代克里奥尔人(Creole)已经发展出与宗主国不同的民族认同。但西方性一直存在于拉美的血脉里,其主要语言与主导性宗教都来自西方。无须期待拉美摆脱这种“西方性”,因为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祖先。真正重要的是,拉美能否在政治经济上摆脱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支配和压迫,为自身多元因素混合而成的传统获取自由舒展和生长的空间。
拉美在思想上所贡献的最为深刻与普遍的成果,大多与对霸权的抵抗有关。在认识层面,拉美思想者对西方的各种“辉格派史观”进行祛魅——这种“辉格派史观”认为西方的繁荣源于其内在制度的优越性,而制度优越性又可以追溯到其遥远的文明源头。自1980年代以来,这样的叙事模式对中国的思想界与学术界影响深远。但拉美学者集中审视内外关系,指出其殖民宗主国的富裕,首先并非因为制度和道路有何内在优越性,而是凭借强大的暴力,在外部进行剥削和压迫,汲取了额外的财富,从而改变了自身发展的环境和条件。殖民地依附于宗主国的局面一旦形成,即便照搬那些所谓“优越”的制度,也无法摆脱依附和不发达的状态。著名的“依附理论”就源于拉美思想者的探索,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弗兰克(Gunder Frank)、卡尔多索(F. H. Cardoso)、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等学者均有深刻贡献,后来又有阿明(Samir Amin)这样的拉美以外的第三世界思想家加入。而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则通过综合依附理论与现代化理论,创立世界体系理论。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的结构主义发展观虽然没有促成拉丁美洲国家摆脱不发达状态,但在第三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以林毅夫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学家正是在普雷维什的结构主义发展观的基础上,推进“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设。
在政治层面,墨西哥学者海因茨·迪特里希(Heinz Dieterich)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这个口号被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Hugo Chávez)接过去并进行新阐释,一度对拉美的新自由主义产生强大冲击。在“21世纪社会主义”口号之下,查韦斯发起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后改名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抵制美国倡导建立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巴西学者、政治家昂格尔(Roberto Unger)引领了美国的批判法学运动。拉丁美洲也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的基座所在,许多共产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参与了这个论坛的讨论。拉美丰富的民粹主义运动也产生了重要的理论成果。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欧洲与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阿根廷思想家拉克劳(Ernesto Laclau)对民粹主义的解析,获得了全球性关注。
此外,更不用说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的《百年孤独》给1980年代的中国作家带来的冲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坦言自己和马尔克斯“搏斗”了多年。当然,莫言只是借用了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与技法。而正如书中马孔多屠杀所集中体现的,殖民主义、霸权和反抗,是深嵌在《百年孤独》中的主题。对于1980年代急于“走向世界”的许多中国作家来说,《百年孤独》激发的是他们对于中国文明的绝望感,甚至20世纪的中国革命也被他们纳入了对于历史轮回的想象之中。而到了21世纪,全球政治与经济版图的变迁,让我们越来越能看清,我们经历的绝非一场轮回——没有20世纪的中国革命,就不会有独立自主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和吸引全球注目的经济崛起,也不会有今天美国统治精英对其全球霸权失落的深刻恐惧。
在今天,1980年代“走向世界”的问题意识,有必要获得新的发展。关键的问题是“走向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国需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努力,打破既有国际秩序的霸权结构对于发展权的种种不公正限制,而这意味着中国自身主体性的某种更新。二战后的日本思想者竹内好曾从主体性塑造的角度立论,倡言“以亚洲为方法”。在他的视野中,“亚洲”代表着一种“抵抗”的主体性,而不是一个地理性的实体——因此,古巴也可以属于“亚洲”,而以色列则不属于“亚洲”。类似地,可以说拉丁美洲代表着这样一种主体性:其内部包含西方文明的许多因素,却又受到现实的西方尤其是美国霸权的压迫;它不断地进行着抵抗,探寻新秩序的可能性。尽管尚未走出一条很成功的发展道路,但它的探索与抵抗本身就是对这个霸权秩序的不公正性的揭示。正如拉丁美洲的“结构经济学”在中国激发“新结构经济学”,拉丁美洲思想者对另一个可能的世界的思考,很多是相当深刻的,恰恰可以和中国的思想者形成“接力”关系。
当然,在日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回应:强调对霸权的抵抗,也可能带来受制于霸权所设置的议程的结果,因而走向一种相反的一元化秩序想象。这正是沟口雄三对竹内好进路的担忧——竹内好对中国近代以来道路的肯定,将日本置于反思对象的位置之上。而沟口自己的“以中国为方法”,则试图用中国前殖民时代的历史经验和原理,来理解和解释中国近代以来的一系列变化,通过一个特殊的中国,将西方特殊化,从而展示出世界的多元图景;在这样一个多元世界中,日本也能获得一个比较舒适的位置。
而我们无须过多卷入这些争议细节之中。竹内好的视角将古巴与“亚洲”关联在一起,这正好提示我们,中国一度大力倡导的“亚非拉”认同具有多么强大的思想力度。在反抗世界的霸权结构方面,中国与拉美有着相通的历史记忆和共同利益,拉美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思考和实践,是中国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的重要参照。在原住民文明被殖民主义摧毁的拉美,像沟口雄三研究中国那样挖掘前殖民时期的历史经验和原理看起来是极其困难的。但我们可以梳理所谓“地理大发现”以来历史的层层累积,在其中可以看到,一些殖民主义的因素后来被转化为反抗的资源。比如,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传教士曾经在殖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今天神学可以转化为批判霸权的资源。拉美共产党人在处理与天主教的关系方面,有着许多独特实践。而经历过拉美“解放神学”熏陶的方济各,已经成为天主教世界的教皇。在这方面,中国与拉美恰恰能够互为镜鉴,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特殊性,同时也更深刻地认识到彼此社会实践的强烈共时性。
无论我们通过美国还是拉美,认识世界和自我都是可能的。从美国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或许可以直观地认识到支配的快感,让认识者或认同既有的支配结构,或生长出“彼可取而代之”的雄心。然而,以中国的巨大体量,一厢情愿地认同和寻求“融入”既有的支配结构,并不会获得霸权力量的接纳;而如果寻求对霸权力量的简单替代,不仅会遭遇反击,更无法得到既有支配结构下被支配者的认同。
相比之下,取道拉美而认识世界和自我,也许更能接近世界的真相——而这不过是20世纪历史已经揭示的一个道理: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最为坚实的基础在于“第三世界”;只有当中国与全世界大多数民众站在一起的时候,才有可能凝聚起足够的力量,突破支配体系的“薄弱环节”。正如马克·吐温所言,历史并不会重复自身,但会押韵。一个片面寻求“融入”支配体系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个更为自觉地建设更加公正的国际秩序的时代已经开启。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刚刚落下的韵脚之处,与拉丁美洲重新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