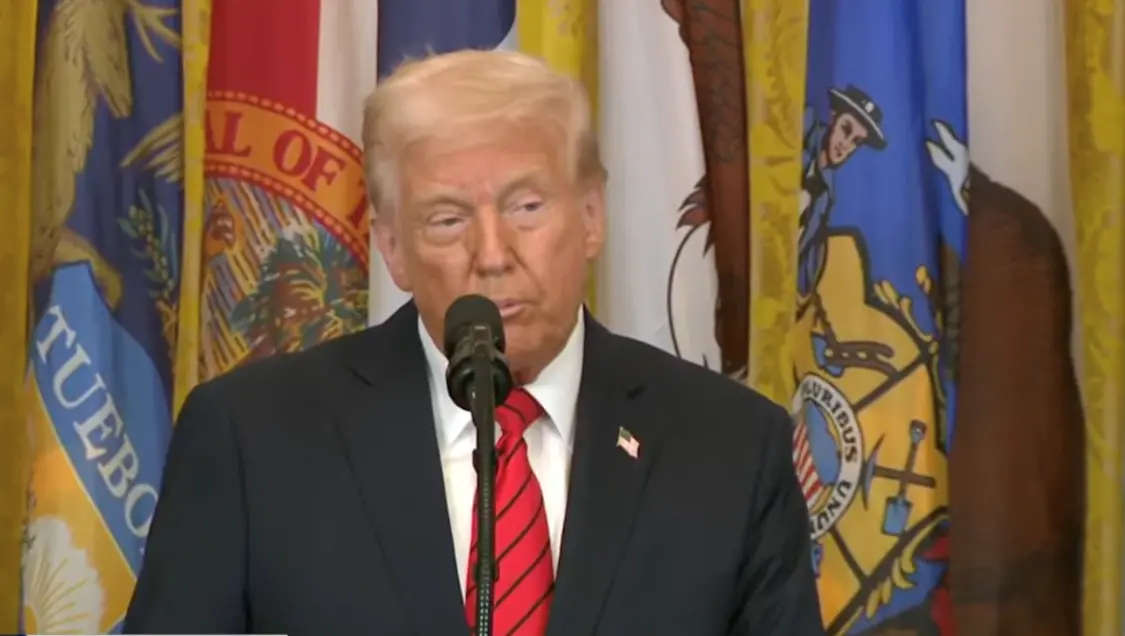普拉沙德:灾疫之年,重归马克思
2022年5月5日,文科高研所邀请印度历史学家、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主任维杰·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通过Zoom举行在线讲演。此为主讲人提供的讲稿,由志愿者Alvin、于同、李蕤伶、惊雷进行翻译,特此感谢!

Vijay Prashad在线演讲截屏
在三大洲社会研究所(Tricontinental),这个我参与指导的机构中,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密切关注饥饿现状。我们关注饥饿问题,因为它对世界而言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它使生活失去尊严,是对我们人类本质的侵害,是最严重的人权犯罪。为什么饥饿在世界如此多地方持续存在?殖民时代的宗主国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对此有一个老旧的理论解释,认为是有太多的嘴要吃饭,而生产的食物太少,也就是人口过剩理论。事实证明这一理论是完全错误的。201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全球农业生产的食物足以供120至140亿人食用,这是地球人口的两倍。然而,大约有10亿到30亿人——接近世界人口的一半——生活在饥饿之中。一头是饥饿的群众,另一头是食物,但饥饿的群众却无法获得食物。为什么会这样?除了这个人口过剩的虚假故事,资产阶级的思想并未给出答案。它只是说,抽象的市场力量会在遥远的未来以某种方式奇迹般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抽象的市场力量几百年来早已失败,它们不会解决任何问题。而且它们甚至不是“抽象的”,因为这些力量是通过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顺从(市场体系)的政府来驾驭的,它将我们社会大多数的财富分配给那些拥有私有财产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仅仅两千多名亿万富翁所占有的财富能超过46亿人的总和,即地球人口的60%。
食物匮乏的人因为没有钱仍然挨饿,他们没有钱是因为他们没有工作或报酬不足。财产遭到剥夺使他们易于陷入饥饿,而随着国家和公共行动从社会福利和救济中撤出,饥饿也不会得到改变。他们在挨饿,而饥饿导致了两个彼此并不总是冲突的方向:绝望和愤怒。
所有这些关于剥夺和金钱的讨论让我们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框架。再没有其他理论能够恰当地解释为什么饥饿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居高不下,以及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或社会主义政府——它们本身就管理着贫穷社会——能够消除绝对贫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做的)或结束饥饿(如卢拉总统在巴西做的)。其他理论无法解释饥饿问题的持续性以及其它顽疾,也不能解释为什么需要有秉承社会主义意志的行动来对抗抽象市场力量的压倒性优势。在这个危险的世界上,我们这种不设边界的马克思主义(boundless Marxism)是必要的。为什么是不设边界的?因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宗教, 作为对资本主义最激进的批判,它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发展。
这种不设边界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一百年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一场辩论,在这场辩论中,列宁确立了以下政治事实:
1.自由主义无力解决饥饿、文盲、居无定所和健康损害等顽疾。要在世界范围内真正实现人权,就需要超越这些顽疾。而这在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中是根本不可能的,自由主义的目标是保护私有财产,后者恰是人权的障碍。
2.殖民主义不允许殖民地的生产力发展,因此工业资本主义并不会从殖民主义中产生。这种现代生产形式将使一个社会得以生产克服侵害人类尊严这一顽疾所必要的财富。没有多样化的现代经济,就没有实现人权的希望。
3.在殖民地,包括在沙皇俄国的部分地区,社会主义事业必须既反对殖民主义,又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换句话说,社会主义事业必须把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结合起来。这就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给出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激发了从秘鲁到印度支那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以及左翼力量的联合。
4.列宁和同行们(译注:指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发展是,在殖民地不仅工业无产阶级是历史的必要主体,而且农业无产阶级和从事资源开采的无产阶级也是如此。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工农联盟"的概念得以发展。甚至在一个世纪前就很清楚了,农民之所以是农田中的无产阶级,是因为这个阶级越来越多地由无地雇农组成,他们创造剩余价值,而不只是对剩余进行再分配(who generate surplus value and who do not merely redistribute the surplus)。
5.最后,不设边界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当它从资产阶级手中赢得政权时——在俄国(1917年)、在越南(1945年)和在中国(1949年)——它既要发展生产力,又要使生产关系社会化,这种双重任务在经典著作中没有得到很好的阐述。同时,这样的双重任务产生了它自身的诸多理论,其中的每一种都值得仔细研究。
我们继承了这种不设边界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但由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
要做出哪些必要的改变呢?
一、任何国家的社会发展都离不开对世界体系的全面把握。这个世界体系植根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相互交织的历史过程:这个体系压制了全球南方国家的主权,这样他们的工资和税收就可以被人为地压制到 "热带 "水平,同时大都市银行系统中的利润就可以累积到天文数字。早于资本主义的世界贸易在长期发展中建立起了相互联系,加上资本主义试图将世界上每一个地方都卷入其体系中,这需要我们对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有准确的理解。由于乌克兰战争,现在许多事件都发展得非常快。但早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就有一些趋势显露端倪,决定了今天事件的发展速度。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理解这些趋势。
1.单极化
从1990年苏联解体,到2013-2015年,美国建起了一个世界体系,使得总部设在美国和其它七国集团国家的跨国公司可以从中获益。有两组重要事件彰显了美国的压倒性力量:一组是美国1991年入侵伊拉克和1999年入侵南斯拉夫,另一组是1994年创建的世界贸易组织。苏联解体后,实力大不如前的俄罗斯加入了七国集团,成为北约的和平伙伴,意图进入这个体系。1993年到2013年,中国在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位总书记的先后领导下(1993-2003; 2003-2013),也通过提供劳动力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进行了一场谨慎的博弈,在行动中不去挑战美国。
2.标志性危机
美国在两件事上显示出力有不逮 (overreached its power)。
a.国内经济过度杠杆化。银行过度杠杆化,非生产性资产大于生产性资产。
b. 试图同时打几场战争,包括阿富汗、伊拉克和萨赫勒战争。
2003年入侵伊拉克和这场战争的惨败,以及2007-08年随之而来的信贷危机,都是美国力量减弱的标志性危机。美国内部政治两极化和欧洲的合法性危机紧随其后。
3.中俄的崛起
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和俄罗斯出于不同的原因,都改变了相对谨慎的策略。
a. 中国的崛起有两大支柱。
i. 国内经济方面,中国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同时它通过贸易协定和对高等教育的投资,积累了科学和技术知识。在机器人、高科技、高铁和绿色能源方面,中国企业赶超了西方企业。
ii. 对外关系方面,2013年,中国发起 "一带一路"倡议,意欲提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展和贸易议程的替代方案。“一带一路”从亚洲延伸到欧洲,并进入了非洲和拉丁美洲。
b. 俄罗斯的崛起也有两大支柱。
i. 国内经济方面,普京与部分寡头进行斗争,加强国家对关键商品出口部门的控制权,并通过石油和天然气等商品积累国家资产。
ii. 对外关系方面,俄罗斯在2014年和2015年分别介入克里米亚和叙利亚,以保护其暖水港口和盟友。这是自1990年以来美国受到的第一次军事挑战。
与此同时,中俄两国在各个领域深化了合作。
4.全球门罗主义
美国将1823年的门罗主义推向全球,并提出后苏联时代的整个世界都是其统治范围。它开始反击中国和俄罗斯的主张,比如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战略,通俄门和乌克兰事件。美国发起的新冷战是一场混合战 (hybrid war),其手段包括制裁伊朗和委内瑞拉等三十个国家,严重破坏了世界稳定。2018年,美国的战略宣称,反恐战争已经结束,而现在美国将利用其强大的武力削弱俄罗斯和中国,确保不会出现"几乎势均力敌的对手 "。与此同时,美国也退出了主要的军备控制组织。2002年,它退出了《反弹道导弹条约》,2019年,它退出了《中程导弹条约》。
5.对抗
新冷战对抗激化了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局势。台湾海峡仍然是一个热点,而在拉丁美洲,美国试图在委内瑞拉引发一场热战。美国试图在玻利维亚等地部署自己的力量,但未能成功。目前乌克兰冲突的根源有许多因素,包括乌克兰多元民族主义的消亡,但也与欧洲独立的问题紧密相关。美国把北约当作“特洛伊木马”,操控欧洲。现在,“全球北约”是使欧洲服从于美国利益的工具,哪怕它损害了欧洲人的利益,使得欧洲人失去了自身粮食经济所依赖的能源供应和天然气。俄罗斯侵犯了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可是西方想方设法地加速了这种对抗的升级,不是为了乌克兰着想,而是为了它在欧洲的利益。
6.终极危机
脆弱性是美国力量的主要特点。它并没有急剧减弱,但也不是毫发无伤。美国的力量的三大来源还相对安然无恙。
a. 军事力量。
b. 美元-华尔街-IMF制度。
c. 信息力量。
还有一些权力的来源也受到了重创,比如美国两极分化的政治格局,以及它无力调动资源让中国和俄罗斯退出国际舞台。
必须强调全球国际主义事业的两个关键部分。
a. 围绕以下要求,振兴全球和平运动。
i. 美国恢复强有力的军备控制制度。
ii. 控制军事开支升级。
iii. 加强反战文化,可以考虑恢复“广岛日”。
b. 加强民间外交、社会运动外交,这是国际人民大会的特点之一。今年5月1日,100名来自美国的年轻活动家来到古巴哈瓦那,与500万走上街头的古巴人民一起庆祝,这彰显了社会运动之间的团结。
二、世界上仍有一些国家是社会主义,包括中国、越南、委内瑞拉、古巴等。尽管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它们仍然受到帝国主义的猛烈攻击,被动处于防御地位。这是因为美国拥有巨大军事优势,其中包括无可匹敌的毁灭性核导弹库,以及对世界金融、贸易和商业网络的统治地位。再加上美国及其盟友在国际通信网络方面的有利条件,这种优势将被进一步放大。美国及其盟友可以选择宣传他们认可的事件版本,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拥有网络的所有权,也与什么能够成为新闻有关。换句话说,现在的新闻关注的是事件。这些事件往往断章取义,添油加醋地将西方描绘成是人权和民主的捍卫者,全然不见西方殖民史及其近些年所犯下的累累战争罪行和对人权的侵犯(伊拉克便是一个例子)。
社会主义事业在消除贫困和建立合作化的生产形式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这些成果都被刻意忽略了。例如,印度喀拉拉邦的大规模合作社有效防止了区域性的饥饿危机,降低了文盲率,而这在印度其他地区比较普遍。这些社会主义事业正受到制裁和其他混合战争工具的疯狂攻击,面临被消灭的危险。今天,摆在马克思主义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正确分析社会主义事业的情况?它们正面临着来自帝国主义集团的巨大威胁,帝国主义在政治上脆弱但军事上非常强大。与之关联的问题是,这些社会主义事业与其天然盟友—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之间是什么关系?
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消灭了人们集体生活的意识,并通过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加深了原子化的绝望。第一,破坏工会运动,打击根植于工联主义的公共行动和工作场所斗争,从而扼杀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第二,用“消费者”替代“公民”的概念,即把人定义为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人的主体性主要通过对物的欲望来体现。
社会集体的瓦解和消费主义的兴起使绝望变得更加深刻,它逐渐演变成各种形式的倒退。举两个例子:
第一类是退回到家庭网络中。社会服务消失、家庭照料工作增加、通勤和工作时间延长使得家庭网络不堪重负。
第二类是走向宗教、仇外等毒化社会的组织形式。这些组织提供了集体生活的可能性,但却不是为了人类的进步,反而限制了社会的可能性。我们怎样才能拯救集体生活?我们必须建立植根于社会救助(social relief)和文化愉悦(cultural joy)的公共行动形式。它们可以作为暗淡生活的解毒剂,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左派的日历中,我们将2月21日定为红色书籍日——在这一天走到公众面前,阅读各种红色书籍。今年,仅在印度喀拉拉邦就有50万人阅读红色书籍。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有根植于左派传统的公共行动日,每个月甚至每周举办活动,就可以吸引越来越多、数以百万计的人一起行动,从而拯救集体生活。在新冠疫情期间,拯救集体生活的努力得到了生动的展示。喀拉拉邦的工会、青年组织、妇女组织、学生会在公共领域建造洗手池、缝制口罩、建立公共厨房、运送食物,挨家挨户进行调查,以便每个人都能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20岁的年轻学生Arya Rajendran就参与了调查。她后来当选喀拉拉邦首都特里凡得琅市现任市长,也是该市历史上最年轻的市长。
四、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扰乱了生产,使各国的工厂变得碎片化。工业生产形式的瓦解导致通过国有化建设无产阶级力量的策略失效,并导致最重要的、高密度产业的工会被削弱。没有组织,没有工会,通勤时间长,全球工人阶级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即国际劳工组织所说的“不稳定无产者”(the precarious proletariat)。失去组织的工人阶级和农民,以及失业者和勉强就业者,发现几乎不可能从他们的斗争中建立起与资本直接对抗的理论和信心。工人阶级和农民运动可以从印度正在酝酿的斗争中学习经验。在过去的十年里,印度每年都有3亿工人参与大罢工。数百万农民在一年内进行了罢工,迫使政府在试图将农业工作“优步化”(uberise)的新法案上让步。
在印度,90%以上的工人都从事非正规工作,而且工会密度很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如何做到上述的?在过去20年中,由于非正式工人(主要是从事照料工作的女工)领导了大量斗争,工会开始把非正式工人(主要是女工)面临的问题作为整个工会运动的议题。在争取长期聘用、合理的工资合同以及女工尊严的斗争过程中,不同行业的工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看到的主要斗争都是由这些非正式工人领导的。他们的战斗力现在注入到工会的组织结构中。一半以上的劳动力是妇女。她们不认为与她们有关的问题是所谓的“妇女问题”,而是所有工人都必须争取和赢得的议题。同样的,在涉及种族、种姓以及其他类型的社会区隔时,他们也将其视为同样事关工人尊严的共同议题。此外,工会一直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和社区福利问题,为用水权、排污权、儿童受教育权以及反对各种偏狭行为而斗争。这些 "社区"斗争是工人和农民生活的一部分。因此,通过参与这些斗争,工会将自己扎根于拯救集体生活的进程中,为向社会主义迈进建立了必要的社会结构。
我们有底气想象未来吗?一个后苏联时代经久不衰的迷思是,我们不会有后资本主义的未来。这个迷思来自于以胜利者自居的美国知识阶层内部,他们的 "历史终结"情结助推了经济学和政治理论等领域的正统观念,阻止了对后资本主义的公开讨论。即使正统经济学面临无法解释的普遍存在的危机,包括2007-2008年的经济全面崩溃,其正统自身也保留了合法性。这些迷思在好莱坞电影和电视节目中大行其道:灾难片和反乌托邦电影表现的是地球毁灭而不是社会主义转型;想象地球的末日比想象社会主义世界更容易。
在经济崩溃期间,"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这个短语在公众意识中沉淀下来,强化了资本主义的永恒性,同时使让动摇其基础的尝试看起来更加危险。该系统处于停滞状态。紧缩政策向没有安稳生计的人发出咆哮,小企业因缺乏信贷而瓦解。然而,超越资本主义依然没有成为大众议题。世界革命并没有出现在眼前的地平线上。这种片面的现实扼杀了人们对超越这个系统的可能性的希望,因此这个“大到不能倒”的系统现在看来是永恒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反对悲观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必须自始至终以希望为骨架。但这种希望的物质基础是什么?这一基础有三个层面:
首先,饥饿和文盲、无家可归和屈辱这些顽疾必须被看见。那些身处其中,其处境却被否认的人也必须被看见。如果不解决这些顽疾,他们的物质条件也不会消失。否认只会带来凄苦和愤怒。
第二,工业、农业和服务业领域全球生产的巨大进步让我们可以开始想象一个超越必然性而通往自由的世界。一个人不可能仅仅通过一项法律命令就获得自由。自由要求克服上述的顽疾,而我们几十年以来所生活这个世界有能力满足人类的这些要求。
第三,全球生产的巨大进步不仅是由于科学和技术的改进,而且更关键地取决于劳动的社会化。所谓的全球化是指从资本的角度,从规模收益增加的角度来看待整个过程。然而,它不承认的是,这一巨大进步的产生是由于工人的跨洋劳动,而这种劳动的社会化正是国际工人阶级一体化的积极证明。劳动的社会化与狭隘的、令人窒息的私有财产的界限背道而驰,后者为了自己的蝇头小利实际上阻碍了更大的进步。正如马克思的预测,劳动社会化和私有财产之间的冲突加深了财产社会化的斗争,也即现代社会主义的基础。
资本主义已经失败了。它无法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问题,无法解决那些直逼我们眼前的顽疾。只求生存是不够的,人们必须还要求生活和发展。当然,社会主义是不会神奇地出现的。我们必须积极争取它,用更深刻的斗争,更强的社会联系和更丰富的文化。这就是我们漫长旅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