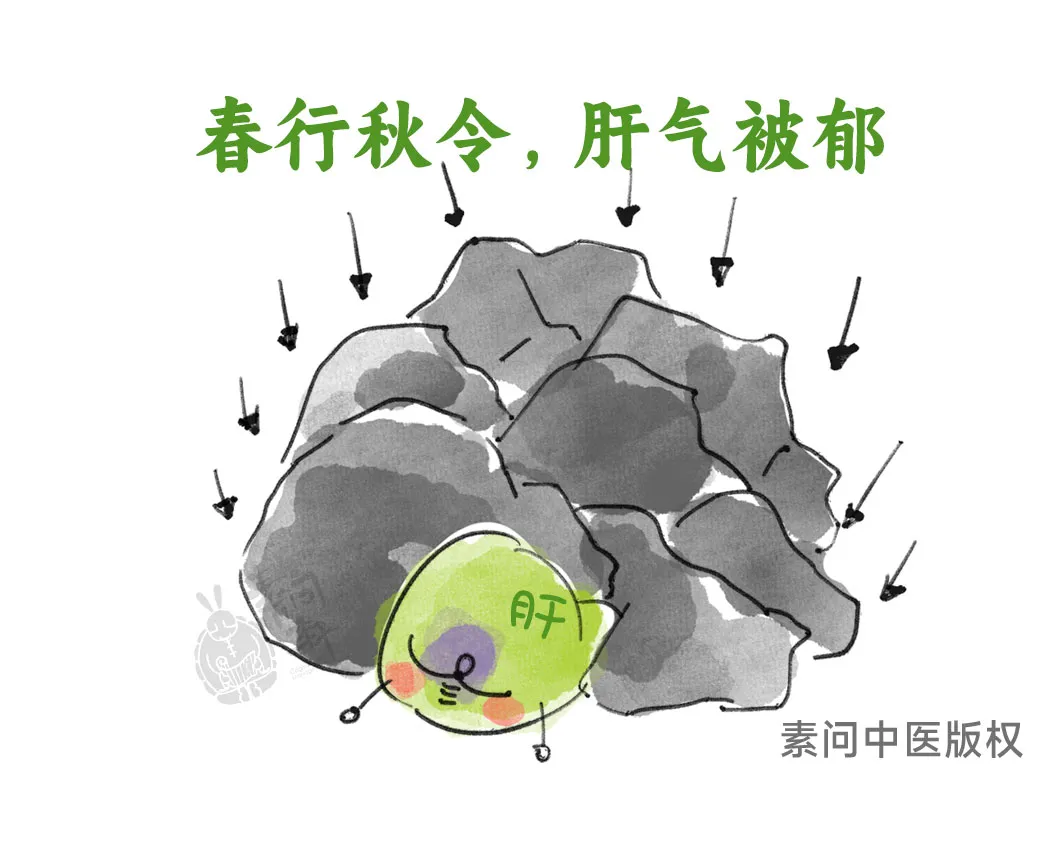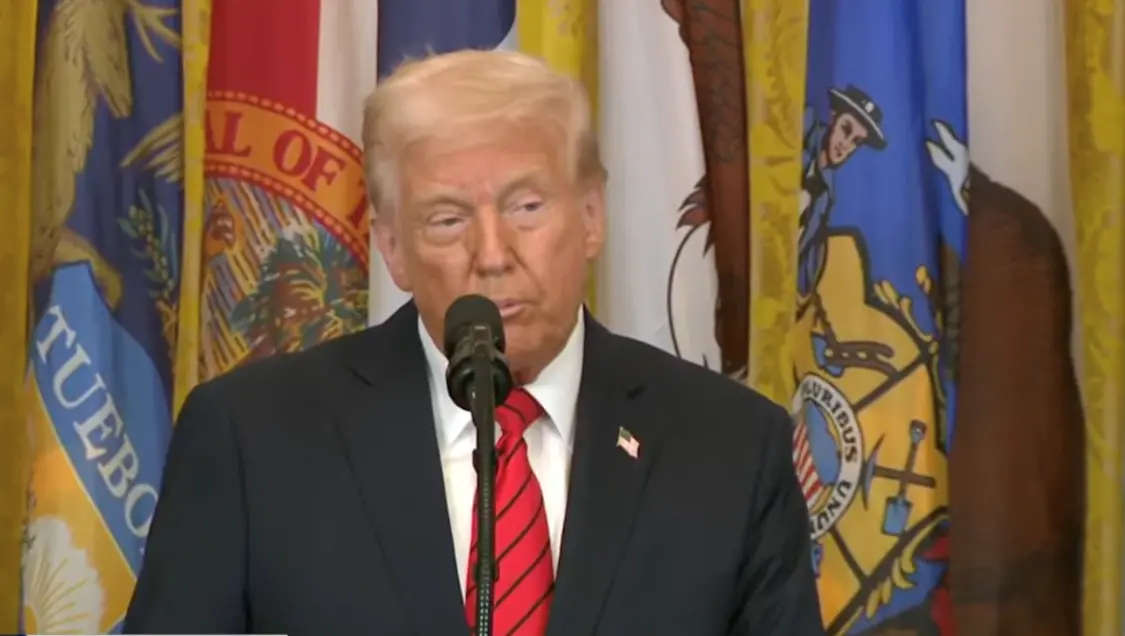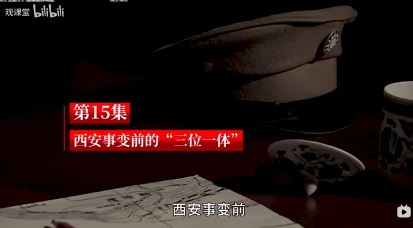让我们开始工作吧——美国左翼谈“融工”
这是一篇关于“融工”(salting)策略及其在美国工人运动中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的文章。作者埃里克·福尔曼探讨了左翼运动和工人阶级的关系,及其在劳动运动中的转变与挑战。文章认为,融工策略——即有意识地将激进分子安置在工作场所以促进组织活动——曾是美国工运成长的基石,并且在当前右翼势力增强、工人权益受到威胁的背景下,重新发挥其复兴运动的潜力。
文章回顾了近一个世纪美国工运的历史,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激进分子通过融工策略在工作场所内部开展组织活动,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这些激进分子,包括那些自愿当工人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激进左翼分子,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带入工厂,通过日常的互动和组织,增强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集体行动的能力。
文章强调,面对当下的挑战,融工不仅仅是工人运动的历史策略,还应成为当代工人运动的关键组成部分。这要求左翼和工人阶级更加紧密地合作,重新激发工运活力。
文章的核心观点在于,工人自己应成为改革和重建劳动运动的主体,而不是由上至下的策略所驱动。通过培养工作场所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工人可以重新夺回对自己命运的控制权,实现从被动接受到积极参与的转变。作者呼吁,工运左翼需要采取实际行动,通过融工等策略,重建和强化工人阶级的组织能力和斗争精神,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
文章内容供参考,不代表本号观点。
作者:埃里克·福尔曼(Erik Forman)
译者:小花
“融工”造就了美国的劳工运动——现在也可以复兴运动

露西·费舍尔(Lucy Fisher) / Flickr
左派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就是问自己“怎么办?”(英语中列宁这一名作的标题被直译为“什么需要被做”——译者注)。自从列宁提出这个问题以来,它不断地引发人们的思考,同时它也是一种号召,呼吁人们在任何一场社会运动陷入困境时积极采取行动。
“怎么办?”从一场运动到另一场运动,从一场危机到另一场危机,有时会凸显出左派更根本的生存问题。本着这种精神,《雅各宾》(Jacobin)最近一期的“基层工人”审视了我们当代更紧迫的问题之一:如何重振工人运动?
这期杂志的撰稿者们给出了大量的分析和建议。查理·波斯特(Charlie Post)指出了激进的少数派在20世纪工人运动的成功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简·麦卡利维(Jane McAlevey)呼吁“全体工人组织起来”;乔·麦卡汀(Joe McCartin)敦促工会不要浪费弗里德里希案判决(指2016年3月29号发布的弗里德里希诉加州教师协会案中,最高法院以4比4的分歧做出裁决,维持了下级法院的裁决,该裁决允许公共雇员工会评估从集体谈判和工会代表中受益的非会员的费用。这一决定是劳动人民的胜利,即使他们自己没有加入工会,他们的权利也受到强大工会的保护。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iedrichs_v._California_Teachers_Association。——译者注)与下一次攻击集体谈判权之间的短暂窗口期;萨姆·金丁(Sam Gindin)提出了“以阶级为基础的左派”作为社会运动工会主义的替代方案。
自这些文章发表以来,工人运动的危机进一步加深。右翼现在控制着联邦政府的全部三个分支和大多数州政府。继弗里德里希案之后,杰纳斯诉美国州县市雇员联合会一案已被提交到最高法院,使全国的公共部门工会受到了生死攸关的威胁。关于全国工作权法案的讨论正在蔓延。
弄清楚“怎么办”变得更加紧迫。但这里有一个“语法”问题,“怎么办?”的主语是谁?谁来做必须做的事情?
主语的缺失不仅仅是一个语法问题——它代表了左派工运的问题。激进的少数派小到忽略不计,甚至不清楚谁将负责重建工作。左派知识分子和它所谈论的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在把持左翼话语的传声人里,工人阶级的声音很少见。大多数左派理论家的文章,都是从凌驾于阶级斗争之上的知识分子的角度来写的,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之中的工人的角度来写的。
工人运动的决策者往往与自己的基层群众有着深刻的隔阂。因此,我们更多地谈论工会组织工人,而不是工人组织工会。工人被定位为自己组织的客体而不是主体。
这种疏远表现在多种方面:会员不参加会议,没有准备好或不愿意罢工,接受谈判中的妥协,并且正如最近的选举所表明的那样,对右翼候选人的支持程度令人震惊。
工人运动中的自由派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小修小补来纠正:使用社交媒体,与社区组织签订纸面上的盟约,在小范围内搞一些反对某些右翼立法的活动,以及其他类似的能保持工会结构保持不变的小战术调整。目前的情况表明,这些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没能扭转劳工的衰落。
即使这些办法行得通,也不会有多少前途。工运左翼不仅必须寻求挽救工人运动现有的组织,而且要改造它们并建立新的组织。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工人成为自己的组织和历史的主体,而不是客体。
我们为工人运动的复兴开出的处方需要新的语法。与其问“需要做什么?”,我们不如换个问题:“我应该做什么?”
事实证明,那些质疑我们的右翼分子只说对了一半:我们应该找个工作。然后我们应该做我们一直告诉工人要做的事情:在我们的工作单位里开展组织活动。
这种策略拥有悠久的历史。它的名字叫“融工”(此处原文为salting,取自电影《社会中坚》。这部电影的原英文名为Salts of the Earth, 因此salt被引申为动词,指像盐分渗入土地一样渗入工人阶级。本译文将其译为汉语中广泛使用的“融工”,指盐粒融入工人阶级大海。——译者注),它是美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基础。
社会中坚
“融工”在工人运动和左派的历史中有着深厚的根源。它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专注工业(industrial concentration)、“殖民化”(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使用的一个不伦不类的词),以及法语中的“树立(l'Établi)”,意思是在工作单位里树立自己的地位。
每个术语都反映了略有不同的实践中的同一基本思想:找到一份工作,并在工作中自觉地在工作单位内开展组织活动。
“融工”创造并维持了20世纪所有主要的工人运动涨潮。事实上,它曾经是工会活动的基础,那时它甚至没有名字——受激进意识形态指导的工人们只是在他们所在的地方组织起来,边走边建立劳工运动。
劳动骑士团和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都将其成功归功于把移民和流动工人引入激进政治,这些工人又把激进政治带入了工厂和血汗工厂。每个成员都是融工者,每个人都开展组织活动——而不仅仅是由职业活动家去开展。
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在斗争中培养了整整一代组织者,其中许多人随后加入了其他激进团体并建立了产业工会联合会(CIO)。这些战士熬过了20世纪20年代的低迷时期,保持了激进工运的种子的活力,在政治气候改变时,这些种子就生根发芽,发展成激进斗争。
多年来,各个社会主义组织中的激进工人小组一直坚守在基层,苦苦地开展组织活动,1934年的全部三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总罢工——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旧金山码头工人罢工和托莱多汽车工人罢工——都是由他们促成的。
激进的少数派催化的群众罢工导致了工人运动被体制收编,1935年通过的《全国劳动关系法》便是工人运动被体制收编的标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体制化产生了矛盾,并在几十年后引发了基层工人的新一轮斗争。
当激进的少数派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再次出现时,它不仅要面对雇主,还要面对更习惯于与企业苟且而不是对抗的工会。
就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群众行动一样,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野猫罢工浪潮(记录在《基层的造反》一书)始于激进分子将他们的政治付诸实践。这一次,不是信仰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移民,而是黑人权力活动家、校园激进分子和退伍军人,他们都是刚刚经历过越南战争和反战运动的人。
特别是在底特律,自觉的组织活动促成了群众的自发激进化。由深深扎根于该市黑人工人阶级的学生和工人激进分子创立的革命黑人工人同盟(LRBW),在工厂里、在汽车工人联合会(UAW)领导层里、以及更广泛的社会中组织起来,反对美国资本主义的种族主义等级制度。
当底特律在1967年的大暴动中燃烧的时候——这是一场工人阶级起义,当局出动了17000名士兵,发射了155576发M1子弹才把它镇压下去——革命黑人工人同盟采取了一项革命性战略,即在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激活黑人工人阶级的工业力量。融工很快成为他们武器库中的关键武器。
该组织的主要激进分子之一,杰纳罗尔·贝克(General Baker)在道奇总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后开始进行组织工作。1968年5月2日,组织工作取得了成果:四千名工人发起了野猫罢工,关闭了工厂,以应对种族主义解雇事件。该公司以更多的种族主义进行报复:贝克和其他12名工人因组织罢工而被开除。
汽车行业试图将贝克列入黑名单,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拒绝为他或他的同事辩护。但他最终以化名在福特红河工厂(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并很快成为汽车工会在该厂的分会的主席。
革命黑人工人同盟继续把工厂、医院、UPS配送中心、底特律新闻报以及全市的工人组织起来。它策划野猫罢工,挑战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不民主的、种族主义的做法,抗议警察的暴行,为一名杀死两名工头的工人赢得了无罪释放,促使该市解散了一个种族主义的镇暴警队,通过一个广受欢迎的读书俱乐部建立了一座通往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白人的桥梁,还创建了一家出版社、一家书店和一个新闻机构,并制作了一部关于他们工作的纪录片。
革命黑人工人同盟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那些在工作中开展组织活动的激进分子与激进化后组织起来的工人,两者在工厂内外有机地结合了起来。革命黑人工人同盟的成就,以及随后在20世纪70年代初掀起的全国范围内的野猫罢工浪潮,以及60年代社会运动已达到极限的看法,激励了一代激进分子转向工人阶级。
转向工人阶级
马克思主义者将底特律称为“美国的彼得格勒”。以前的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开始成群结队地来到这座城市进厂找工作,并希望帮助形成一个工人阶级主体,试图将前十年的社会运动推向革命。
这是一个全球现象。在法国,许多激进分子将1968年总罢工的失败归咎于工人和学生激进分子之间的联系太弱。少数激进分子拥护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将工业无产阶级视为卓越的革命主体,他们进入工厂,努力理解和克服工人缺乏革命动力的问题——罗贝尔·林哈特(Robert Linhart)扣人心弦的第一人称小说《装配线》(The Assembly Line,法文原名为L'Établi)中讲述了这个故事。
在意大利,1968年的造反运动持续了整整十年。数十个打着“自主”(autonomia)旗号的独立工人组织在工厂中涌现,在建立一个持久的、可以让激进少数派通过它来影响全国政治的组织这个方面,它们比其他运动都更最接近成功。
马克斯·艾尔鲍姆(Max Elbaum)讲述了美国激进分子转向工人阶级的故事。他指出,民意调查显示1971年有300万美国人支持革命,当时美国人口比今天少三分之一。这三百万人中,有一万多人组成了新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
构成这场运动的不断变化的各类组织,其成员主要来自以白人为主的前学生运动圈子和有色人种社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启发,许多团体将成员派往重工业,用各种方式推动他们的同事参加反资本主义的斗争。
根据历史学家基兰·沃尔什·泰勒(Kieran Walsh Taylor)的说法,这些激进分子取得了一些成功,特别是在支持罢工和推动改革、削弱白种工人的种族主义,以及在职场和工人运动中更广泛推动女权主义等方面。但沉重的政治包袱,使他们的骨干难以长期发挥影响力。
泰勒解释说,矿山、工厂和车间里的毛派试图鼓动他们的同事进行计划不周的战斗,更糟糕的是,他们与运动中的其他政治组织进行斗争,相互扣“修正主义”帽子,消耗了自己的政治资本。
此外,这场运动常常把模仿工人阶级的刻板印象,以及父权制下的性别分工和同性恋恐惧症理解成“无产阶级化”。男性成员应该留短发,避免反文化表达,并过上党认为的正常工人阶级生活。
讽刺的是,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发生在工人阶级越来越多地放弃传统习俗的时候。女性正在与性别歧视作斗争,LGBTQ运动正在挑战同性恋恐惧症,而激进主义总体上正在增长。
新共产主义运动未能认识到解放的政治已经发生转变,而是神化了列宁主义的正统观念——对他们来说,先锋党知道要怎么办,他们必须将这个消息传递给工人。
这种自上而下的运作模式影响了骨干的生活方式。成员经常被派去从事他们在体力或社交方面都没有做好准备的工作。有些人在繁重的劳动中竭力与来自不同阶级和种族的同事保持联系。所有这些因素都缩短了这些组织工作的寿命,并且大多数组织工作最多只坚持了几年后,然后就崩溃了。
在新共产主义运动的迅速落败中,有一个具有启发性的例外,可以告诉我们如何努力做得更好。迈克尔·施陶登迈尔(Michael Staudenmeier)在《真相与革命》(Truth and Revolution)中描述的“真理化身组织”(Sojourner Truth Organization ,STO),将他们的介入(行动)建立在对工人阶级的形成的更为动态的理解上:这种理解源自葛兰西(Gramsci)和W·E·B·迪布瓦(W.E.B.Dubois)的“双重意识”理论。
STO认为,工人对现实同时持有多种相互矛盾的理解。在他们的表述中,激进分子的任务是在消除落后思想的同时,激发工人意识中社会主义的一面。这种活动并不先于集体行动,而是在阶级斗争本身的过程中发生的。
党的任务就变成了:
“发现并阐明工人革命潜力的思想、行动和组织形式。这些模式在每一次真正的斗争过程中都在萌芽中显现出来……党的真正工作包括将这些零散的自主要素联系起来,并将它们社会化,使其成为一种新的斗争文化。”
许多STO激进分子在芝加哥的工厂里“融工”,进入了一个充满工人阶级斗争的世界。在那里,他们参加并鼓励厂内抗争,促进基层激进分子之间的联系,并提供资源,使工人能够在没有工会官僚、甚至是在遭到工会官僚敌视的情况下赢得竞选。
20世纪7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早期阶段,扼杀了吸引新共产主义激进分子的有机战斗性。理论争论——比如中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时的正确方向——当然还有个人冲突等更普通的问题,最终导致了这场衰落的运动的分裂。
在斗争高涨时期,融工者和基层造反工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仅革命黑人工人同盟的情况如此,劳动骑士团和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情况也是如此。当造反浪潮退去时——就像20世纪70年代初那样——激进的少数派最终会被孤立,成为无海可游的革命之鱼。
虽然大部分左派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经精疲力尽、分崩离析,但仍有一股激进分子成功地维持了自己的生存:他们几人是国际社会主义社(International Socialists,IS),他们的组织创立了劳工笔记计划,后来分裂为团结社(Solidarity)和国际社会主义组织(ISO)。
三十多年来,《劳工笔记》(Labor Notes)一直试图通过反对派小组(的活动)在工会内部建立基层群众的权力,由激进分子接管并改造他们的工会。基姆·穆迪(Kim Moody)的小册子《基层策略》(Rank-and-File Strategy,文件链接:http://www.solidarity-us.org/pdfs/RFS.pdf)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策略,它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有1997年“卡车司机争取民主工会”(Teamsters for aDemocratic Union)的UPS(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罢工,还有2012年由激进分子小组用类似方式组织的芝加哥教师罢工。
当第一期《劳工笔记》于1979年付印时,它的出版者根本不知道它将成为基层工人反对妥协谈判(concessionary bargaining)斗争的编年史,这些斗争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工人运动的标志。《劳工笔记》不仅是火焰的守护者,还激起了战斗性工会主义的复兴。它是对工会教育联盟(Trade Union Educational League)的现代诠释,这是一个由劳联会员组成的网络,试图“从内部改造”保守派工会,并将其转变为激进组织。
商业工会主义
《劳工笔记》帮助改变了当代的许多工会,引导了几次罢工,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商业工会自身也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的方向使得扩大战斗性少数派的任务变得复杂了。这种演变并不是预先注定的或天然的。它源于一场政治斗争——大部分左派都输掉了这场政治斗争。
20世纪30年代工人运动的重大胜利,全都源于美国各地普通工厂工人的反抗。斯托顿·林德(Staughton Lynd)的《我们都是领袖: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非主流工会主义》(We Are All Leaders: the Alternative Unionism of the Early 1930s)通过一系列详细的案例研究勾勒出了这段历史。不幸的是,这些工会建立民主、激进政治、社区联系和群众直接行动潜力所代表的道路,是美国工人运动未曾选择的道路。
1935年全国劳动关系法(NLRA)的出台,是早期斗争的一个标志。该法案规定:
“美国的政策是消除对商业自由流动造成某些实质性障碍的原因,并在这些障碍发生时通过鼓励集体谈判的实践和程序来减轻和消除它们。”
它的目标是将阶级斗争从街道(工人大军与警察大军作战)转移到办公楼和法庭,使生产能够畅通无阻地进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共产党和大多数左翼组织最初反对这个法案,认为这是将权力转移到雇主和州政府官员手中的第一步。毫不奇怪,更具官僚意识的工运领袖支持该法案的通过。
工运领袖通过同意遵守企业自由主义规则,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保持生产正常运转,在谈判桌上得到了一席之地。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称他们为“新掌权者”。但他们进入权力殿堂是有代价的。1948年,米尔斯写道:
“在目前的情况下,工运领袖的策略是通过努力将斗争体制化,缩小斗争的范围。然而,他急切地想要在法律和制度中寻求安全保障,这意味着他必须充当约束工人的角色,这是他可能拥有的任何权力的基础。他先是强调工会合同的神圣性,然后变成了由政府控制劳动关系,而在这方面他几乎没有实权。”
基层群众与领导层之间的鸿沟扩大,工会领导与企业和国家官僚的关系越来越近。
从全国劳动关系法通过到今天,工运左翼在与这些所谓的新掌权者的一系列战斗中失败,使商业工会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会费扣除条款和封闭式工厂迫使工会领导人更多地依赖与老板和政府的良好关系,而不是与自己的会员的良好关系,导致工会越来越不愿呼吁罢工。
1947年《塔夫特—哈特利法》(Taft-Hartley Act)施行后,这一趋势变得更加强烈,该法案禁止间接抵制、群众纠察、联邦竞选捐款以及政治团结和联邦政府雇员罢工。它还允许各州通过工作权立法,并要求工会领导人签署反共宣誓书。
到1950年,大多数工会已将共产党人从领导职位上清除,剥夺了工人运动急需的政治想象力。商业工会主义成为工会工会本身的代名词。
汽车工人兼学者马蒂·格劳伯曼(Marty Glauberman)在总结这一重大转变时写道:
“今天的美国工人目睹了20世纪30年代伟大的产业工会变成了今天的一党制国家。他们发现,他们为保护自己免遭歧视性解雇和晋升而努力争取得来的工龄优先权,变成了将年轻人和黑人拒之门外、阻止半熟练工人晋升到熟练工种的手段。他们看到会费扣除从一种组织工厂所有工人的手段转变为一种使工会摆脱对工人依赖的手段。
“他们看到,会员代表或工会代表变成全职工作后,事情却出了岔,这本来是想让工会代表摆脱管理层的压力的,现在却变成了摆脱工人的压力。他们看到,工会合同和申诉程序从记录工人成果的手段,变成了处分工人的手段。简而言之,他们看到工会变成了他们的对立面,从工人的代表变成了国家资本主义时代约束工人的独立力量。”
我们是这些组织的后继者,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商业工会变得更像公司了。
分工
如今,在商业工会中,职业工会领导高居等级制度的顶层,负责创建或至少维持工会的工作。就像汽车制造业或工业化的农业一样,这一过程已经受到劳动分工的影响:少数(表面上)由群众选出的官僚做出决定,而领薪的研究员和组织者从事日常工作,通常不会与他们在其中工作的群体形成任何持久的联系。
对于极其敬业和勤奋的积极分子来说,把充当工会职员作为他们的终身工作,常常会产生令人心碎的矛盾,特别是当工会领导做出的决定不符合工运积极分子的价值观时。不幸的是,作为工会的雇员,职员对工会大领导几乎没有影响力,而且由工会职员领导的成功改革的例子也很少。
虽然任何优秀的工会组织者都会告诉你,他们的任务是通过向基层工人领头人传授组织技能,而不再由他们自己来做具体的组织工作,但这些良好的意图却与工会分工的现实相矛盾。大多数工会并不会把建立工会所需的技能传授给普通会员,只是让他们定期充当集会上的人头,或是在授权卡上签名。
这些运动顶多只能让工人短暂体验到集体行动的力量,而这种力量通常会在合同斗争或政治运动结束后消退。在最坏的情况下,工人被视为组织运动的对象,而不是主体。
工人领头人的活动由那些研究人员和工会官僚安排控制,他们试图在尽量减少会员参与的情况下,找到与公司博弈的筹码。如果考虑到集体行动的难度和风险,这多少有些道理。然而,它往往会导致无原则的交易。
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国际服务业雇员工会(SEIU)向医疗行业的雇主提出一项交易,内容是禁止工人就医患比例和为患者发声这两项事务开展组织工作。在另一个案例中,它提出支持立法,防止患者因医疗事故提起诉讼。
问题不仅仅限于国际服务业雇员工会,而是系统性的。UNITE HERE帮助赌场开发商发起了伪装宣传运动,鼓吹将工人阶级社区内的赌博合法化,以此换取赌场不抵制工会的承诺(UNITE HERE是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个工会,拥有大约300,000名活跃会员。该工会的成员主要在酒店、食品服务、洗衣、仓库和赌场博彩行业工作。该工会于2004年由针线贸易、工业和纺织员工联盟(UNITE)和酒店员工和餐厅员工工会(HERE)合并而成。——译者注)。建筑工会中对工人的险恶叛卖比比皆是,其中许多工会支持诸如Keystone XL和Dakota Access(两者皆为管道修建项目名称)等生态灭绝项目。他们的领袖最近在白宫求见特朗普总统,讨论推进这些项目,同时对总统把工人阶级的其他部分推入地狱的计划保持沉默。
随着雇主越来越擅长反对工会化,一些劳工组织做出了调整,做出了政治上有利的交易来保护工会,但出卖了其成员和潜在的社区盟友。
然而,即使不从其性质、而是从其成效来看,当代的商业工会主义也很不妙。这种模式本身并不奏效:工会会员不断流失,迫使他们对这种商业模式上不断地小修小补。
修补工人运动这艘漏水之船的一些尝试包括“融工”。鉴于其根源于基层工人的激进传统,这不仅引发了人们对建立更大规模的工人运动的希望,也引发了建立左翼工人运动的希望。
例如,在过去十年中,UNITE HERE经常使用“融工者”。它招募学生——通常来自精英大学——去指定的企业找工作,协助开展组织活动。
这些运动中的一些融工者专注于在同事中培养阶级意识。然而,更常见的是,UNITE HERE使用“融工者”,主要是为了打入企业内部,找出有影响力的工人,将组织的繁重工作留给专职人员。决策的核心仍然是指挥系统的高层,劳动分工限制了工人对工会的控制。
许多报道——现在甚至有一本书——揭示了商业工会融工模式的一些问题。UNITEHERE的 “融工”故事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激进分子的故事,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将他们从一个工厂转移到另一个工厂,这限制了他们与同事建立持久联系并成为社区一部分的能力。
可以肯定的是,UNITE HERE对融工者的使用在全国各地取得了无数的组织胜利。但他们对“融工者”的功利肤浅的利用,与融工者对工作的高度投入和对同事的真正关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这些融工者为组织做出了重大牺牲,但他们的工作的影响却被以邻为壑的组织策略所削弱,这种策略常常伤害整个工人阶级。融工者在工人中建立了阶级意识,而UNITE HERE却在帮赌场游说或鼓吹给豪华酒店减税。
主导着商业工会的分工意味着,官僚和高层职员负责思考,而下层职员、普通会员和偶尔的融工者则负责行动,通常是为了妥协的目的,而且对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没有什么控制权。
如果允许融工者和工人委员会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并民主地合作,融工者就能恢复不到一个世纪前所拥有的变革力量。我们可以称这种模式为“以工人为中心”的组织。
以工人为中心的运动
开展以工人为中心的运动不仅会改变所涉及的工会会员,还会改变他们所属的工会。这跟由工会干部推动的运动不一样,工人会发现和开发自己推动变革的力量。
在以工人为中心的运动中的融工者,他们有时是研究员,有时是政策分析者,有时是律师,有时是社会工作者,有时是纠察员,有时是公关人员,有时是社区活动家,但都是组织者——致力于建立一个由同事组成的委员会,在其中学习这些技能并开展组织活动。这是我在2006年至2012年期间作为一名快餐工人和IWW成员所熟悉的模式。
2004年,IWW协助纽约市星巴克咖啡师成立了工会,受其启发,我于2006年在美国商城(Mall of America)的星巴克找到了份工作,目的是组织工会。在上大学之前和上大学期间,我就一直在一些咖啡馆工作,后来也需要找个地方工作。我决定在最艰难的地方找工作,然后尝试组建工会。
在开始与同事谈论工会之前,我与经验丰富的组织者一同参加了两天的培训。一名前工会工作者定期与我通电话,在他的支持下,我和同事在美国商城的星巴克和全市其他地点组织了一场为期两年的地下活动。从德克萨斯的沃斯堡到魁北克城,还有其他很多地方的星巴克,我们引发了新一轮争取建立工会的斗争浪潮。
后来,我在明尼阿波利斯一家拥有十家分店的吉米·约翰加盟店找了份工作,与六七个基层积极分子一起致力于建立美国第一个快餐店工会。2010年,在“争取15美元时薪(Fight for $15)”成为快餐行业工会运动的共识的几年前,我们的运动就在该市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的青年运动。
数百名年轻人参加了声援行动和其他社会活动来支持工会运动,并经常将组织的种子带入自己的商店,发起了更多运动。工会并没有出去组织工人——是工人自己在组织工会。
咖啡师、收银员和其他服务部门的员工开始主动告诉我,他们想要在自己的工作单位开展组织活动。在吉米·约翰工会选举前夕,数百名年轻人未经允许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参加了游行。我们之前曾举办过安静的家庭聚会来筹集组织资金;突然之间,我们举办了仓库狂欢活动,吸引了数百名年轻工人。
自1934年以来,人们头一次觉得在明尼阿波利斯组织工会是件很酷的事。这场小规模革命的费用约为80美元,相当于一桶廉价啤酒的价格,可以让来自不同商店的工人聚集在一起。
当然,我们并没有完全成功。明尼苏达州的低工资经济仍在。我们没有能够建立明尼苏达双子城苏维埃(Twin Cities Soviet)。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以较小的预算完成了很多工作。那么,要从这个例子出发,上升到重振工人运动,又该怎么做呢?
尽管资金肯定会有所帮助(拜托,工人阶级想要更多的啤酒),但真正的限制因素是人。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愿意花几年时间在工作单位里组织工会,成为社区的积极成员,并尝试新的工人组织形式,直到找到有效的方法——就像掀起20世纪30年代热潮的激进分子所做的那样。
即便只有一些像这样的运动在大城市兴起,也能改变劳工运动。在明尼阿波利斯,几个融工分子发起了一场运动,几个月来一直占据当地新闻头条,激励了数十名工人开始新的组织运动,并让人们重新意识到“工人可以组织自己的工会”。想象一下,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其他五个、十个或二十个城市,又会怎么样呢?
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的经验可以为更大、更主流的组织提供借鉴。对于商业工会来说,钱似乎确实是限制因素。2012年,“争取15美元时薪”和“我们的沃尔玛”这两个运动,似乎表明主流工人运动终于超越了以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为中心的工会运动的过时形式,找到了能够与最受剥削的工人建立联系的策略。
此后的四年里,“争取15美元时薪”通过政策改革取得了非常显着的工资增长,但它未能在快餐业建立战斗性的工会。请记住,最初的要求是时薪15美元和建立工会。“我们的沃尔玛”运动确实在普通员工中建立了基础,但其上层工会在一场短视的官僚内讧中削减了资金,迫使组织者去寻求其他收入来源。
随着工会组织率下降到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成立前的水平,以及工作权立法蚕食劳工金库,主流工会将需要寻找新的组织方式。
如果工会失去了法律实体地位,并且无法再为由干部推动的组织提供资金,那么“融工”可能是把尚未参加工会的工人组织起来的最佳选择。向无工会的单位“融工”的转变将有助于发展一种敌后斗争文化,从而产生新的运动。
融工还可以帮助解决已有工会的工作单位中工人运动的权力危机。正如乔·麦卡汀(Joe McCartin)所写,在已有工会的工作单位内开展组织活动,并复兴直接行动的战斗精神以促进共同利益,是扭转对公共部门工会的攻击的最佳方式。护士工会可以领导争取全民医保的斗争,建筑工会可以领导争取绿色能源和公共住房的斗争,教师工会可以领导争取高质量公共教育的斗争,运输和汽车工人可以领导争取新的公共交通系统的斗争,等等。
但在许多情况下,工人有工会但没有组织起来。为了重建团结和战斗精神,使这些代表阶级的更广泛需求的运动成为可能,工会可以培养当前或未来的会员成为普通组织者——实际上也就是去已经建立了主流工会的工作单位“融工”。
历史经验表明,融工对工人运动最伟大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从20世纪30年代的突破,到70年代的基层工人造反运动,到80年代《劳工笔记》激发的改革斗争,再到今天各种独立的和由工会领导的、充满活力的组织斗争。但问题仍然存在——谁来做必须做的事情?
成为一个工人阶级的英雄是值得的
选举日以来,我国正在坠入反乌托邦的现实,震惊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他们在震惊之余涌入了左翼组织。他们来寻找“我应该做什么?”这个长久以来的问题的答案。
反特朗普运动越来越多地转向经济形式的直接行动:妇女罢工、出租车罢工、杂货店罢工、科技工作者罢工,现在还呼吁举行总罢工。如果在生产环节没有大规模的组织,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为了扩大胜利,我们得让自己的政治活动发挥作用。
对去年转向社会主义的数千人来说,转向工作单位是合乎逻辑的一步。融工为激进行动提供了一个有意义且容易进入的切入点,因为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必须出卖劳动力为生。千禧一代尤其正在经历历史性的低谷。可能不是我们去找阶级斗争,而是阶级斗争来找我们了。
通过在工作单位里真正地接触工人,“融工”可以帮助克服左翼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与在工会或者非政府机构找个工作不同,也与在业余时间做活动家或者成为学者不同,以工人为中心开展组织工作,这种方式可以迅速融入工人群众,而且不依赖官僚机构的薪水——这些官僚机构在接下来的几年就有可能被拉拢收买或者被破坏。
虽然支持“融工”是工会的基本共识,但目前的那帮工会头头可能愿意也可能不愿意这样做,特别是因为被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已经在采取行动将其定为非法。
工运左翼必须带头这样干。我们应该协调我们的行动,把力量集中在关键雇主和部门,并从事能够促进运动建设的工作,最好是在我们已经工作的领域内,以尽量减少“组织者”和“被组织者”之间的距离。或者成为工人阶级的英雄,在工人组织可以产生巨大影响的领域寻找工作,比如物流。
如果它成为现实,大规模转向“融工”可能会通过将工人置于中心来改变劳工运动和左派。“融工”是激进工人运动的开始,这也是一切可以重新开始的地方。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告诉工人们是时候组织起来了。现在,工运左翼需要听取它自己的建议。我们知道要做什么。所以,找份儿工作,让我们开始干活吧。
原文:https://jacobin.com/2017/02/labor-unions-workers-salts-students-organiz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