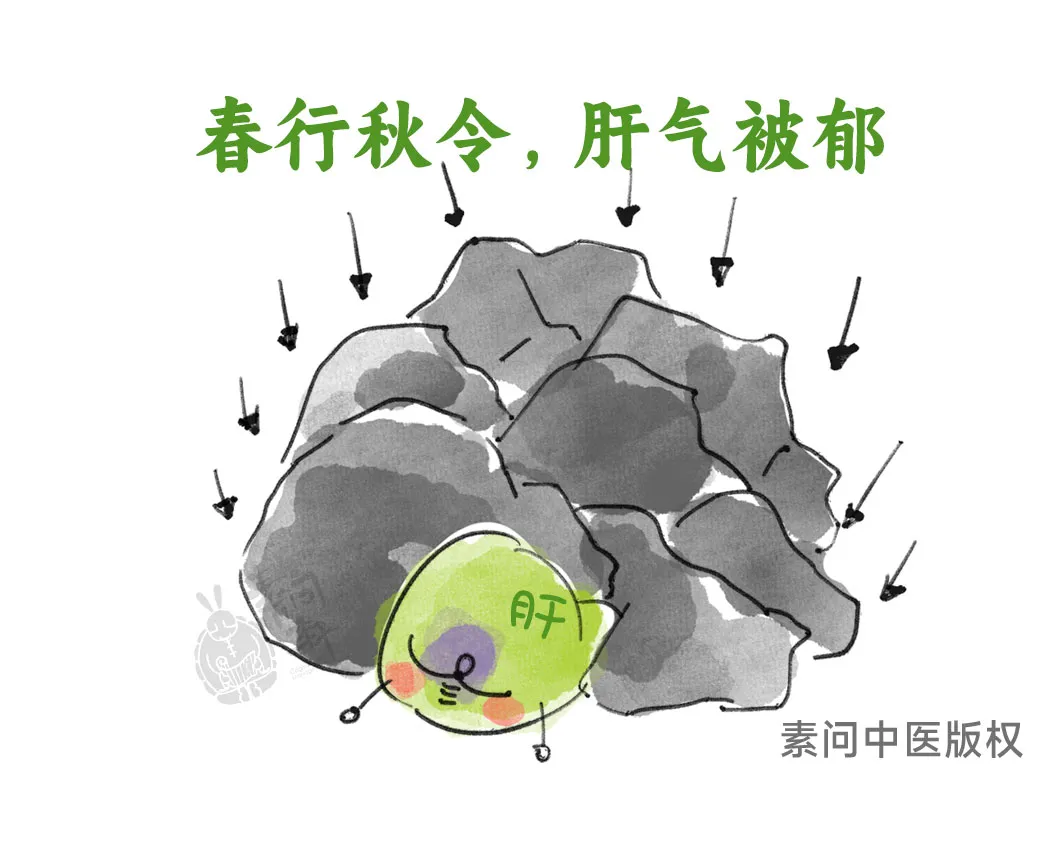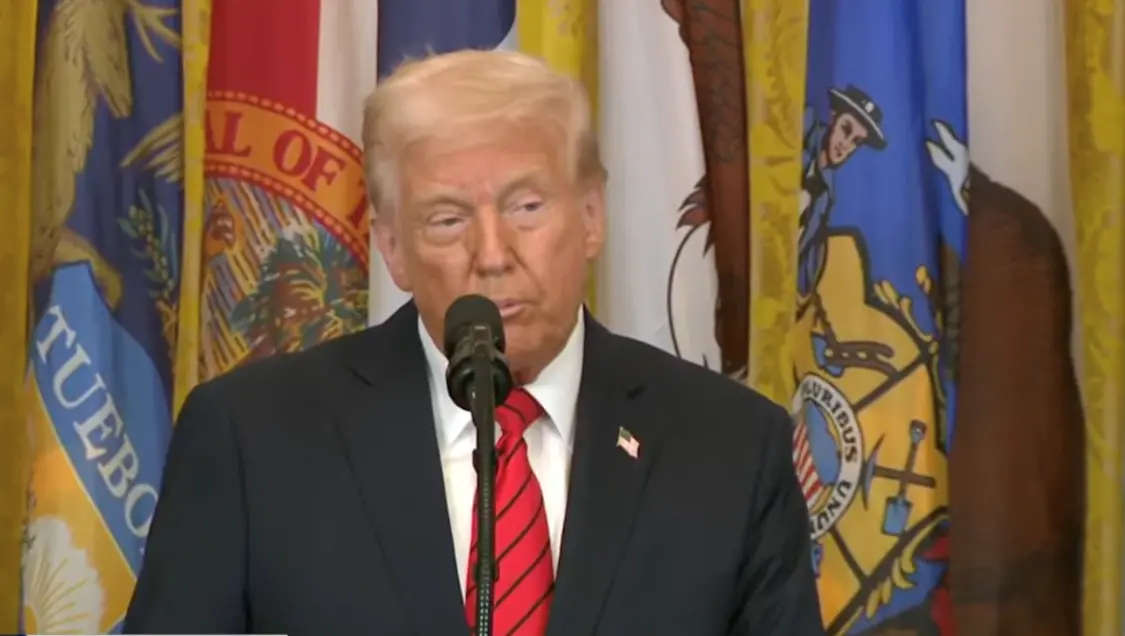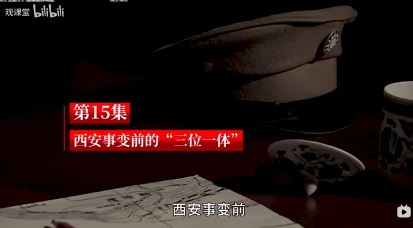严海蓉:对劳动者的话语规训,从来都不曾少过
原编者按
在中国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打工者”是极为重要的劳动主体。但城乡阶层的差异,导致这一群体成为被市场和资本征用、规训的主力军,产生了大量诸如“素质”“自我发展”等主体想象的话语。在余秀华、范雨素等人的故事逐渐深入人心的今天,这篇旧文,对进入打工者们的精神世界,仍然是一道门。
我有种感觉:我不能像过去那样。我有一种……自觉的……想改变自己的感觉。因为在这之前吧,在别人家,我们老乡跟老乡都知道,买菜,一毛,我说一毛五;回来记账就贪污。跟她们这么学,好像都习惯了。反正那时候那个“素质”吧,你不觉得可耻,反而觉得应该。
——访谈打工妹小华(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打工妹面临着许多困难,但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小华对一群打工妹如是说(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七日)
为什么小华,一位来京多年的打工妹,有这样的自觉,这样的改变自己素质的欲望,使得她自愿摈弃人类学者近年来津津乐道的“日常抵抗”活动?随着司科特(J.Scott)《弱者的武器》的出版,“日常抵抗”成为许多西方左翼研究者们寻求和肯定弱势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反抗性和能动性的重要领域。小华的转变却引导我探索我们当前的社会话语情境,正是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语境使得小华认定她和同乡们的做法是缺乏“素质”的表现。

《弱者的武器》书影(来源:douban.com)
“自我发展”作为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话语,致力于塑造一种新的、按照市场和发展主义的逻辑塑造自己的打工劳动主体。这种新的理想劳动主体,以高“素质”为标志,与市场有着共生的关系。新的打工主体在市场上交换她们的劳动的同时,她们也被激发着在劳动过程中,在她们的市场经历中,为“自我发展”创造“素质”,使她们自己可以成为具有高素质的现代性的主体。当今市场的话语告诉我们,“素质”可以像古典剩余价值一样,进入市场流通。当小华和其他打工妹一样为不被时代抛弃,不至于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而奋斗挣扎,而致力于自我发展的同时,在她们与“自我发展”的话语之间又存在着一种紧张。这种紧张来源于话语自身内在的矛盾。打工妹从内部体会这种紧张给予她们的痛苦和挫折,因为这种矛盾使她们不能把自己塑造成为“发展”所需要的现代性主体。

电影《特区打工妹》剧照(来源:douban.com)
国内众多的媒体报道告诉我们打工群体的进步:八十年代他们出来是求“生存”,九十年代他们出来是求“发展”。隐含在对这一进步的欢呼里的是马尔萨斯式的对“生存”仅仅作为体质上存活的一种厌恶,因为这种“生存”被界定在“发展”之外,仿佛仅仅服从自然的生命周期,从始点到终点,缺乏一种现代性的自我意识,收获最好的时候也只是个零,而在最坏的时候,这种没有目的的“生存”消耗了资源,阻碍了民族的发展。这种对“生存”的认定来自于“发展”话语领导权。“发展”把“生存”界定为自己的对立面,从而确定自己才是领导历史潮流的权威。
一九九六年国内一家刊物发表过一篇题为《无为:保姆效应》的文章,讲述了安徽无为县的农村姑娘们在北京从保姆到企业家的经历。伴随这种戏剧性的社会地位的变化的,是她们整个人的变化:“进城不久,这些灵慧勤劳的姑娘经过锻炼,很快成为城乡文化结合的一代新人,她们走出乡村田野时,带着一身土气和力气,当她们归来时,不仅带回了资金、信息、技术和市场,还带回了新思想、新观念和家乡人所不具备的开拓市场经济的本领。”文章告诉读者,无为姑娘的经验给出一个启示:“外部世界天宽地阔,走出狭窄的田野就能改变一切,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要依靠自己去创业,去奋斗。”与改革前外出做保姆的“求生”型妇女相比,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姑娘们从只有“力气”可卖的廉价劳动力变成了开拓市场的新企业家。

电影《黄山来的姑娘》剧照。20世纪80年代,无为曾被称为“保姆之乡”。据说无为当时约有5.5万妇女在北京等地当保姆。这部电影说的就是无为小保姆的故事(来源:douban.com)
在知识精英的话语中,市场和资本成为历史的生力军,使国民经济起死回生,焕发精神,并成功地改造着中国劳动大众的“素质”。市场和资本不再是意识形态中的反角,而成为非意识形态的中性催化剂。前述文章描述打工妹在市场的劳动交换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打工妹们除了以劳动换取工资以外,她们的劳动还会创造令人羡慕的剩余价值:她们提高了自身的素质。市场从姑娘们那儿买了力气,姑娘们得到了市场的训练和磨炼。这种训练使她们变成具有现代性的主体——自觉接受纪律支配的工人,或楚楚动人的白领小姐,或最理想的现代主体:能掌控市场和资本的企业家。从打工妹到企业家,成功的要领在于她把市场对她的培训再作用于市场。由此,她在初始的劳动过程中创造的“素质”进入市场流通,“素质”的积累最终使打工妹变成具有信息和资本的企业家。
在一篇以《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九九七)为题的书中,作者庆贺中国从落后的生产力进步到比较先进的生产力,从“阶级”进步到“阶层”。“阶层”突出社会地位的流动性,社会群体之间和谐的共存性和文明性——这一切都建立在繁复的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之上。在作者的笔下,“阶级意识”是“人类的一种初级意识,反应敏感,逻辑单纯,导致暴烈而孤注一掷的行动”。“阶级意识”与历史上中国农民暴动相联系。作者的分析隐指“农民”与“暴动”的某种天然联系:似乎“暴动”所带有的暴力和体力的成分漫溢到“农民”这一符号中,而“农民”这一符号被赋予的“原始性”也带出了“阶级斗争”的“原始性”。于是,阶级不仅意指一种社会对立,也包含了令人惊心的、与农民饥饿的身体寻求生存相关联的暴力的幽灵。原始的、暴力的,与生存相联系的“阶级”应该为先进的、文明的、与“发展”相联系的“阶层”所取代。更有甚者,“阶级”还将进一步被“自我发展”的话语所取代:社会对立被重新安置于一个个体的意识内部——最大的敌人不再存在于外部,而被移置于个体的意识内部。结果是小华的话:“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书影(来源:douban.com)
一九九八年,深圳安子的故事出现在全国的媒体上。安子,从打工妹到总经理,从千万个打工妹中脱颖而出,成为模范。安子的故事成为打工妹成功的寓言故事在电视台播出。安子自己荣幸地被列为一九九八年“改革开放二十年二十人”之一——二十人中两位女性之一。安子在二十人中出现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因为把她作为改革的荣誉人物标志着发展对于新的劳动主体的召唤。
“打工者”并不孤立于九十年代的发展话语中。她们的出现伴随着城市下岗工人在精英的眼中日益成为依恋和依赖计划时代社会福利的不灵活的群体。罗莉莎(L.Rotel)在对一家国营纺织企业工人研究后指出:如果改革前这些纱厂女工被认为是社会进步的英雄的话,她们现在却被认为是代表了“一种内在缺失,其可能阻碍中国达到现代性,因为她们本身的存在就是把过去带到了现在”。
这种对城市工人的他者化,特别是对城市下岗工人的他者化,使他们被界定为发展必须克服的障碍。资本的灵活积累所需要的劳动力是来自农村的年轻打工男女,给予某个“代表人物”的荣誉和报刊上的颂扬无非是一个姿态。国内的和跨国的企业,每年吸纳数以千万计的打工男女进入几乎毫无保障的工厂或作坊。每年都有数以万计受伤的、病倒的、累垮的身体被扔回农村。农村成了为各种资本迅速、灵活、原始地积累而吸收和释放劳动力的蓄水池。在外出打工普遍的地区,家庭责任田成了最后的福利依靠和劳动力再生产的微薄的物质条件。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农村经济改革本来是为了刺激农业生产,但在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的“接轨”和“全球化”进程下,生产责任田变成了福利田。如寒丁所指出:“现代史展开给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在今天,农村再一次成为“大后方”,不过这一次是为市场革命和前线资本的灵活积累提供无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希望通过市场和跨国资本的催化使中国与世界接轨的欲望使得精英们“通过折射国际资本的价值观来对本国的劳动力质量进行审视,把中国的劳动力看成是低于现代标准的、廉价的、没有劳动纪律的劳动力”。今天在许多城市我们都可以通过巨大的条幅感受到这样的价值观:一个城市人口的文明程度和城市形象直接与资本在本地登陆的可能性(投资环境)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全球资本价值观直接深入到我们的“素质”和“文明”话语的核心,也通过“素质”话语积极地参与了在新的市场条件下对国民的管理。在北京有很长一段时间,城市地铁的高音喇叭时刻谆谆教导每天成千上万的乘客们如何做一个“文明的现代人”,从不要拥挤到不要跷二郎腿。提高全民人口的“素质”和“文明”程度成为新的管制目标,也同时成为精英们可以施展精力和权威的用武之地。我在南方一个小城市的大道上看到的标语一语道破天机:“处处是城市形象,人人是投资环境。”

2015年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细说责任田》,作者陆德生,是关于责任田制度从酝酿到推行的“第一手资料”(来源:item.jd.com)
当然,市场的训练和磨炼并不一定能在来自农村的打工妹中产生市场和发展所需要的素质。这样的市场过程也不能自动地把打工妹群体变成一个个安子。警示寓言和花边新闻常常见诸媒体,讲述打工妹的成功和堕落。“自我发展”的道路似乎像唐僧取经一样充满诱惑和挫折,只有那些不畏艰难的人才有可能达到那光明的境界。
在她们登上追求“素质”的道路之前她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什么样的自我认识呢?小华们要接受某种自我认识才能使她们渴望自我的改变,开始一个自我的改造,把自我既当成改造的主体,也当成改造的客体。因为改变自我成了小华们的欲望,这种改造,这种自我的生产过程似乎是来自题目自身的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却是把含有全球资本价值观的“素质”话语内在化,使得小华通过这一话语审视自己,把自己看成亟待改造的对象,自己是“最大的敌人”。这样,小华的能动性把矛头指向自己,要求自我的改造,而不是向外要求社会的改造。可能出现的“阶级”意识和对社会改造的要求暂时被置换了。在九十年代,打工妹们被召唤做发展的主体,但同时她们生活在发展的边缘,随时可能沦为被抛弃的多余人。在当今发展话语为她们决定的现实中,“边缘”和“多余”已写进打工妹们的自我意识之中,成为鞭策自己自我发展的动力。一位打工十七年的打工妹对我说:“我们就怕被社会抛弃。”

《论再生产》书影。阿尔都塞著名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从这部重要手稿中抽取的片段组合而成,整合了主体建构、劳动力的再生产与国家机器等概念(来源:douban.com)
正是在她们“自我发展”的奋斗中,打工妹们强烈地体会到她们被困置在长期的挣扎之中,极少有可能成为发展的主体。小华从意识到自己素质不足的时刻起就把“我”从“我们”(她和她的同乡们)中剥离出来。但是在她以下的叙述中,阶级的幽灵似乎又不期然出现了,把小华掷向她意欲离开的“我们”。小华的“自我”从“我们”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自我”和雇主、同乡们的三角关系:
我刚出来的时候给人家看孩子,当时十七岁。夫妇俩对我挺好,希望我对他们孩子好。那孩子刚一岁多。他们家原来有一个阿姨,刚离开,因为别人家给的工资高一点儿,她就走了,但离那儿还是很近。然后我看孩子的时候她(老乡)就老来——那两口上班以后家里只有我一个,因为我跟她是老乡啊,好像就是老乡跟老乡之间“窜”那种。她跟我说这两口怎么怎么不好,两面三刀,可是,然后(她自己)又给那孩子织毛衣,当那父母的面做人情。我觉得她挺不好,不想跟她这种人打交道。我就跟那孩子的父母说,我说,她说你们不好——当然我那时也是小孩子啊。他们就好像一下子看清她的面目似的。他们就觉得我挺好,我跟她们不一样,不跟她们窜。孩子的父母就对我挺好。那几个人呢(老乡),因为我不跟她们来往,就特生气。我出去,她们还堵着我,不让我走。有时候看见我好像还骂我。实际上,我也没跟她们吵。因为我不愿跟她们为伍,她们就特生气。所以这样一来,她们好像跟我对立,小孩儿的父母好像跟我站在一边了。所以,这样一来好像我跟他们(小孩儿父母)更紧密似的……从此以后我就跟她们断了,就整天围着那孩子了,整天给他写卡片,教他认字。
“窜”是城市雇主常用的一个动词,“窜”不仅指相互走访的行为,而且隐射这种行为是偷偷摸摸的,或是过度的,可能超出了礼仪或道德的界限。雇主们常常在背后皱眉头或直接不允许打工妹之间在雇主家相互走访。打工妹们常常不得不在雇主不在家的时候见面或在别处相聚。在大多数城市雇主的眼里,打工妹(保姆)之间的“窜”是他们最头疼的事之一:“窜”被看作没有素质,没有自律性,不能洁身自爱的表现。隐伏在这烦恼之中的是一个担心:打工妹在一起会相互攀比工资的多少,工作条件的好坏和传播有关雇主的家长里短。城市家庭所渴求的私密性因为保姆的存在而变得可渗可漏,因为保姆是在家庭和市场之间、内和外之间流动的角色。当市场关系和意识渗入社会每一个层面而使家庭日益被期望成为稳定、安全和亲密的避风港的时候,雇主们担心他们的保姆因为参与“窜”而成为一个不满的、离心的角色。通过引用“窜”来描述她的老乡,小华向她的雇主和老乡们表明她的立场和意识,把自己和老乡们区别开来。信号的发出引发了雇主、小华和老乡们三方面的相互关系和行为的调整。小华对于话语呼唤的应答并不是一场独角戏,而是依赖于上述三方的反应和互动来进行小华的建立一个与“我们”不同的“自我”,一个追求“素质”的过程。
小华对自己低素质的认知和她改变自己的决心在一年以后当她到一位作家家里工作时得以实践:
可到了作家家里,我从内心崇敬和仰慕作家,觉得作家很神圣,自己不能让他们看不起。作家夫人第一次跟我结完买菜账,还余下一分钱。我们相视而笑。这以后,她再也没有跟我结过账,非常信任我。被人信任的感觉真好!这个时候,我才慢慢体会到人活着,有一个“人格”这东西。我欣赏着新的自我。虽然后来离开了作家的家,不管别人是否信任我,我都不再会贪污了。因为我的自我注视着我自己,我不能干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事。
小华的“自我”出现在她到作家家里后,“自己不能让他们看不起”开始,过渡到后来“我不能干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事”。在这一过程中,外在的、“他们”的审视眼光内在化了,成为内在的、来自于新的“自我”对自己的审视。小华新的“自我”的出现把这一审视——通过作家夫人的眼光——进一步带进她个人的主体意识之中。当小华和作家夫人在第一次结完账后“相视一笑”,她们间目光的相聚和微笑是欲望和纪律的相聚和相互认同。具体来说,作家夫人,在此代表纪律的审视,承认小华是一个有“素质”的、值得信赖的打工妹。而小华从被承认中得到快乐,因为她改变自我的欲望在承认中得到了满足。当小华和作家夫人相视而笑时,(小华的)欲望和(作家夫人对小华的)纪律得到了相互认同和统一。她们的相视一笑对后来雇主给予小华的信任以及小华“自我”的出现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小华的新的“自我”的诞生在她的“本我”(ego)中引进了现实原则。(这一过程类似拉康对一个孩童的“我”的形成过程中的“镜像阶段”的心理分析。)作家夫人的目光和微笑向小华反射出小华想追求和认同的一个镜像,使她欣喜地与这一形象认同。这相视一笑的时刻对小华新的理想“自我”的出现具有关键意义。她欣赏新的“自我”仿佛欣赏一件艺术品。这当然不是要用这一“自我”的形成来说明小华与一个孩童相当,而是想说明,我们意识中理想“自我”的形成其实是一个不断的社会过程,而并不止于孩童时期。我同时还想说明小华的想像、欲望和对这一“自我”的喜悦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与具体条件下“自我发展”和“素质”话语息息相关。在这一过程中,起先“现实原则”由作家夫人的审视目光所代表,到后来就直接来自于小华的理想“自我”。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现实原则是对快乐和欲望的压制和束缚。但在小华的叙述中,现实原则和欲望跳起了双人舞,在相互认同中仿佛融为一体。“素质”话语在小华的意识中激发对“素质”的欲望,这一欲望在作家夫人对她的“素质”的肯定中得到满足,与此同时,作家夫人作为审视者的权威得到了肯定和强化。

冰山比喻与弗洛伊德所说的精神之间的关系(来源:wikipedia.org)
然而这一不平等的和谐好景不长。不久,小华就陷入了痛苦。她与理想自我的喜悦的认同被粗暴地中断了。作家夫人的微笑仍然伴随着这一过程:
离开作家的家,是因为他们家的活太多。我整天忙碌,像个干活机器,一天下来,精疲力尽。我提出想走,作家夫人要求我等他们找好了接替的人再走。一个星期后,作家夫人告诉我,新的保姆已经找好了,要我当天离开。我在等他们找新的保姆的时候,自己却傻傻地干活,到头来,自己被撵,还没个落脚之地。作家夫人的脸上,那一贯的慈祥微笑,让我感到心头冰冷!临走时,她说要检查一下行李。她说这是规矩,谁走了,都要检查的。她是怕我偷他们家的书。我心里不愿意,嘴上却答应了。我是多么恨自己的懦弱啊!为什么不敢说“不!”多年以来,我为自己感到可悲!我们这些从农村走出来的姑娘,穷,无知,自卑太深了!我们渴望社会的尊重,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站起来,又指望谁?我们这些当保姆的女孩比那些卖菜的,在餐馆打工的和商场卖东西的,有着更深的体会。我们进入社会的基本细胞里面,城乡之间的文明和愚昧,人与人之间的美好与丑恶,毫无掩饰,直接冲撞,从冲撞到融合,是个痛苦的,觉醒的过程。
在这里,一个幽灵出现了——小华发现自己成了“干活机器”。在我初读时,发现“我像个干活机器”似乎有些别扭,因为“干活机器”是个重复表达——机器当然是干活的,有必要说“干活机器”吗?然而,这一看似奇怪的比喻又不能轻易地被如此理性地化解掉。在由“像”联系的比喻中,干活被重复地表达,而在这一奇怪的不平衡的比喻中,身体和精神在过度繁重的劳动中消失了。当力气和意识如此消损,以至于消失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成了无意识的机械的“干活机器”。小华干不下去了,因为当精神和意识难以存在时,“自我发展”的基础在哪里呢?那慈祥的微笑曾经提供给小华她欲望中的镜像,给她带来新生“自我”的喜悦,现在这同样的微笑却使小华感到“心头冰冷”。小华所感到讽刺的是,前后似乎两种截然不同的功能居然由同样慈祥的微笑体现出来。小华可以认出这微笑,她在第二次微笑中看到上一次微笑的影子,也开始从这一次微笑中重新体会第一次微笑的含义。从对小华的吸引到对小华的排斥,这两次微笑互为伴侣,从属于同一关系原则。在这两次微笑中,小华的“自我发展”被摔出了轨道,给她以难以忘却的创伤,多年来不能释怀,为自己感到可悲。这最后一次微笑和行李检查把小华抛回了她的阶级群体——照作家夫人的话说,这是(对保姆的)规矩。小华在她痛苦的反省中,把自己和打工妹群体联系在一起。但是,小华的叙述中所指的“觉醒”是什么,小华并没有说清楚。她所用的反省的语言谈及“文明”“愚昧”“美好”“丑陋”和“人与人”,类似流行的启蒙式的话语。但是从上文看来,她并没有把城市与“文明”“美好”,乡村与“愚昧”“丑陋”划上等号,而是把文明与愚昧,美好与丑陋置于城乡之间、人与人之间。从与老乡在一起,到拒绝与老乡来往,到呼唤“打工妹”群体,小华做了一个从“我们”——离开“我们”——再到“我们”的辩证的回归。小华的这一回归并不只是回到原来以家乡为纽带的老乡群体,而是把自己置身于“我们”从农村走出来的打工妹群体。现在,打工妹们是勇敢地走出来了,但小华的经历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她们勇敢地走出来以后,发生了什么?近一个世纪了,鲁迅对娜拉出走玩偶之家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的时空中再次回荡。
(James C.Scott,Weapons of the Wea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Lisa Rofel,Other Modernit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William Hinton, 1998, “The Importance of Land Reform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Monthly Reviews50, No.3:147-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