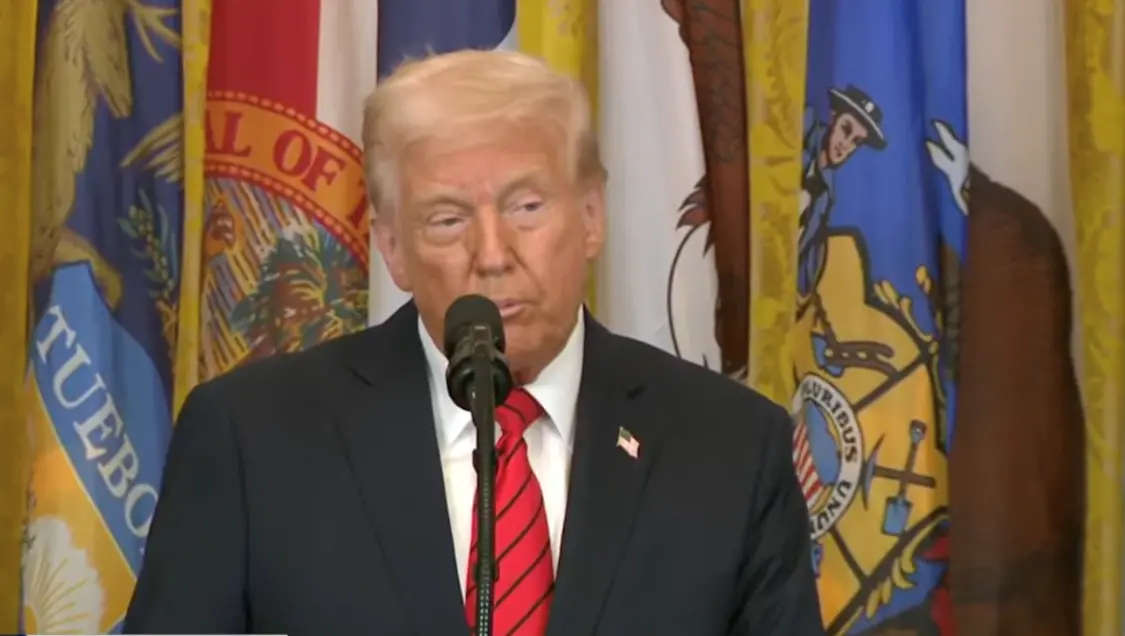严海蓉:今天,我们如何定义“农民”?——关于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讨论

当提到“农民”,你会想到什么?或许是稻浪翻滚中洋溢着丰收喜悦的笑脸,或许是西装革履大谈“科技”“创新”的农业企业家,或许是网络平台“分享生活 ”“带货”的博主,也许是忘不了因农产品滞销而布满辛酸的面容……“农民”一词的内涵已不再单一。
经营成百上千亩土地的“农民”企业家恐怕难与老人留守农业、躬耕数亩的“农户”家庭共情。当讨论“三农”时,应当考虑到农民内部的这种分化,以及宏观的社会背景,再去思考“农业发展道路”应去哪里、能去哪里?
如何定义当下中国农业的性质?小农户经营农业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是什么?该选择怎样的农业发展道路?《开放时代》2015年第5期“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专题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文是该专题的导言,本号会陆续推出与该专题相关的文章,敬请关注交流。
作者 | 严海蓉,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社会学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农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迁。在2012年《开放时代》第3期,黄宗智教授组织了“中国新时代的小农经济”专题【编者注:具体内容见今日第二篇推文】,并在专题导言中提出了关于理解中国农业转型的两个关键问题(黄宗智,2012)。
第一个是:“隐性农业革命的生产主体到底将是资本主义型的雇工大农场,还是小家庭农场?”
对此,黄宗智、高原、彭玉生提出了一个论点,认为中国农业正在经历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
第二个是:“新时代的家庭小农场面对的主要经济问题是什么样的?”
对此,黄宗智提出了第二个论点,即小农所面临的挤压主要在流通领域,不在生产领域,“他们大多受到商业资本的摆布,在流通过程中丧失相当部分自己所可能得到的利益”。
本期专题再次提出如何理解农业转型的问题,与2012年的专题形成对话和争鸣。这期专题中,黄宗智和贺雪峰基本上承接了2012年专题的中心论点,认为中国农业仍然以小农或小规模经营为主体,小农经济不仅具有价值上和功能上的合理性,而且在现实中有着顽强的生命力(黄宗智,2015;贺雪峰,2015a)。贺雪峰称这样的观点为小农经济派(贺雪峰,2015b)。这两位学者激烈批评了以龙头企业引领规模化农业的政策导向,提出了以小农为主体的农业现代化路径,并各自提出如何使小农与社会化生产对接的政策建议。
另外四篇文章通过宏观数据和案例分析,认为中国农业资本化已经开启了农业资本主义道路,资本积累的动力和农村的社会分化同时伴随着中国农业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小农虽然数量仍然庞大,但是在丧失主体性,开始直接地或间接地隶属于资本化农业(严海蓉、陈义媛,2015;孙新华,2015;陈航英,2015;黄瑜,2015)。
以小农经济的主体性为出发点,黄宗智认为今天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需要建设小农场+合作社的一体化体系,而建设这样的合作化体系则需要走出崇尚农民自发性合作和崇尚规模经营这两个误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农民合作体系发挥了政府的扶持功能,避免了英美大而粗的规模化经营,从而建立了小而精的东亚合作化模式。今天中国是否有条件来建设这样的体系?
黄宗智认为,尽管公益性合作社的发展在中国面临着“十分强大的制度性障碍:国家全力招商引资,偏向资本主义企业和大户,偏向借助个体逐利的激励机制来促进经济发展”,但中国具有“比战前日本农政更完全、更有力的农政体系”来实践日本二战后的合作化改革。在他看来,这样的农民合作化道路不仅是“农政民主化”,而且可以成为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的突破口。
然而事实是,今天日本也在失去维持合作体系的条件。资本主导的逆向土改正在席卷亚洲各国的小农,侵吞他们在20世纪前半叶通过斗争获得的果实。在亚洲许多国家,小农正在被资本化农业所驱逐,土地再次呈现加速集中的趋势。
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在2003年至2013年间,规模农场增加了54%,种植园增加了19%,而小农数量减少了16%。日本也不例外,自2000年以来,日本农民的数量下降了40%,而农业生产公司的数量翻了一倍,达到14333个(GRAIN,2015)。
如果中国实践日本战后的合作化模式,那么问题的关键是:
黄宗智指出的“十分强大的制度性障碍”如何克服?
除了国家招商引资等行为是制度性障碍,资本主义企业、大户的行为和利益诉求是否也是发展公益性农民合作社的资本障碍?
中国今天的农业转型有哪些推动力?能否提供日本当年合作化的条件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深入探讨2012年专题提出的问题。
作为小农经济派的代表人物,贺雪峰对中国农业有一个基本判断,即今天中国农业的主要矛盾是小农户难以与社会化大生产对接。面临这一矛盾,如果说黄宗智倡导的是东亚模式的合作社,以此解决农户与市场的对接问题,那么贺雪峰倡导的是国家支持基本农业设施的改善、村社统筹共同生产事务。
与黄宗智对经济和治理民主化的关怀有所不同,贺雪峰以世界体系的基本逻辑和结构作为必须接受的前提,把中国当前的发展总目标设定为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此为本;三农的价值、功能和定位在于为总目标服务,此为末。在这一本末关系框架中,贺雪峰提出了三农的底线功能,即保障粮食安全、提供农业就业、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农村稳定器。
在三大底线功能中,贺雪峰认为“稳定器”的功能最为重要,是否服务于这一功能因此成为衡量农业现代化成败的方针,成为评价政府政策的指南。他认为推动强富美的农业现代化政策是本末倒置,因为国家扶持农业规模经济主体的方法恰恰有悖于三农作为“稳定器”和蓄水池的功能,而农村自由经济和市场内生的农民分化则与三农的“稳定器”功能并行不悖。
对于2012年专题导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本期另外四篇文章显示了中国农业的资本化伴随着无产化的趋势。针对当今中国农业资本化的讨论,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引入了列宁-恰亚诺夫的争论,计算出中国农业雇工比例约为3%,因此认为中国的农业资本化没有伴随无产化,中国农业转型符合恰亚诺夫的命题。严海蓉、陈义媛、孙新华计算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的雇工比例远远高于3%。他们关于中国农业资本化性质的分析没有局限于农业雇工。
农业雇工虽然是讨论农业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维度,但不是唯一维度。
黄宗智等似乎把农业资本主义等同于使用农业雇工的大农场,把农户经营等同于非资本主义,然而本期另外四篇文章认为小农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并不形成各自独立的平行体系,并不分别代表非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
农业资本主义是一个体系性的存在,在农业资本化的过程中,无论是资本化的大农场,还是普通小农户,都动态地存在于同一个生产关系里面,相互关联。
当然,毫无疑问的是,小农户和资本化主体在这一体系中处于不同的位置。农业资本化一方面把越来越多的小农排挤出农业,同时也使未被挤出的小农吸附到农业资本的产业链条上。
在此背景下,小农家庭经营的存在本身既不足以说明农业的非资本主义化,也不构成另类的道路。
从列宁关于农业资本化道路的论述延伸出来,严海蓉、陈义媛(2015)认为中国农业资本化既存在着自下而上的动力,即通过农民分化产生的资本化经营主体,如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外出包地农场主,甚至一些地方龙头企业,也存在着自上而下的动力,即资本下乡,还存在着上下并举的动力,即国家资本通过支农政策下乡与农村大户精英的资本结合,加速推动规模化和资本积累。
从改革初期到90年代中后期的二十年间,中央主要通过鼓励农民分化来推动自下而上的资本化。最近十来年,中央和地方一方面继续支持自下而上的资本化,鼓励种养专业大户、合作社,一方面开始支持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如鼓励龙头企业跨区运作、企业集群建立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
贺雪峰(2013)认为小农立场即国家立场,然而,严海蓉、陈义媛的研究表明,国家立场并非小农立场,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鼓励农民分化,推动农业“去小农化”。
孙新华(2015)以一个农业乡镇为调研点研究农业转型,具体回应了2012年专题导言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他把河镇农民分化分为两个阶段,2007年前是“有分化未突破”的量变阶段,以中农和小农的分化为主,2007年后随着政府积极推动农业转型,分化进入资本化主体兴起的质变阶段。
资本化主体的兴起以土地集中和农业雇工的存在为条件,政府帮助创造的正是土地集中这一条件。随着土地从小农和部分中农中流出,他们需要通过农业务工来补充自身和家庭生存所需的收入,资本化主体需要农业雇工的条件也同时一箭双雕地实现了。
在河镇,资本化主体农业雇工率高达30%以上,远远高于黄宗智、高原、彭玉生呈现的3%。河镇农业一方面有着资本化主体的新兴,一方面有着无产化的趋势。
孙新华的研究也使得我们不能无视农民的分化,尤其是中农的分化。即便是在“有分化未突破”的阶段,河镇的农民分化也不能从恰亚诺夫的人口学视角来解释。在分化突破的质变阶段,部分中农加入兴起的资本化主体中,还有部分中农变成小农。
贺雪峰把中农看成农村的稳定力量,然而研究显示中农有内在和外在的不稳定性。内在不稳定是因为他们具有资本积累的动力,“河镇的很多中坚农民都有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只要总收益不断增加,即使增加雇工他们也非常乐意”。
外在的不稳定是使中农保持为中农的社会条件不可能稳定。当在政府推动下,条件发生变化,内外因结合,部分中农的扩大再生产的愿望得以成全时,另一部分中农则成为小农。
陈航英(2015)的调查研究在同一乡镇展开,对2012年专题导言的第二个问题做了很好的回应,即小农户面对的主要经济问题是什么。陈航英发现,资本主体的出现也再造了“小农”,使得小农不再是80年代初相对独立的直接小生产者,而成为资本主体的土地和劳动力的提供者。
黄宗智认为小农面临的问题主要在流通领域,而陈航英的研究显示,资本主体对小农的排挤和覆盖不仅包括流通领域,也包括生产领域,直接吸取小农的土地和劳动力这些生产要素。
陈航英的研究和黄瑜(2015)对广东雷州半岛养虾的研究同时反驳了黄宗智和贺雪峰提及的恰亚诺夫的命题——小农的坚韧性。这是小农经济派的乐观主义源泉。然而,这一乐观似乎是建立在一个错位的假设之上,以为资本与小农的竞争是刀对刀、枪对枪的竞争,以为市场竞争是谁多打粮食、谁多养虾的竞争。
实际上,今天资本与小农的竞争是航母对小帆船的竞争,资本可以通过产业链的覆盖,攫取全部或部分产业链利润,以此取胜,压倒小农。陈航英的研究显示,与资本化主体相比较,小农从购买农资到农产品销售有许多吃亏的环节,而黄瑜的研究正是展示了资本如何从上下游延伸到生产环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小农在大量流失,直到中国农村出现空心化、出现老人农业、出现未来谁来种地的担心,因此小农的坚韧性值得商榷。
以小农的性质来说,现在的小农不同于80年代初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小农。本期有四篇文章认为,现在的小农,直接或间接地隶属于资本,为资本提供土地或劳动力,或为资本承担其不愿意承担的生产环节的高风险。此小农非彼小农也。这些作者认为形式的貌似背后是实质的不同,主体性的不同。农民的农业、社区的农业的确比资本的农业有优越性,不是攫取利润方面的优越性,而是更可能发挥农业在文化、生态、社区的维护和再生产上的多功能性。
但是我们应该客观清醒地看到,在市场化、资本化的过程中,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农业资本化的另一面是小农在分化,小农的独立性被不断扼杀,小农对资本体系的隶属性在增加。
参考文献:
陈航英,2015,《新型农业主体的兴起与“小农经济”处境的再思考》,载《开放时代》第5期。
贺雪峰,2015a,《为谁的农业现代化》,载《开放时代》第5期。
贺雪峰,2015b,《当前中国三农政策中的三大派别》,澎湃新闻网,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02826。
贺雪峰,2013,《小农立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黄宗智,2012,《〈中国新时代小农经济〉导言》,载《开放时代》第3期。
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载《开放时代》第3期。
黄瑜,2015,《大资本农场不能打败家庭农场吗?——华南地区对虾养殖业的资本化过程》,载《开放时代》第5期。
孙新华,2015,《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兴起与突破性农业转型——以皖南河镇为例》,载《开放时代》第5期。
严海蓉、陈义媛,2015,《中国农业资本化的特征和方向: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动力》,载《开放时代》第5期。
GRAIN,2015,“Asia’s Agrarian Reform in Reverse:Laws Taking Land out of Small Farmers’Hands,”http://www.grain.org/article/entries/5195-asia-s-agrarian-reform-in-reverse-laws-taking-land-out-ofsmall-farmers-hands.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5年第5期
原文标题:“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专题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