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在3月10日的美国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获得最佳女主角奖的美国女演员艾玛·斯通对颁奖人、华裔女演员杨紫琼视而不见,转而与另两位白人女演员拥抱,在东亚网络舆论场引起关于“种族歧视”的争论。来自不同族裔、国别、阶级的女性有摒弃各种等级偏见而并肩团结的可能吗?需要什么样的内因和外因?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学到哪些经验教训?
1949年在北京举办的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可谓是里程碑式的妇女国际主义的宣言,却几乎已被世界遗忘。来自亚洲、非洲、中东、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妇女代表们冒着敌人的封锁迫害、围追堵截,搭乘飞机、火车或者轮船,甚至步行,怀着共同的责任与使命聚在一起,分享经验与见解,决计共同埋葬代表着罪恶与压迫的殖民帝国主义。她们身上迸发出的信念与活力,展现的真知与卓识,不免引发我们诸多思考与感悟。
本文选译自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教授所著的《埋葬殖民主义——1949年的革命女权主义会议》一书,书中勾陈历史档案,重构了这次妇女代表会议台前幕后的来龙去脉。了解当年这段生动鲜明的世界妇女解放运动历史,对于今天我们通过反殖反帝斗争,追求妇女解放、性别平等乃至所有人的解放、世界的公正和平无疑有启示意义。扫描文末二维码可以阅读全书。
作者|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Elisabeth B. Armstrong)
翻译|Ripple 丁卯 律成 于同 开心的贾鱼 杨文 蓝走走
校对 |侯泠
责编 |律成 杨文 丁卯
后台编辑|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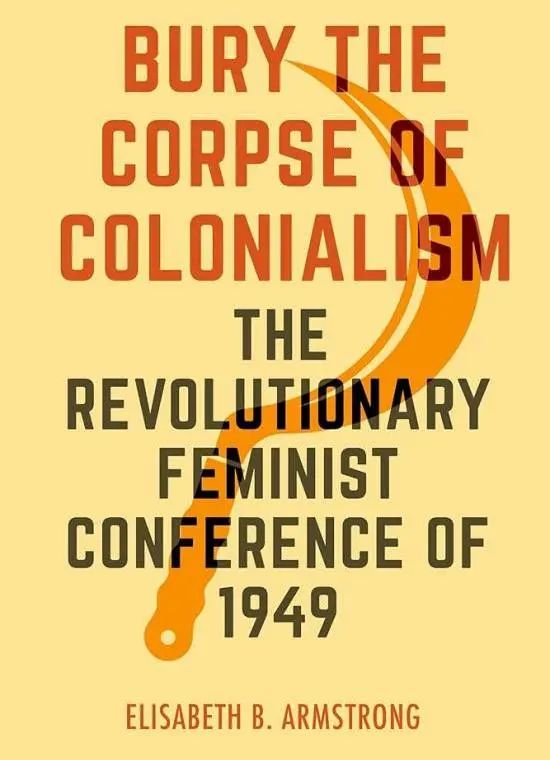
《埋葬殖民主义——1949年的革命女权主义会议》,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著。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是美国史密斯学院妇女与性别研究项目教授,除了这本著作,她还著有《性别与新自由主义:全印度民主妇女协会及其抵抗策略》(Gender and Neoliberalism: The All India Democratic Women's Association and Its Strategies of Resistance)和《从组织中撤退:美国女权主义的重新概念化》(The Retreat from Organization:US Feminism Reconceptualized)。
一、五湖四海聚一堂,
斗争图谱放光芒

在北京举行的为期12天的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吸引了来自亚洲、非洲、加勒比地区和南美洲的代表,“铸就了一场全面反对殖民主义、要求平等权利和完全主权的妇女运动”,性别研究学者伊丽莎白·B·阿姆斯特朗写道。
上图是此次会议的朝鲜代表团 | 图片来源:索菲亚·史密斯档案馆,美国史密斯学院
人们来自五湖四海——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斗争图谱,源于其历史和文化,也受到气候、土壤、山脉和降雨的影响。这些叠加的因素塑造了人们的活动和性情,也培养了人们的视野。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乌萨·帕特内克[1]和普拉巴特·帕特内克[2]所说,亚洲的气候、地质、淡水资源、辽阔的陆地面积和众多的岛屿,在漫长历史中创造了文化财富,形成了人类定居和再定居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亚洲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物产资源,亚洲的沃土无疑具有巨大的农业潜力。
1949年,来自世界各地的妇女向北京进发,她们带着各自的斗争历程,汇入整个亚洲大陆的妇女行列。有些人,比如来自越南北部共产主义自治区的胡德明,于会议开始日期的六个月前就已启程。她步行穿越雷区、冒着被低空扫射和被殖民者的巡逻队逮捕的危险。她们希望与亚洲姐妹们聚在一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创造一个没有战争的新世界,尽管此时她们还不得不荷枪实弹,随时准备战斗。她们离开了养育自己的农村或城市,离开了遭到欧洲强权殖民侵略的故乡。她们带来了斗争的经验教训,有些是彼此共有的,有些是她们家乡独有的。她们齐聚北京,希望用积累的丰富经验彻底埋葬资本主义的贪婪,取得阶级斗争的胜利。
二、反帝团结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
1949年11月23日,丽拉·索里普诺(Lillah Suripno)在莫斯科登上了“海参崴快车”。丽拉是唯一一位参加亚洲妇女代表会议的印度尼西亚代表。由于印度尼西亚动荡的革命形势,印尼妇女组织Kowani[3]与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WIDF)[4]断绝了联系。也许对于联盟中的穆斯林妇女来说,这种关联太危险、太有争议了。丽拉住在阿姆斯特丹,她领导的工人阶级妇女团体的成员有印尼厨师、保姆、学生等。虽然规模很小,而且受到荷兰警方的严密监视,但保持了组织的完整性。丽拉并非出身工人阶级,她受过良好教育,博学多才。她尽其所能地把在荷兰的工人阶级印尼妇女组织起来。她的行动威胁到了殖民政府,因为正在进行的印度尼西亚革命从这种远在荷兰的跨阶级的团结中汲取了力量。

国际妇女民主联合会会刊 | 图片来源:网络
在莫斯科,丽拉参加了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并对其关于针对欧洲和美国妇女的外联工作和宣传活动的讨论感到不满。支持反殖民主义是第一个议程项目,在这方面大家达成了共识,但对团结一致反帝国主义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则充满分歧。瑞典成员安德莉亚·安德林(Andrea Andreen)在1948年布达佩斯大会上的发言仍然影响着一年后的执委会会议。安德莉亚认为,考虑到受众主要在美国、法国、英国和荷兰,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反帝国主义出版物过于激进。她认为,会刊关于和平的措辞可能会疏远这些身处帝国主义国家的妇女,应该不偏不倚地呼吁和平,比如呼吁和平的信函应该寄给所有国家,包括苏联和其加盟共和国。丽拉不同意这一观点。根据她的经验,低调处理帝国主义问题从未为自由运动赢得过任何胜利。
在莫斯科,丽拉与她的同志们——她熟悉的荷兰共产党妇女——保持着密切联系。她十九岁初抵阿姆斯特丹时,就已听说过她们的行动。在激进的印尼学生中间,这些妇女反殖民军事主义的举动被传为佳话。在英吉利海峡沿岸的艾梅登码头,这些妇女高喊“要房屋不要军营!”和“从印度尼西亚撤回军队!”的口号,她们迫使武器装备被送回卡车上。她们和码头工人一起横卧在马路上,迫使卡车调头。她们要求驳船空载,不许装子弹、机关枪、炸弹或其他用于镇压殖民地人民的武器。荷兰共产党妇女也因为她们的反帝斗争受到了迫害。
丽拉年轻时,纳粹入侵荷兰之前,议会中的荷兰共产党员抗议政府对印度尼西亚人的残酷镇压。殖民主义是一套从殖民地榨取财富并输送到帝国中心的体系。但荷兰共产党人在工人阶级中传播了另一种观点——所有工人的劳动都被剥削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远隔重洋、受到差别待遇、不平等的生存竞争制度使印尼工人与荷兰工人被割裂开来,彼此对立。这些荷兰共产党人在公共场合高声谈论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而在丽拉位于苏门答腊岛的家乡巨港(Palembang),这些甚至是不许低声讨论的。
丽拉亲眼目睹民主文明的假象只为荷兰公民维护,他们可以公开辩论殖民主义。而在她的故乡,这种“文明使命”并没有得到履行,殖民地人民甚至不需要认同所谓殖民的正当性,他们只需要臣服。统治秩序的这些残酷事实并没有软化荷兰共产党人,他们为了团结国际工人、抵抗腐朽资本主义分而治之的策略,进行了激进的斗争。他们始终坚持,在每个人都获得自由之前,没有人是自由的。
丽拉成长于医生家庭。她的父亲拉登·苏斯洛(Raden Soesilo)是荷兰殖民统治下的东印度群岛公共卫生服务疟疾防治部门的代理负责人。丽拉、她的母亲娘惹(Nyonya)和兄弟布伦塞尔(Brenthel)陪父亲到阿姆斯特丹继续医学学业。她父亲习得高超的医学知识后独自回到了印度尼西亚。在1941年日军侵占印度尼西亚之前,他成为马辰(Banjarmasin)的驻地医生。丽拉留在阿姆斯特丹,与母亲和兄弟住在位于Euterpestraat 167号的房子里。他们打算等布伦塞尔在鹿特丹完成经济学学业,就回去与父亲团聚。然而世事莫测,丽拉再也无法回到印度尼西亚,甚至连丈夫被处决了也不能回去埋葬他。

1958年中国为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发行的
纪念邮票 | 图片来源:抖音百科
三、小车厢里的大争论
1、二等车厢故事多
丽拉登上开往北京的西伯利亚列车,和她的阿姆斯特丹同志汉娜·阿弗林克(Hanna Averink)与芮里·利普斯·阿丁诺特(Rie Lips- Odinot)在二等车厢。丽拉欣赏汉娜,也喜欢芮里。二战期间,汉娜一直如履薄冰,从未离开过战斗前线,无数次像溜冰者一样灵巧地从虎口脱险。有人说汉娜1930年代在莫斯科受过间谍训练。而芮里则是作为一名政治犯,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度过了战争的大部分时间,[5]但大家都知道她爽朗爱笑,倾听时紧抿嘴唇,说话时高举双臂,充满活力。在芮里被捕前的几年里,所有这些都吸引着丽拉。1945年两人出狱后,关系更加密切。
1930年代,丽拉和其他印尼学生加入了印度尼西亚协会(Perhimpunan Indonesia),简称PI,这是一个与共产党关系紧密的民族主义组织,其中大多数学生并非来自她这样的职业家庭。很多人出身贵族,或者富有,或者既富且贵。他们举办过奢华的聚会,用壮观的、怀旧的文化活动来宣传自己的家乡。因此,甚至在纳粹入侵荷兰之前,丽拉就加入了荷兰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那时她已经认识了每个人,足够信任他们而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参与斗争,即使她最亲密的朋友因被出卖而进了集中营也不胆怯。丽拉和兄弟布伦塞尔加入抵抗运动的目的很明确: 抵抗法西斯入侵。他们协助人们进行地下活动,其中大部分是荷兰犹太人,也有涌入荷兰的德国移民。他们在费吕韦森林里为一些犹太儿童找到了藏身之处,好让孩子们能幸存下来,远离恐怖的占领、士兵、铁丝网和已上膛的武器。

1940年在荷兰的印尼学生联合会部分领导人合影,前排左二为索里普诺(丽拉的丈夫)。
该联合会曾募捐支持中国抗战 | 图片来源:islamadani.wordpress.com
丽拉和布伦塞尔与一种他们在印度尼西亚时就再熟悉不过的法西斯主义作斗争,它迫使其统治下的广大人民成为文盲。这种法西斯主义不仅窃取了印尼所有矿产资源为其工业和利润服务,还强迫儿童在幼年时每天工作六到七个小时,十岁起每天工作十一到十二个小时。丽拉一家在印度尼西亚相对享有特权,但她父亲每日治疗的疟疾患者讲述了不同的故事:人民在殖民地法西斯主义的铁蹄下艰难度日。
丽拉也在这一时期成为了共产主义者。她自豪地大声谈论敏感话题,参加在她家里举行的抵抗组织的秘密会议。她和同志们一起在自家的阁楼上工作,用藏在那里的模板印刷机出版抵抗运动的报纸和传单,大量分发违禁新闻给民众。纳粹从没在阁楼上发现这个印刷机,尽管它与德国臭名昭著的安全部门——党卫队保安局(Sicherheitsdienst)总部在同一街区进行反法西斯宣传。
列车车厢里只有几个挂钩,所以丽拉、汉娜和芮里把衣服都装在行李箱里,塞在下铺底下。火车上太冷了,外套都得穿着,没有多余的挂钩也就无所谓了。她们做好了长途旅行的准备。有人玩多米诺骨牌和其他游戏来消磨时间。像所有参加亚洲妇女代表会议的人一样,她们相互交谈,跟其他同在二等车厢的参会代表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斗争。
这是许多对话中的两个片段:
一天晚上,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吉赛尔·拉贝萨哈拉(Gisele Rabesahala)在车厢里讲述了她与法国人斗争的故事。[6]吉赛尔在任何地方都能独当一面:她是马达加斯加独立共产主义大会党的创始人。两年前,她领导马达加斯加团结委员会要求释放九万名政治犯,这些人被指控参与了反抗法国占领的暴动。她描述了古老的殖民战争策略,即让塞内加尔和苏丹士兵镇压他们,因为根据法国的殖民逻辑,“你不能指望马达加斯加士兵压制他们自己人。”但是,她说,分而治之的做法在马达加斯加内部也很见效: 法国殖民者和本地精英造成了那些住在高地的人与住在低地的人之间的对立。搞民族主义,必须在一个有不同宗教、文化和方言的国家内形成统一意识,作为一个整体来塑造,而不能互相分裂。她讲述了欧洲战争结束后,法国在马达加斯加的殖民恐怖活动有增无减,现在她被迫完全在地下状态生活和组织工作。
中国著名作家丁玲总结了赢得群众(绝大多数是农民)支持的革命策略。“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她在解放区工作多年,土地改革第一次让无地妇女和男子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但在此之前,她说,“我们共产党人必须降租、减税、进行土地改革……过去,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归了地主。佃户须得出肥料、种子和劳动力;地主只出土地。在收获季节,佃户必须把收成最好的一半上缴给地主。当农民无力支付时,就不得不向地主借高利贷,从而陷入永远还不清的债务”。除了土改之外,干部们还为儿童和成年人的教育普及及有普选权的地方人民代表制度而斗争。
来自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代表萨尔玛·布米(Salma Boummi)、阿梅涅·阿莱夫·哈桑(Amine Araf Hasan)和维多利亚·海露(Victoria Helou)关系密切,就像丽拉与汉娜和芮里一样。如同丽拉的圈子,她们来自穆斯林和基督教宗教文化的社会,但对争取妇女权利有着共同的热情,憎恨殖民占领。不过在积极参与社会运动之外,她们都有孩子和家庭,且生活富足。
来自伊朗的玛辛·法洛琪(Mahine Faroqi)和丽拉一样年轻,也没有孩子。伊朗的共产主义人民党[7]被国王政权取缔,再次转入地下。就在一年前,伊朗最著名的妇女解放活动家玛丽亚姆·菲鲁兹(Maryam Firouz)在布达佩斯参加了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大会并发表了激烈讲话,强烈要求美国代表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菲鲁兹说:“让美国人民知道,他们选出的领导人下令大规模监禁、屠杀和严刑逼供。告诉你们的人民,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武装下,伊朗的反动派镇压了阿塞拜疆的青年运动。”菲鲁兹在国王政府那“恶名昭著”,意味着她不可能在1949年离开伊朗去北京开会。玛辛·法洛琪很年轻,在警方中的知名度不如菲鲁兹高,她设法获得了前往莫斯科的签证。不像丽拉,玛辛还没有失去她的爱人。丽拉的丈夫是一位勇敢无畏、信念坚定的同志,因为他对独立的印度尼西亚的忠诚而被处决,头部中弹。
2、丽拉的家庭与革命故事
丽拉的丈夫姓索里普诺(Suripno),曾在莱顿大学学习化学,在印度尼西亚协会的每一次行动中都站在最前线。他很有魅力,脸上总是笑盈盈的,也常与人进行激烈的争论。他始终坚持印度尼西亚独立的诉求,拒绝妥协于取得荷兰联邦内的地位,也拒绝荷兰资本将印尼经济捆绑在永久债务和依附上。1941年,印度尼西亚协会领导人库尔托苏迪乔(Kurtosudirdjo)被德国人逮捕,一年后死于达豪(Dachau)。这时,出身贵族家庭的索里普诺开始担任印度尼西亚协会的领导者。索里普诺编辑的《解放者》(De Beurijding)每周出版三期,到战争结束时印数已达两万份。他还成立了“Surapati”,一支在莱顿接受训练的国内武装特遣队。他们领导了针对纳粹的军事行动,窃取并储存武器,用以日后杀死德国军官。索里普诺的勇敢始终未曾减色,丽拉也一样。
在纳粹占领期间,丽拉仍然勇敢地进行各种活动,她把每个夜晚都用来秘密写作、印刷和分发抵抗出版物。学校停课后,她和印度尼西亚协会的朋友们仍然忙碌。她的同志们来自不同种族,打破了不同殖民地的界限。1943年8月,丽拉在阿姆斯特丹的Schouwburg剧院表演了一场舞蹈,这是她为抵抗运动筹款而精心准备的,她也因此成为公众焦点。为了捍卫美好的事物,尽管在纳粹占领下不断受到监视和骚扰,所有尚未入狱的印度尼西亚学生都抓住了抵抗的机会。就在演出前几个星期,印度尼西亚协会的秘书被从床上叫醒,关进了牢房。与前印度尼西亚协会秘书库尔托苏迪乔一样,他也死于达豪。尽管如此,丽拉还是在舞蹈节目《翻转的船》(Tangkuban Prahoe)里跳了舞,这改编自巽他地区的传说。伴随着现场的加美兰音乐和达朗叙述者[8],她用舞蹈向观众讲述着一切。
一张照片记录了她在《翻转的船》中的表演。她的身体被从侧面打来的光束照亮,在她背后投下阴影,裸露的肩膀显出些许脆弱。她若有所思低头凝视着倾覆的船体,背景是茂密的森林。这些文化表演也是政治性的,售票所得资金都资助了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照片中,她平静、放松的姿势展示了她如何扮演命途多舛的公主达延扬·松比(Dayan Sumbi),但也展示了她如何塑造另一个角色——在法西斯军队占领的殖民地首都的文化大使。

丽拉·索里普诺出演《翻转的船》时的照片,1943年8月摄于荷兰阿姆斯特丹 |
图片来源:哈里·波兹(Harry Poeze)
丽拉从不为她的勇敢而后悔,她仍然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演出后的几天,她得知父亲被占领印度尼西亚的日本军队公开斩首——这是对整个岛屿的警告,昭示要镇压任何不服从行为。抵抗组织的一位同志深夜从被纳粹禁止收听的广播中偷听到了这一消息。就连她的父亲,这位在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机构受过训练、能够治疗导致日本法西斯军人大量死亡的疟疾的医生,也不能幸免于日寇的报复。他的民族主义对侵略者的威胁,超过了他医疗知识的重要性。最后他身首异处,日本侵略者企图通过这种方式终止他的行动,埋葬他的理想。
得知父亲被害之前,丽拉跳舞和演戏。她可以投射出神话中的公主达扬·松比母亲/情人式的遗憾和悲伤,及一位印度尼西亚演员在异国他乡分享自己文化时那种纯粹的典雅。演出结束后的几天,也就是在她得知父亲惨死的噩耗后,盖世太保来抓她和布伦塞尔。她被关进荷兰菲赫特(Vught)集中营,并被指控协助地下活动。这些指控掩盖了她在法西斯分子眼中的诸多更严重的“罪行”:她的共产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立场、作为破坏分子、反法西斯宣传者、犹太人的保护者、印尼民族主义者的女儿以及人民的舞者等这些身份。最终她活了下来,法西斯主义者无法压制她的献身精神,尤其是这时她已经几乎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3、妇女吸烟的批评与争议
在西伯利亚铁路上,吸烟并不方便。深夜穿过乌拉尔山脉时非常冷,火车车窗上不断凝结出水雾,从蒙着灰尘的玻璃上滑下来。妇女们得迅速打开和关闭车厢的门,以防温热的呼吸和体温逸出。在更加寒冷的蒙古大草原,吸烟几乎成了一种惩罚。也许是因为寒冷,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的三位法国领导人很少离开头等车厢到二等车厢跟人们交谈。她们在头等车厢的另一个同伴——捷克斯洛伐克议员安娜·荷第罗瓦(Anezka Hodinova)也没有,她很少说话,白天裹着毯子蜷缩着,专注于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

西伯利亚铁路的自然条件
图片来源: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微信公众号
在旅途的几天里,来自巴黎中央办公室的两名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成员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金耐特·凡尔米什(Jeannette Vermeersch)是法国议会议员,也是法国共产党有影响力的党员;贝蒂·米拉德(Betty Millard)是一名美国共产党党员,一直在巴黎工作,负责协调活动、回复国际会员的信件及编辑国际民主妇联的出版物。贝蒂批评了国际民主妇联领导人在头等车厢脱离群众的、封闭的生活。金耐特在旅行的第四天回到了二等车厢,也许是为了回应贝蒂的批评,但她没有直接说什么。她宣称:吸烟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她这样指摘着坐进二等车厢,并透过贝蒂吞吐的烟雾,列举了原因。
车厢里挤满了人,大家各抒己见。丽拉察觉到贝蒂冷静的目光因法国女人的指责而变得坚硬冷峻。贝蒂似乎一点也不介意坐二等车厢,与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巴娅·阿劳奇切(Baya Allaouchiche)和来自蒙古的两位同志吉斯维格鲁丁·多龙玛贾娃(Jsivigruydin Dulmavshav)、塔玛拉·卡努姆(Tamara Khanum)同住一个包厢。当巴娅或塔玛拉对烟味表示反感时,贝蒂就溜进寒冷的走廊独自享受吸烟的时刻。她会泰然自若地披上那件长至脚踝的毛皮大衣,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凝视着结满冰霜的车窗。
在莫斯科,贝蒂的态度和友好的美国式自信并没有促成她与丽拉的友谊。贝蒂很爱笑,正如当时许多照片中记录的那样。然而,从她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种幽默背后往往带有一丝嘲讽和疏离;幽默可以成为抵御令人不舒服的谈话的盔甲。丽拉让她感到不舒服,贝蒂日记中不止一次提到了这一点。贝蒂描述丽拉“矫揉造作”、“跟火车汽笛较劲”。对丽拉来说,抵抗帝国主义,而不仅仅反对殖民,才是问题的关键。象征性地呼吁声援亚洲妇女,对于她这样经历过父亲被斩首、同志-丈夫被杀害的人来说,都只是微弱的安慰。实际行动中的团结比模糊的同情心或遗憾感更为困难。
帝国主义是贝蒂要承担的——北美资本、北美武器、北美军事基地、北美利润、北美对丽拉祖国所有资源的吞噬。美国作为全球帝国主义的新头目,资助荷兰殖民者及其印尼傀儡政府。丽拉的兄弟布伦塞尔曾在抵抗运动中与她并肩作战,后来他认为是美国人将他从集中营解放出来,这导致他们之间出现立场分歧,最终关系破裂。二战结束后,布伦塞尔立即加入了印尼军队,并很快晋升为日惹地区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与第一位被派往印尼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阿图罗·坎贝尔(Arturo Campbell)建立了合作关系。
这列火车还载着埃茜·罗伯逊(Essie Robeson)和艾达·杰克逊(Ada Jackson),美国著名的反种族主义运动积极分子。她们对团结有恰当而深刻的把握。埃茜的丈夫保罗·罗伯逊 (Paul Robeson)在本国和丽拉的丈夫在本国一样声名远扬(在反共圈子里也恶名昭著)。埃茜在她的会议日记和会后的新闻报导中多次重申了亚洲妇女的口号:“殖民主义已死,剩下的就是我们埋葬其尸体。”丽拉或许可以想象与埃茜一同挖掘那个坟墓,她们都对国内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国外帝国主义行径愤怒不已,寤寐不忘。
另一边,贝蒂才思敏捷,常与记者奥尔加·米洛舍维奇(Olga Milosevic)一同学习俄语,在火车上呼朋引伴,谈笑风生,穿梭于车厢间,仅凭神采和逗趣便能畅通无阻。她轻松自然的魅力与丽拉的强烈意志形成鲜明对比。当金耐特开始教训贝蒂的吸烟问题时,丽拉起初抱着看戏的心态。金耐特说,男性可以吸烟,但女性不行,因为这不女性化。奥尔加可能尚未意识到这种攻击的实质,表示同意金耐特的观点:像贝蒂这样没有孩子的女性尚能吸烟,母亲则不行。奥尔加和她的同伴娜杰日达·巴菲诺娃(Nadezhda Parfenova)也在二等车厢,几乎不停歇地投入到各种交流当中。
金耐特洞察到了她这句话的意图,她知道奥尔加与贝蒂交好。金耐特继续说,吸烟不仅不女性化,还暴露出对男性的嫉妒,是对男性不良习惯的模仿;香烟是一种象征性的占据上风的方式,尽管只是潜意识中的。随后,娜杰日达令争论进一步升级。她说,在苏联,只有在“机关”(办公室)工作的妇女才抽烟,而工人阶级妇女没有时间抽烟。临别前,金耐特又“补了一枪”:“卡萨诺瓦是个大烟枪,生活却如此幸福,真奇怪。他的妻子很爱他。”
贝蒂似乎陷入了沉默,因为她的日记中没有提到任何机智的反驳。后来,奥尔加告诉她要坚定地反击。贝蒂在日记中用法语写道,金耐特是“une donne des eclairsoisements et des armament”,即“一个头脑清醒、全副武装的女人”。金耐特最后那句话,是否暗指卡萨诺瓦这个传说中的好色之徒,可能是贝蒂想要模仿却永远无法成为的人?贝蒂对同性的性吸引力可能已经被金耐特和在国际民主妇联巴黎办事处的人所知。后来,她在回忆录中将在巴黎的时光描述为她一生的转折点,她在同性性爱的纯粹探索中获得了慰藉甚至快乐。她写道,在巴黎,女性与其她女性的性生活是公认的社会生活结构的一部分。
在火车上,为了打破尴尬的沉默,奥尔加转移了话题,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她年幼时,父亲在苏联内战中被杀害。她小时候在烟草厂工作,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她筹集了资金,让她在几年内无需工作,心无旁骛地学习。奥尔加之所以能成为一名出色的记者,是因为共产主义者对她这样无家可归的孤女孩的信任和鼓励。
贝蒂对国际民主妇联领导层脱离群众及阶级特权的批评,次日依然令金耐特感到不快。她又回到二等车厢,带来了关于吸烟的六点想法,其中一些想法是重复的。第一,吸烟令人反感;第二,吸烟是对男性的模仿,产生变得强大的错觉;第三和第四点:吸烟是一种精神支撑物;第五,吸烟是在工作时试图不全心投入——确切地说,是“逃避斗争、自我沉醉、做白日梦”的行为。第六点想法则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提醒:晚饭后吸烟可以,就像喝杯餐后咖啡一样。
4、唤醒革命天真派
金耐特关于吸烟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的观点似乎醉翁之意不在酒。贝蒂对于领导层未能在漫长寒冷的火车旅途中与更多妇女代表打成一片的批评虽然话里带刺,但并没有上升到对共同理想的背叛。对丽拉而言,这些争论太过琐碎。正如她在妇代会上的发言所揭示的,她与其他同志在是否需要绝对的战斗性来摧毁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有着更根本的分歧。两周后就是索里普诺因煽动叛乱罪被处决的一周年纪念日:1948年12月19日,他倒在印尼哈达(Hatta)政府的枪口下。据丽拉所知,她有势力的兄弟提供了监视情报,导致她丈夫被杀害。
帝国主义的干预镇压了印尼人民的革命——为这场革命奋斗和牺牲的主体是工人阶级和农民,而不是像她这样的中产阶级或像她丈夫一样的贵族精英。敌人是谁,自始至终一目了然,她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这勇于消灭它的运动。

1951年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第四届理事会会议上,捷克妇联向中华妇联赠送礼品 |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二战一结束,丽拉就与索里普诺结婚了。索里普诺渴望投身于印尼独立运动,并在1945年率领印尼学生代表团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会议。此后,他返回印尼,加入了独立斗争的前线。1948 年,应印尼总理阿米尔·谢里夫丁(Sjarifuddin)之邀,他代表印尼参加国际学生联合会,前往其总部布拉格。谢里夫丁还任命他为全权大使,开始与苏联就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问题进行微妙的谈判。
新成立的印尼共和国国际地位不稳,其合法性没有得到多数西欧国家和美国的承认。伦维尔协定[9]签署后,荷兰和印尼达成了暂时休战协议。然而随着谈判僵持不下,原本作为第三方承诺保持中立的美国公然倒向了荷兰。荷兰对爪哇岛的印尼共和国实施经济封锁,禁止任何物资出入,导致岛上资源极度匮乏。而美国政客却对此视而不见,并对荷兰违反协议、试图用经济手段扼杀独立共和国的行为采取了放任态度。
毫不奇怪,在这种背景下,经济问题成为了谈判的核心。荷兰拒绝在殖民主义的核心问题——即占有和控制印尼生产资料——上做出妥协。他们要求将其所有国内资本债务转移给印尼人,尽管设立在荷兰的外国公司早已榨干了这些行业的利润。谈判的唯一胜利令人心寒,即荷兰人同意印尼人可以用“印尼人”(Indonesian)这个词来自称,而不再是荷兰殖民时期的“土著”(native)一词。荷兰对经济利益和资源的贪婪压倒了其“欧洲文明优越感”的体面。
面对荷兰的强硬态度,联合国无视印尼人民的正义诉求,所有西欧国家都拒绝承认印尼共和国。索里普诺前往布拉格谈判,争取苏联对印尼共和国的国际承认。他成功了,然而当苏联人宣布这一决定时,哈达(Hatta)政府因与美国政府深度绑定,拒绝接受苏联的外交援手。索里普诺被召回印尼,苏联的国际承认成为他的耻辱和他脖子上的绞索。
随后,情况更加复杂——1948年9月,远离首都的茉莉芬(Madiun)市爆发了一场工会斗争。这场劳工斗争升级为左翼民族主义团体与保守的哈达政府间的武装冲突。哈达政府因此逮捕了三万五千人,包括索里普诺。但是,哈达政府显然无法同时与国内的左翼力量和荷兰殖民势力这两条战线作战。此时,荷兰违反了伦维尔协议,对日惹发动军事进攻,并逮捕了印尼共和国领导人,这打破了权力平衡。面对荷兰军队的进攻,哈达政府不能失去印尼民族主义者们的支持——他们需要这些被逮捕的民族主义者站到自己这边。因此,除了十一名左派领导人外,三万五千名工人、劳工领袖和左翼人士获释。1948年12月19日,这十一名左派领导人被哈达政府枪杀,索里普诺是其中之一。

1948年9月保守政府在茉莉芬逮捕抗议民众
图片来源:荷兰国家档案
对丽拉和印尼共产党(PKI)人而言,索里普诺为直击资本主义核心的独立而斗争。印尼共产党及其盟友看到了哈达政府与荷兰政府谈判中所面临的经济欺骗,这种欺骗被以美国为代表的其它参与方积极煽动。到了1950 年,这种欺骗变成了独立的代价——将金融资本主义的所有武器,包括印尼银行、重要企业及大片宝贵土地交给了荷兰人。名义上独立,但经济上依附。印尼终于获得了“自由”:自由地在荷兰银行和荷兰公司的阴影下挨饿。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荷兰仍然掌握着印尼的生产资料,并通过控制货币供应,将印尼的剩余价值抽取到荷兰的口袋中,简直是印尼经济的金融紧箍咒。
贝蒂·米勒德可以表达她对争取独立的印尼妇女的声援,但她不清楚这对她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她的政府在丽拉所投身的运动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丽拉那“火车汽笛”(用贝蒂的话说)般的愤怒,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力量,一种唤醒美国人从他们的天真中觉醒的力量。
金耐特在对吸烟的性别、性取向和阶级政治问题上获胜后,更频繁地来到二等车厢,发表对世界的看法。她毫不含糊地说,“法国工人阶级不是种族主义者。”尽管贝蒂和丽拉曾在莫斯科就美帝国主义和有意义的反殖民斗争团结问题交锋,但丽拉告诉贝蒂她对火车上关于吸烟的辩论的看法。那是当她们在沈阳,将要回到火车上时。再在天津停一站,就到北京了。面对贝蒂警惕的目光,丽拉说:“这不是很有趣吗?有些人不吸烟是因为她们想更接近工人阶级。同时,她们对其他问题并没有太大兴趣。”
丽拉的推论很清楚:金耐特认为没有必要解决欧洲工人阶级中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问题,那就像晚饭后喝咖啡或抽烟一样自然。她拒绝看到自己存在本能的等级观念的可能性,也拒绝承认跨越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这些真正的障碍而建立国际工人团结的困难。我猜那一刻丽拉看到贝蒂的脸舒展了,眼里闪过一丝微笑。“她说得有道理,”贝蒂当晚在日记中写道。
四、穿越火线:徒步参会与
未能成行的妇女代表们
并不是每个人都乘火车或飞机去参会。一些南亚和东南亚的代表徒步前去。为了参加全球左翼妇女的集会,她们跨越了由来自尼泊尔、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塞内加尔等殖民地的士兵巡逻的军事化的边境。这些士兵由荷兰、英国和法国殖民者雇佣或征召,被殖民者根据需要运往世界各地。三个妇女代表团前往中国,没有护照和签证,也没有大使馆的签名或公章。
这些妇女是武装战士,来自当时的英属缅甸(今缅甸)、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和北越(今越南)。每个人都穿过危险的战区前往北京参加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在所有代表团所在的国家,反殖斗争都不可能轻易或迅速取得胜利。如果没有与亚洲人民一样渴望自由的同志之间的团结,胜利更是遥遥无期。每个代表团都有按时到达的成员,但她们的旅程漫长而危险,有的人无法成行。
1、历经千难万险,只为民族独立

越南革命斗争中的妇女 | 图片来源:2SAIGON
胡德明比其他五位被选为代表的同志提前三个月离开,因为她原计划早些到达,协助会议筹备。最终,这段旅程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她是越南代表团中唯一及时抵达的代表。她从越南北部高地的解放区开始了旅程,沿着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走过的路前行。在北越,她在民族解放阵线的同志们正在准备进行持久战。
从世界各地殖民地集结的法国军队已在越南南部增兵,准备破坏来之不易的越南人民的独立。法国殖民者的小规模进攻主要通过空投威力巨大但精确性不高的炸弹,他们企图恐吓越南人民令他们屈服,放弃自由共和国的尊严,同意回到法国殖民体系,像绵羊一样温顺。但这些目的遭到挫败。殖民者的炸弹以学校和民房为目标,也摧毁了桥梁、道路和军事哨所。地面上的殖民军队进行着类似的暴行:毫无理由地屠杀整个村庄的男女老少。这些屠杀发生在每一位妇女、老妪和女童被强奸和用步枪、棍棒和瓶子性侵之后。她们的尸体被刺穿和肢解,没有在家里焚烧,而是被陈尸于野,警告周围村庄的村民:好好种水稻,低下你们的头,纳税,不然那些被夏天的雨水腐蚀的伸出的手掌就是你们的下场。
胡德明两次避开法国军事警戒线抵达越南海岸,试图乘船前往中国。这两次她都被逮捕、拘留、遣返。第三次,她尝试了另一条路线:她乘船去了法国,再从法国乘船到中国。她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才到北京,赶上在会议的第一个晚上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共舞,却没来得及按计划帮助筹备会议。

1949年12月,胡德明和金耐特·凡尔米什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拥抱 | 图片来源:美国史密斯学院的索菲亚·史密斯档案馆
殖民者持续不断地袭击,拒绝接受他们的独立宣言,因此胡德明和她的同志们放下武器,从支持武装抵抗的重要工作中抽出时间,参加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及发表演讲、参与聚会和起草决议。她们寻求在最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革命妇女建立区域团结。她们寻求对其国家陷入困境的独立事业的承认,在帝国主义国家眼中,这种独立短暂而易被遗忘。
1948年,在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越南代表范恩顺(Pham Ngoc Thuan)描述了亚洲妇女代表会议超出国际外交认可的重大意义。“我们强烈希望,亚洲各国代表之间的交流,以及各国人民的斗争经验将有助于大会制定决议,确保大力支持亚洲妇女的抵抗运动。”
林朗(Ling Lang)从马来亚步行然后乘船到中国。[10]与越南一样,马来亚最安全的地区是最偏远的深山老林。她的同志们是农民和种植园工人,有些是马来人,大多数是印度人或华人后裔。他们被英国殖民者运送到这里,以确保橡胶和其他种植园工人内部的分工等级矛盾。[11]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刻,这些同志都保护着她的安全。林朗参加了会议并致辞。
丁天桂(Ting Thien Gui)从缅甸一路走来。缅甸正被内战撕裂,起因于1946年英国允许其独立的背信弃义的承诺。名义上“独立”,但仍受制于远程殖民主义(long-distance colonialism)的财政枷锁:英国公司仍然掠夺着他们工业、矿业和橡胶种植园的所有利润。越南、马来亚和缅甸的傀儡政府依赖殖民地金融和美国武器来维持政权。人民对这种新的殖民主义代理人统治(colonialism-by-proxy)的反抗引发了殖民者所谓的“内战”——这些不过是人民与殖民军队、帝国主义炸弹和投掷这些炸弹的资本主义飞机之间的“内战”。丁天桂并不是独自出发的,可是她的同伴被英国士兵开枪打伤,被迫返回。
还有其他国家的几位妇女被禁止参加会议。美国非裔民权活动家兼记者夏洛塔·巴斯(Charlotta Bass)被美国政府拒发护照。泰国华侨代表魏德(Wei The)也描述了类似的情况:“还有三位代表本来准备参加这个里程碑式的会议,但由于銮披汶·颂堪(Songgram)反动政府横加阻扰,她们被耽搁在途中,至今无法参会。” 菲律宾唯一的代表已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1948年,美国支持的菲律宾政府镇压了吕宋岛上共产主义者和工人参与的虎克军起义(Hukbalahap Rebellion)。[12]美国还确保加强对菲律宾人进出这些岛屿的控制,以防止反对美国傀儡政权的持不同政见者离开或进入菲律宾。
日本代表团中只有旅居中国的日本革命妇女田长滨乐(Tanaga Hamaku)能够参会。她代表了被美国驻日本麦克阿瑟总部禁止参会的大型日本代表团。学者小碇美玲(Mire Koikari)描述了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重要领导人宋庆龄与日本民主妇女委员会领导人宫本百合子(Miyamoto Yuriko)之间的信件。为了抗议美国占领日本当局拒绝给妇女代表发放出境护照,日本妇女活动家于1949年12月16日和17日在东京举行了平行的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宋庆龄致宫本的信中热情洋溢地描述了北京的大会:“所有人都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为世界带来永久和平、解放被殖民人民的共同意愿。”
2、大会开始,她们寻求所有人的解放!

1949年12月,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图片来源:美国史密斯学院的索菲亚·史密斯档案馆。
这些妇女共同参与的运动并不认为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相比处于次要位置。作为共产主义的独立运动,她们寻求所有人的解放:农民、工人、妇女、各民族、不同宗教人士和原住民。她们认识到这些人际关系形式之间的差异;所有人都看到了妇女组织的必要性,即使已经有青年团体、农会和工会。她们希望建立的世界超越国别,包括所有被资本主义抛弃的工人阶级和农民。
胡德明向亚洲妇女代表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指出法国妇女庄严宣称妇女权利只有在公正的世界中才有可能实现,她要求法国妇女更坚决地团结起来支持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她在大会的第一天致辞:“作为直接从越南抵抗运动中来的人,我很高兴向你们致以越南妇女的问候和表达团结的愿望,她们在越南妇女联合会的队伍中团结一致。”正如越南解放领袖胡志明所言:妇女占社会的一半。如果她们不解放,社会的一半就没有获得自由。妇女不解放,社会主义就建设不起来。
当各国妇女代表抵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首都北京时,天寒地冻,她们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座位上裹得严严实实。主会场横幅上写着“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与世界和平而斗争”,庆祝这一历史性的反帝妇女活动家大会。来自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和马来西亚的妇女描述了将妇女权利埋葬在废墟下的殖民战争的状况。在殖民军队的攻击下,他们的庄稼被烧、桥梁被炸、道路被毁。
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将独立国家的妇女权利想象为和平,尽管她们必须通过武装斗争来实现这一愿景。亚洲妇女代表会议没有忽视世界其他地区而只支持亚洲人民的诉求;相反,它在各国妇女中寻求一种足够强大的国际主义,使其能够抵抗世界各地的殖民再奴役和帝国主义。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寻求妇女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结婚和离婚权、同工同酬、结束暴力和一夫多妻制、国家支持儿童保育,以及妇女的财产权。她们与所有寻求妇女解放的人们有着共同的目标。简而言之,大会寻求以妇女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为框架的公正和平。
林朗、丁天桂和胡德明长途跋涉来到北京参加会议,每一步都衡量着她们走过的距离和激励她们的愿望,她们代表着成千上万的参与斗争的妇女。与会妇女代表们将从斗争中获得的经验汇集起来,共同创建了一种妇女国际主义理论,它将指导遍布全球的反帝妇女的斗争实践。

识别二维码 阅读原文
译者注:
[1] 乌萨·帕特内克(Utsa Patnaik),印度经济学家,她的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农业和以农民为主导的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问题,以及与食品安全和贫困有关的问题。
[2] 普拉巴特·帕特内克(Prabhat Patnaik),印度经济学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坚决批评者,被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倾向的社会科学家。据他称,在印度,经济增长的提高伴随着绝对贫困程度的增加。
[3] 印度尼西亚妇女大会(印度尼西亚语:Kongres Wanita Indonesia),通常简称为Kowani,是印度尼西亚妇女组织的联合会,成立于1946年。
[4]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WIDF,World Women's Democratic Federation)是一个国际性的妇女组织,成立于1945年,旨在促进妇女的权利和参与。
[5]拉文斯布吕克妇女集中营建于1938至1939年间,位于柏林以北50英里。二战期间,这里共关押过13. 3万名妇女、儿童和青年。
[6]马达加斯加共和国,是位于非洲东南部的印度洋岛屿国家。
[7] 伊朗人民党(Tudeh Party of Iran),1941年9月20日成立。由伊朗共产党人拉蒂马什等人在苏联的支持下重建党组织,定名为人民党。
[8] 印尼语Dalang,指印尼哇扬皮影戏(Wayang Kulit)的表演者。
[9] 伦维尔协定由印尼与荷兰于1948年1月17日签署的,规定荷兰和印尼就地停战,这使印尼的领土大部分为荷兰所侵占,并要求印尼加入荷兰主导的“印度尼西亚合众国”;
[10] Malaya, 现马来西亚半岛,1963年与其他几个区域联合组成马来西亚联邦。
[11]分化不同族群是英殖民者的典型殖民手段,意在保证底层互害,避免不同族群团结起来反抗殖民者。
[12]虎克军最初为农民游击队,后发展为不同阶级与职业的革命者参与的反帝运动。
—END—
文章来源:选译自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教授所著的《埋葬殖民主义——1949年的革命女权主义会议》一书,因篇幅有限,原文注释略。
原标题:The Journey to the Conference

 188金宝搏体育官网 SZHGH.COM
188金宝搏体育官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