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政治运作模式本质上都是精英和大众的相处方式。
从生物学上看,人类基因的突变是随机的,并不区分精英和大众。这一科学事实决定了,无论人类的能力或品质受先天因素的影响有多大,它们总是相对均匀地出现在人群中。
然而,属于少数的社会精英总是想垄断优质的后天资源,将它们变成只为自己服务的私产,为此不断压制属于多数的大众,由此产生的矛盾是一切政治冲突的根源。
它带来的撕裂足以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从内部崩溃。如今,这一过程正在美国轰轰烈烈地上演。
传统的建制派精英越来越不受草根民众的欢迎。在他们眼中,帝国的心脏华盛顿已经变成一片肮脏的,充满腐臭的“沼泽”,是由私利和诡计编织而成的“深层政府”。

更加可悲的是,此前所有慷慨激昂的变革呼声和选举承诺都被证明是精英阶层的谎言,那些站在大学讲台或者电视镜头面前痛斥社会不平等的教授或政客,本身就是精英阶层的一份子,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与真正的社会底层打过交道。他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
而另一方面,在传统精英们看来,这个世界正在变得日益“民粹化”。这个词语是专门用来形容那些原本温顺的民众正在变得越来越不服从,不愿听从正确的教化。传统精英们一边可怜这些“无知的群众”,一边痛恨他们将特朗普这样粗鄙之人送上了总统的宝座,让整个帝国变得岌岌可危。
从各自的角度看,这两个视角都有自己的道理。然而,正是这两种“道理”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揭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西方民主的虚伪本质以及自由主义为何会失败。
1.代理问题
在西方政治用来论证自身的所有谎言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命题是“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这句话经常被视为票选政治能够有效沟通精英和平民的重要依据:既然官员的权力来自选民,就必然会对选民负责。
但实际上,票选政治既无法保证官员的权力来自选民,因为相比于选民,选举资金、媒体关系、政治盟友等因素在选举中要重要得多,另一方面更无法保证选出来的官员会对选民负责。
在这一点上,西方的经济学要比政治学诚实得多。在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叫做“委托代理问题”。
它研究的场景是公司股东作为委托人,聘用具有专业技能的职业经理人,也称作代理人来管理公司的日常运作。但是,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代理人会为了自身利益,做出有损于委托人利益的行为,由此产生的问题被称作“委托代理问题”。

显然,在这个模型中,职业经理人的权力来自公司股东。西方经济学直接了当地承认职业经理人会以自己的利益行事,也就是说“权力实际上只对权力的拥有者负责”。
西方经济学为了解决委托人和代理人利益不一致的问题,发明出了很多复杂的理论,如何设计激励制度,如何消除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不对称的信息等等。
但是,当前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承认这些手段都无法彻底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权力的拥有者总是能找到漏洞,为自己谋取私利,这还是在委托人拥有复杂、严密的监督手段的条件下。
奇怪的是,到了政治学领域,西方“大儒们”突然就变得异常乐观,似乎用一句轻飘飘的“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就完成了论证。
而且,在现实中,选民对官员的监督手段远比股东对职业经理人的监督手段要少得多。
当然,你可以说,选民可以用投票惩罚不合格的官员。不过,放在经济学场景里,如果一个公司仅仅用几年一次的考核来约束职业经理人,所有经济学家都会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这样做根本行不通,企业很快就会因为资产被掏空而倒闭。
但是,西方的政治学家面对类似的情景却显得非常轻松,认为一个国家这样做不仅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是人类迄今为止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办法。
西方经济学家的严谨和政治学家的宽松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服务的对象都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那些拥有亿万身家的上层精英。
严谨的经济学可以帮助他们守住巨额的财富,宽松的政治学可以让民众放松警惕,沉迷于“至少我还有的选”的自我安慰。
从今天开始,如果再有人在你面前引用“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这样的蠢话,请告诉他该升级一下知识库了,“权力只会对权力的拥有者负责”。
正因为如此,在票选政治模式下,精英和民众之间看似非常紧密的联系实际上是极其表面化的。政治精英们养成了在几年一次的政治选秀中卖力表演的习惯。

他们每一个人都以“为民请命”的姿态声嘶力竭地叫喊着,然而每一个慷慨激昂的承诺在他们上台之后都变成了狗屁不如,一点味道都不曾留下,直到台下的观众终于感到了厌烦,走向了精英们所定义的“民粹化”,将大大咧咧的特朗普捧到了台上——至少他还愿意摔碎一些瓶瓶罐罐,让观众们听个响。
那么,事情究竟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
2.时代变迁
大约200年前,法国贵族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对当时美国的政治生活表达了积极的赞许。
托克维尔当时刚刚经历过法国大革命,对于贵族和平民之间能够爆发多么激烈的冲突仍然心有余悸。美国那时仍然是一个有着浓厚庄园文化的农业国。托克维尔对这个新生国家的政治运作方式赞叹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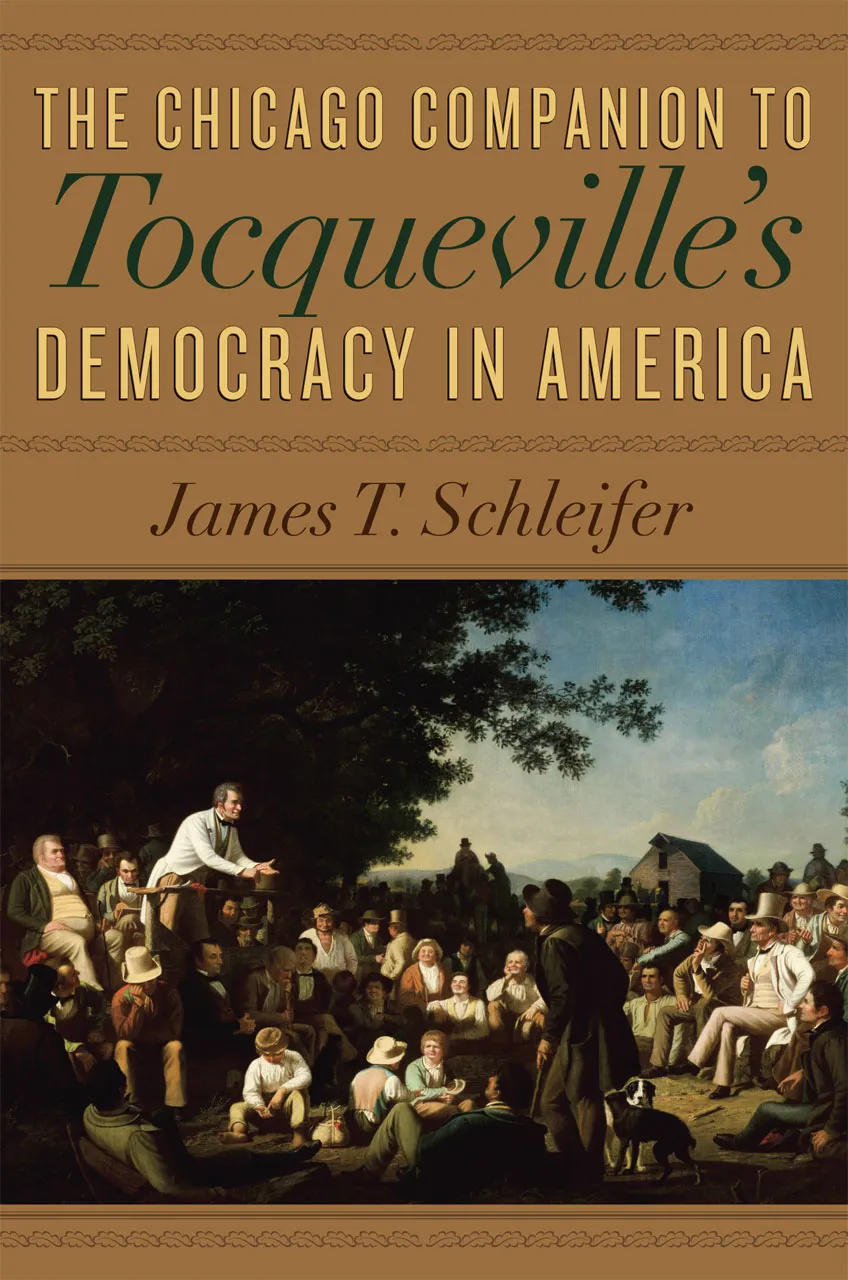
那时这个国家的大多数精英跟平民都生活在同样的乡土社区,每天操心着类似的事情:今年棉花的长势如何,葡萄酒的价格上涨了多少,以及附近哪里又看到了的印第安人出没等等。
他们的区别只是精英们一般会有更多的土地,豢养了更多的奴隶,以及知道如何跟城里来的人打交道。
精英和民众在精神上生活在一个世界中,共享着类似的历史记忆和生活体验。在那时,像希拉里、奥巴马那样精雕细琢的演说并不会受到乡民们的欢迎。他们更喜欢跟自己一样张口就来的说话风格,其中透露出的熟悉和真诚更加能够赢得本地人的信任。
在托克维尔看来,共同的乡土生活是当时美国的民主政治能够良好运作的关键。本土化的精英尽管也会透露出傲慢和贪婪,但是对于维护他们共同的社区和生活方式仍然会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不过,托克维尔同时也对工业经济的发展会破坏这种精英和民众的关系表达了担忧。
进入工业时代,企业主居住在高档社区的别墅,工人们则生活在距离很远的底层社区甚至贫民窟。他们之间的关系仅由一份劳动合同来维系。尽管美国的政治运作方式没有发生变化,但精英和平民的联系已经变得十分淡薄。
这一状况在美国进入全球化的金融时代后变得更加恶化。如果说在工业时代,企业主们还需要依靠工人们赚钱,还会与工人们打交道,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那么金融时代的精英和底层已经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了。
一个典型的美国社会精英,在经济上会在全球布置金融资产,在精神上则是做一名世界公民。
精英群体不再是而且已经没有能力成为底层民众的代表,而是变得日益同质化,像是从同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复制品。中国人对这种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精英形象也并不陌生:他们言必称古希腊,喜欢使用精雕细琢的语言,其中夹杂着一些听起来十分高雅的社科术语;比起人类,他们更加愿意对猫狗表现出同情心,这会让他们的情感显得更加高级,层次更丰富;他们也热衷于扮演为民请命的形象,但是一旦遭遇挫折,就会立刻指责大众已经变得“民粹化”,不再尊重“知识分子”,失去了成为文明人的机会。
他们只愿意在四年一次的选举中“关心”一下平民。而且,在精英们眼中,平民只是一个个的统计数字,政客们所做的只是根据统计结果,从语料库中挑选对应的词汇组成一篇篇演讲稿,像调情一般不断刺激大众的爽点。谁的手法越高明,谁就能取胜。
甚至,新时代的政治精英们连这一点也已经做不好了。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连大众的爽点和雷区究竟在哪儿都找不到了。这时就轮到特朗普这样的人物上台了。

但问题是,特朗普也不是答案。他只是人们宁愿选择“双输好过单赢”的结果。然而,双输毕竟也是输,而且最终承受更多代价的大概率还是平民。
实际上,美国政治衰败的过程很可能说明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最优的制度是不同的。类似“祖宗之法不可变”,或者“历史已经终结”的结论是最要不得的。
这是未来的人类社会在探索解决之道时,最应铭记的教训。
3.探索之道
坦白地说,古往今来,所有的政治体制都是精英的统治。一百多年前的经济学家帕累托早已证明,所有的政治运作方式本质上都是寡头政治。人人平等的状态从来没有存在过,精英们一直拥有比普通人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话语权。
不过,一个国家的确应该由更有才能和远见的人来领导,精英主义也并非问题的根源所在。
问题在于,在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的结合下,精英们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已经跟民众断开了联系。
当社会精英们都以当一名国际公民为荣,以断绝跟脚下这片土地的联系作为文明程度的标志,如何还能相信他们能够代表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众的利益。
从美国平民的视角看,日渐国际化的精英们不仅不愿守护他们最后的家园,反而一直在鄙视它、摧毁它。这也是他们对疯狂涌入的外来移民如此痛恨的原因。
在大学校园中,这个国家未来的精英群体也正在被以同样的方式培养着。

他们一进校门就被告知要成为一名国际公民。他们在校园里获得的所有“领导力和创新力”与这片土地没有任何关系,应该拿到国际市场上去交换最丰厚的报酬。他们的道德观念就如同资本家雇佣的职业经理人一样,除了合同规定的雇主以外没有任何忠诚的对象。那么,这样的精英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受到这片土地上的民众的尊敬?
两百多年前,当美国的开国奴隶主根据庄园时代的社会逻辑设计政治制度时,他们没有想到时代的变迁会让精英和平民的关系发展成如今的模样。这套选票政治的逻辑也已经被证明无力应对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割裂。
美国社会并非不存在能够识别出金融资本和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并纠正偏差的人物。但是,选票政治的逻辑注定了这样的人不会得到资本的支持,无法在政坛出头。
即使真的出现了这么一号人物,那么他也会被精英们集体视作对“民主制度“的最大威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精英主义统治的威胁。
这意味着,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已经决裂,彼此之间成为了对方的敌人。走到这一步证明这套政治制度已经失败了,已经到了要拯救它,就必然要推翻它的程度。
对于我们来说,更关键的是,美国的教训可以教会我们什么?
时代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当前西方世界推崇的政治理论,仍然是18世纪的西方学者在他们成长的社会条件下提出的。
那时的欧洲社会,“人人生而不等”算是常识,精英和平民之间被血缘关系的区隔牢牢地分成了两批人。贵族们作为社会精英经常被默认天然拥有更优越的德性。这种虚伪的政治宣传,以及与现实之间的错位,给了他们长久盘剥民众的理由。
然而,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宣传则造成了另一种虚伪,似乎民众能够投出一票,就已经跟精英们实现了完全的平等。
西方的政治宣传长期以来一直在系统性地制造虚伪的平等,以掩盖真实的不平等。这跟西方流行的快乐教育理念是共通的。它告诉民众,你已经很优秀了,不需要再苦哈哈地学习了。
这导致西方国家“真实的政治过程”长久地被这种虚假的平等所掩盖了,让民众误认为社会已经不存在任何重大的、根本性的冲突,剩下的无关紧要的分歧也可以通过投票来解决,而且投票就是真实政治进程的全部。
但是,民众不会被长久地欺骗。这种虚伪和与现实之间的错位会让民众日渐怀疑,表面的投票活动之下,还有一个由精英们独自操纵的秘密政治议程,也就是所谓的“深层政府”。
直到这种怀疑积累到一定程度,主流精英们落入了即使说实话也不再被民众信任的“塔西佗陷阱”,整个游戏便走到了尽头

 188金宝搏体育官网 SZHGH.COM
188金宝搏体育官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