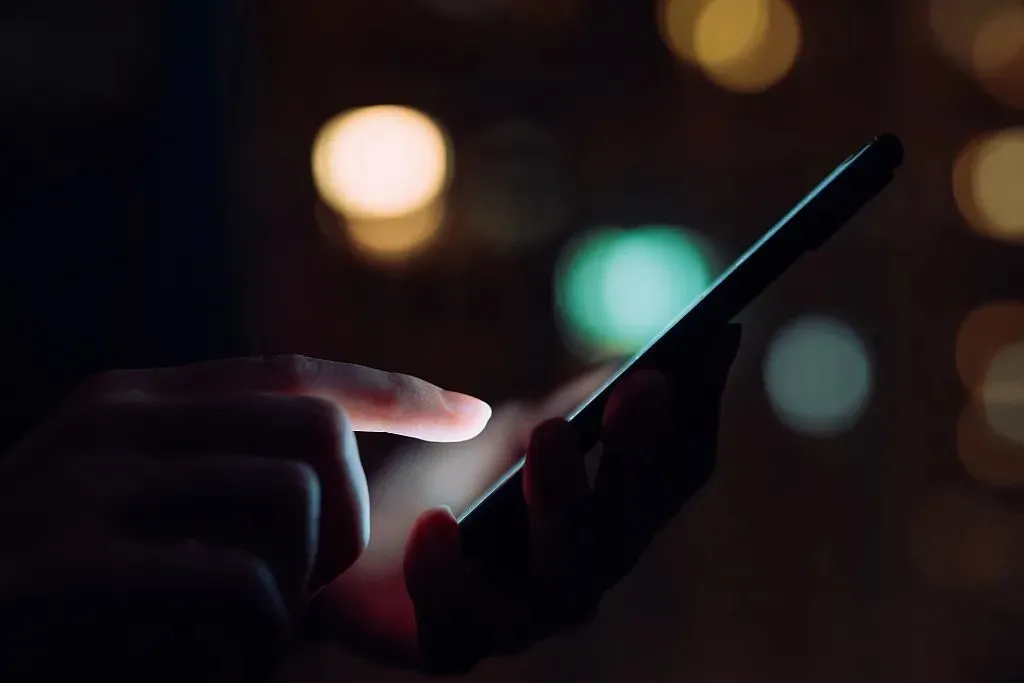下岗、失语、等待春天——评《漫长的季节》
打个响指吧,他说
让我们打个沉默的响指
破碎的理想同样震耳欲聋
远处的人们定会无声地复颂

*前排剧透预警,原片与剧评更配哦
时与间
刚打开《漫长的季节》第一集时,我是带着一个很大的疑问的——漫长的季节,究竟指的是哪个季节呢?
是春天吗?那应该是个很美的故事吧。东北的春天很美很美,与偏南方的常绿阔叶林不一样,在以年为周期再生的东北落叶林,绿色从来都没有厚重,不管过去的一年里有多少残枝败叶,多少虫蛀干腐,到了新一年的春天都全然成了脱胎换骨的婴儿,过去的一切皆记不得了。
用东北话讲——翻篇儿了,在这里,仿佛树都跟人一样心大。
会是冬天吗?最好不要是冬天,作为古代的边疆,无人问津的苦寒之地,东北的六七个月都是冬天,长的实在是有些令人不可思议。尽管冬日的尽头又是一个春天,可那些没有做好准备的动物,病害严重的树木,却并不一定能有幸参与下一个勃勃生机的春天,而是被永远留在了寒冬里。
一会儿功夫,答案揭晓了,原来是秋天。
秋天嘛,肯定是很美的,范伟老师在苞米地(玉米地)的那段戏中,道路两旁都是成熟的大苞米棒子,这是成熟的季节,也是准备入冬的季节,因为凛冬将至。
但很不幸的,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在98年的那个秋天,在仿佛如约而至的大下岗潮里,王响、龚彪与一众工友们如同即将过冬的毫无准备的松鼠,被从丰衣足食、硕果累累的秋天里,直接丢进了皑皑白雪、严酷冷硬的寒冬中。
如何活下去,活到下一个春天,就成了人们唯一要考虑的问题。但98年的火车司机王响显然不太有这个问题,在经历了中年下岗,理想破灭,信仰崩塌,丧妻丧子之后,对于生存的考量都显得有些多余。
于是王响选择了卧轨,选择死在自己最熟悉的桦钢,最熟悉的火车轨道上。如果不是被遗弃的,后来的养子王北仿佛命中注定般的啼哭,王响多半会留在那个异常萧条的秋天。
至于王北为什么会被亲生父母遗弃,笔者认为也跟大下岗带来的普遍经济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
时间确定了,那地点呢?
现实中,东北的黑龙江省确实有一个叫桦林的地方,但那里并没有钢铁厂,城市也并不足够大。由此看来,桦林很可能是个虚构的城市,并不存在一个现实原型,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仍然可以通过一些蛛丝马迹中去寻找导演心目中的桦林。
从演员上来看,王响的演员范伟和龚彪的演员秦昊都是辽宁省沈阳人,范伟更是沈阳市大东区人(笔者此时此刻就在沈阳市大东区),剧中也多次出现了沈阳本土的俚语(与两位沈阳主演的临场发挥有关),另外沈阳最为出名的食物——鸡架也有登场,还提到了真实存在的赫赫有名的铁西区,如此看来,桦林市的原型仿佛就是沈阳市了。
可是,正当观众可能如此认为的时候,导演却特意安排了龚彪是“来自沈阳的大学生”这一人设,明确地告诉了你桦林不是沈阳,而且如果您对沈阳有所了解的话,就会知道这里的大型工厂林立,并无任何一家能像桦钢一样完全代表“桦林”。
于是,当观众们试图再一次仔细整理线索,打算顺藤摸瓜揪出桦林真实身份的时候,人们终于发现,桦林这个地方其实哪里都不是,却又哪里都是。
光铁西这个地名,沈阳、鞍山、四平都有;
马大帅联动地点维多利亚,位于铁岭开原市;
剧中出现的道里道外,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叫法;
殷红母亲在世时卖的煎粉,是吉林的著名小吃。
剧组仿佛有意给桦林公平地添加每一个东北著名城市的要素,把整个泛东北地区的兄弟一个不落地全都带上,所以,与其说桦林是一个具体的明确的城市,倒不如说是导演与编剧们虚构出来的一个泛东北工业城市概念,一个名为共和国长子的九十年代下岗命运共同体。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98年秋天的桦钢火车司机王响,才可以是每一个东北下岗工人。当荧幕里的他带着继子从大下岗萧瑟的秋天,走到集体主义落寞的冬天,又走到了市场经济生根发芽的春天,从世纪前走到北京奥运会后的这一晃18年,从最骄傲的工人阶级劳动模范,变成了一名普通的,维持社会基本运转的出租车司机,这一路走来的是王响的人生,也更是几百万东北下岗者的命运影射——
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事业从此变成了工作,一把年纪仍要坚持赚钱,各种疾病开始显现,外表垂垂老矣拎着个保温瓶,半辈子归来仍然住在曾经厂子分配的老房子里,新盖的楼那么多,但都不是曾经的工人阶级买得起的(这点与笔者的现实观察基本相符)。
观众还没来得及感慨岁月的刀子在王响身上留下的钝痕,镜头一转,却发现即便是这样的王响,也是旧时工厂熟面孔中过得相对像样的。
桦钢女工李巧云,丈夫残疾儿子患病,不得已下海陪酒养家,之后成为了一名按摩师;
厂办大学生龚彪,罹患糖尿病,跟姐夫王响一起倒班开出租,每天不务正业东拉拉西扯扯,做着不切实际的发财梦;
厂医院护士黄丽茹,下岗后在家做私人美容,无照营业;
曾经的桦钢保卫科长邢三儿,罹患尿毒症,靠着非法经营假汽车牌照为生。
这些人一起,构成了一幅曾经开天辟地、打下共和国工业基础的最后一代工人阶级的晚年群像——在那个天量岗位随着一声响指而泯灭的秋天里,无论你是下海出卖身体,还是暂时倒把投机,只要你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只要你让自己跟家人活下来,那都是伟大且光荣的。
在旧有产业体系、旧有消费阶级——工人阶级全面崩塌之时,社会必然会陷入混乱,有人能乘着混乱的阶梯扶摇直上,而他们之外的绝大多数,却几乎必然跌至谷底。
随着20世纪人类社会逐渐走向工业化城市化,其规则之一,便是作为城市原子的新人类必须在城市中找到个人的分工,并以其分配成果进行交换从而构成正常的社会运转,反之则必然会被城市体系排除,游离于社会之外。
如今几百万的东北人,从一个时代最骄傲的工人阶级摇身一变成为了社会的边缘人,怎么办?
自然是不惜一切代价重新挤进去。

▲混乱是阶梯,有人要爬上去,有人只想找个台阶稳当坐着
工人做不成了就去给私人帮工,没活儿干就摊鸡蛋饼,卖鸡蛋饼的太多就去烤串,不会烤串就去菜市场卖菜,这些最容易想到的,最“市井”的买卖构成了再就业1.0,并得到了迅速扩张。
几乎也是同一时间,鸡架在沈阳逐渐流行起来,这东西好吃么?好吃,特别好吃,您亲自尝尝就知道,我每次回沈阳能一天吃俩。可是当你给几百万人做命题烹饪,哪怕是鞋垫子,也能做的香喷喷。
让我们先回到当时当刻,当下岗人员都在卖东西,都处在第三产业,而旧有的社会消费中坚力量又突然坍塌时,那么究竟谁能来充当消费者呢?正如刚才所说,工业化城市化分工明确的社会并不需要这么多“计划外” 的餐饮业从业人员,“进化”后的社会的整体收入水平也并不能供养得起被迫急速扩张的第三产业,于是意料之中的混乱接踵而至。
从小商小贩饱和的那一刻起,小偷小摸的城市分工就迅速上线,那句话叫什么来着,有工作要做,没有工作创造工作也要做。
在我五六岁刚开始记事儿的时候,也就是零三零四年左右,沈阳中街后身那里有条街专门有群小年轻在贩卖那些来路不明的二手自行车。您一听就知道,肯定是偷来的嘛,我们家放在楼道里的自行车就曾经丢过两辆,锁的再严也没有用,而且丢了之后还得老老实实去再跟这些人买,因为我们也没钱。
价格我记得特别清楚,50一辆,童叟无欺。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能在这个“城市自行车流转经纪人岗”任职,也依然能称的上是“幸运”的,毕竟还没有走到豁出身体甚至性命的那步。而如果真的是那种上有老下有小,无法承受一丝丝经济链断裂的风险的家庭的话,那继续向下的求生,就随时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自古以来,人类有什么是天然可以用于贩卖的?
答:男性的武力,女性的身体。
于是在后来者的讲述中,东北的黑社会特别猖獗,东北的按摩店都亮小粉灯。而像剧中的巧云那样丈夫残疾、儿子白血病的家庭,她的陪酒生涯就几乎成了必然。
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平心而论,像剧中这样对巧云“陪酒”的处理其实已经算是某种程度上的理想化了,在东北大下岗时,有太多伟大的女性通过某种事实违法的途径以期为家庭带来相对稳定的收入,她们都是可敬的,并且大多留下了终身的心理阴影,也使得人生的走向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如果没有陪酒生涯,也许巧云晚年会更加自信坦率地与王响在一起; 如果有更好的职业选择,也许殷红就不会在冒牌港商那里对人性失去最后一点信心,也许她还会是那个帮巧云挡酒的殷红。
但是呢,没有如果。如今我们能从东北出身的导演的优秀作品中重走那些历史的片断,感受她们一步步妥协、转化的心路历程,已经实属难得,也更加突出了时代本身和作品本身有关命运的主题。
小偷小摸、诈骗、黑社会、色情服务、甚至是抢劫、谋杀、贩卖人口等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共同构成了当年“下岗再就业”的2.0版本。
这里再补充介绍下保健品这一我不知道是否该归类于诈骗的产业。
看过《钢的琴》的朋友应该对保健品已经有了大概齐的了解,主角陈桂林的妻子小菊就改嫁给了一个卖保健品的商人,具体的配方大概就是一斤面粉兑一粒儿扑热息痛,这就是“保健品”。

这药嘛你说是假药吧,它还真他娘的有效,你说不是假药吧,扑热息痛啥价它啥价!
就是这种让人无语的保健品在东北一直搞到今天,在一众产业萧条的同时,这种吃不死人的小药丸凭借一己之力促成了如同自行车循环一样的财富“增值”,达成了老年人与中青年人间的财产再分配...
在中街的“二手自行车窝点”消失了那么年后,保健品凭借其高工资低技术的优势在辽阔的黑土地上依然坚挺,特别坚挺,在东北,谁还不认识个卖保健品的亲朋好友?
我特别厉害,我认识仨。
当这一切违法的不违法的、绝望的破碎、老实的投机的一个个选择在数年中不断重演并重塑东北这片土地时,我们最终会看到一个怎样的东北?故事的主人公又会变成何种模样?只能说,《漫长的季节》的导演和编剧是惯会使用时间的。
丰子恺先生在《渐》中写到,在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渐”;造物主骗人的手段,也莫如“渐”。假使人生的进行不像山坡而像风琴的键板,由do忽然移到re,即如昨夜的孩子今朝忽然变成青年;或如朝为青年而夕暮忽成老人,人一定要惊讶、感慨、悲伤,或痛感人生的无常。
同样,当剧组越过世间百态的磨损,将跨越18年的时间切片并紧挨着呈现在我们眼前时,当火车司机王响,90年代大学生龚彪,刑警队长马德胜忽然之间变成几近颓唐的模样时,观众们是一定要惊讶、疑惑、悲伤、或痛感人生的无常。
如果说曾经的三人意气风发得就像是跑在广阔田野里的火车的一声鸣笛,那么如今的三人那赖了吧唧、得过且过的样子,就好比是那架泡了水的发动机。
在那段有可能会被载入影视剧史的邢三儿的尿袋情节之中,我们同情曾经的邢科长,但画面中有尿袋的,又何止他一个。
尿袋代表的,就是那些不愿面对的、无可改变的,却又始终过不去的坎,每次意识到它的存在,就使人万分难堪的事物。虽然主角三人组好似身体健全,但当他们的“尿袋”被大剌剌地展示在我们面前时,事实证明,崩溃也只是一瞬间的事,而这种“尿袋”般的东西,何尝不是从东北每一个产业工人、行政人员下岗之时就开始挂上了。
这种痛苦的本身不止来源于下岗,不止源于个人的失意,而是出于所熟知的一切都轰然倒塌,它不是个人的阶级滑落,而是一个阶级的阶级滑落——从此,显性的伟大的工人阶级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在场的缺席者。
而当如此级别的改变到来,现实中的普通人究竟该怎样继续自己的生活?
只能说剧组确确实实是懂东北的,《漫长的季节》所呈现给我们的,正是我们如今依然能看到的,东北下岗工人普遍存在的三种样貌——老实本分、自暴自弃、跟醉生梦死。
劳模王响,下岗后依然兢兢业业地工作,即便在出租车司机界也达到了那种舍我其谁的地步,厂办龚彪,家庭与事业都一塌糊涂,基本上是放弃思考天天摆烂,刑警队长马德胜(即便他并不是下岗工人),那种稀里糊涂,得过且过、逃避现实、醉生梦死的精神状态,只能说每个东北人都见过。
因为我是沈阳人,所以还是拿我所熟悉的沈阳举例吧。我父亲从年轻时,便一直在沈阳市汽车发动机厂生产汽车所需要的曲轴等零部件,98年买断下岗之后,他去了沈阳钢管厂给人打下手,然而没过多久钢管厂也黄了,他又去附近工地干零活,后来一直力工做到现在。我前阵子问他还会玩车床不,他说那哪能不会,正经干了十几年呢。
在我心里,父亲一直都是老实本分的代表,而和我的父亲相比,我大爷几乎是另一个极端。打从下岗之后,他的日常便是每天到处跟人借钱和吹嘘,后来大爷家的孩子因为贩卖违章车进了监狱之后,便彻底跟我们家断了来往。
自暴自弃型这不就有了,至于醉生梦死型则更是常见。
如果您是外地人,如果您想要有朝一日来沈阳旅游,那请一定不要错过极具沈阳特色的酒蒙子一景。他们的潜伏地点主要在沈阳的无数四季抻面馆,或者是西塔大冷面的一楼大堂中,特点是喝的离了歪斜,吹的天花乱坠,一碗五块钱的抻面就五瓶啤酒,一顿饭从凳子上掉下来三回。
全天都是最佳观赏时间,年龄基本集中在五十多岁六十岁,算一算正是当初下岗的那一批人,有热情、有激情,却没什么钱,说话又极其大声。
为啥上一辈人,尤其是退休的工厂人普遍说话都那么大声呢,无非是因为在车间铁与铁相互摩擦的一片嘈杂之间,人声是如此的微小且转瞬即逝。
只有幽默,特别幽默
有人说,喜剧的内核是悲剧,但我觉得对于东北来讲却不尽然——在这里,幽默更多时候是一种语言上的特性。
如果您平时有关注脱口秀、相声等艺术形式的话,便可以发现,与其说东北小品中的笑点是一种演绎出来的故事性,倒不如说这里的幽默是一种内生的天然性,语言讲述了什么不大重要,反倒是语言或行为呈现出来的状态,很重要。
比如说王响形容家里乱的时候会说“造的皮了片了的”;
比如王北照顾王响时说:“爹你这袜子掉地上都能支棱起来”;
比如丽茹问龚彪说你有心么,龚彪说“有啊,你听,咣咣的”;
比如邢三儿跟主角组撕吧的时候说“大衣你都给我濑坏了”。
这些生活中的细节刻画都很难说背后蕴藏着多么大的悲剧,只是这种贱嗖的、哏纠的感觉就是让人觉得很好笑,由轴,一根筋,与浓烈的表达欲组成的东北人就是招人稀罕。好比脱口秀里来自铁岭的李雪琴,只要她站在你面前,你没来由的就是想笑。
这当然是东北人的天赋,但同时也是一种另一种诅咒——毕竟谁也不想在极度悲伤的时候看上去依旧那么好笑(此时的内核的确是悲剧了),不过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由不得你的搞笑属性,使得春晚舞台上的东北小品人才辈出,使得东北的搞笑属性早早地被抽离出来,从而获得了一种纯粹的,无关于悲伤的幽默。
这种抽离在大下岗之后的体现则更加令人恍惚。
曾经的共和国长子,生产了中国第一辆汽车、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第一台轮式拖拉机、第一艘万吨级货轮、第一炉钢水的东北工业基地,如今所产出的招牌产品却是没有杂质的幽默,这本身不就怪好笑的么?
如果说,原本的东北是一只整鸡,工人阶级是其肉身,劳动与奋斗是其体肤,幽默是其内在的骨血,那么现在,仅剩的鸡架就是我们的全部。

玩吧,乐吧,搞笑吧。
为啥如今东北会成为文艺的热土呢,一方面是共和国打下来的基础使得这里充满了故事,另一方面,则是这片土地的文艺工作者们实在无法接受这种程度的抽离,如此惊涛骇浪般的无视,哪怕硬拉着你,把你变成精神东北人,也要告诉你这里曾经发生过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漫长的季节》的导演辛爽是,《钢的琴》的导演张猛也是。
在2007年拍摄《钢的琴》之前,铁岭人张猛曾经是赵本山的小品编剧,对于如何抽离东北人特有的幽默感,曾编出过《功夫》、跟《说事儿》的张猛显然是驾轻就熟的,但他并不满足于单纯塑造一个幽默的东北。
就在白云黑土坐着拉砖拖拉机去北京接受小崔采访的第二年,张猛掏出了自编自导的电影处女作《耳朵大有福》,讲述的是由范伟饰演的在沈阳铁路机务段(没错又是铁路机务段)干了四十年光荣退休的王抗美面对着妻子患病、自身有疾的窘迫现实,从退休第一天便开始找活儿干贴补家用,从而遇见的一系列荒诞现实。
平心而论,尽管这些年国内外的电影看了无数,但若是说哪部电影最能让我感觉悲伤,这部《耳朵大有福》绝对榜上有名。它的绝望从人物无数个谨小慎微的神态,一次又一次被“社会分工”拒绝,以及主角自身所无法改变的亲人所处的境遇中一点点地弥散出来,给你讲述了一个没有下岗,而是平安退了休,却依然困顿他绝望的平行世界里的王响的故事。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电影,一部在我看来根本没想往幽默上拍的电影,一部就算是有笑点,也都存在于东北话本身的片子,在豆瓣的标签之一却是“喜剧”,那些想要轻松一下的人,按着喜剧分类搜进来的人,最后估计得哭着关电脑。
到了三年后的2010年,张猛掏出了其导演生涯的第二部作品——彻底以下岗为主题的电影《钢的琴》,影片讲述了主角陈桂林为了与前妻争夺学琴女儿的抚养权,与其他几名下了岗如今在“就业2.0”高就的技术工友们再度聚集,想要手搓一台工人阶级钢琴的故事。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许久,但这部片子依然可以说是我看过的最浪漫的影片之一,从头到尾,那种不怕困难就是干的气质让我从那时开始真的相信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一本苏联《钢琴制造工艺》就能造琴,一个车间就能改变世界,哪怕如今大环境不再,他们也能让你见识到曾经工人阶级的本领与多才多艺。
科幻不是分为软科幻跟硬科幻么,如果浪漫也分软硬,那么《钢的琴》绝对是硬浪漫,它是一部东北工业史的回响,也是一路火花带闪电的中国工业奠基史的核心精神——想干,肯干,就能干成,就能实现。
只能说,最好的他们并没有碰上最好的时代,而这部壮丽的影片也在院线惨淡收场,出身东北的主演们倒贴钱拍出了这部《钢的琴》,而它在斩获了一系列电影大奖之后,也在豆瓣上收获了另一个喜剧tag。
毫无疑问的是,《钢的琴》的确比《大耳朵有福》具有更加浓厚的喜剧色彩,尽管这与他们听上去给人的感觉正好相反,笔者对于喜剧这一标签当然也没有任何不满,只是想表达一种观点——当幽默实际上作为东北人的内在特征之一时,无论你是否想要,这片土地上所有衍生出的文艺作品都事实上成为了一份份竹筒饭,不论里面所装着的是锅包肉、烤冷面、还是素烩汤,都被名为幽默的竹子紧紧包裹在里面,哪怕有一天锅包肉被装在瓷盘子中呈上来,大家也会称做它为“打开了的竹筒饭”。
当幽默被看做是东北的全部,那等待它的就只会是更浅的关注与更深的孤独。就像小时候的漩涡鸣人,无论如何也得不到大家的喜爱,只能通过耍怪逗人笑来使人爱怜,他努力的表达鲜少有人愿意仔细聆听,最后只能通过出更大的丑,一遍一遍地重复这个循环。
幽默可以救赎很多,却也可以掩盖很多,东北人可以很幽默,但这并不意味着东北只有喜剧。也是因为这样,当在笔者看来远比张猛导演的两部电影作品笑点密集且哏纠的电视剧《漫长的季节》播出,且没有收获“喜剧”标签时,内心中的某种情感仿佛得到了释放,仿佛比起面前的“竹筒”,大家终于更加看重里面装着的到底是什么了。
一个人的表达能被看见,一个人的故事能被听见,对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幸事,在这一点上,东北从来不缺故事,也有好酒。
回头看看,然后继续往前走
比起传统的犯罪类电视剧而言,《漫长的季节》的慢节奏显得不太犯罪,也不太电视剧,它没有急于渲染紧张的氛围和窒息的犯罪手法,好冷不丁的吓你一跳,震你一惊,让你快速知晓社会的可怕。它仿佛只是真心实意地想要让你感受下什么是真实生活的漫长,今天带你下厨做做锅包肉,明天带你怀旧下马大帅里的门童,后天又安利下东北冷面店拌的桔梗,去个烤肉店都得是篦子烤肉,贼地道。
而这样做的目的便是——批量制造东北人,当你已经开始意识到事情的发展走向不受控,当你已经发现危险与侵害的事实发生时,你已经对在场的人物们产生了广泛的共情,你已经对所处的时代有了一定的把握,你已经对东北产生了一定的乡愁。
一群从没来过东北的没吃过锅包肉的人,如今通过一部剧变成了爱吃锅包肉的精神东北人,与几百万东北人一起害怕下岗,这不就是《漫长的季节》所特有的魔力么。
可以说,这才是这部剧真正的目标——对于那个秋天的重走,对于那个时代的回忆,从而再次回归它真正的主题——命运,相对而言,犯罪与其说是主题,倒不如说是将这些人的故事串联起来展现给我们的线索与工具。相比于剧中着力刻画的每一个情感丰实、故事完整的人物所组成的那个时代,剧组对于犯罪本身的描述,就好比一桌子满汉全席里单给你讲了开水白菜的做法有多精彩。
这就是群像的魅力,每个人都能找到打动自己的地方,他们的故事你永远也穷不尽,写不绝。
命运无常,大势已定,剧组只管奏响了《悲惨世界》的最后一曲One day more,投机者宋玉坤与“港商”在日落前瓜分掉最后一点资产,邢建春利用职权多拿一点是一点,巧云在夜总会努力陪酒,全然不知要持续多久,王阳与沈墨自大桥上一跃而下宛如飞蛾扑火,王响刚正不阿直到最后,却既不能保全工作也无法逆转妻儿的死亡。
剩下的,就让观众自己想吧。树能过冬,至于草,就只能留在过去一年的秋天。也许巧云与王响一家三口去了北京旅游呢,也许王北考上了美院呢,也许马德胜脑血栓恢复的很顺利又去欺负健身器材了呢...
真正重要的,可能就是电视剧结尾处,头发花白的王响于想象中追赶着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时,告诉他的那句——往前看,别回头。不要回头,不要沉浸在过去,不要让悲伤吞噬了你,要永远向着明天而活。
如果说不回头,能让人们更加有勇气直面未来的人生,如果说陷在过去实在是太痛苦太痛苦,那么就让他们大步地往前走,就让新一代的东北人,代替他们回头吧。
回头,是为了更好地往前走,如果没有回头,也就没有《漫长的季节》,没有《钢的琴》,没有《耳朵大有福》。
永远要有人向前走,也永远会有人回头、回忆并复颂着前辈们的故事。有句话讲说,每个人都是一本书,这排属于东北人的迎头砸下去的铁质书架,未来一定会有人接力将它扶起。
以前是张猛,如今是辛爽,以前是马大帅,是辽北地区著名狠人范德彪,如今,又变成了桦林舞王龚彪。
一代又一代的东北人在寒冷的冬天里向前跑啊跑,把北大荒跑成了粮仓,把湿地跑成了油田,也许有一天,人们将同时记得最寒冷的那场雪,而又不再害怕冬天。
回头看看吧,然后继续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