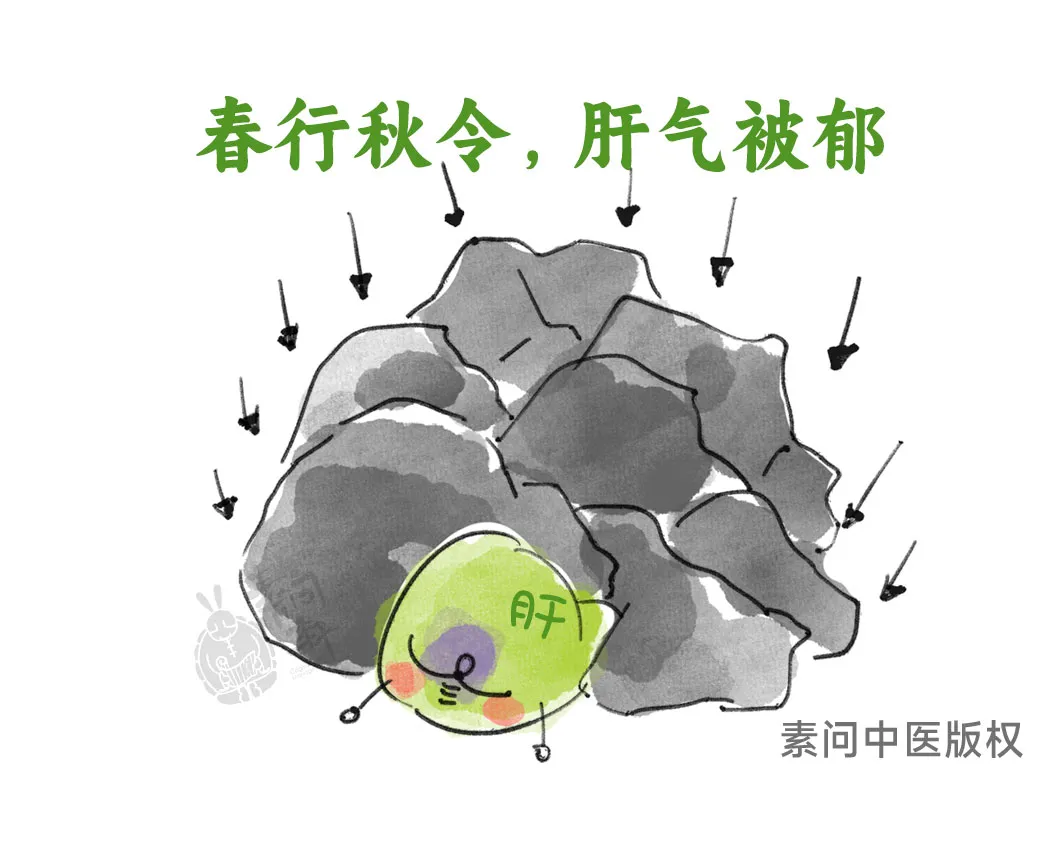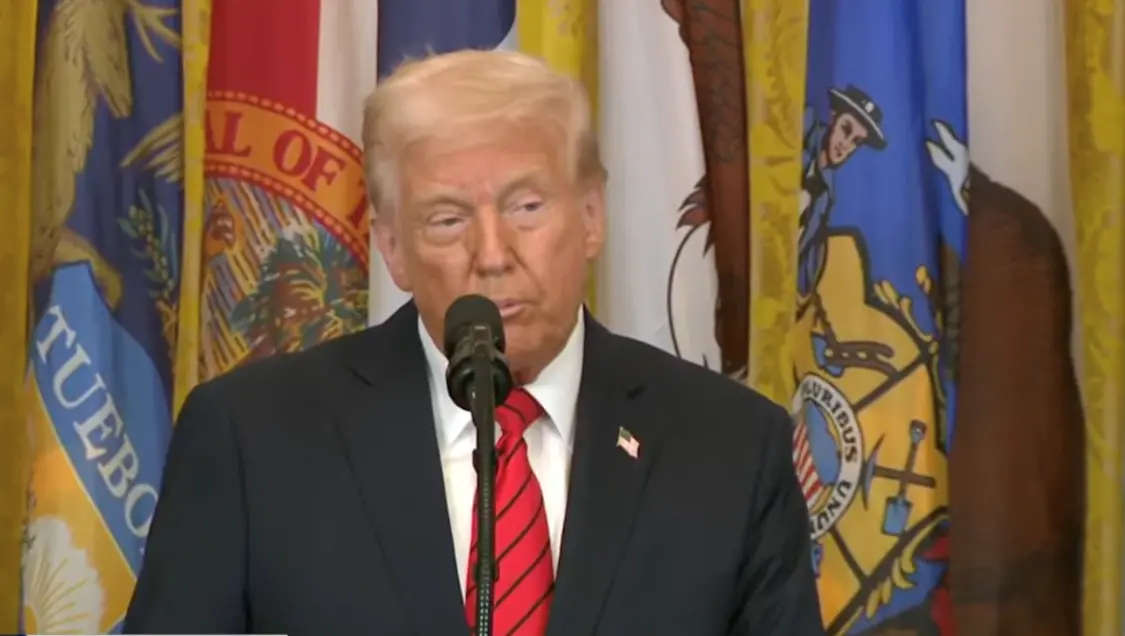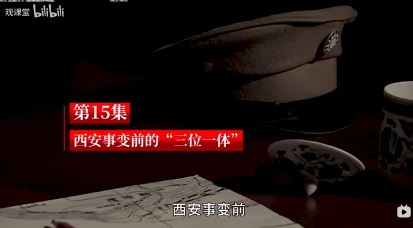邓广铭: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
今年春天,我曾写了一篇短文,论证岳飞的《满江红》词并不是一首伪作,后来发表在中华书局编印的《文史知识》第三期上。该文发表之后,不久我即陆续接到一些读者来信,仍然就这一问题与我进行讨论。其中,有些人是不同意我的意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我对于前此那些持否定论者所提出的论据和论点,并未能一一加以辨证和纠驳,但多数人对我的意见表示赞同,而且还有人向我提供了更有力的论据。这两方面的意见都对我大有帮助,也都促使我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细致的考虑。现在写成的这篇就是我在发表了前一篇短文之后,根据读者来信所提意见和所补充的资料,在最近几个月内反复考虑的一个结果。
—、这首词肯定是岳飞的作品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在古今词人的作品当中,传诵之广、之久,影响之大、之深,大概再没有能和上面抄录的这首《满江红》词相比并的了。历来相传,都以为这首词是南宋名将岳飞所作。岳飞是河北的一个农家子,少年时曾在北宋大官僚韩琦的后裔家中做过佃客,年二十以后投身军伍,过了将近二十年的戎马生涯,在抗金战场上立下了不朽勋业,他在三十九岁那年,即被赵构、秦桧诬陷、惨杀。
似这般出身的一员武将,有能力填写这样一首词吗?换言之,这首《满江红》词果真是岳飞的作品吗?
我的回答是全称肯定的:岳飞有谱写歌词的能力,这首《满江红》词确实是岳飞所作。
尽管岳珂(飞孙)在《鄂干行实编年》(《宋史》中的《岳飞传》完全脱胎于此书)中所说的,岳飞在小年时即于“书传无所不读,尤好《左氏春秋》及孙、吴《兵法》”等话语是不尽可信的;然而,当赵构在应天府即帝位之初,岳飞就已能“上书论事”,且因此而致得罪、免职。这时岳飞的军职尚极卑微,自然不会有幕僚为之代笔,而是由他本人起草、誊录的。这就足可证明,他当时的文化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了。岳珂以《家集》名义收录的岳飞的作品共有十卷,自奏议、公牍、书檄,以至律诗、歌词与题记,无所不有。其中的奏议和公牍等虽必有出自幕僚之手者,而诗、词、题记则必皆岳飞亲自写作的。这说明,岳飞是具有写作《满江红》这首词的才能的。
从确为岳飞写作的一些“题记”和诗篇的思想内容来看,也可以证明《满江红》词必是岳飞所作。今摘引几段于下:
(一)建炎四年(1130),岳飞驻军宜兴县,因事到附近的广德军去公干,在其地金沙寺的墙壁上写了一段“题记”说:
余驻大兵宜兴,沿(缘)干王事过此,陪僧僚谒金仙,徘徊暂憩,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飞题。
(二)岳飞从广德军又“拥铁骑千余”回驻宜兴之后,同年六月又在宜兴县张渚镇张大年家的厅事屏风上写了一段《题记》说:
近中原版荡,金贼长驱,如入无人之境,将帅无能,不及长城之壮,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小大历二百余战,虽未及远涉夷荒,讨荡巢穴,亦且快国仇之万一。
今又提一垒孤军,振起宜兴,建康之城,一举而复,贼拥入江,仓皇宵遁,所恨不能匹马不回耳!
今且休兵养卒,蓄锐待敌。如或朝廷见念,赐于器甲,使之完备,……即当深入虏庭,缚贼王,蹀血马前,尽屠夷种,迎二圣复还京师,取故地再上版籍。他时过此,勒功金石,岂不快哉!此心一发,天地知之,知我者知之。建炎四年六月望日,河朔岳飞书。
此据赵彦卫《云麓漫抄》摘引。岳珂所编《家集》亦收此文,文句较简略,标题为《五岳祠盟记》。
(三)绍兴二年(1132)七月,岳飞因追剿军贼曹成的匪众而进军湖南,当他班师经过永州祁阳县的大营驿时,他也写了一段《题记》,其文为:
权湖南帅岳飞被旨讨贼曹成,自桂岭平荡巢穴,二广、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圣远狩沙漠,天下靡宁,誓竭忠孝。赖社稷威灵,君相贤圣,他日扫清胡虏,复归故国,迎两宫还朝,宽天子宵旰之忧,此所志也。顾蜂蚁之群,岂足为功!过此,因留于壁。绍兴二年七月初七日。(岳珂编《家集》卷十)
(四)南宋人赵与时的《宾退录》卷一,有一条记事:
绍兴癸丑(按即绍兴三年,亦即1133年),岳武穆提兵平皮、吉群盗,道出新淦,题诗青泥市萧寺壁间云:
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
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候。
淳熙间,林令(梓)欲摹刻于石,会罢去,不果。今寺废、壁亡矣。其孙类《家集》,惜未有告之者。
(五)在岳珂所编《家集》卷十,还收录了两首律诗,都没有载明写作年月和地点。其中一首的题目是《题翠岩寺》,全文为:
秋风江上驻王师,暂向云山蹑翠微。
忠义必期清塞水,功名直欲镇边折。
山林啸聚何劳取,沙漠群凶定破机。
行复三关迎二圣,金酋席卷尽擒归。
这里既有“秋风江上驻王师”句,又有“山林啸聚何劳取”句,则其写作时间可能是在镇压了虔州和吉州两地的起义群众之后,也可能是在追歼曹成所率领的那股游寇之后,也可能是在镇压杨幺所率领的湖湘地区起义群众的前后。虽难断言其确在何时,但总应写在绍兴二年至五年这一时间内,却是可以判定的。
另一首律诗的题目是《寄浮图慧海》,其全文为:
湓浦庐山几度秋,长江万折向东流。
男儿立志扶王室,,圣主专师灭虏酋。
功业要刊燕石上,归休终伴赤松游。
丁宁寄语东林老,莲社从今着力修。
岳飞只有在绍兴六、七两年内,为了守母丧,以及为了接管刘光世的军队事而与张浚发生嫌怨,曾先后两次在庐山住了较长的时日,估计他与浮图慧海的相识相熟,也应在此时期内。因此,这首七言律诗的写作时间,最早应在绍兴七年他又回到鄂州军营之后,最晚应在绍兴十年进军中原去抗击女真铁骑。
以上引录的几首诗和几篇题记,其内容所表达的全都是岳飞的忠君爱国(此“国”字只指宋政权,非指“中国”)思想,全都可以证明,他随时随地都是念念不忘报君父之仇、雪国家之耻的:他讨平了流窜湖南的军贼曹成,而却说他的志愿唯在于“扫清胡虏”,仅仅平定了“蜂蚁之群,岂足为功”;他提兵镇压了虔吉二州的农民起义军,而却说他只是志在“斩除顽恶(按指女真入侵者)还车驾”;他既一再说要“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深入虏庭,缚贼主,蹀血马前,尽屠夷种”;又一再表示“必期清塞水”,“直欲镇边折”,“功业要刊燕石上”,“金酋席卷尽擒归”。上边引录的这几首诗和几篇题记当中的这些语句,按其意境和感情来说,和《满江红》词可以说是完全属于“无差别境界”的。把这样一些语句加以洗炼,并使用虚实并举的手法,重新排列组合一番,用长短句的体裁并写出来,岂不就是那首《满江红》吗?
《题翠岩寺》诗中的“功名直欲镇边圻”句,和《寄浮图慧海》诗中的“功业要刊燕石上”句,所表达的志趣,粗看来似与《满江红》中“三十功名尘与土”句意不相符合,实则也并不然。前两句所表达的是他的愿望,及至已经得到了节度使等类的很高的官衔之后,再与夙志稍加对照,便感到这功名并非因“镇边圻”而得,而这“功业”也更远远不能刊刻在燕然山上,当然他就要视同“尘与土”了。
基于上述种种,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可以做出判断说,谱写这首《满江红》歌词的,和写作上引那些《题记》与那些诗篇的,正是同一个人,即南宋名将岳飞。
二、否认岳飞为此词作者的几个论点和论据
自从这首《满江红》词为世人传诵以来,直到21世纪的30年代为止,从来没有人对此词是否为岳飞所作提出过疑问。到30年代末,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印行出来,其中有辨证四库馆臣对明人徐阶编《岳武穆遗文》提要的一篇,首次断言徐阶收入《岳武穆遗文》(即《岳集》)的这首《满江红》词并非岳飞所作,其言曰:
至《满江红》词,则(弘治时浙江镇守太监)麦秀实始付刻,其字为(赵)宽所书,非(岳)飞之亲笔。然宽不言所据为何本,见之于何书,来历不明,深为可疑。……
《满江红》词不题年月,亦不言作于何地,故无破绽可指,然不见于宋元人之书,疑亦明人所伪托。(桑)悦《记》(按:此指桑悦所作《刻<送紫岩北伐诗>碑记》,见徐编《岳集》卷五)中已有“踏破贺兰山缺”之语,则其伪当在悦以前,第不知出何人之手。……
自徐阶收此等诗词入《岳集》,李桢从之,嘉靖间钱如京刻《程史》,又取而附之卷末。后之重编武穆文者,若单恂、黄邦宁、梁玉绳等复从《程史》转录入集,而李桢、单恂更增以伪作,于是8文史交融: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传播遍天下,而《满江红》词尤脍炙人口,虽妇人孺子无不能歌之者,不知其为赝本也。
然以伪为真,实自徐阶始。阶不足道也,四厍馆诸臣何其一无鉴别也哉!
或者曰:“《送张紫岩诗》其伪固无可疑,若《满江红》词真伪皆无实据。其中如‘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及‘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等句,足以励迈往之风而作忠义之气,于世道人心,深为有裨,子何必以疑似之词强坐以伪也哉?”
应之曰:“考证之学之于古书也,但欲考其文之真伪,不必问其理之是非。……号称武穆之《满江红》词,虽为人所信,以视‘经典’则有间矣。其词莫知所从来,……吾何为不可疑之哉?疑之而其词不因我而废,听其流行可矣。至其为岳珂所未见,《鄂王家集》所无有,突出于明之中叶,则学者不可不知也。”
余先生的这些意见,应当说是具有一定的分量的。因此,此论一出,为学术界的很多人所接受,夏承焘先生即其中的一人。夏先生在1961年写了一篇《岳飞<满江红>考辨》(已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月轮山词论集》中),除接受余先生的论断外,还进一步做出新的论断,不只以为“这首《满江红》词不是岳飞之作”,而是“出于明代人之手”,而且以为其真实作者“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
余嘉锡先生所不曾提出而为夏承寿生所反复加以论辩的,是这首词中的“踏破贺兰山缺”一句。他所举出的疑点是:
1.以地理常识说,兵飞伐金要直捣金国上京的黄龙府,黄龙府在今吉林境,而贺兰山在今西北甘肃、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地区。这首词若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
2.南宋人实指宋金边塞的,多用兴元(汉中)之北的大散关,(陆游诗:“铁骑秋风大散关”、“大散关头又一秋”等),从来没有人用贺兰山的;因为贺兰山在那时是属西夏国境的兴庆府,它和南宋国境中间还隔着金国泾渭流域的庆原路、凤翔路一大块地区;假使金人攻西夏,可以说“踏破贺兰山缺”,南宋人是决不会这样说的。……《满江红》词里这样说,正是作这首词的明代人说当时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
3.明朝的北方少数民族是鞑靼族。鞑靼入居河套,骚扰东北西北,从中叶一直纠缠到明亡。……《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也说:孝宗弘治十一年,“越以‘寇’、‘巢穴’贺兰山后,数扰边,乃分二路进‘剿’”。这是明代汉族在贺兰山抵抗鞑靼族的第一回胜仗。……我们可以设想,“踏破贺兰山缺”,在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绝不会有此的。
4.元人杂剧有《宋大将岳飞精忠》一本,四折都是岳飞一人唱,而没有一句引用这首《满江红》。第一折“寄生草”云:“堪恨这腥膻丑陋契丹人,我学取那管夷吾直杀过阴山道。”云“阴山”而不云“贺兰山”。……那时若已见到这首《满江红》,岂会放过不用?可见在元代还不曾流传这首《满江红》。 既然贺兰山是明代的汉族与鞑靼族互相争夺的主要地点,而王越又是在贺兰山战胜鞑靼的主将,所以夏先生便又进而推论说,《满江红》这首词,若非王越所作,便是他幕府中的某个文士所作的。
5.王越是明代边防名将,贺兰之捷,已七十多岁;就在这年的冬天,因谏官弹奏太监李广,连累及他,忧恨死于甘州。他是中过进士的文人,积战功至大将,工诗。钱谦益《列朝诗集》丙集之三,录他的作品十五首,称他“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渠磨盾、悲歌出塞之思”。他弘治十一年这次战功和他不幸的政治遭遇,在当时士大夫中间可能会有相当大的影响;这首词里点出“贺兰山”一辞也许与此有关。如果如我的猜想,这首词的作者是参与这场斗争或对这声斗争有强烈感受的人,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他的身份正和岳飞相同),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
余嘉锡、夏承焘两先生先后提出上述的一些疑难问题之后,据我的见闻所及,似乎很久很久再没有人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直到去年,我从报刊上看到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又对这一问题纷纷发表了意见。但是,意见尽管很有分歧,而彼此所使用的资料和论据,却大都不出余、夏两先生已经使用过的那些。因此,我现在仍只对余、夏两先生的意见进行一些商榷。
三、我对上述疑难诸问题的解答
第一个应当解答的问题是,如果《满江红》词确系岳飞所作,何以不曾被岳霖、岳珂收集到,不曾编入《家集》之中?
据岳珂在《家集序》中所说,其父兵霖对干搏集岳飞的各类作品,确实是做过一番极大努力的,而岳拉本人在这方面却沿有做过什么工作,只是加以编次刊印而已。试看他的原话:
先父臣霖盖尝搜访旧闻,参稽同异,或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稿之所存,或备于堂札之文移,或纪于稗官之直笔。掇拾未备,尝以命臣,俾终其志。臣谨汇次,凡三万六千一百七十四言,厘为十卷,阙其卷尾,以俊附益。……异时苟未洁先犬马,誓将搜访,以补其阙而备其遗。……
这篇序文是嘉泰三年(1203)写的,而到端平元年(1234)岳珂又把《金佗续编》(《家集》即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金佗续编》重行汇合刻印,距《家集》之初次刊行已达三十年之久,他在序言中所说“阙其卷尾以俟附益”者,却仍是一句空话。即如收录前引岳飞《题新淦萧寺壁》那首七绝的《宾退录》,在嘉定末(1224)或宝庆初(1225)即已印行,岳珂如真的立志“搜访”、“补阙”的话,不正可以采辑了来“附益”于《家集》的“卷尾”吗,而事实上他竟若罔闻知,未加采辑。(上文所引《云麓漫钞》所载岳飞写在宜兴县张大年家的那段《题记》,较之岳珂收在《家集》中的那篇《五岳祠盟记》,文字多些,也更翔实些。《云麓漫钞》刊行于开禧二年(1206),早于岳珂之重刻《家集》凡二十七八年,而岳珂也没有取相参订,或迳改用其文,而却标了一个极为费解的《五岳祠盟记》作题目,这也足见岳珂对于搜访岳飞遗文,是不够辛勤认真的。)
我们不能因为岳飞那首《题新淦萧寺壁》的七绝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之中而否定其为岳飞所作;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那首《满江红》词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之中而断定它不是岳飞的作品。
第二个应当解答的问题是,何以这首《满江红》词也不见收录于宋元人的笔记、杂录一类的书中呢?
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不曾见到,就断言宋元人书中全未出现过这一作品。试想,在明初所修《永乐大典》当中所收录的宋元人的著述,稍后不是就有许多种散佚失传了吗?从清人修《四库全书》时辑自《永乐大典》的宋元人著述之多,可以推知其未加辑求着为数必还不少。怎么能够断定此词不正是收录于南宋人的某一书中,其书尚为明朝中叶的桑悦、赵宽等人所及见,并即据以刻石岳庙,至其后却又散佚失传了呢?赵与时的《宾退录》幸而不曾失传,但徐阶收入《岳集》中之《题新淦萧寺壁》一诗下亦并未明著所出,假如《宾退录》也不幸而在明代中叶以后佚失,就从而断定此诗亦出明人伪托,亦为“赝本”,那就实在是疑于不当疑了。
第三个应当解答的问题是,这首《满江红》词,果真是在明朝弘治年间赵宽写出刻石时才首次出现的吗?果真是从徐阶开始,才把它“以伪为真”的吗?
在河南汤阴县的岳庙中,迄今还矗立着一块刻着这首《满江红》词的石碑,是汤阴县一个名叫王熙的秀才在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所写。全词共写了五行,只有末句作“朝金阙”,与通行本之作“朝天阙”稍异,余俱同。在此五行之后,明确地写有“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共十五字。杭州兵庙中的那块《满江红》词刻石,乃是明孝宗弘治十一、二年(1498、1499)内所写刻,汤阴县岳庙王熙的这块刻石,最少要比它早了四十年: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则早了七十八年。有这一件实物作证,则此词首次出现于弘治年间之说,以伪为真始自徐阶之说,便都不攻自破了。
然而还可以更进一步加以推考。
汤阴之有岳庙,是在明代宗景泰元、二年内(1450、1451),经由徐有贞倡议、汤阴县学谕袁纯负责创建的。庙宇落成之后,袁纯接着就又“辑庙祀事始末”,选录岳飞的部分诗文,以及后代人纪念和歌颂岳飞的诗文,编为《精忠录》一书(此据商《精忠录·序》),而此书的第三卷即把岳飞的这首《满江红》词收录于内(据1769年朝鲜铜活字本)。据书中的几篇序跋文看来,知《精忠录》之付刻虽在景泰六年(1455),而其编辑成书却在景泰二、三年(1451、1452)内。这与王熙写刻的《满江红》词石碑相较,又早了七八年。是则此词的出现,至晚应在十五世纪五十年代的初期。
徐阶所编《岳集》卷三,摘录了赵宽的重刻《精忠录》的序文,据知袁纯所编之书又在杭州重行刻印。然则杭州岳庙中那块由赵宽书写的《满江红》词刻石,如果没有其他书作为依据,则必即是从袁纯书中照抄来的。这样,似乎就不应当说“来历不明,深为可疑”了。
袁纯把《满江红》词收编在《精忠录》中,我们说这是这首词的首次出现,这只是就我们今天所见所闻的范围来说的,南宋以来的一些著述,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致失传的,不知已有多少,其中有许多,我们是连书名和作者也全不知道的。因此,我们今天虽然查不出《精忠录》所收录的这首词的“来历”,但其必有“来历”,必非出于袁纯或王熙或与他们同时代人的伪造却是肯定无疑的。究竟它是来源于南宋人的著述,抑或是来源于元代人的著述呢?我们在目前虽还不能确说,然而我们却可以断言:二者必居其一。
第四个应当解答的问题是,能不能因为《满江红》中“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就可以断定它是明代的具有文武全能的王越一类人所作的呢?
有了上面所做的解答,这一个问题原已相应地得到了解决;但是,夏承焘先生所举出的那些论据,在上文中却还大都没有加以论辩,也许有人会因此而还感到不能涣然冰释,没奈何,且再分为以下诸层次,专对夏先生所举论据进行商榷:
1、我以为,《满江红》词后半阕点出的贺兰山与匈奴,全是泛说、泛指,不应当过分拘泥于贺兰山的位置所在。因为,既然把斗争对象称作匈奴,则不但在河套地区的贺兰山可以入词,就连阴山以及更西边的祁连山也同样可用。似不应因此而责备作者“方向乖背”。稍晚于岳飞的辛稼轩,也是一个毕生以抗金为职志的人,然而在《稼轩词》中,既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之句(《水调歌头》),又有“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之句(《满江红》),我们将责备稼轩“方向乖背”呢?还是将不承认这两首词为稼轩的作品呢?显然这都是不应该的。
2、在夏先生的《考辨》文中,曾据北宋释文莹的《湘山续录》而引录了姚嗣宗在庆历年间(1041—1048)的驿壁题诗云,“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穷鳞。”然而,众所周知,南宋人诗词之脱意或模拟北宋人诗词语句者,实不乏其例,姚嗣宗诗在北宋后期既已广泛流传,则南宋初年的岳飞,把此诗首句亦换为“踏破贺兰山缺”而写入其《满江红》词中,这岂不也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件吗?既然是把前人成语作为典实来使用,那当然就不存在“泛指”或“实指”的问题了。
3、南宋人诗中以大散关作为宋、金边界的,虽确实有之,但那些诗全都是宋、金订立了“和约”,把东起淮水中游、西至大散关划作两国分界线以后所赋写的,而宋金“和约”却是在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才订立的。在此以前,南宋人万万不会把大散关实指为宋金分界,自然更不能要求岳飞在填写《满江红》词时就率先这样做。夏先生所举陆游诸诗,更皆为宋金“讲和”二三十年以后所作,不能用来作证。
4、专就“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孤立地进行推敲是大有问题的。因为,此句之上是“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诸句,如只就“贺兰山”句而断言其为明人所作,则势非把“靖康耻”云云断定为“泛说”或“泛指”不可;但是,亡国惨祸是何等严重事件,而容得词人信手拈来,对明朝时事进行暗射、比拟耶!土木之变虽是明王朝一次灾难性事件,但不久明英宗即被放回,何得与“犹未雪”的“靖康耻”相比拟呢?更何况,在此句之下,还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一句,这与明朝的实际情况也完全不相符合。在明朝统治期内,中原与河朔地区的所有山河全未为鞑靼所攻占,怎么会激发出写此词者要去“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念头呢?所以,若不把这句话与上下文联系起来进行理解,那是不会得出“达诂”的。
5、《满江红》词前半阕中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两句,与岳飞的生平事功十分吻合。若把此词作者定为王越,而且定为贺兰山捷后所作,那就必须把“三十功名”改为“七十功名”才行。因为,当取得贺兰山后之捷时,王越已经七十余岁了。而且“八千里路”之句也与王越行踪不符。若谓此词乃其幕府文士之作,则两句更全无着落了。
6.元人杂剧“宋大将岳飞精忠”中乙个冒用“两红”词中语句,这似乎只能怪这本杂剧作者之所见个),个应再做过多的推论。其实,何止是不曾引用《满江红》词中语可,就连雷飞与在“题记”当中和《题新淦萧寺壁》等诗当中的那些富有发国热情和报仇雪耻决心的语句,也全不曾被引用过一句。我们又怎能据此断言这些“题记”和这几首诗全非岳飞所作呢?如果这本杂剧的作者所依据的只是一篇《岳飞传》(在《宋史》行世之前,宋章颖的《南渡四将传》已流行甚久),则其对岳飞作品之概不引用,便完全可以理解了。(这本杂剧竟至把女真人写作契丹人,也可见其知识面是很有局限的。)
7、王越在弘治十一年取得的贺兰山后之捷,诚然“是明代汉族在贺兰山抵抗鞑靼的第一回胜仗”。但是,王越在取得了第一回胜仗之后,由他自己或其幕府文士把这次战功记录下来,则直接敷陈其事,亦犹勒功燕然,事极平常,本不存在什么犯嫌疑、犯忌讳的事,无所用其顾避,为什么竟要牵扯到北宋的亡国,并要嫁名于岳飞呢?这显然是很难解说的。
8、如果说,此词虽为王越或其幕府文人所作,但当其写作之初,本即要托名于岳飞,因而,此词中的“三十功名”、“八千里路”诸语固都切合于岳飞身世,即其后半阕中语句,除“壮志”“笑谈”二句外,也全都是实写而非用来影附明朝的时事、政局的,我以为这也同样很难解说。因为,不论王越或其幕府文土,总都了然于岳家军抗金的主攻方向及其所悬拟的进军路线,是要经由河部“直捣黄龙”,怎么会硬把不在这条行军线上的贺兰山填写讲来呢?若出自不明悉贺兰山方位之人犹有可说,王越及其幕府文士则必定能避开“当时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而不应故意露出这一破绽,留与后人作为辨伪的证物和根据的。
以上的论证,我以为是可以把余、夏两位先生所提疑点一一祛除,使其不再存在的。既然如此,则其最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我们进行讨论的这首《满江红》词,既不像余嘉锡先生所说,是出自明人伪托的一个赝本;更不像夏承焘先生所说,是明代首次战胜鞑靼族的主将王越或其幕府文士所作;其唯一毋庸置疑的真正作者,只能是南宋名将岳飞。
(本文原载于《文史哲》杂志1982第1期,2020年6月收录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史交融 ——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