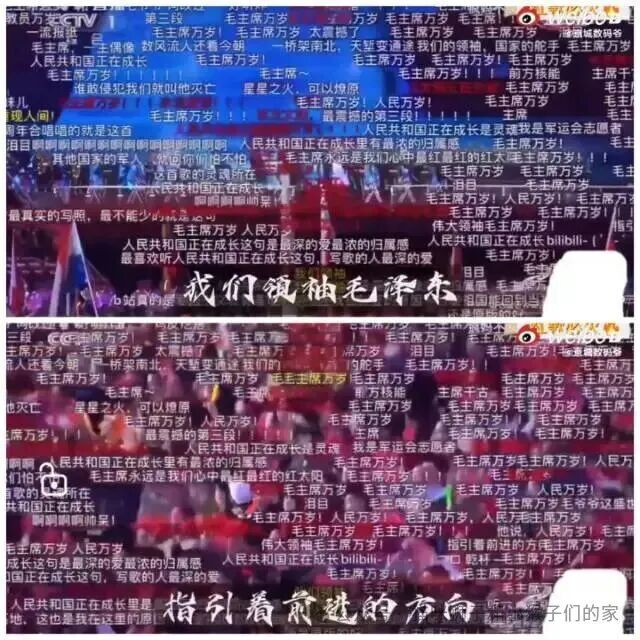孙锡良:戏里戏外

戏里戏外
在我很小的时候,村里便有戏可看,主要是地方采茶戏,偶尔也能看到文曲戏和黄梅戏。按今天标准,当年看到的各类戏都只能算是土戏,戏台土,服装土,道具也土,碰到没电的时候,挂几盏大油灯或者点个火把,也可以锣鼓喧天地唱起来。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新玩意儿多了,年轻人都把看戏的人说成是老古董,而我恰恰在这个时期就爱上了这门艺术。换句话讲,我还没长大就成古董了。说喜欢看戏,当然也是朦胧的,并没有看懂什么门道,就喜欢那种不同于现实生活的服饰、腔调及表演方式。真正对戏剧产生一点通感大概是在结婚成家以后,央视戏曲频道成了我的好老师。
在正式品戏之前,很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个人对中国戏曲艺术的文化理解,就算是入戏前的一点铺垫吧!
中国历史虽然很久,但戏剧史并不算长,按目前公认的说法,十二世纪以后才诞生有传承价值的戏剧,也就是宋朝晚期,比希腊和印度晚了一千多年。中国的戏剧文化与希腊及印度的戏剧不同之处在于,希腊和印度的戏剧起初并不是大众文化,是贵族文化,这种贵族文化又不同于中国汉唐宫廷的歌舞女表演,它包含剧本、演员、剧场、观众和戏台五个要素。
中国宋以前并没有类似的专业演出队伍,也就没有定式戏剧。宋代是一个转型期朝代,饱受侵略,疆土亦大幅缩水,避居求安,导致人口往中南部地区高度集中,农业文化开始向市民文化过渡,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的汴京,人口已达一百多万,禁军数多达几十万,承平日久,国家无事,市民闲暇时间便多了起来,戏剧文化由此兴起实属自然。
宋朝另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方是杭州,“西湖歌舞几时休”还不足以描述当年盛况,《武陵旧事》中有记载:遍呈队舞,密拥歌姬,脆管清吭,新声交奏,戏具粉婴,纷然而集,箫鼓振作,耳目不暇给。
比较遗憾的是,中国戏剧自诞生起便是俗文学和俗艺术,产生于民间,根植于民间,发展于民间,杂耍和俗曲通常让文人不屑于研究戏剧,历代文人都喜欢求雅脱俗,只有梨园戏子混在市井,倡优所扮,谓之戾把戏。文人不屑戏剧,但也不是不看戏,只是总抱着“既好之,又耻之”的虚伪心态,仕大夫承认游戏人间,戏文倡优乃供笑工具。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看出文人对舞台戏剧的不尊重,自宋以后至清朝中期,几乎很难发现有戏剧脚本流传下来,更没有看到科举考试里会考到戏本,这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待遇就大不一样了。
到了清末,文人仍是把戏人当作玩物看待,只有少数官宦对上门入户的戏班有稍许尊重,关键看班头如何能以戏文讨得主子的欢心,除能歌楼作乐散闷消愁,还要能让戏里的词句唱到戏外人的脸上,做场作戏,要谎人钱,恭奉造神是少不了的。
民国之后,戏子是否步入正位?也没有。直至解放前,中国还是有句俗话:儿女不争气,不是学打(武),就是学戏。无论京班、汉班、浙班还是沪班,无论多有影响的名伶,都不过是权贵或江湖首领的玩物,给你脸,就很有脸,不给你脸,戏台就没了。
千年戏子,只有到1949年后才开启了新节点,新中国把“戏子”改叫“文艺工作者”,并且成了“国家人”。现在,又流行叫戏曲演员或者称角儿。
仍在流传的中国戏剧种类凡几百种,只有真正的戏剧工作者才能从艺术的角度做全面分析。这门艺术的魅力在于其对唱腔、表演、文学、历史、道具等多种文化的高度融合,因地域广大和风俗差异显著,戏剧艺术内部又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样性。作为一看戏人,唯一能触点皮毛的切入方式恐怕只能就戏论戏了。
如果把戏文也视为文学的一个分支,可能很难入文学大家法眼,它比文学大类的戏剧著作又要低上一个层次,最大原因在于戏本的俗性。所谓俗性,既是指它的民间性和大众性,又指它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等级差距。然而,正是因为中国戏剧的俗性才决定了它的普遍性和生命力,只有俗了,才接地气,才入民心,几千年的面朝黄土和听天由命,几人能雅?雅者多矫情,不附也罢。锡剧《珍珠塔》里<前见姑>部分唱段就是民间麻衣相术的活生生体现,尖酸刻薄的姑母把人间世太炎凉在亲侄儿身淋漓尽致地展示透彻。
姑唱道:
方卿若有高官做,日出西方向东行;
方卿若有高官做,满天月亮一颗星;
方卿若有高官做,毛竹扁担出嫩笋;
方卿若有高官做,铁树开花结铜铃;
方卿若有高官做,滚水锅里能结冰;
方卿若有高官做,井底青蛙上青云;
方卿若有高官做,晒干鲤鱼跳龙门;
方卿若有高官做,黄狗出角变麒麟;
方卿若有高官做,老鼠身上好骑人。
……………………………………….
稀毛瘌痢发不好,日后难戴乌纱帽;
猢狲爬树手不好,祖传家产守不牢;
左肩低来又肩高,怎能身穿大红袍?
鹭鸶脚杆细又小,高靴怎么脚上套?
《羞姑》的“十好”与“十不好”可谓是唱到绝无可绝,堵气与解气之间,全仗姑侄针锋相对,此处不作详解。
如果从戏剧大类上对戏本的文学性进行细究,个人以为,近代出现的越剧可以说是将文学与戏剧的结合美推向了顶峰,这与江浙地区厚重的文化积淀是密不可分的。“门掩了梨花深院,粉墙儿高似青天”把那个多情张生幽会的急切心理映照得栩栩如生,《琴心》何止是红娘在理丝桐,天下的闺女哪一个不想把风月弄?步摇得宝髻玲珑,裙拖得环佩叮咚,娇鸾雏凤失雌雄,伯劳飞燕各西东,一曲断肠夜,千古此心同。如此妙句,放在任何名著佳作中都不会退色减分。
骚人十支曲,捌玖不离情,爱情永远是文学的主角,戏剧自然也不会例外。浪漫的许仙与白娘子,法海的水漫金山,隔得开恋人,淹不没情愫;大爱的七妹与憨厚的董永,仙人感应的奇遇背后是穷人爱情绝望后的奢望;高洁的公主与多情的沙漠王子,绝世情缘中包含着忠贞与坚守;就算是当了皇帝,对于爱情,也会充满着无奈与痛楚,《长生殿》里无圣旨,马嵬坡下有悲情,玄宗再即位,也只能等着去蓬莱岛上会旧人。国破家亡之下,《西凉辽宫月》竟把当年身在逃都重庆的周恩来同志唱得泪如雨下。
悲情戏表现手法不全在戏词和剧情,更在唱腔,豫剧唱腔可算得上悲情戏的突出代表,它抑扬交错,铿锵有力,吐字清晰,行腔酣畅,富于表达人物情感,加之枣木绑子拍打的特殊效果,每每能让观众深入戏中,《三子哭坟》、《清风亭》、《大祭桩》、《卷席筒》、《程婴救孤》等戏可以唱哭一院观戏人,看一次,让你哭一次。
我们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换句话讲,也可以说成:戏即世事,世事在戏。戏里到底有哪些人生与事呢?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着那当上西凉王的薛平贵,忠贞守节,苦忍清贫,终换得与代战公主东西并立,这是多么美好的结局啊!当然,与之相对,戏剧中也有陈世美忘恩负义、抛妻弃子、绝情秦香莲的反面教材。大义灭亲不只有包清天,还有不畏强权舍生取义的才女李素萍,《陈三两》的骂堂一节既展示了卖文不卖身的烈女气节,又展现了不离不弃的姐弟深情,既催人泪下,又发人深省。七品芝麻官冒犯诰命,弱书生斗胆直参严嵩,恐怕都只能在戏里才能看到。《一缕麻》里的痴呆周少爷,《卷席筒》里的仓娃,《五女拜寿》里的三姑娘,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善良形象,都是好人遭难、结局美好的理想主义。每次观演,总是由淡然入场到泪流满面,再到轻松微笑结局,虚迹能谈实事,假象可传真情。
讨论中国戏剧,最后,我必须讲到新中国的现代戏。古装戏,多重借古鉴今,现代戏,重在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突出鲜活的人物特性。因某些历史原因,新中国现代戏于近四十年被扭曲得面目全非,“八个样板戏”成了年轻人对现代戏的固化认知。殊不知,若单从剧本创作的时空段而言,新中国现代戏有资格占据整个中国戏曲史的重要一页,即便是京剧,也不只有八个样板戏,全国各地至少创作了100部以上,其艺术水平和思想水平之高,不能说前古后无来,过去一百年,很难有任何文化成就能出其右,未来一百年,中国不可能再创作出超越毛泽东时代的现代戏曲。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不会再有那样真实、健康、纯净和无私的创作环境,不由钱推动、不为钱编剧、不为钱演出的纯艺术土壤已成绝唱。国粹整理工作比较完整而有体系,今不做赘述。地方现代戏曾经也是精彩纷呈,总计不下千部。豫剧《朝阳沟》、《刘胡兰》、《李双双》、《小二黑结婚》等都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剧目,每一部戏,都是共产党人精神面貌的一个缩影。评剧的《杨三姐告状》、《黛诺》、《银河湾》、《弄假成真》、《高山下的花环》等曾让观众印象深刻。《打铜锣》,《补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何人不知?哪个不晓?
戏剧发展到今天,看似繁花似锦,却又孤衣寒兢,现代化正在吞噬现代戏与古装戏,无论是戏剧中重复着的道德伦理和家庭爱情,还是表演过程的唱念作打与情景切换,都在与年轻人的文化需求拉大距离,这门艺术正在畸形地行走在封闭与委屈之中。封闭,是指大戏院和大演员与广大观众的距离在不断变大,普通人看不到大戏,看不起大戏,大牌戏角不属于大众娱乐。委屈,是指多数地方戏班缺资少银,虽不缺底层观众,毕竟简陋的土台无法滋养咿咿呀呀的繁荣。“优伶之子恒为伶”是一种悲哀,“优伶之子不为伶”难道不是另一种悲哀?再过百把年,后人恐怕连借戏浇愁的机会也没有了,但愿他们能过得更自由真实。
于我个人而言,看戏,既是半懂半不懂的所谓艺术欣赏,又是寻找避世畏俗的假想桃园,自身不可能伟大,却可以与戏台圣贤同行,思想意志不可能自由,但惬意于跟戏中侠士的勇敢产生共鸣。天下事无非是戏,世间人何须弄真,《窦娥冤》的提醒与虚实从来都不能掉以轻心,台上英雄且放眼底,宦海忠佞认准当时,开心才是福,观戏不古人。
附言:
我为何会讲感谢“芦沟桥事变”?7月7日,我在微信圈讲过感谢“7.7事变”,原因很简单,没有“芦沟桥事变”,就没有中国的全面抗日,在此之前,蒋军与日军相处友好,两军军官时常相互邀请举办酒会,华北东北的日军如同身在自己国家,日本在华北东北的军事和经济组织蓬勃发展,有了事变,才有转机。悲哉事变!幸哉事变!
写于2019年7月7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