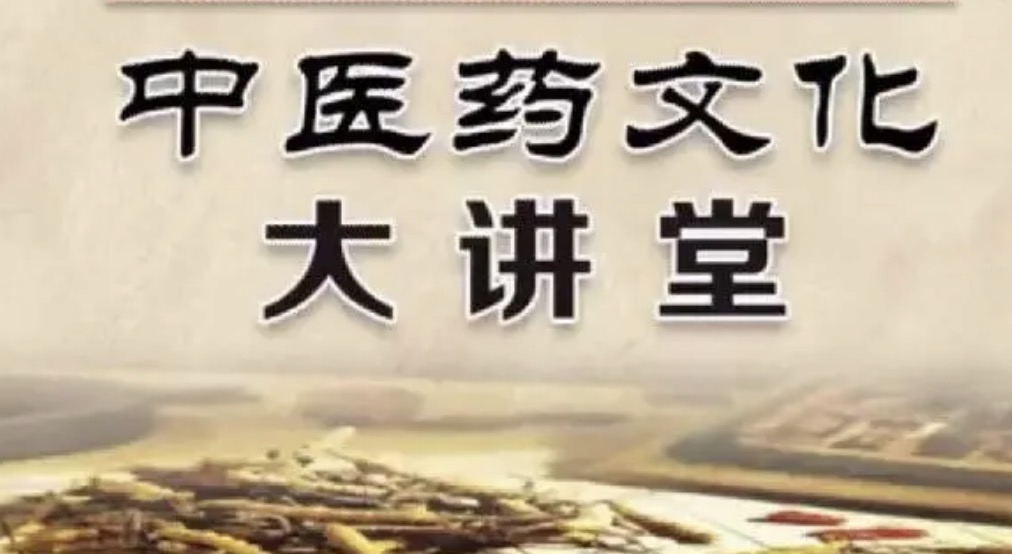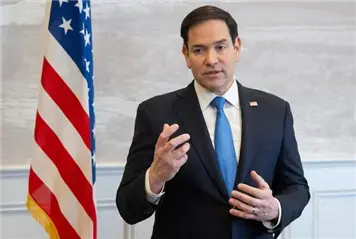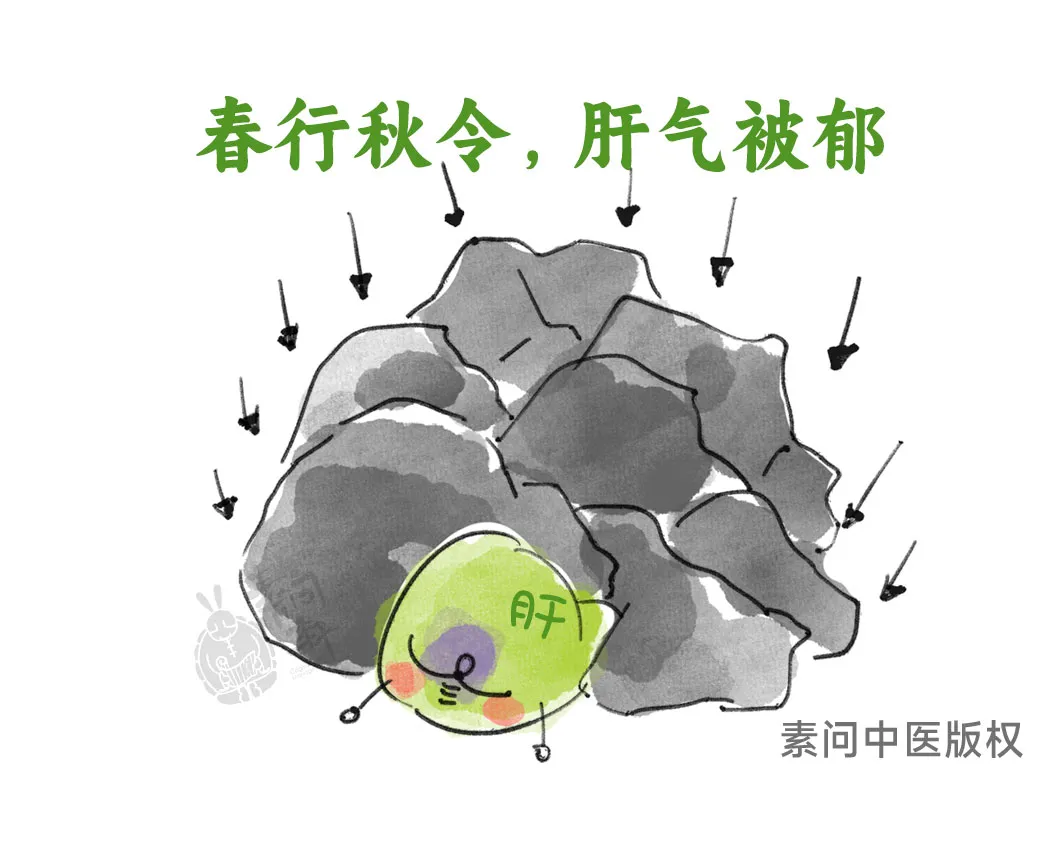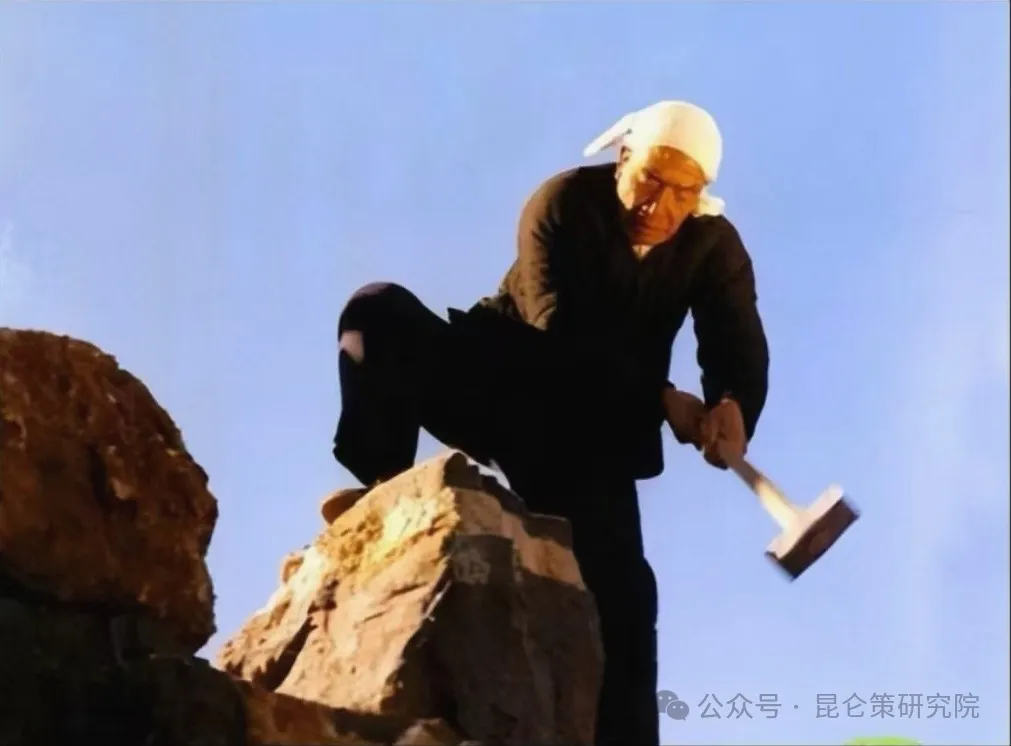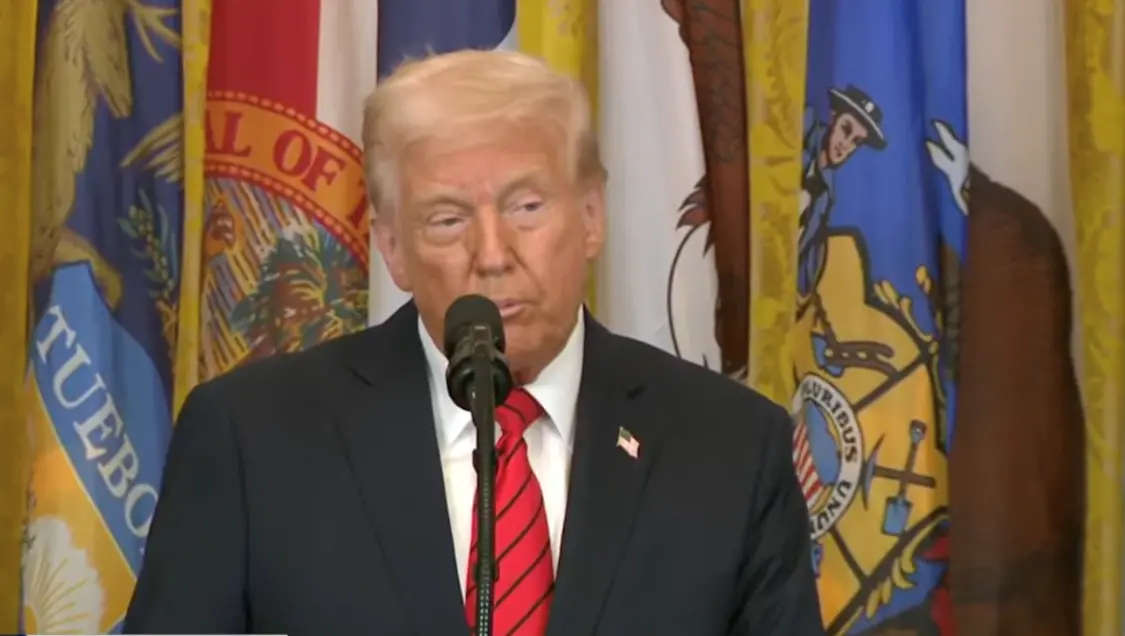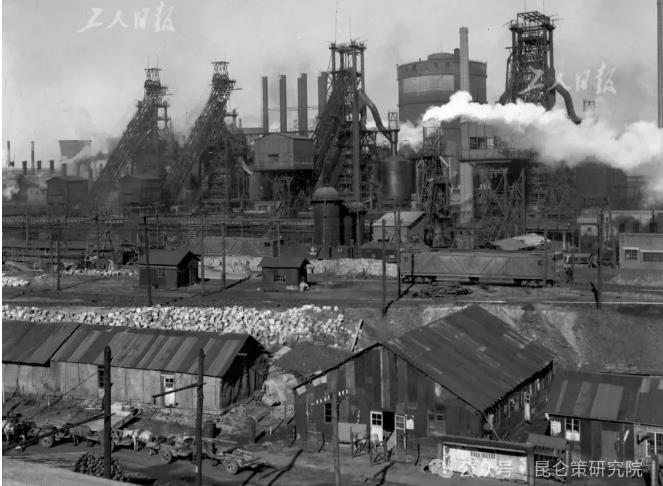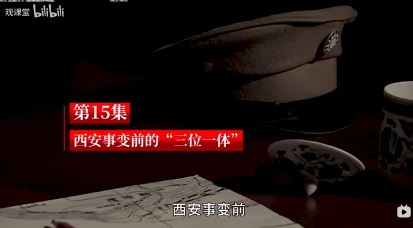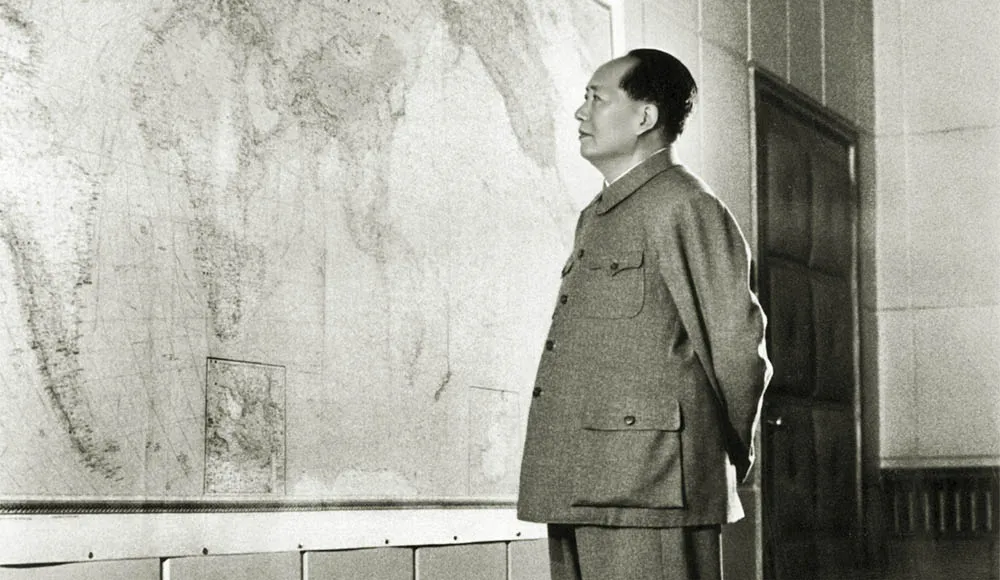周立波败不在“冒犯”,而在“局里局气”越来越浓!
周立波粉丝似乎注意到,“海派清口”和周立波复出的脚步越来越近,但满腹狐疑的是不再熟悉的“上海方言”,而是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最要紧的是假借“敏感”话题炒作,实质一股“局里局气”。
忽地想起少不更事!
我爸从不笑,懂事后大概读中学吧,在我妈的诱导下渐渐原谅了他――不再有事没事吵,老妈说“原谅他!他没恶意,只是性格”。
但!不全是性格,其实他是会笑的,第一个会“笑”的场合是守在电视机旁看周柏春和姚幕双表演的“上海滑稽”――这种场合我们也会笑,但“笑”不出声,也不写在脸上,只是心里有种愉悦的感受;他也笑不出声,但明显的写在脸,他的喜悦感明显的写在脸上――明显的感到他与以前不是同一个人,他不是一具僵尸,而是有表情的人。
这是我们兄弟几个共识的,第二个会“笑”的场合是见到邻居,碰到邻居见面会微笑的,但只要一跨进门槛就立刻收容,一付肃然“僵尸”相――这也是我们兄弟仨的共识,并几乎默契一致:他对我们不好,我们就得“对付”他!
老人家已在天上,会不会原谅兄弟仨默契一致“对付”他的呢?是的,最迟中学毕业那个年龄已不再纠结这个事,已懂得很多,并每次周柏春和姚幕双表演场合总会浮现老爸脸上的“笑”意,其他值得回忆的温馨场合几乎记不清了!
爱屋及乌,不但喜爱这门艺术,也喜爱由此衍生的一切事物,包括周立波的“海派清口”。
“上海滑稽”在北方就叫“相声”,从周柏春和姚幕双的表演路数上看,很可能就是从“相声”得到灵感,用吴侬软语替代铿锵北音而已,但效果却是大相迳庭,竟然能使对“相声”没有“笑”基因的人――比如我老爸那种吴越类型的人――也能露出笑意,艺术上肯定一脉相承的。
据说周柏春和姚幕双只收了一个徒弟,就是今天大红大紫的周立波――怎么只收一个,完全偏离了原来的艺术形式?我也不是门里的,不知怎么回事,但我宁可相信是真的。但我很快不喜欢,我曾写过几篇解释了原因,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曾写过几篇对“海派清口”和周立波本人的看法。
最初的原因就一个――众所周知他的“咖啡大蒜之喻”。
就艺术上人们完全可以接受“咖啡大蒜之喻”,事实上“海派清口”就形式上更接近美国传进来的“脱口秀”――号称“冒犯的艺术”,这点“冒犯”不能接受,那么嘴巴除了吃饭就不能其他用处了!
不在冒犯,不在艺术形式,而在拿捏的“度”。
“咖啡大蒜之喻”显然过了那个“度”,就象今天杨笠拿“两性话题”开玩笑过了那个“度”。拿南北人民的“生活习惯”、“语言腔调”开开玩笑,拿“两性话题”开开玩笑有啥大不了的――事实上他也是“相声”经常用的“包袱”,或“上海滑稽”的“噱头”, 这玩笑开不起,活着太累了。
今天不谈杨笠――关于“她”已有共识和结论,十多年前我对周立波和他的“咖啡大蒜之喻”写过评论:他已背离了“开玩笑”,其实是当时意识形态的某种“反映”――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两极分化”严重,相当部分“跃居”者不是通过他们自述的“智商”、“劳动”、“努力”、“机遇”诸如此类达到,而是明显的“不公平”甚至“暴力”手段达到,一旦达到就会营造舆论,“创新”意识形态。“喝咖啡”只是某种“意会”而已。
以周立波的“智商”,他未必理解其中的“意会”,他只是凭直感领悟其中的“价值”――他要凭此收获“流量”。
当时的周立波没什么大“恶”,只是要获取“流量”,活着的人谁不为此奔波劳累呢?但当有人善意提醒(包括鄙人,我)不可越界,许多人已经被你伤害,被严重的伤害,“赌棍赌一把成功后倾向于舆论上碾压他人”不能在你身上重演……
诸如此类善意提醒在他完全耳旁风,并且愈益得意来收割流量――直到被郭德纲等北派笑星一致“黑脸”连续击打,他才有所收敛!
十多年前写他时仍不认为他“人品”上有瑕疵或其他问题,而是“智商”和“情商”有缺陷――他没法辨认人们的“悦感”与“羞辱”,当时的他没法分辨这根“界线”在哪,虽然活了三十多岁,但是这个能力他没得到成长,当年的他因此失败了!
一晃十多年过去,直到后来被外人扇嘴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美国人扇嘴巴,美国人可不会惯着你!此后我也不再关注他。
最近再见他,似乎“第二春”,许多短视频上火得很!但风格转变――明显的转变是,已不再“上海方言”,而是一股蹩脚的“普通话”口音――这才陡然记起,他的风格早已转向,早已不再“吴侬软语”的“海派清口”,并且话题和内容浓烈的“敏感”味――事实上他从未有过“相声”或“上海滑稽”的民俗趣味性。
十多年后待再写一篇,怎么个写法?
×××××××××××××××××××××××××××××
脑子一直在盘算,怎么个写法?
十多年前写他:未必“人品”有问题,而是“智商”和“情商”有缺陷,他达不到,他只能理解“流量”而没法辨认正常人的“悦感”与“羞辱”,他失败了,他没这个天赋吃这碗饭,还是换个行当吧!
今天呢?一直冥思苦想这件事!
“快手”上忽地看到一群人在争吵,一个白燕升另个叫“安万”的人,围绕他俩“快手”上吵的厉害呢!我静静的围观已有好几日了。知道了大概意思,也想下场“置喙”几句,刚待开口,忽地传来当地政府竟也分成两派,一派支持的自不必说,另一派态度狐疑,非但冷淡,竟有派人“力劝”的?
直觉其中复杂,或已超出白燕升与安万的艺术见解,或涉政府“管理”等诸多不便之说;等等看再说吧。
但就七嘴八舌看,围绕着一个主题,几十年来的一个不变主题: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怎么和谐共存问题。
是的,这个主题我是可以写的,不必等等看的;白燕升我熟知,显然他是代表“阳春白雪”派的,那么安万只能代表“下里巴人”了,但从白燕升力辩看他也是支持“下里巴人”的,争吵的原因是其他――难怪政府管理当局也分成两派。我从现场录像看,人潮涌动,大家一起跟着唱,浓浓的“关陕”味,并且和唱者各个情绪饱满。
这不就真正的“秦腔”?以前看到的也许“舞台腔”,白燕升误把“舞台腔”当“秦腔”――轻者误导“知识”,重者误导中国文化和中国认知!
确实,本想下场谈谈这个看法的,刚待开口传来当地政府的狐疑态度,直觉其中有蹊跷,不便冒昧,不如借“海派清口”与周立波往事谈出来吧?
“海派清口”与周立波一再喊响“接地气”――但他一开始就偏离了这个方向,并且是他故意设计。
十多年前我写他曾有个细节:那时我还年轻,与同学们有所交往,那时我从他们得知一个消息,一些同济或复旦的同学会组团购票去看他的表演,显然其中有商业操作原因(也许团体购票价格很“香”),但是同学们为何并不拒绝,并且大多数是外地同学,上海本土话生活用语还能听懂,舞台上基本听不懂的,同学们为何踊跃?
我听外地同学说,正好借此机会领略“真正”的上海音,真正的上海口音。是的,同学们是真的,宿舍、饭堂、校舍三点一线度过美好四年,可怎么就算来过上海呢,以后人生怎么证明呢?
“海派清口”深谙同学心灵,于是借着“商业”有了那时的亲密接触;但我以为有着更深用意,拉近同学们未必最好的“接地气”――这是我十多年前的看法,因此将这个细节写了进去;十多年后再看“接地气”的最后标识“本土方言”也不见了。
由此可见,“海派清口”设计初衷就是个噱头,“上海方言”+“接地气”就是个噱头,他真正要走的是“高端”+“精英”路线,他的同学们加持只是个门面,“喝咖啡”是不得不的“宣示”――他的“智商”和“情商”到此为止,只能靠露脸就被打的方式来“宣示”。
走“高端”+“精英”路线,不说“普通话”是走不通的,最近见他复出意欲“第二春”忽地有所感悟。
设计初衷有误,以后可否更改?
很难,但未必不可,对“海派清口”、周立波以及他的团队,我的建议是:
(1)坚持本土方言,别假借“普通话”实质一口“局里局气”;
(2)内容贴近世事百态,别意图“敏感”招徕;
(3)我老爸那代人还没死绝,编几段到他们那测试测试,他们脸上有笑意,或许你就成功了,离收钱不远啦?
别意图同学们“高智商”掌声,你知道他们背后怎么踩你的吗?一个瘪三,上海小瘪三!咖啡从早喝到晚仍然瘪三相!
×××××××××××××××××××××××××××××
最后借着此机会再说说白燕升与安万之争吧。
“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争在当下中国是存在的,从郁钧剑与赵本山的“草根辩”,到那英与刀郎的“主流歌坛辩”,再到郭德纲与姜昆的“三俗辩”,再到今天白燕升与安万的口舌之争,每隔几年来一次;
这在当下中国不全是观念之争,而是有实质意义的,上面所提几个“阳春白雪”代表事实上还拥有相当的“权利”,他们还对外声称“国家形象”、对外代表“民族文化”,拥有可观的物质资源和经济支持;
但从“草根辩”、“歌坛主流辩”、“三俗辩”的最后民意看,谁在理?谁不在理?这都明显摆着,一开始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阳春白雪”派最后一个个都败下阵来,一开始就被踩的“下里巴人”却在真正的“代表”着!
――――【最近刀郎火的要死,传有国外机构或团体纷纷邀请邀请,我劝刀郎团队慎重,最好别去,咱不缺钱,更不缺那个“世界影响力”,谁知邀请是为了艺术还是咋的,多事之秋还是慎重为好。
但也反证:一开始就被踩的“下里巴人”却在真正的“代表”着,代表着华人,代表着我们民族。
是驴是马拉出来溜溜,谁是“代表”?并不期待分得你现实中一杯羹,只是希望保持庄严和礼貌,别有踩没踩的踩踏他人】――――
当然最后再次声明:这篇文章不针对白燕升与安万之争,他俩之争具体情况莫明,要等等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