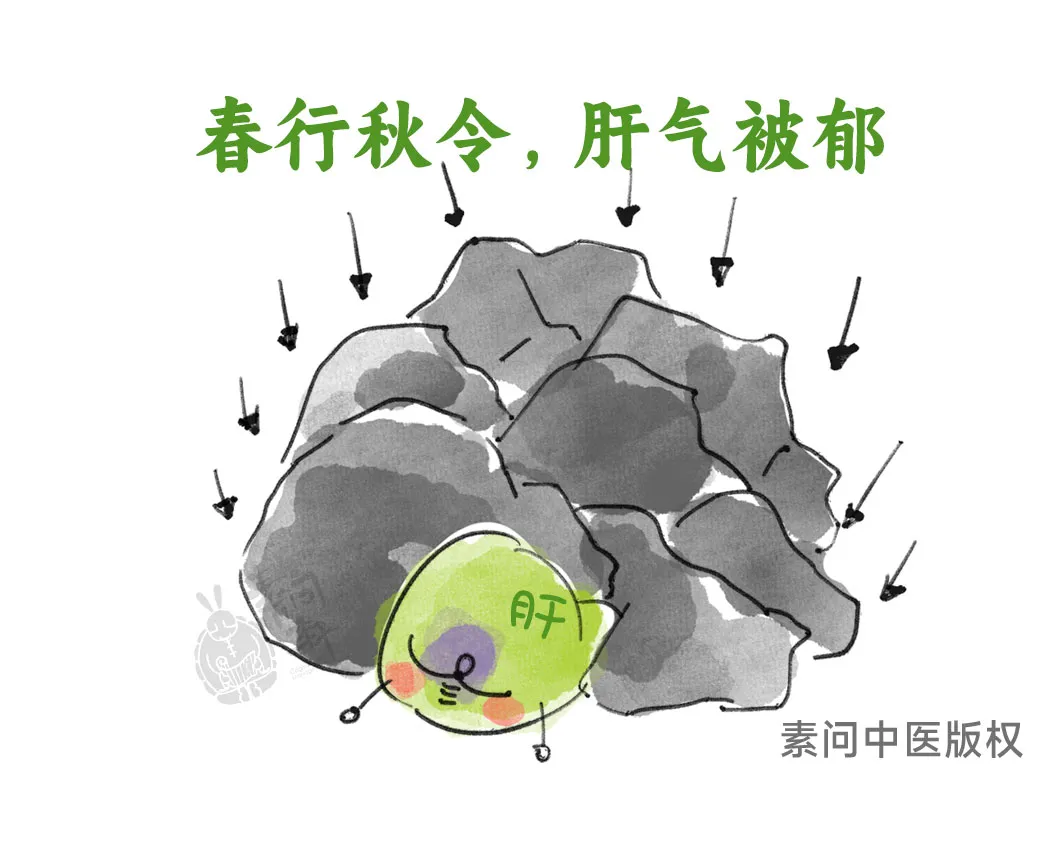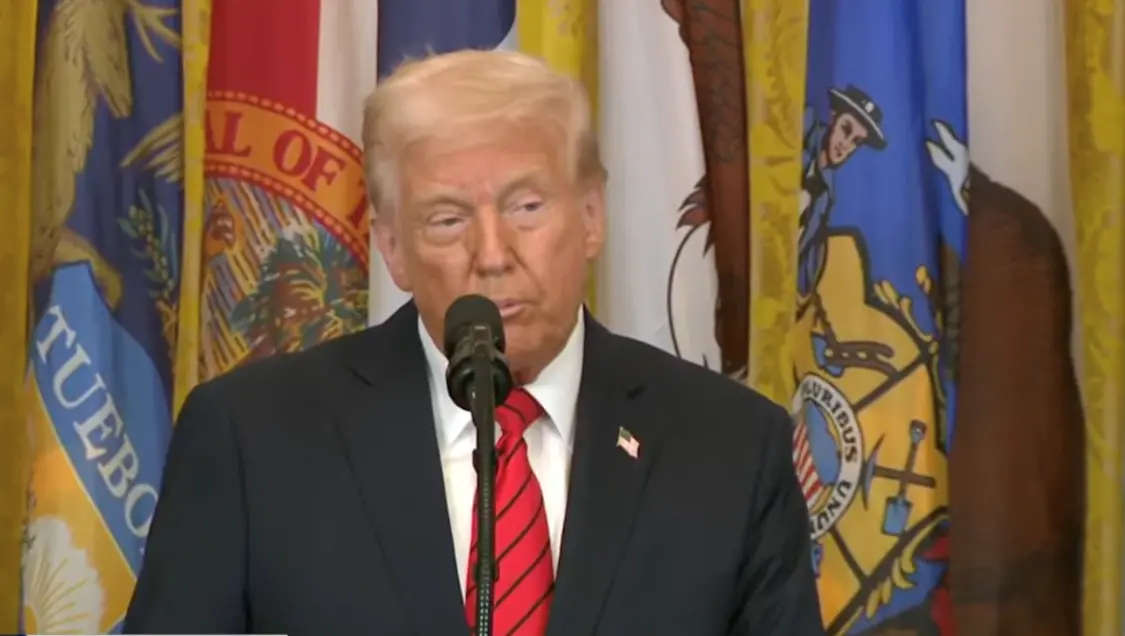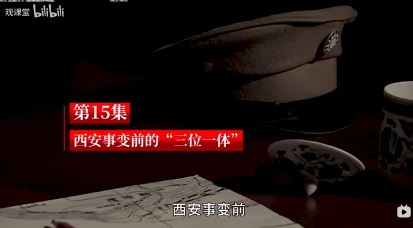龚婵:看到私有制
其实,每一个无产阶级男女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共同解放自己的使命。
文 | 龚婵
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在主张男女平等的问题最多能看到的是父权,却一直看不到父权因何产生;反对父权,却从不反对产生父权的经济基础——私有制,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自相矛盾。越来越困于性别,困于对表面符号的纠结与编造,而对导致压迫的真正原因置若罔闻,这是资产阶级女权的盲目浅白;鼓励所有女性走向权力中心,但实际只有资产阶级女性可以生辉;拥趸着消费主义的皇冠,主张中自觉不自觉拥护着改良着资本主义,认可着私有制等级的金字塔并且要站上去——而这恰恰压迫着任何一个因没有生产资料而受雇佣劳动摧残的无产阶级妇女。资产阶级女权就是这样高呼着平等与解放——而这正是最最虚伪之处。
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总是抽象地认识“人”,不明白人是历史条件下社会关系的产物,社会关系是生产关系塑造的,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塑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抽象的属性塑造了人。并不是自人类诞生就分有的性别导致了不平等,而是私有制在人类社会的广泛确立导致了一切不平等。不少女权主义是有了解过人类学历史的,如果她们没有秉持着唯心主义史观断章取义的话。翻开人类的历史,就会知道人类社会最初并没有私有制,人类最初过着氏族原始共产的生活。那时候极其少数的生产工具和田地是一整个群一起使用,人们赖以生存的模式依然是外出采集寻觅生活资料,然后一起享用;不论是家庭的事物,还是外出采集打猎的分工,都不是私人的事。一个社群中的女性不论在生活资料的获得,群的决策,还是内务劳动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女性不论是选择专门负责采集,还是选择专门负责内务当”家庭主妇“都不影响她的社会地位。在一些可考的历史里,一些妇女恰恰是在家庭内务中发挥主导,而受到尊敬。因为社会大分工尚未出现,那种共产经济家庭模式里的内务和外务是同等重要。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由于社群生育的崇拜、后代对母体的确定,女性是拥有更高的地位。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详细列举了众多人类学历史研究的成果,列举了民族社会大分工前不同民族原始社会的生活面貌,都反映出这种共性。在这里,或许要庆幸,在人类文明整体进入私有制社会后,并发展到资本主义时期的时候,还有局部地区保留着过去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模式。让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人、以后的人能看到原来那种人与人之间,男女之间平等的公社生活不是乌托邦,而是早就存在的,并且在现代地球上依然存在着——翻开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在第一章的第二节“食物采集者的生活”中列举了传教士在20世纪50年代对加拿大东部蒙大格拉斯—纳斯卡比印第安人的考察,发现他们社群中的两性关系依然如17世纪发现的那样平等,不论男女都拥有高度的自治感和安乐,这里既没有阶级社会的主人和奴隶,也没有家庭里的主导与附庸。
上述这种例子穷举不尽,历史的考古和发现正说明,男女既然是可以真正平等的,而且老早就存在过这种平等的。那么出现男女不平等的源头绝不是“性别”。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后来的不平等,怎么出现了社会的主人和奴隶,怎么出现了家庭的主人和仆从?那就是私有制的诞生。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金属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生产领域的扩大带来社会财富的富余。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诞生》中指出财富一旦归家庭私有并迅速增长起来,就给了原始社会共产家户经济强力的打击。生活资料的占有开始不平,最重要的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出现,私有制诞生了。我们知道,私有制产生后,社会开始分裂出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和不占生产资料的被剥削阶级。社群公社那种共同耕作的土地被分配给各个家庭私人占有,社群的共有转向私有,个体家庭就成了社会的最小经济单元。原始氏族社会那种共产的生产模式解体了,共产经济的家庭也转向了私有制下个体的家庭,原始共产中家务的料理也失去了它的公共性质,它与个体家庭以外的社会不相干,这就变成了一种私人服务。这时候家庭以外的分工也不同了,这种家庭劳动同社会上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相比变得相形见绌,一个人的家务劳动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因为在家庭中占主导而受尊敬——这就是私有制下的家庭,谁是生活资料的主导谋取者,谁就是这个家庭的主人,而只限于家庭劳动的人就不可能得到平等地位。我们都能看到,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后,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时代到来前,不论是在奴隶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那种农耕经济、畜牧经济模里,男性因为体力因素占据了谋生的主导,这种家庭的大家长,便也有权支配家庭的其他成员——这是私有制下形成的父权制、家长制。
所以,正是因为诞生了私有制,社会才有了阶级的对立,是因为私有制摧毁了原始共产经济,社群公社财产的私有化,让个体家庭成了社会的经济单元,父权制才诞生了!并不是因为社会存在男性,并不是因为家中有爹,父权才会诞生!
当资本主义工业化到来,工业革命中大机器工厂碾压了传统手工体力,男女的体力差别在大机器的威力面前变得渺小。大机器齿轮的转动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让大批妇女进入社会化大生产,也进入社会的运动中。恩格斯前往英国工业区所做的调查中,已经看到许多工人家庭里,女性和儿童因为某些条件符合资本家生产的需要而比一些成年男子更受欢迎,于是在一些家庭中,女性反而发挥着经济支柱的作用。所以恩格斯才会说:“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所以,以上野千鹤子为代表的这类资产阶级女权主张给家庭主妇发工资,简直就是对女性解放事业的第一步的阻挠!因为越是让家庭中的丈夫支付妻子家务劳动的工资,就越是造成家庭中妻子对丈夫的依赖。上野千鹤子也主动提到一些听她课的日本女孩讲述她们或因为忍受不了工作的摧残,或是因为进入劳动市场困难,工作难找,而选择把家庭当避风港。只要丈夫支付自己的家庭劳动工资,自己就这样一辈子服务一个人也是可以的。这些女孩甚至感谢上野千鹤子让她们看到这样做也是有价值的!上野千鹤子不深思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劳动让人恐惧逃避,为什么市场中工作难找,为什么女性会容易被排斥。她不对资本主义,不对私有制,不对雇佣劳动进行思考和批判,而是干脆帮助妇女重新回于家庭的私人服务,鼓动“支付家务劳动工资”来给这些家庭妇女以价值认同,让她们待在家里。上个世纪女性主义文学主张娜拉出走,而上野千鹤子的信徒却鼓励她们回去。如果一定要给家务劳动付工资,还不如鼓励这些妇女走出家庭去干家政。
当然,我们注意,恩格斯说的回到公共事业中是被压迫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不是完成条件!就像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中思考,资产阶级文学家在《玩偶之家》后也没有回答娜拉到底怎样。娜拉她固然是逃离了家庭,但是她作为无产阶级女性,她依然处于被剥削压迫的地位,她逃到哪里都不会得到真正解放,她不是丈夫的傀儡,但依然会使统治阶级的玩偶。我们能看到,在私有制下,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下,大部分无产阶级妇女都必须进入劳动市场出卖劳动,必须有一个被剥削的机会才能生存,因为无产阶级女性和无产阶级男性一样都不掌握社会的生产资料!当一个人无法掌握社会的生产资料,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就不得不承受资本主义劳动带给人的痛苦。或者根本被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排斥了,我们能看到一些人沦为卖肉身的地位来养活自己,一些人则渴望找个能养得起自己的男人嫁了退回娜拉出走之前;或者梦想着攀附资产阶级富人,沦为被寄养的玩物地位。不论怎样,都更加证明,无产阶级妇女想要真正获得的解放,要砸碎雇佣劳动的锁链;而要砸碎雇佣劳动,就比必须砸碎资本主义,更说穿了是砸碎私有制的锁链——在这里所有无产阶级都有了共同的任务!
但资产阶级女权却看不到这些,她们喊着走到权力中心去,都不喊着消灭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她们说走到权力中心去是为了广大女性的解放,就比如起码的,去当企业家,开一个由女性管理的公司;去从政,去主导话语权,这样从方方面面女性的就业歧视都会少很多。可是,无产阶级的妇女连生产资料都无法获得,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如何走到权力中心去?难道无产阶级的妇女解放是要靠资产阶级的女精英代表吗?难道这些人不明白只要私有制存在,资本主义存在,雇佣劳动存在,即使一个女资本家极度善良,也不能改变她依然客观会剥削女工人的事实吗?难道还不明白还察觉不到:
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不断扩大再生产和不能停止生产,正是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也就是对利润的唯一追求),才让时间就是一切的市场排斥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吗?因为女性怀孕的时间影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争分夺秒,所以女性才容易被排斥,而不是因为公司主管是男人,公司领导是男人,所以女性才被排斥!董明珠也丝毫不同情自己公司的女工啊!我曾在小红书看到过一些女主管写的帖子,她们一边说自己给女工争取了产假福利,或者各种福利,为自己为女性主义事业的“贡献”沾沾自喜额;一方面又责怪女性入职不久就怀孕了,影响了工作,于是不得不考虑取消,并且说这些福利就是被这些女性破坏的。一边说女性有无限可能,一边不满女员工怀孕的自由;一边自诩为女性谋福利争话语权,一边又拥护压迫无产阶级女性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为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人格化,什么性别在这里都是最无关紧要的!资产阶级女权争取的产假,甚至男女一起放产假,是没用的,只要不反对雇佣劳动和私有制,这些调和的福利要么不会落实,要么会成为更加排挤女性进入职场,因为归根到底这些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违背。
而只有当社会生产资料不再归私有所有,只有在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生产的目的不是追求利润的时候。女性才不会在职场中因为生理期、怀孕期被歧视、被排斥,而且只有在这时候,产假才会真正被落实。这些并不是遥远的期望,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不论是法国的国际友人夏尔贝特兰,还是美国的斯诺都看到过由工人集体管理的工厂是怎么样的状态。不仅是女性工人怀孕有产假,而且每月生理期如果不舒服也可以有几天假,所以有月经在上个世纪也有称为“例假”。在农村,上世纪50年代末,山东河南等地大批农民公社都试行“妇女劳力保护挂牌制”,劳动妇女可以根据经期、孕期、哺乳期的具体情况合理安排休息时间,既保障妇女健康,又能让公社正常运行。因为这时候的生产并不为市场服务,并不是为了追求利润,而是为了无产阶级的需要服务,不论是妇女的生育,还是整体劳动者的休息,都不会影响生产。如果说贝特兰和斯诺聚焦了公社时期的劳动妇女地位的情况。那么韩丁的《深翻》则是聚焦了农村在又回到个体家户经济时期的情况。他扎根河南农村三十年以上的经历,亲眼见证了农村从农民公社时期农民被改造,而当私有制回归后,农村女性又从“半边天”的地位转到到地位极度低下的地位——共产转到个体家庭的历史又上演了一回。
所以,说到这里,一切又指向是私有还是共产的问题。所以,性别问题,被压迫的妇女的解放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性别问题,而是生产关系的问题。而资产阶级女权不想着去消灭这个私有制这个物质基础,而是一直停留在用现象去对抗现象。她们还不明白词汇语言作为意识形态思维的物质外壳,是生产关系产生出的最表面的东西。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评来消灭的,也不是通过把它们消灭在“自我意识”中消灭的,而是通过实际地推翻产生这种意识形态的生产关系而消灭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如果不明白这个意思这个道理,建议去学习一下《德意志意识形态》。
在今天资产阶级女性主义的抗争对象是“老登”“普男”“男宝”,宣言是“英雌”“母道”“herstory”“shero”“爸根”;她们宁愿秉持唯心主义历史观在奴隶制、封建制的社会中粉饰出女权主义的代表,高举资产阶级的女资本家、消费主义代言人作女性解放的代表,都不愿意宣传真正为妇女解放和为全人类解放而牺牲的女共产党人。因为这些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总是捍卫对于劳动人民剥削和奴役的制度,捍卫通过剥削获得的财富,而女性共产党人是真的要批判私有制;在一些网络平台,你能看到她们一边高举者资产阶级的女性精英代表说着“女性力量”喊“girls help girls”,一边把最恶劣的揣测标签贴到被精英压迫的无产女性身上:因为她贫穷,住在出租屋,某一天可能和一个男人报团取暖,于是她们开始臆想这些组合的穷女穷男如何懒惰不堪过着发臭的日子——但实际上需要出卖自己劳动的无产女是不可能懒惰的,因为不工作她就活不下去;相反那些把光鲜亮丽建立在剥削他人的基础上,不用工作,想着每日精致下午茶,陶醉与奢侈品,百般服美役的却是真正懒惰的寄生虫和吸血虫。
资产阶级女性不鼓励女性向私有制挑战,而是鼓动无产女性和她们一样到“上流”来,但怎么上去,像资本家对员工那样鼓励她们奋斗?还是高嫁?实际上最腐烂发愁的地方就在社会的上流。她们一边说着女性勇敢做自己,可是却在打着“大女主”旗号的影视里最忌讳女主拥有真情。这年头不断情绝爱不做“修女”怕是不能叫进步。同样是结婚,无产阶级女性找了无产阶级男性,那必然是有罪,是男性不能给女性带来物质财富的罪,是这个女性没有高嫁而只能在底层的罪。同时,她们对嫁给资本家、嫁给上流社会的女性从来不飞唾沫,她们高赞其会借力而为,她们把明知是利益捆绑和交换的买卖婚姻叫做“理智不恋爱脑的大女主决定”。因为在资产阶级女权眼里,穷人不配有正常的感情需求。她们永远为每一个就表面说表面的女性主义电影高潮欢呼——可是却不从生产了父权意识形态的生产关系里思考问题。所以我对我的朋友说,什么时候有女性主义电影能考察了父权和私有的联系,触及了对私有制的批判,而不是困在性别里,什么时候我再去买电影院买票。
好了,上述混乱不堪自相矛盾的虚伪不胜枚举,让我们再回到产生这一切的矛盾(不论是阶级矛盾还是所谓性别矛盾)的经济基础上——私有制上吧!看到了当今一切阶级的、婚姻的、性别的问题都是因为生产资料的私有,怎么做?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那么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是被剥削压迫的,就应该明白了,只有摧毁私有制的统治,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所以,其实,每一个无产阶级男女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共同解放自己的使命。
所以等到到掌握了真理的物质力量强大到足够摧毁了产生上述种种矛盾的经济基础的时候。那时候,情景再现: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私人的家务再次变回社会的事,孩子的抚养和教育也成为真正公共的事,人们只会因为爱而结合——这次,人类准备迈入一个高级的共产时代,人与人之间平等,男女之间平等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