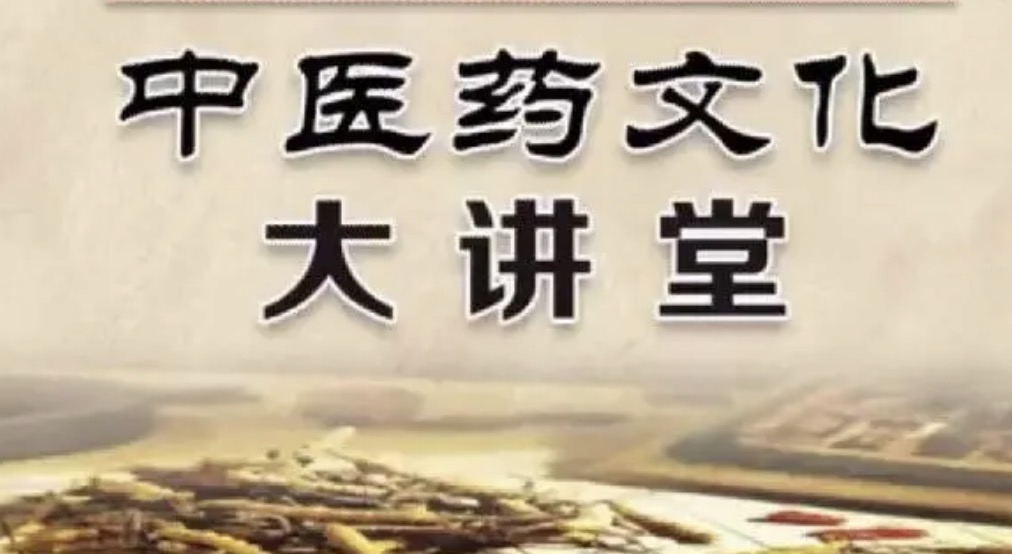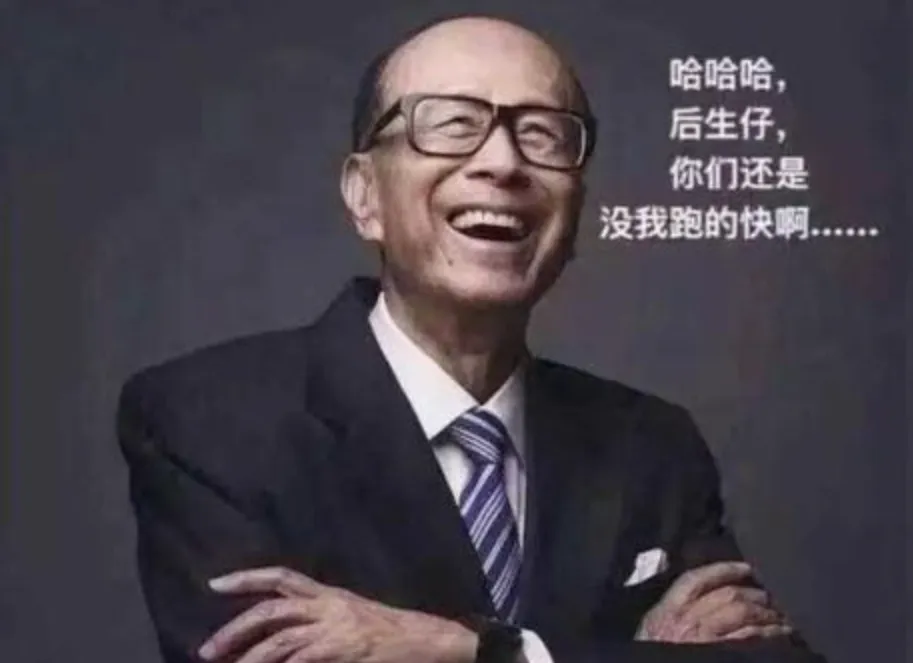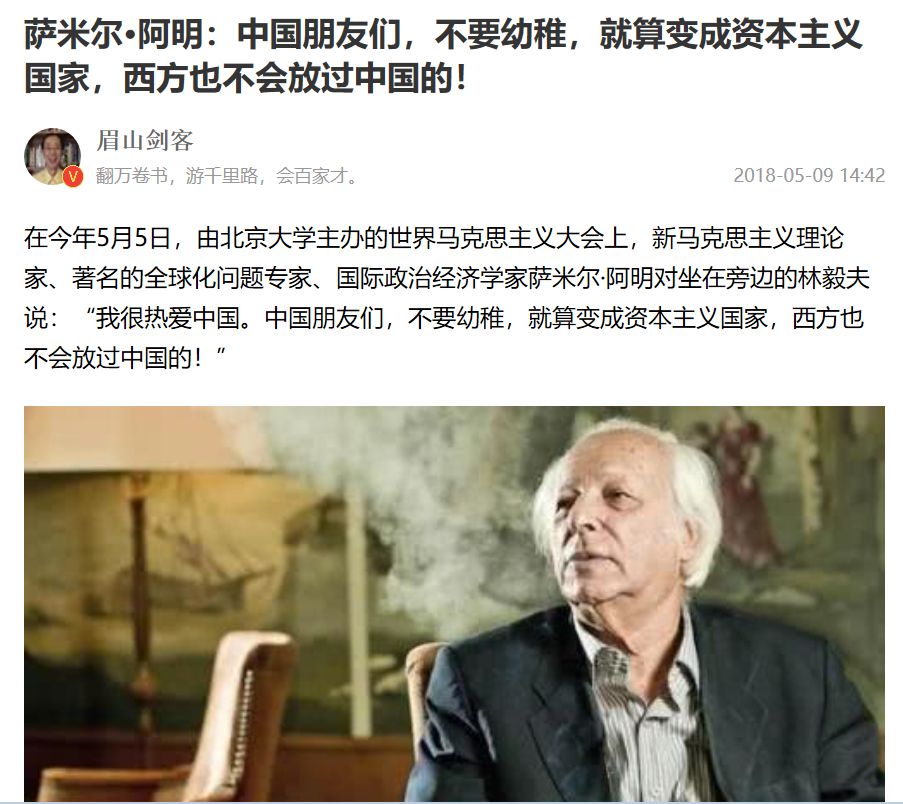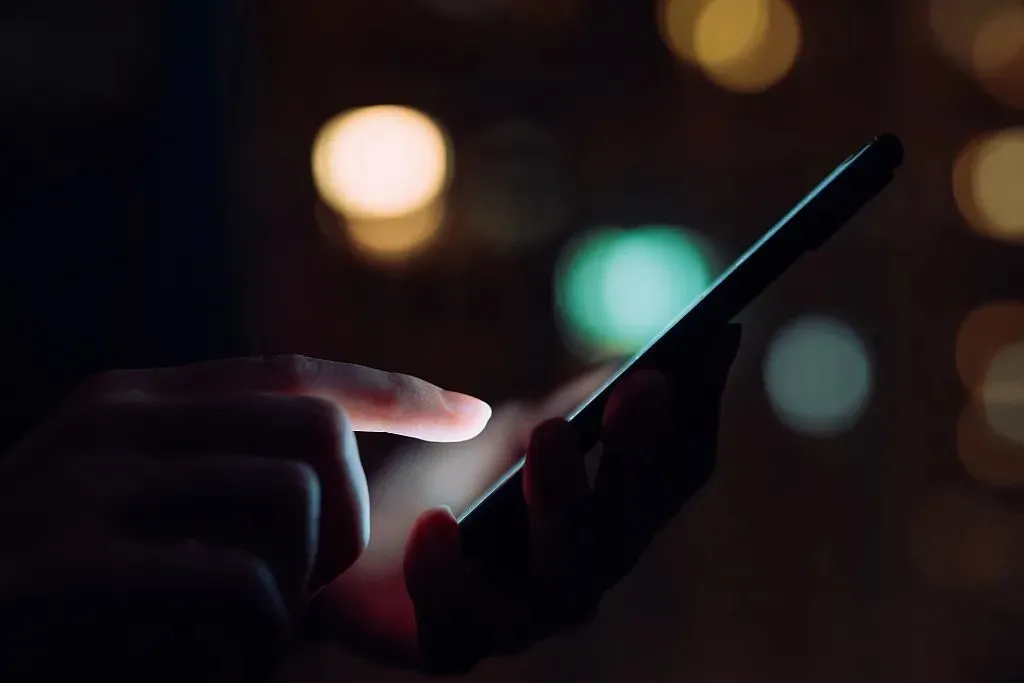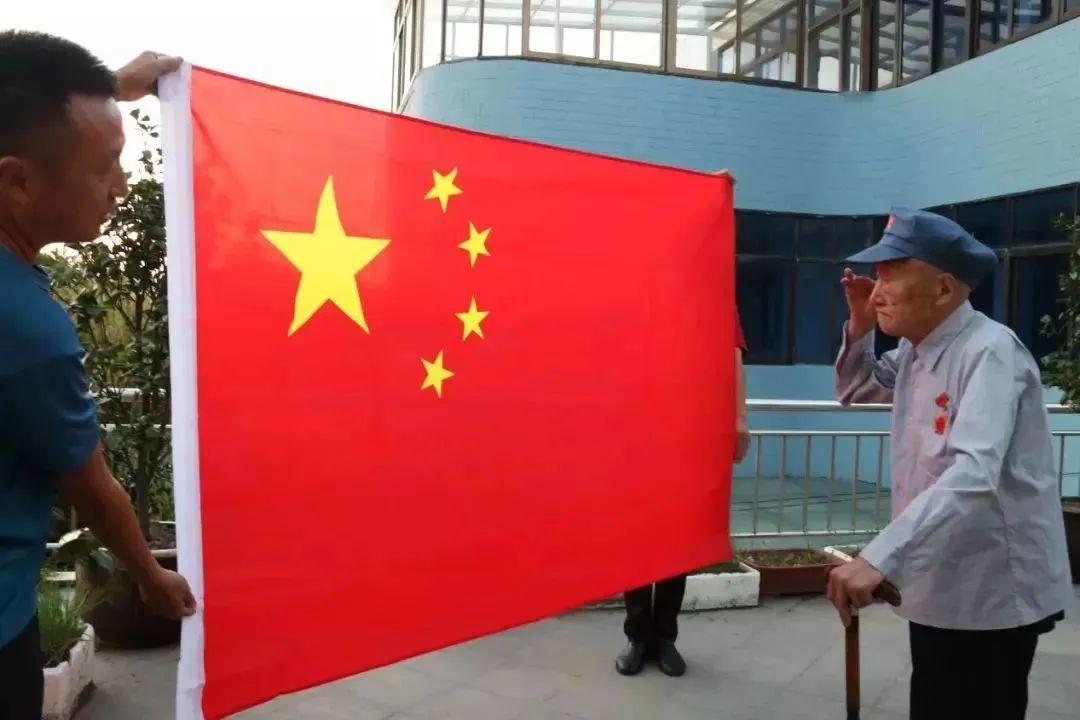留不住的家乡,找不着的活路
大年十五已过,村子渐渐安静下来。鞭炮声不再震耳,红灯也渐渐笼落了灰,门口的“福”字虽依旧鲜艳,却映衬出门庭冷清。青壮年们陆续踏上出门打工的路,奔赴广东、浙江、上海,或者更远的地方,村子里再次只剩下老人和孩子。这似乎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律,年复一年,从未改变。
总有人问我:“你什么时候出去?今年去哪儿?”
我总是回答:“今年不想出去了,我想在家种一年田。”
对方总是愣住了,脸上浮现出疑惑和难以置信:“你认真的?种田?那能赚几个钱?”
我点点头,纵然我百般解释,说自己只是单纯地想种地,想认真的观察和感受这片土地,他们还是不信。有人甚至觉得我是犯了傻。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不信,因为种地不赚钱,甚至还会亏本,这是所有人心知肚明的事实。
我也知道,他们不信我,不是对我有意见,而是对现实失去了信心。毕竟,当前的农村困境太过真实,太过沉重。
分田单干后,小农经济的弱点暴露无遗。没有了集体组织,农民各自为战,失去了规模效应和公共保障,风险完全由个体承担,抗风险能力极低。
种子、化肥、农药、机械租赁,样样都要花钱。到了收获季节,卖出的粮食扣除成本,所剩无几。若遇上自然灾害或市场行情不好,连肥料钱都收不回来。靠几亩薄田,根本养不活一家老小。要想过得好一点,就得出去打工。
可是,谁又愿意背井离乡,去城里吃苦受累、被人呼来喝去?可不出去又怎么办?种地是赚不到钱的。这不是一户两户的问题,而是整个农村的问题。
于是,年复一年,年轻人走了,村子也空了。
在我们家乡方言中,找工作称之为“找活路”。这三个字听起来简单,却是沉甸甸的,仿佛压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肩膀。找活路,不只是为了谋一份收入,更是为了活下去、为了撑起一家老小的日子。
“活路”二字,说尽了生活的艰难,也道出了现实的无奈。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工作是为了梦想、为了成就感,而对更多人来说,工作只是一条活路。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这份工资,往往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甚至连温饱都难以保障。为了活下去,他们必须不断出卖自己的生命时间和体力,被迫在工作和生活的重压中挣扎。
资本家的利润来自哪里?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他们压低工资、延长工时、提高劳动强度,把工人的汗水和血泪变成自己的财富。对劳动者来说,工作不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而是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找活路”这三个字里,藏着深深的无奈和无助。它揭示了劳动者被资本支配的命运:他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只能在资本的掌控下,为了一口饭、一张床、一个屋檐而拼尽全力。资本家剥削的是工人的劳动价值,但真正被剥夺的,是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和自由。
在这种条件下,劳动者被迫接受被剥削的命运,却被灌输一种错误的观念:贫穷和困苦源于自己的能力不足、努力不够,而不是社会条件的问题。于是,他们默默忍受,努力工作,幻想着有一天能“出人头地”。可他们不明白,只要资本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他们就永远无法摆脱被剥削的命运。
经济繁荣时,工人拼尽全力,也只能勉强糊口;经济危机来临时,失业、降薪、裁员接踵而至,“活路”变得愈加艰难。这并不是个体的失败,而是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必然结果。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不断扩大生产、榨取工人剩余价值,而当市场饱和、利润下降时,倒霉的却总是最底层的劳动者。
“找活路”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被迫。它背后,是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是阶级对立的深层矛盾。要想真正摆脱这种困境,劳动者必须觉醒,认识到自己的被剥削地位,联合起来,反抗资本的统治。只有夺回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改变被支配的命运,才能真正改变“找活路”的悲哀。
当我们再听到“找活路”时,不仅要想到生活的不易,更要意识到,这是一种被压迫的状态,是一种阶级矛盾的体现。只有打破资本的枷锁,让劳动者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才能让“找活路”不再沉重,让生活重新焕发出希望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