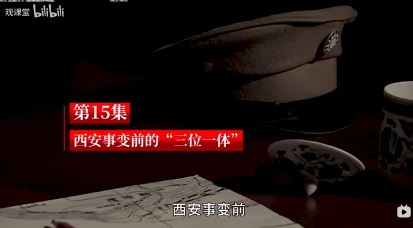杨昭友:对莫言获诺奖“感言”的感言

今年是莫言先生因诋毁中华民族而获得西方大奖10周年。
结合今年曝光毒教材问题,莫言获得西方敌对国家奖赏之事又成了热点话题。
为什么时过十年又成了热点呢?
因为莫言的获奖给隐藏在中国的恨国势力打了强心剂,原来恨国可以这样名利双收。于是乎,莫言获奖之后,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妖风甚嚣尘上,歌颂人民英雄的文章相继被移出课本,代之以毒插画、毒文章充斥于大中小学教材之中,志愿军头号仇敌麦克阿瑟的文章也成了学生的必读。而文坛上则屎尿腥臊横流。
由此联系起来,我们终于看清了西方授予莫言诺贝尔文学奖的深意。

诺贝尔奖对莫言的颁奖辞是对莫言立场的最好诠释。

【诺贝尔奖对莫言的颁奖辞↑】

与颁奖词相呼应的是莫言的获奖感言。
莫言的获奖感言洋洋洒洒八千余字,可谓是字字血声声泪,与丑化中国的颁奖词配合默契,和他的小说一样,把生他养他的祖国描绘得暗无天日。
莫言的感言比较冗长,为了不给读者添加愤懑,这里只截取一小段。读者从中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 ,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有感于莫言的“在我看来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目的,文学艺术就应该是揭露黑暗的”名言,我这里也对莫言的感言发表一点感言。

既然“文学艺术就应该是揭露黑暗的”,那么文艺批评更应该拥有这个功能。莫言说揭露社会黑暗,而莫言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他同样可以被列为揭露的对象。
我们不反对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揭露阴暗是为了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光明。但是,揭露社会的阴暗面要有真凭实据,而不是无中生有的杜撰。
恨国作家方方曾教训明德先生说,你有杜撰才能,不写小说太可惜了。由此可见,当今的恨国作家都是编造谎言的专家。
对方方这番高论,没见过莫言有不同的意见,因为获得西方炸药奖的莫言算得上杜撰大师中的大师。莫言能给出《酒国》中“烧烤三岁孩童肉是最精致的美味”的准确时间、地点?吃“三岁孩童肉”的人物原型是谁?
如果没有原型,岂不是揭露了作者阴暗心理?

【童年莫言(左)】
扯远了,还是回到莫言感言中向洋人哭诉他母亲挨打这个故事上。
莫言的母亲拾麦穗并挨打这段文字,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当时的中国遍地饥荒,人们要依靠拾麦穗果腹;二是暗无天日,拾点麦穗还被毒打,可见那时代是怎样的不堪回首。
一般读者看到莫言这番话,必然产生共鸣,对莫言描绘的那个社会深恶痛绝。而恨国公知则如获至宝,视莫言的感言为反华反共的利器。
笔者不会写小说,不会杜撰,只能从莫言的原话推理还原莫言母亲拾麦穗挨打的真相。
莫言所叙述的时代,中国人民的确还吃不饱、吃得不好,这是事实。可是,这吃不饱,并不是共产党带来的,是封建社会和国民党反动派给我们留下的遗产。
刚解放时,中国的农业生产相当落后,水利设施缺乏,肥料严重不足,种子基本是延续千年的老品种。要想吃饱,只能是在党的领导下,人民自己艰苦创业、艰苦奋斗。天上不会掉下粮食,共产党也不会带来粮食;共产党能做的,就是组织人民,依靠人民,发挥人民的创造力。因为共产党也是人民。改变这种落后面貌,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需要长期艰苦奋斗的。
中国人民什么时候解决温饱的?是基本修建好了大量的水利设施,保证了种植面积,是勒紧裤带建起了满足中国农业需要的化肥厂,是全国社会主义大协作,培育出高产良种。所以,在农业高产条件没创造出来之前,中国人民是难免饿肚子的。要知道,这些条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中国人民用血汗奋斗出来的。
今天的中国与莫言所怀念的时代相比较,物质上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不仅已经吃饱,而且减肥广告铺天盖地。中国这一切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劳动人民为莫言提供了衣食住行,为莫言提供了创作条件。可是,莫言的小说,从来不歌颂中国共产党,不歌颂劳动者,不赞美劳动光荣,我们也没看到莫言写自己和母亲参加集体劳动的文章。这说明莫言是极端鄙视劳动、仇恨劳动者的 。若全国人都如莫言,今天的中国人能吃饱饭吗?没有人劳动,莫言母亲去哪里能拾到麦穗?
莫言说的拾麦穗时代,中国粮食的确不是很充足。因此,农民爱惜粮食,把地里散落的麦穗拾回家是可信的。可是,莫言的母亲去集体地里拾麦穗并被人打得嘴角流血是不是事实呢?这一点,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清楚,城里人也搞不清楚。
我和莫言是同时代的人,他穿过军装,我也穿过军装,他饿过肚子,我也饿过肚子。只是,我参加过集体劳动,热爱集体劳动,我了解农业农业生产。
是个人都知道,要解决吃饭的问题,除了水、肥、种三个关键要素,最重要的就是劳动。没有劳动,有再好的条件,地里也不会长出粮食。所以,在社会主义集体时期,不论男女,只要身体健康,都有参加生产的义务。不劳动,粮食能从天上掉下来?
莫言的母亲也不例外,有参加集体劳动的义务,尤其是农忙季节。我的母亲也是小脚,是积极参加集体劳动的,只是不能在南方水田里劳动。当然,生产队会安排小脚妇女力所能及的劳动。
拾麦穗季节,是农村最忙的季节,社员们要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劳作的 。那时候,学校都放农忙假,让学生支援生产。
莫言在《卖白菜》一文中说,1967年他12岁,从莫言的年龄推算,他母亲那时候在40岁左右,正当壮年,理所当然地要参加麦子的抢收。莫言母亲是小脚女人,应参与的劳动是割麦子或在打谷场给麦子脱粒。这就是说,莫言母亲不可能在农忙季节不顾抢收大事而去地里拾麦穗。
须知,抢收麦子,是虎口夺粮,如果因懈怠耽误抢收,麦子就会枯萎在地里,必然损失严重;再就是抢晴天,若不及时抢收,遇到阴雨天气,麦子就会在地里发霉。
试想,这时候,莫言的母亲是应该在生产队参加抢收,还是去地里拾麦穗?当然,麦穗掉在地里很可惜,应该尽最大努力将麦子颗粒归仓。但这不是壮年劳力应该干的,而是发动老人和小孩去做这些事 。有的生产队允许老人小孩把拾起来的麦穗带回家,也有的是主动交到生产队。那掉落地里的麦穗看着是心痛,可真的去拾起来,一天下来一人也只能拾那么几斤。如果为拾麦穗而误农时,就得不偿失了。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莫言的母亲生来就是坐享其成;无论再忙的季节,都不肯参加集体劳动。莫言在《卖白菜》一文中说,他母亲卖三棵白菜都懒得被背,还要拖着12岁正在上学的儿子送到邻村集市。这就是说,莫言的母亲是打死不会参加劳动的。这么说来,莫言的母亲不参加集体劳动而去拾麦穗,或有其事。不参加劳动也能按人口分到粮食,拾麦穗反而比参加集体劳动的人吃得饱,足见莫言母亲的精明。
莫言的母亲拾麦穗会挨打吗?从莫言获奖感言的叙述来看,不仅他和母亲拒不参加农忙抢收,而且还有很多人放着大片庄稼不收,都去地里拾麦穗。我不禁要问,你们村里人在那样的农忙季节不去抓大头,把大片的麦子收回来,而去地里拾麦穗,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成熟的麦子耽误一天收割,其损失不是地里那点麦穗可比的。
莫言说守麦田的人一耳光把他母亲打得嘴角流血。我们可以从这句话看出这守麦田的是一个壮汉。这样一个强壮劳动力,在抢收麦子的季节,不去参加抢收,却守着掉了一点麦穗的空地?这种事情会不会出现?假使来不及抢收,麦子枯倒,或遇到阴雨天气,那损失不是比地里散落点麦穗更大吗?莫非高密的人都是这般弱智?这般分不清轻重缓急?所以,莫言母亲在麦地拾麦穗不可能挨打,因为生产队不会派一个强劳力干那傻事。
有没有人看守麦子呢?歇工的时候,打谷场和生产队的仓库可能有人看守,要防人偷盗。
继续推理:如果莫言的母亲真的是被人打得嘴角流血,读者可以想象应该发生在什么地方?是在地里拾麦穗,还是在打谷场或生产队的仓库“拾”集体的麦子?如果一个不下地劳动的人去集体打谷场或仓库“拾”麦子,是不是犯罪?
莫言《卖白菜》文中说:“我曾经背着母亲将一大把化肥撒在它的周围” 。须知,那时的化肥是紧缺的生产资料,都是供应给生产队的。私人家里不可能有化肥。如果莫言给小白菜施肥之言不虚,我们有理由怀疑莫言家里的化肥是来自生产队的仓库。
由化肥来源的展开,再到莫言母亲拾麦子挨打,莫言笔下的母亲形象在读者眼里一下子就“高大”起来了。
抹黑国家,顺带把母亲黑了,也只有这种不肖子孙编得出这样的谎言。
怎么养了这么个寡廉鲜耻的文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