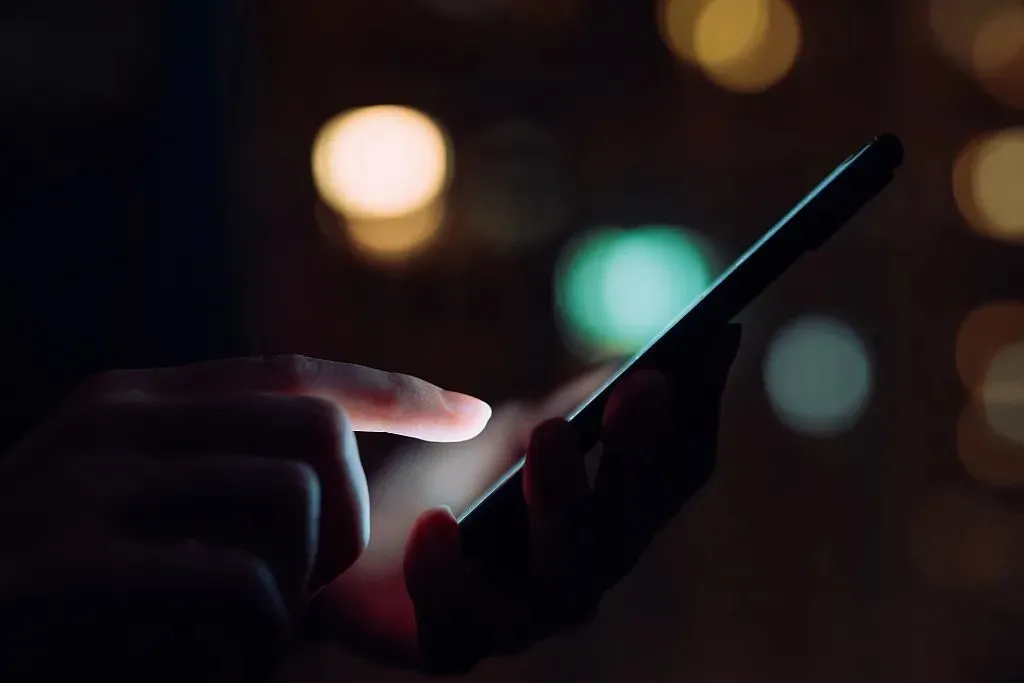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看待代孕
代孕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2017年初,新浪微博就围绕是否支持代孕合法化展开了辩论,当时80%左右的人都反对代孕合法化,因此合法化的呼声也不了了之。但是,最近某明星代孕加弃养的爆炸性新闻再次将这沉寂已久的话题带上了热搜,然而赞成与反对的双方仍然各执一词。为何代孕始终存在这么大的争议?问题的关键只是在于代孕应不应该合法化吗?
这首先得从大众是如何看待代孕合法化的问题来入手。
在代孕合法化的支持者看来,中国不孕不育率的迅速攀升,是造成代孕需求的客观条件,但是法律却远远落后于这样的需求,使得代孕仍然处于灰色地带,既无法规范代孕中介的行为,也无法保障买家和卖家的权益。如果代孕合法化,能让你情我愿的买卖变得更公平,不孕不育的夫妇可以喜得一子,拥有完整的家庭;底层妇女也可以通过代孕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改善自己及其子女的生活,还能获得法律的保护。
可是现实真的有那么理想吗?
参照一下少数代孕合法化的国家,如印度和美国,就会发现,无论是否合法化,它都是一条吃人的产业链,区别仅仅在于是在阳光下吃人还是在黑暗中吃人罢了。
从一开始,代孕的买家和卖家就呈现了鲜明的阶级分化:2002年,印度开放了商业代孕合法化之后,成了世界闻名的“代孕天堂”,慕名而来的都是世界各地的富商巨贾,最不济也是财力优渥的中产。因为代孕要消耗巨大的财力,从选择什么样的基因、什么年龄段的孕母,到是否剖腹产以及婴儿的性别选择,每一个选项都要层层加码,少则十几万,多则上百万。代孕并非如传闻所说,是不孕不育家庭的福音,有能力选择代孕的,很多是为了保持容貌和身材、减少生育风险和时间成本的有产阶级。日本NHK纪录片就总结道,选择代孕的中国家庭,年收入至少在200万元左右。
而“愿意”做孕母的女性,各国无一例外,大多是别无出路的底层妇女。在印度,底层的妇女会为了逃离丈夫无处不在的家暴和极端困苦的生活环境,也为了改善自己及子女的生活条件而选择代孕这种“不体面”但是能提供临时避风港和可观收入的职业。而在中国,代孕妈妈也有类似的生存困境。有学者做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发现孕母并非完全“没有主体性的受害者”,而是在权衡了利弊之后,相比于在低收入且压抑的富士康大厂做工,选择了相对来说收益更大但风险也更大的代孕行业而已。

先不说这样的“自由选择”是否是真正自由且值得被提倡的(毕竟还存在着不少丈夫强迫妻子去代孕赚快钱的“被自愿”情况),代孕背后的残酷和不自由却是真实存在的。
在印度,孕母一旦签了合同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被软禁在集体宿舍,没有任何娱乐设施和人的尊严,吃穿住行都被严加看管,防止意外流产和逃走。这比996还不自由,996起码还有下班时间,而孕母必须24小时几乎全年无休,只为生出满足客户需求的孩子。在美国某些州,对孕母的各种要求甚至写进了代孕法中,比如不能自己开车等,如此精细的条款,和监狱生活没什么区别。
而且代孕中各种严苛的要求对孕母身体的伤害也是致命的。比如胚胎成功移植到孕母子宫中的几率并不高,如果失败了必须反复移植,直到成功为止,孕母完全没有喘息的机会;如果客户有多胞胎的要求,孕母也只能承受突破身体极限的痛苦;更可怖的是,如果对胎儿有性别的要求,孕母还要被迫打掉不合格的胎儿,直到怀上客户想要的胎儿为止。
因此,在中国,反对代孕合法化的理由就显得十分合理了——代孕合法化是对女性的物化、是对底层妇女的盘剥,违背了公序良俗和人伦道德,触碰了人性的底线等等。但法律禁止了代孕,就真的能解决问题、一了百了吗?
事实上,中国的法律确实禁止代孕,但只禁止了一部分。2001年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第三条明文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第二十二条规定: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买卖配子、合子、胚胎的;
(二)实施代孕技术的;
(三)使用不具有《人类精子库批准证书》机构提供的精子的;
(四)擅自进行性别选择的;
(五)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档案不健全的;
(六)经指定技术评估机构检查技术质量不合格的;
(七)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人口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中曾有过更严格的规定:“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但是后来又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中删除了“禁止以任何形式进行代孕”的条款。
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在法律层面只是规定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代孕技术,但对商业代孕机构几乎没有监管措施,而且违法也只是由相应的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处3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成本如此之低,地下代孕市场也就有了野蛮生长的空间。实际上,代孕在我国早已形成一条完整且成熟的产业链。
在网上搜索一下就会发现,光武汉就有200-300家做代孕的公司,1年代孕的业务量能达到2000件左右。而国内创办最早的一家“AA69代孕网”公司表示,其网站自2004年开创中国代孕行业至今,已经成功诞生15000余名婴儿。该网站创始人兼董事长吕进峰宣称自己是中国从事代孕产业的第一人,在1月19日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吕进峰指出,刨除风险成本,代孕业务的利润率仅有10%左右。但1月21日,凤凰网财经就报道代孕市场利润高达60%。

可观利润的背后却是极端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利润中的大头被中介独占,孕母承担最大的风险,却只能拿最多20%的小头,也就几万块,最高能逾十万。2019年央视记者曾暗访代孕机构,了解到代孕的费用“全包65万,选性别的话是85万,双胞胎或龙凤胎再加10万,但不能保证成功。如果失败就按照选性别包成功85万计算。”据记者了解,“包生男孩”的代孕者如果怀上女孩要被强行打胎,如果胎儿存在缺陷,甚至会弃婴。这简直让人匪夷所思,这些代孕妈妈和婴儿们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但是此刻她们都是被明码标价的商品,等待出售!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代孕应不应该合法化,无论是否合法化,代孕都无法被真正规范或杜绝。而应先了解清楚,代孕产业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代孕在中国是有很大“潜在需求”的,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中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从1990年的2.5%—3%攀升到近年的12%-15%左右,不孕不育者约有5000万人。但这些不孕不育的夫妻本可以通过领养小孩来满足自己的愿望,并非只能通过代孕这种对他人身体造成极大伤害的方式来达到目的。
这种需求之所以能转化为产业,根源在于一切皆可买卖的市场化逻辑。在市场经济下,任何可以产生利润的,任何可以转化为资本的,都会导向投机与买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绞首的危险。”巨大的收益同时也伴随着致命的风险和沦丧的道德,但是代孕中介们不在乎,他们不惜违反法律、践踏代孕妈妈和她们肚子里孩子的生命,甚至推出各种包客户满意的定制套餐,只为赚得盆满钵满。
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利润成了最大的权威,法律的威严在巨大的经济收益面前不堪一击。就如器官买卖、毒品交易这些被政府打击多年的违法交易仍然在现实中存在着,代孕也绝非一纸条文所能杜绝。而同暴富的代孕中介相对的,是仍然处在最底层的妇女,代孕没有根本改善她们的生活,也没有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
因此,只要还是市场的力量在控制社会,代孕作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产业,就不会自行消失。而且它将始终被掌握在有钱有权的人手中,不仅剥削底层妇女的身体,还剥夺她们身为人的最后的尊严;所谓的“自由”只是有产者的自由,对于底层女性来说,她们的自由只是选择出卖给这个吃人的产业还是那个吃人的产业的自由,却没有选择不出卖自己身体和尊严的自由。资本扭曲了人伦道德,却还打着“底层妇女最后出路”的旗号,假惺惺的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
所以,我们要反对代孕,但又不止于反对代孕,更要看到背后是什么力量创造出了这一切牛鬼蛇神,群魔乱舞,反对造成这一切乱象的根源。反对代孕并非如某些人所说,是中产阶层的视角,是对底层妇女的不理解,是在堵住底层女性为数不多的出路。恰恰相反,反对代孕,正是考虑到底层妇女们最根本的利益,希望底层妇女也能有尊严的工作和生活。只是,在代孕没法完全从这片土地上自行消失以前,如恩格斯的观点所言,“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作为现存社会制度牺牲品的妓女本身的利益,并尽可能地使她们不致遭受贫困,至少不要……利用强制的手段,通过法律和警察的卑鄙行径而使她们完全堕落。”
因此,只要逼迫大部分劳动者沦落到一无所有的贫困地步的制度还存在,试图通过法律手段完全禁止代孕就是一种伪善。但是我们可以为她们做的还有很多:一方面,对已经不能从事代孕的妇女们应当给予妥善安置,如社会培训和转业,让她们拥有一技之长,能维持自己以及子女的生活,不至于被社会抛弃。另一方面,对于选择代孕的妇女们而言,可以从法律和社会层面给予一定的保护,如补充相关法律,对于代孕中的强制堕胎等恶劣行为予以打击,一定程度上保障弱势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同时组织社会机构给予代孕妇女们足够的社会关怀,在代孕期间指导她们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并提供必要的心理疏导和陪伴等,让她们在代孕之后有能力恢复正常的生活。
毕竟归根结底,我们期待的不是一个强制堵死底层劳动者们所有出路以维持表面体面的社会,而是一个不需要任何人沦落到出卖自己来维持生计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