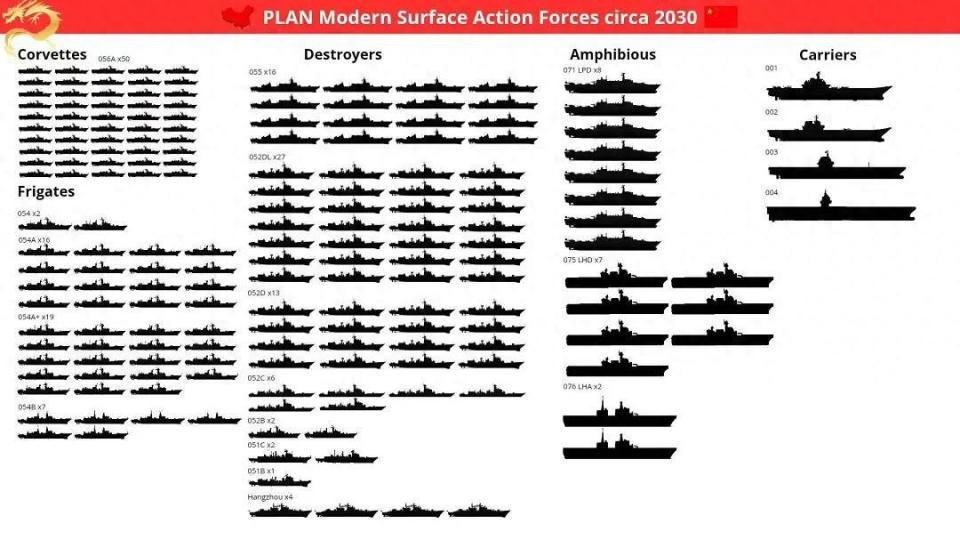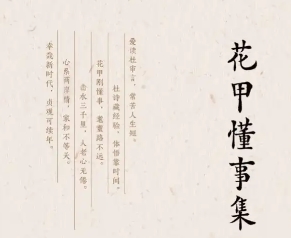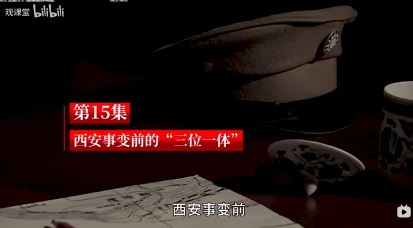女性问题之社会基础(一):经济独立之斗争
纪念国际劳动妇女节
1910年,德国社会主义者、工人运动领袖克拉拉·蔡特金在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强调了劳动妇女在劳动解放事业中的重要职责,随后的10年间,全球劳工运动高涨,女性工人在斗争中觉醒并担起重任。为正式纪念全球妇女在人类解放斗争中的功勋,俄国共产党人柯伦泰提议将三月八日确定为国际劳动妇女节。为纪念第114个妇女节,小镇读书会特别搜集了几篇该节日的正式确立者、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家、妇女解放运动家柯伦泰的相关文章。
“妇女节”在近几年似乎渐渐恢复了部分它应有的样子。力求与妇女节撇清关系的三月七日的庆典喧嚣大不如从前,有关“女性的称呼”的争辩似乎也少多了。甚至连某些商业场所也打出了“妇女节是庆祝妇女解放”的标语——当然是以另一种商业广告的形式。暂且不论这些商业化的“解放广告”是否会让女性陷入另一种枷锁之中,但至少从形式上来说,三月八日的第一重进步涵义,即“女性权利”,正在重新成为当下人们常识的一部分。我们认为,这和近年来各种进步力量在各个空间领域的工作是紧密相关的。在今天这个特殊的节日里,我们向你们、他们,当然也向我们自己致敬。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女性议题越是受到重视,相反的力量越是强大,排斥的声音也愈加尖锐。一方面,一切以保存现有秩序的“老人”极尽污蔑谩骂举报之能事,认为一切的进步运动皆是不怀好心、受人指使;另一方面,制度本身也常常树几尊无害神像,用家国叙事将“女性权利”重新包装。可见,就算是妇女节的第一重内涵,即“女性权利”,其发掘、宣扬,仍有很长的路需要走,其中的联合与争辩,也必然是难以避免。
但我们仍然相信,总有一天,“三月八日国际劳动妇女节”的第二重、第三重甚至是第四重进步内涵,也会逐渐清晰。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到,妇女节原来和百年前的美国与德国有关,它远远超出某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狭隘界线,这是节日名称中“国际”之内涵;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了解到,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人类解放的天然关系,这是节日名称中”劳动“之内涵;而女性权利、国际团结、劳动解放,断然不是嘴上说说就可以实现了的,这需要我们行动起来一同争取,这或许就是节日名称中”三月“之内涵——巴黎人民在三月架起大炮,俄国工人在三月赶走沙皇,march!march!让我们向阶级压迫的历史第一种形式——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宣战!让我们如柯伦泰所说,”为妇女节而庆祝,愉快地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同时为她们自身的解放而奋斗!“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1872.03.31~1952.03.09
以下文章转自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译者蓝巴勒。
原编者按:柯伦泰是早期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国际共运中女权脉流之重要一人。诚然,作为一个世纪前的“女性主义者”(她十分反对“女性主义”一词),她的文章不如后现代派般“华丽”,甚或有些“政治不正确”。但她的文章于当代女性主义,尤其是如何理解、处理性别与阶级关系的问题上,依旧意义重大。更重要者,她是布尔什维克妇女部(Zhenotdel)之创立者,是一度使苏联在世上于女性权益走得最前的人。若要使女性主义回归到其革命根源,让女性主义真正成为解放政治的一部分,这段历史,这些思想资源,仍值得承继。
《女性问题之社会基础》是柯伦泰在1909年所著的一本小册子,是她首篇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作品。要理解这篇文章,先应了解当时沙俄女权运动。
俄国的女性解放运动肇始于1861年的农奴解放。当时的启蒙贵族与中产女性争赴外国(主要是瑞士)留学,深受社会主义思潮——尤其是巴枯宁(Mikhail Bakunin)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她们回国后,有的投身俄国民粹派,有的加入当时方兴未艾的社会民主党。简的来说,起初俄国的女性运动是具明显工农倾向的。然而,自1904年后,中产女权派眼见芬兰女性普选权运动的成功,开始投向主张君主立宪的自由派,成立了妇女平等联盟(Union for Women’s Equality),尝试推动一个“统一女性运动”。参与者不仅有社会显达、慈善家与中产专业人士,亦有不少社会民主党人。这篇文章不单尝试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性别政治理论,亦是对运动的双重批判:一方面,批判资产阶级女性主义的“普世女性”观念;另一方面,批判于女性问题上与“女性主义者”合流,鼓吹阶级合作的党内人士,借此抗击当时于俄国影响力日增的修正主义潮流。时至今日,文中不少对自由派女性主义批评依然十分合时。
让资产阶级学者在那些关于性别优越性,或是较量男女大脑重量和心理结构的讨论中自得其乐吧。历史唯物主义的追随者完全接受每种性别的自然分殊,只要求每个人,或男或女,享有最完全和最自由的自决,以及最广泛地发展及实现他们的自然倾向。
历史唯物主义的追随者拒绝承认有任何独立于当下普遍社会问题而存的特别女性问题。女性之从属地位背后的是特殊之经济成因,而自然属性只是这个过程的次要原因。只有这些成因彻底消失,只有在过去某些节点征服女性的力量更迭,才可根本地影响和改变女性的社会地位。换言之,只有在一个基于新的社会及生产路线组织的世界之中,女性才能变得真正自由和平等。
然而这并不代表不可能在现代体制框架下局部改善女性的生活。工人问题的激进解决方案只在完全重构现代生产关系时才有可能实现,但这是否必然意味着我们不可以着手推动那些满足无产者最迫切利益的改革吗?相反,工人阶级的每一战果都代表着人类迈向自由王国与社会平等的一步:每一项女性争得的权利都使她们接近全面解放的目标。
社会民主党破天荒的于其纲领内要求女性平权;党何时何地也在演说和出版物中要求取消一切对女性的限制;正是党的影响力使其他政党和政府都推行利于女性的改革。而在俄国,这个党并不只在理论立场上捍卫女性,它在每一方面也奉行女性平等的原则。
那是什么令我们的“平权份子”无法接受这个强大且久经历练的党的支持呢?事实是,不论这些平权运动份子有多“激进”,他们依旧忠诚他们所属的资产阶级。政治自由现正是俄国资产阶级成长和力量的必要前提,没有了它,后者的经济福祉之基础便会极为脆弱。对女性而言,对政治平等的诉求是脱胎自生活的必然性。
“专业就业”的口号已不再足够;只有全国直接参与政府事务才能保证对提高女性经济境况的支援。因而中层资产阶级的女性才如此渴望获得公民权,亦因而她们如此敌视现代的官僚制度。
但是,我们的女性主义者在要求政治平等时就像她们的外国姊妹般,对社会民主知识所拓展的广阔视野依旧十分陌生和不明所以。女性主义者在现有阶级社会的框架下寻求平等,她们绝不攻击这个社会的根基。她们为自己争取特权,而不挑战现有的特权和优裕。我们不会因为资产阶级女性运动的代表无法理解这个问题而指责她们,她们对事物的观点无可避免的从其阶级立场派生。
经济独立之斗争
首先我们一定要问问自己,究竟在一个基于阶级矛盾的社会以内,是否可能存在一个联合的女性运动。每个不带偏见的看倌都很清楚,参与解放运动的女性并不代表一个同质的群众。
正如男性的世界,女性的世界也是分为两个阵营的;其中一组女性的利益与目标使她们向资产阶级靠拢,而另一组与无产者有着紧密的联系,其对解放的要求包含了彻底解决女性问题的方案。因而即使两者都跟随着“女性解放”这普通的口号,她们的目标与利益是不同的。每一群人也无意识地以其所属的阶级利益作为其她们的出发点,这使她们自我设定的目标和任务无不染上特殊的阶级色彩。
无论女性主义者的诉求怎样貌似激进,都不能忽视因其阶级立场,女性主义者不能为当代社会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之根本转化而战——而这正是彻底的女性解放所必须的。
即便在某些环境下各阶级的女性的短期要务一致,两个阵营的终极目标最终亦会因为长期上受其决定的运动方向及策略而南辕北辙。当女性主义者视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框架下达至与男人同等权益为已足够具体的自足目标时,对无产阶级女性而言,现时的平等权益不过是推进工人阶级与经济奴隶制斗争的一种手段。女性主义者视男性为主要敌人,因为男性为着自己不公地夺去了一切权利与特权,除了锁链和责任,再没为女性留下什么。对她们而言,只要把此前仅为男性享有的特权让与女性,这已算取得胜利了。无产阶级女性有着另一种态度。她们并不视男性为敌人与压迫者;相反,她们视男性为与她们共负每天苦差,与她们一起为一个更好的未来而奋斗的同志。女性和她的男性同志被同样的社会条件奴役;他们所痛恨的资本主义锁链压迫着他们的意志,剥夺他们生命中欢乐和美好之处。诚然,当代体制在某些特殊方面使女性担负了双重的压力,而雇佣劳动的条件亦有时把女工变为男性的竞争者和对手。但在这些不利的境况之下,工人阶级深知错在谁身上。

女性工人的苦况并不比她们的兄弟少,她们痛恨那头利牙镀金的怪物——它对男性、女性和孩子同样贪婪,只想从受害者吸干一切,牺牲几百万条人命来壮大自身。千条万绪使劳动者互相走近。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女性的目标却看起来十分奇怪、难以理解。她们没打动无产者的心;她们并不向无产阶级女性许诺一个所有被剥削者青眼相看的光明未来。
当然,无产阶级女性的最终目标并不阻止她们改善其地位,哪怕是在现行的资产阶级体制框架内,但这些欲求之实现却经常被由资本主义本质的衍生问题所窒碍。女人只有在一个社会化劳动、和谐和正义的世界中才能拥有平等权益和自由。女性主义者不愿,亦不能理解这一点;于她们看来,当法律在形式化的一纸空文接受平等时,她们便可以在充满压迫、奴役、束缚、血泪与苦难的旧世界中赢得安身之所。而这于某程度上亦是正确的。因为对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女性而言,与男性平权只意味着平等地共负不平等;但对“被选中的一小撮人”而言,对资产阶级女性而言,这真的可以迎来此前只为资产阶级男性所享有的权利和特权。但资产阶级女性所赢得的让步都使她们取得利器以剥削妹妹们,并会使两个对立的社会阵营中的女性持续分化。她们的利益冲突会愈趋尖锐,她们的目标之矛盾性会愈趋明显。
那么,普遍的“女性问题”究竟在哪?女性主义喋喋不休的统一任务和目标究竟在哪?清醒地看待现实,便会发现这种统一性并不存在,亦不能存在。女性主义徒劳无功地试图说服自己“女性问题”与政党无关,以及“其解决方案只有所有政党和所有女人参与其中时只可能实现”;正如一个激进的德国女性主义所言,事实的逻辑迫使我们拒绝女性主义者这种循规蹈矩的幻觉。
通观人类历史,生产条件及形式都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并逐渐把她们编配到被压迫与依附的地位上,而至今当中很大部分依然存在。
在女性可以开始重拾她们失去的重要性与独立性之前,整个社会及经济结构必须出现一次巨大的裂变。一度连最天才的哲人亦难以解决的问题,现已被无生命却全能的生产条件所解决。这几千年奴役女性的力量,于新的发展阶段中,已领导她们走上自由与独立之路。
约在十九世纪中叶,女性问题对资产阶级女性日益重要——这距离无产阶级女性登上劳动舞台已有一段时日。在资本主义惊人的成功下,人口内的中产阶层受到一波又一波需求的冲击。经济变化使小资产阶级与中层资产阶级的财务状态不稳,而资产阶级女性便面对一种进退维谷的两难:不是承受贫穷,便是取得工作权。这些社会群体的妻子与女儿便开始叩谒大学、艺术沙龙、编辑部和办公室,潮涌进那些向她们开放的职位。
资产阶级女性取得科学与文化优势的欲望并不是一种突然、成熟中的需求,它同样脱胎自“讨生活”的问题。资产阶级女性首先便遭罹男性死硬的抵抗。执迷于其“安逸小工作”的专业男性与刚开始讨生活的女性之间便爆发了一场恶战。这场斗争使“女性主义”得以冒起——这是资产阶级女性团结合力对抗敌人,对抗男性的尝试。当她们登上劳动舞台,这些女人便自傲地自号为“女性运动的先锋”。她们忘记了于赢得经济独立上,她们不过是在步其妹妹的后尘,并收割她们那对疱裂的双手中之成果。
所以当各国成千上万无产阶级女性于资产阶级女性运动诞生以前已涌入工厂与作坊,占据一个又一个工业分支时,我们真的可以说女性主义者开拓了女性工作的道路吗?只有在女工的劳动受到世界市场认可时,资产阶级女性才能在社会占上女性主义者引以为傲的独立地位。
我们甚至觉得很难指出在无产阶级女性的斗争史中,一般的女性主义运动对提高她们的物质条件有什么突出的贡献。每当无产阶级女性在改善自身生活标准的方面上有所成就,这都是普遍的工人阶级——尤其是她们自身——的奋斗成果。女工为着提升劳动条件及改善生活的斗争史,便是无产阶级为了解放自身的斗争史。
若然不是恐惧无产者之不满危险的爆发,还有什么驱使工厂主提高劳动价格、减少工时,并采择更好的劳动条件?若然不是害怕“工人骚乱”,还有什么可说服政府为限制资本剥削劳工而立法?
世上没有一个政党如社会民主党般以捍卫女性为务。女工首先是工人阶级的一份子,而无产阶级大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地位和一般福祉愈叫人满意,长期而言,对工人阶级的利益便愈大。
面对日深的社会困局,为了解放事业,真诚的战士必不可陷于悲痛的困惑。她不能不看到一般的女性运动对无产阶级女性那么少的贡献,它对改善工人阶级的工作及生活条件是多么的无力。在那些为平等而奋斗,却仍未采纳无产阶级世界观,或未发展出一个更完美的社会制度将至的坚定信念的女性而言,人类的未来或许灰暗无光、了无生气、无法预料。在当代资本主义仍未被改变时,解放对她们一定看似不彻底,亦无所偏向。绝望会勒紧那些思想更深邃、更敏感的女人。只有工人阶级能在这个社会关系扭曲的现代世界中保持士气。它已坚定和谨慎地往目标迈步前进。它把女性工人带到战列之中。无产阶级女性勇敢地于工人那荆棘满途的道路上出发。她的双脚压弯了,她的身躯业已破损。路上仍有危险的绝壁,残暴的野兽近在咫尺。
但只有在这条路上,女性才可以达成那个遥远却可人的目标——她在一个劳动者的新世界之中真正解放。于这场通往光明未来的苦难行军,直至最近还是被受凌辱蹂躏而毫无权利的奴隶的无产阶级女性,开始学会了抛弃紧捏着她的奴隶心态,一步步把自己转化为一个独立工人、一个于爱情上自由的独立人格。正是在无产阶级战列中奋斗的她,为女性赢得工作权;正是她,这个“妹妹”,为着未来“自由”与“平等”的女性奠基。
因此,为何女性工人应寻求与资产阶级女性主义者结盟呢?谁,在实际上,会在这个同盟中获利呢?肯定不是女性工人。她是她自身的救世主;她的未来就在她手里。女性工人捍卫她的阶级利益,并不被那些言称“所有女性共有的世界”的伟大演说所蒙骗。女性工人一定不可忘记,亦没有忘记,当资产阶级女性的目标是要在一个反对我们的社会框架中保障她们自身的福祉,我们的目标便要在这个老旧过时的世界中,建起一座普世工人、同志情谊与自由之乐的辉煌圣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