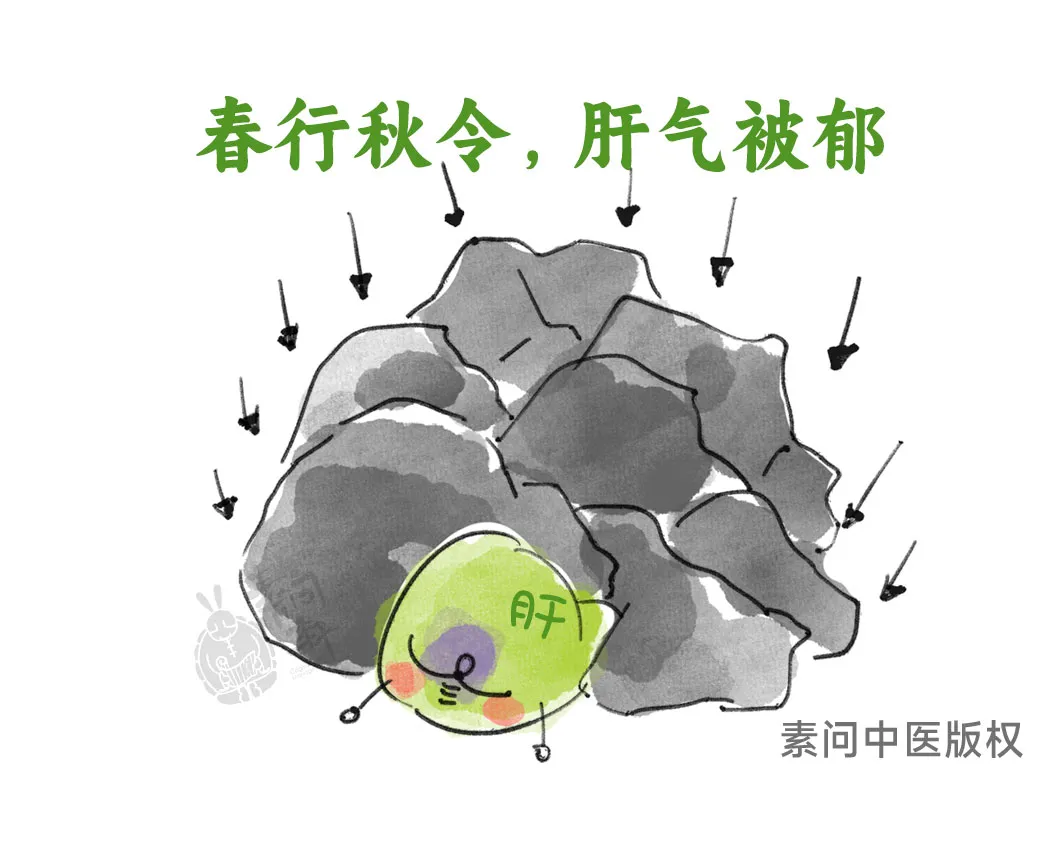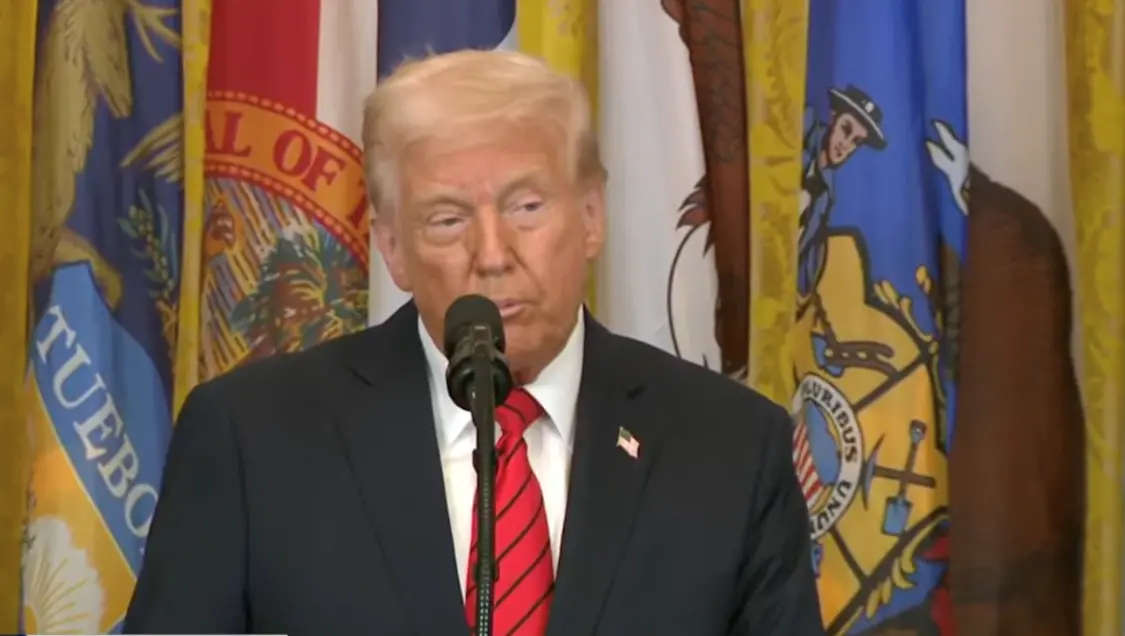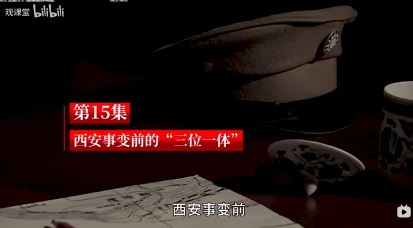白刚 | 数字资本主义:“证伪”了《资本论》?

数字资本主义:“证伪”了《资本论》?
白刚 | 文
摘 要:数字资本主义借助于网络技术和数字信息,实现了资本主义存在方式的数字化生存以及资本的持续积累和不断增殖。表面上,资本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及剩余价值的获取不再取决于劳动,而取决于信息和技术。实际上,数字资本主义以经济学革命的名义掩盖了私有化生产方式,以技术决定论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真实来源,以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掩盖了剥削,以资本积累掩盖了贫困积累和不平等。在数字资本主义这里,资本主义之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私有制和价值规律没有变。所以,数字资本主义依然处于《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问题域之中,它并没有证伪和否定《资本论》。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资本论》;信息技术;数字劳动;价值规律;资本积累
“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capitalism)是指资本主义进入了信息时代,网络信息技术成为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对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数字资本主义也就是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正如美国教授丹·希勒指出:“在扩张性市场逻辑的影响下,因特网正在带动政治经济向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1]15对此,法国学者斯蒂格勒也强调:伴随着网络的出现,人类纪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网络在今天对我们而言,就像铁路对人类纪的初期而言那样的意义重大。[2]9表面上看,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使资本主义的运转貌似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为激烈的转变。但实际上,变化的只是资本主义的“外围”和“保护带”,也即其具体的运转方式,以通过资本增殖来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资本主义的内核并没有变。也就是说,决定数字资本主义之为资本主义的“资本芯”根本没有变,数字资本主义仍然处于马克思《资本论》所把握和解释的概念与逻辑框架之内。
一、“经济学革命”还是“经济学变形”
表面上看,数字资本主义的出现,好像使今天的经济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因为数字资本主义使我们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全面技术化、数字化了。对此,美国学者尼葛洛-庞蒂形象地指出,整个世界已经因为日益依赖于信息技术而变得数字化,人类已经进入“数字化生存”时代。这一时代“是一个计算战胜了其他一切而成为决策准则的时代”。[2]9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信息技术取代金钱和上帝进而决定和主宰一切的时代。在这一时代,生产方式实现了从物质性的生产的支配地位到非物质性的生产的技术(数字)霸权的转变。正是这一转变,促使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危机的周期性变化,不取决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取决于信息技术市场的风云变幻:“信息技术投资,尤其是网络应用,成为工业与金融巨额资本重组的枢纽。”[1]147为此,意大利著名学者奈格里强调:“数字化技术已经深刻地变革了生产方式以及认知和沟通的方式。”([意]奈格里:《固定资本的占有:一个隐喻?》,见《第四届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暨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大学2017年6月),第147页。)人们已经全面陷入了信息技术控制的汪洋大海之中,信息技术一跃成为了今天最大的意识形态,一种符合新自由主义市场逻辑的意识形态。在此意义上,一些人认为数字资本主义促成了今天经济学的革命,或者说,数字资本主义就是新经济学的代名词。
实际上,数字资本主义的出现,只是表明资本主义的存在形式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从电子自动化到网络信息化的发展和跃迁,并不代表资本主义通过资本增殖而攫取剩余价值的本质有所改变。也就是说,数字资本主义只是表明资本主义攫取剩余价值的手段和方式有所改变,但资本通过汲取活劳动而增殖自身的本性没有变,资本主义攫取剩余价值的目的和宗旨也丝毫未变。反过来,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和技术成了支配劳动者的主体,仿佛比劳动者更具增殖资本的巨大作用。在资(知)本家看来,今天资本的增殖和剩余价值的获取,不是依靠工人和劳动,而是依靠机器和技术,以致“技术创新成了反映资本家欲望的一种拜物对象”。[3]99由此可见,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只不过是“技术拜物教”和“信息拜物教”取代了“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人们由膜拜商品和货币转向了膜拜信息和技术,而经济学的“拜物教本质”———不管这一“物”是商品和货币还是信息和技术———并未发生实质性转变。经济学只是在存在和运转方式上由“生产性生存”转向了“数字化生存”,或者说由“实体性生存”转向了“虚拟化生存”,经济学只是发生了“运转方式”的“变形”,而并未发生“所有制”的“革命”。
其实,早在《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中,马克思就通过论述机器大生产揭示出了科学技术对增殖资本的作用及其本质。机器大生产“这里包含的,不仅是科学力量的增长,而且是科学力量已经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尺度,是科学力量得以实现和控制整个生产总体的范围、广度”。[4]150在这一意义上,今天的所谓数字资本主义,信息技术实际上起了与机器大生产一样的作用。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虽然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发生了形式上的变化———越来越信息化、数字化和虚拟化,但这千变万化的背后,只是表明资本主义攫取剩余价值的方式更具灵活性、隐蔽性和欺骗性,其本质依然是以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逻辑统治。数字资本主义改变的只是资本主义的存在形式和存在样态,而不是存在的本质———资本主义私有制。对此,马克思早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有过明确指认:“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合的生产方式。可见,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4]94所以说,资本主义只有发展到数字化生存的时代,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才获得了它最充分、最完全的发展。而资本最充分、最完全发展的时候,也是资本的矛盾最充分、最彻底暴露的时候。对此,美国著名学者大卫·哈维有着清醒的认识:目前许多人寄厚望于“基于知识的”资本主义,利用科技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但作用有效更有限;其结果是劳动者就业机会不断减少,而资本从知识产权中榨取的租值则越来越多。所以,“虽然新科技和新组织形式,向来对我们摆脱危机大有帮助,但它们从不曾发挥决定性的作用”。[3]19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数字资本主义不仅不是经济学的革命,反而是经济学的危机。随着数字化生存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私有化生产方式及其矛盾也达到了其最极端的可能性。
二、“技术决定”还是“劳动决定”
资本主义进入数字化生存时代,表面上看是运用信息技术的数字劳动在资本增殖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数字化极大地提高了资本增殖的机会,加速了生产线的运转,或者说使其商品获得了速销,因为虚拟的工厂能够在网上发现高技术与低工资间最完美的结合”。[5]29在此意义上,数字资本主义甚至认为数字劳动已经取代雇佣劳动,雇佣劳动走向终结了。但实际上,技术只是劳动能力的延伸,真正在数字化时代对资本增殖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现实的人及其掌握和运用技术的劳动能力。数字资本主义对技术的推崇和膜拜,只是掩盖和遮蔽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使资本主义的存在更具合理性和合法性,剥削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所以,在《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中,一旦我们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解剖术”解构了数字资本主义的信息范式,不是把被信息社会替代的工业社会,而是把资本主义本身作为分析起点,我们就会明白,信息化生产的工业化,尤其是机械复制和数字控制能力本身,就不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事实上,问题的核心在于资本在信息领域的不同商品化策略和积累模式。[6]也就是说,不管资本主义如何信息化、数字化甚至虚拟化,要理解它的庐山真面目,仍然必须面向资本本身。这也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具有的现象学意义。在此基础上,关注数字资本主义的美国学者希勒,在描述信息化资本主义“创造性毁灭”的动力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看到了信息商业化条件下社会财富和资源配置的极度不合理以及公共服务原则的被侵蚀。在实质而重要的意义上,数字资本主义促成生产运作改善的科技及其产品商业化的原动力,与其说是从知识中获致,毋宁说是从追求财富的活动而来。这种介于科技和利润之间的有机关联,是用科学来充当情合之媒的。[7]所以说,真正决定资本增殖及剩余价值获取的,绝不是打着科学和技术幌子的数字劳动,而是现实的人之鲜活劳动。不管资本主义怎样千变万化,现实的人之活劳动依然是创造财富的第一源泉。
在《资本论》第一卷“机器和大工业”一章中,马克思就强调资本主义使用技术和机器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减轻工人每天的辛劳,而是为了使商品便宜,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8]427一句话,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机器和技术只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而不是解放工人的手段。在技术的全面宰制下,资本(数字)借助于信息和技术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独立性和个性,而作为劳动者的人却越来越丧失了独立性和个性,越来越成为数字的奴隶,数字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使人和世界越来越陷入了海德格尔所谓的技术的全面“座架”之中。在此意义上,在数字信息信手拈来的大数据、云计算和“互联网+”时代,人们创造、使用的网络技术及从事的数字劳动,正在演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来支配人、奴役人,从而使人成为数据网络技术链条上的一个个环节。[9]作为劳动者的人被牢牢地绑在数字的战车上,已越来越陷入了通往奴役之路的“数字牢笼”之中。所以说,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控制依然是一种异化和颠倒:“但是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4]244数字资本主义的这种异化和颠倒,必须由工人联合生产的自由劳动才能再颠倒过来,也即机器和技术必须变成“联合的工人的财产”,而不是脱离工人进而宰制工人的“私人的财产”。
由此可见,数字资本主义借助于信息技术而实现的资本增殖及其剩余价值的获取,表面上是网络技术的功劳,实际上是应用和研发技术的活劳动所为。技术只是劳动能力的延伸,而绝不是劳动本身;技术可以提高和发展劳动,但绝不能取代劳动;技术是死的,劳动是活的;正是活的劳动把死的技术变活了,变得富有创造力了。所以说,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依然是资本主义世界结构的枢纽和核心,资本主义财富的创造和获取并不取决于死的技术,而取决于活的劳动,活劳动依然是资本增殖和创造财富的最终源泉。说到底,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里,问题不在表面的技术本身,而在于把技术放置于它所在的社会关系中去看待。无论技术怎样发展,都应该受到约束和引导,以便它不是服务于某人的私利,而是真正为了提高人类福祉。因此,真正决定和推动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不是技术价值论而是劳动价值论。如果离开了劳动,完全依赖于技术,就会导致算法的和机械的东西被具体化、物质化为逻辑的自动化与自动主义,进而催生了虚无主义的降临。[2]9如此一来,单纯计算性的数字资本主义就会成为“自动的物神”(马克思语),就会走向彻底的虚无主义,就会变得更加敌视人了。
三、“价值规律”还是“剥削规律”
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决定了价值增殖规律和等价交换规律的运转不是取决于劳动,而是取决于技术,好像是劳动价值论转变成了技术价值论。由此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更具数字化和信息化的特点,更仿佛与劳动无关。“信息供应链的管理、智能化的开发软件以及在线劳力拍卖,目的都在于营造一种能够把最廉价的劳动力、最好的生产资料、最新的技术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巨大利润的氛围。”[5]29也因此,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技术实现的对劳动者的奴役和剥削更具隐蔽性、欺骗性和迷惑性,反而致使劳动者在不自觉中陷入了更全面的被控制之中。正是在技术的幌子下,表面的价值增殖和等价交换规律的背后,是工人阶级被剥削、被奴役的加强,而工人阶级对此却越来越不自觉和无意识,越来越成为技术的奴隶,技术和数字统治一跃成了资产阶级最大的意识形态。
本来,在《资本论》的视野里,作为人的劳动能力延伸的技术,是为创造财富和解放人服务的。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下,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一方面创造了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的新的强大动机;另一方面,部分地由于使资本过去无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阶层受资本的支配,部分地由于使那些被机器排挤的工人游离出来,制造了过剩的劳动人口,这些人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命运”和规律。由此产生了“经济学上的悖论”,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8]469所以,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本来是服务于人的技术反而变成了“对工人的极端可怕的鞭笞”(马克思语)。由于信息技术的全面控制,数字资本主义会比机器大生产更加全方位地推动劳动者及其劳动,成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的最可靠的手段。因此,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数字)价值规律必然转变为劳动剥削规律。“被称为‘数字比特’的网上资产阶级将拥有利益、潜力和胜利,而这些东西是与物质社会的非在线‘贫民’所追求的东西直接对立的。”[5]28对此,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明确指出:“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8]487也就是说,作为表面等价交换的技术价值规律,在数字化和信息化时代,必然转变为实际不等价交换的劳动剥削规律———剩余价值规律———这正是马克思最伟大的“两大发现”之一。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数字资本主义只是表明机器和技术“比资本更加具有压迫性、更加飞扬跋扈、更加具有剥削性、充满矛盾和邪恶”。[10]这才是数字资本主义之所以还是资本主义的实质,数字只是掩盖其剥削本质的最大遮羞布和鬼话。在此意义上,数字资本主义也就是一种数字暴政。所以说,在《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里,数字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和等价交换规律,必然转变为技术和数字掩盖下的更高级、更隐蔽的对劳动者的剥削规律。但数字资本主义却通过技术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很好地掩盖、遮蔽甚至是美化了自己的剥削本质。因此,数字资本主义绝不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技术改良,而是当代资本主义剥削的技术隐形。而使“隐形者显形”的,正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
在《资本论》这里,资本主义的技术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发展,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矛盾的极端化、尖锐化和全面化的体现。也就是说,正是数字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意味着资本主义依然在自掘坟墓,即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更高级的共产主义创造条件:“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用暴力消灭资本———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4]149由此可见,正是《资本论》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才拨开了笼罩在数字资本主义身上的技术迷雾和神秘面纱,进而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命运。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突出贡献,就在于运用其作为“抽象力”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揭示和论证了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和等价交换规律如何转变为人的贬值和不等价交换的剥削规律,也即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必然走向剩余价值规律,或者说,资本主义价值规律必然伴随着剥削规律,价值规律越发展,则剥削规律越深入。而这一“相生相伴”规律在资本主义发展到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更是得到了深刻的、充分的和完全的体现。
四、“资本积累”还是“贫困积累”
数字资本主义的出现,给人们造成的最大假象就是所谓的“技术面前人人平等”,仿佛信息和技术与国界、民族、政治甚至种族无关。在数字资本主义这里,由于把信息技术领域作为资本积累的新场域,它既拓展了资本积累和增殖的空间,同时也扩大了剩余价值的创造和占有空间。在此意义上,数字资本主义借助于技术和信息,好像既实现了资本的积累和增殖,也实现了人与人之间表面的自由和平等,数字资本主义似乎已经完成了自古典自由主义以来借助于商品、货币和资本所未能完成的“自由、平等和所有权”。数字资本主义俨然变成了“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或“无摩擦的资本主义”(比尔·盖茨语),更有甚者“乃至把资本主义的概念移走”(大卫·哈维语)了。
实际上,数字资本主义借助和运用信息技术,确实比先前的机器大生产的资本主义更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和增殖,更有利于剩余价值的创造和攫取。网络和信息技术使资本的流动、积累和增殖呈现指数化增长,无国界资本流动甚至可以左右世界经济大国的货币政策。在此基础上,技术与资本的联盟,实现和完成了资本积累的最新形态。也就是说,技术和信息的充分运用,为资本的积累开辟了最新最快的高速通道。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仿佛重新获得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资本主义好像重生了。但资本积累带来的,却不是人的真正自由、解放和平等,而是劳动者的相对贫困。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进入数字化生存,伴随着资本积累而来的却不是劳动者财富的增加,而是劳动者相对贫困的积累。由此可见,数字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反而是越拉越大。对此,希勒用大量的数据描述了信息化和全球化带来的新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从长远来看,日趋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带来的种种问题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我们很难认为社会富裕程度的差异是上个历史阶段的残留。这种差异显然是由数字资本主义本身造成的。”[1]281所以在数字资本主义这里:一方面,它会赋予那些靠信息获利的垄断资本更大的权力,实现资本的积累和增殖;另一方面,其他人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剥夺掉一部分权力,相对资本积累的却是贫困的积累。而这必然会造成更大的权力落差,致使贫富鸿沟将来会成为一个“政治问题”。[11]这一“政治问题”,实际上就是当今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一直关注和强调的平等问题。由此可见,数字资本主义造成的“数字鸿沟”也就是“平等鸿沟”,它必将带来新的政治鸿沟、民主鸿沟甚至文化鸿沟,其结果必然是“网络强化了已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不平等,并把它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5]30但是对由网络带来的新的不平等问题,人们却被技术平等的幌子所遮蔽和迷惑,而看不到问题的实质。为此,大卫·哈维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比“对不平等的平等对待更不平等的了”。
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使资本主义陷入悖论之中:一方面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是贫困的积累。对此,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有着清醒的认识: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发展生产力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成为局部的人而畸形发展,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8]743-744故此,马克思才会强调:“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12]更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借助于《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指出了问题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揭示了问题产生的根源:“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8]508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不管资本主义如何信息化、数字化,只要技术是一种“资本主义应用”,资本积累就必然伴随着贫困积累。所以,数字资本主义借助于信息技术不仅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现存的矛盾,反而依然充斥着传统工业资本主义固有的“劳资矛盾”的“二律背反”。
《资本论》所揭示和论证的数字资本主义依然充斥的“劳资矛盾”的“二律背反”,被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进一步证实。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通过对欧美、日本和巴西、印度等十多个国家近三百年发展数据的分析,揭示和论证了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r>g)的事实。由此可见,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借助于网络技术和信息数字,只是掩盖了贫富差距拉大的事实,而根本没有也无法消除贫富差距。而马克思《资本论》的高明之处在于,它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和阐明了在资本积累的进程中,所有权如何变为对他人财产的掠夺,等价的商品交换如何变为剥削,自由平等如何变为阶级支配的不自由和不平等的事实,并为消除这一不自由和不平等提供了最佳的可行性方案———在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协作生产”来“重建个人所有制”。
参考文献:
[1][美]丹·希勒.数字资本主义[M].杨立平,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5.
[2][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论数字资本主义与人类纪[J].江苏社会科学,2016(4):8-11
[3][美]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M].许瑞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99.
[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美]提姆·鲁克.应对数字鸿沟———计算机世界里的严峻现实[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6):26-30.
[6]赵月枝.丹·席勒的信息时代的资本论研究[N].中华读书报,2008-07-23(015).
[7][法]利塔奥.后现代状况[M].岛子,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138.
[8][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27.
[9]李仙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的辩证法[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4-27(004).
[10][美]杜娜叶夫斯卡娅.哲学与革命[M].傅小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66.
[11]王建峰.告别信息崇拜解构数字资本主义[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1-19(002).
[12][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
文章来源:上海大学学报 2018年7月 第3S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