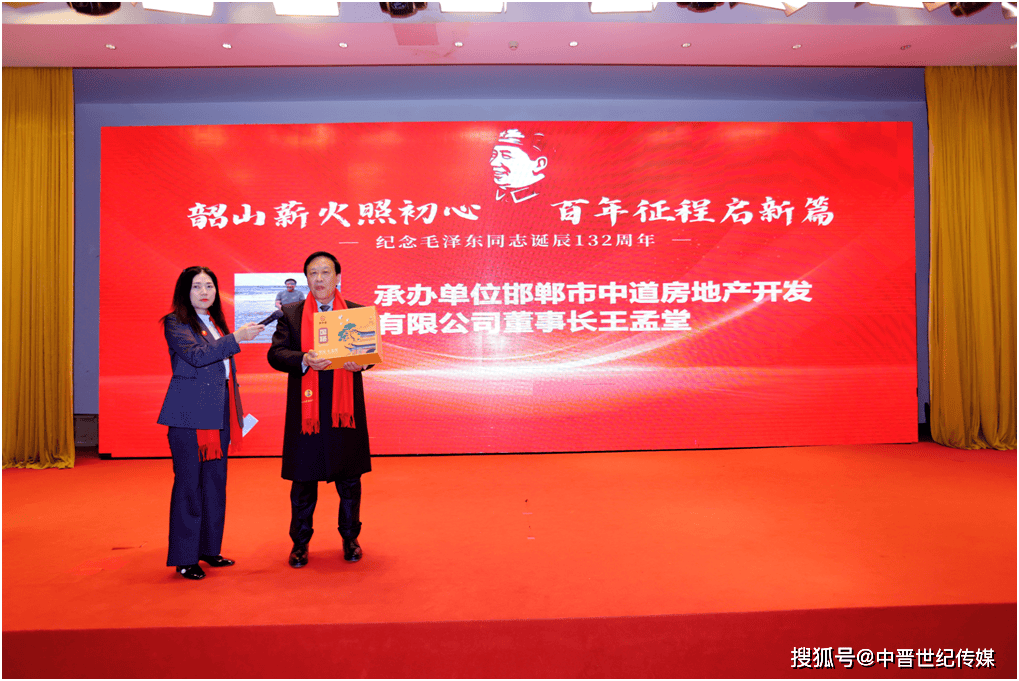张文木:好理论要回答时代问题

我常想,好的理论最重要的是要回答时代问题。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这是我们中信基金会的宗旨。我作为一个学者,拥护这个宗旨而且决心践行它。现在出版的这套《张文木战略文集》就是我践行这个宗旨的学术体现。
坚持事实求是,是我党从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的重要经验。在中国革命的时候,曾经以苏联为榜样,结果丢掉了根据地。在革命中“苏化”不行,那在建设中“美化”也是要出事的。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走得远,中国能够走到今天遵循的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我在做研究的时候,对这一点体会最深。
实事求是里头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唯物论,一个是辩证法。唯物论就是人得吃饭,辩证法就是人的能力是有极限和底线的。国家也是有生命的,也有“吃饭”的问题和战略极限的问题。
国家发展需要消耗资源,这是唯物论,这也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底线。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任何国家都有其能力极限。过了这个极限,国家就会出现衰落。由此我提出“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扩张”的命题,这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命题。国家不能饿死也不能撑死。国家战略的本质是让国家长治久安,而不是让国家拼命的学问。拼命首先是为了长远目标而不是相反,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一赌国运的事我们不干。走得远的路才是路,这就是中国道路。
我们做学问是为什么的,学问是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必须带着刀子。我治学的目的是把学问变成刀子,如果把刀子研究成所谓的“学问”,这样的治学就失败了。北宋时期的文化人就是把刀子变成学问,于是就出事了。现在学界有些人“言必称希腊”,都是把“刀子”变成学问了,仅靠“之乎者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坚持问题意识,解决问题是我的治学导向。
我常想,今天我们的伟大实践,在22世纪的孩子眼中将是怎么的?这就要求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得要认真研究并正确反映这个时代。
一个伟大的时代要有文治,还要有武功。汉朝当然不能没有汉武帝,但也不能没有司马迁。做好“司马迁”的工作,深刻地反映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我们今天知识分子的使命。
22世纪的人认识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取决于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反映这个时代的深度,我们如果不能把这个时代准确地反映出来,那我们就等于辜负了我们的时代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我最怕22世纪的孩子对今天我们时代的伟大实践的理解被那些虚无的东西给歪曲了。怎么办呢?只有把它写好。

我们拒绝“言必称希腊”是对的,但前提是要扎扎实实地去把中国的东西写好,光批评而没有建设是不行的,要把中国的问题扎扎实实解决好了才行。所以,不唯上,只为实,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观察问题,坚持唯物论、辩证法,形成融合事实求是、中国道路和中国学风于一体的理论体系。
研究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服务于党的“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围绕这个主题,这些年我做了这几方面的工作。
迄今为止的西方的战略理论特别是地缘政治理论,是为帝国主义扩张服务的,实际上西方国家的战略理论失败也就是在这一点上。历史上搞帝国的没什么好的结果。西方的地缘政治,从麦金德到布热津斯基,西方国家扩张的特点就是没有节制,这使得一个又一个帝国垮掉。而如果我们“言必称希腊”的话,我们的战略研究也会没有节制,这对中国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对西方的战略理论要改造,在倒掉“洗澡水”的同时要把“婴儿”留下来。
改造当然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改造,唯物论、辩证法,一个都不能少。这就是有多少资源做多大事,有多少干粮走多远的路。经过这样的改造,地缘政治理论就回到毛泽东的“寰球同此凉热”正道。毛泽东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这是毛泽东“不称霸”思想的较早表述,有了这个思想,地缘政治理论就有了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目标与资源相匹配是我考虑中国地缘政治理论的一个基本视角,这个视角使我的地缘政治的理论摒弃了其原有的扩张本性并使之可以为中国的发展服务。跟身体一样,有多大体力扛多重的活。许多国家,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日本等,都是被自己制定的超出自己能力的目标打倒的。目标设计不当是国家失败的重要原因。
为此,我又对世界主要大国战略能力的底线和极限重要一番实证研究。研究世界大国比如英国、俄国、美国等国家扩张的极限,以及它们能守住的底线和它守不住的底线。这些就在世界大国冲突的历史中可以找到:在几百年的国家扩张史中,它们每次在哪失败,在哪成功,在哪些地方就过不去了。
经过历史比较发现,英海权国家必须死守的线大概就从大西洋经苏伊士运河进入印度洋这条线;美国是从夏威夷西进太平洋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这条线,台湾不在美国必须死守的战略底线上,因此美国不会为台湾遑论东北亚做出重大牺牲。
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告诉塔夫脱总统说,东北亚那不是美国可以拿下的地方,美国的力量到不了那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太平洋战场上,美国就没有从阿拉斯加打日本,因为它知道从出击远离美国生命线,因而战略价值极为有限。富兰克林·罗斯福认为:东北亚是俄国、中国和日本的事,美国在这里介入将一无所获,因为这里已超出美国的力量极限,因而不应在此美国投入战略力量。

引力加体重,人能跳的高度也就定了。找到了世界大国的战略底线和极限,也就知道哪里是我们中国的战略张力的底线和极限。战略目标如果超出了国家能力,那结果是自己所获便是打倒自己的原因,这是历史上所有的帝国无一成功的原因。所以国家战略目标不能制定得太远。
在我想将这些血写的经验总结出来,为未来中国参与世界治理时写一部世界政治的《资治通鉴》。由此得出的论断就是:“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亡于世界性扩张。”
海权研究和实践西方一直占据着优先地位,在这方面中国有些学者“言必称希腊”,对中国海权发展不太自信。但我在研究中国的海权时发现,如果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看问题,就会看出中国海权有足以让西方刮目相看的优势。
我们知道,印度洋是世界工业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地区。西方为了获得工业矿产和能源,它必须建立漫长的通往印度洋和波斯湾岛屿链。而中国不同于远离印度洋的西方海权国家。
远道而来的西方海权国家在印度洋只能靠占领岛屿而存在,目前我们能读到的海权理论提供的都是这样的视角。但中国并不是这样的远在千里的国家,而是临近印度洋的亚洲最大的国家:它背靠可称作全球战略制高点的昆仑山,放眼世界面积最大的海域,东接太平洋,南近印度洋,居昆仑观两洋为周边,尽占地利优势,这样的地缘政治形势在世界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
为什么要海权?海权本质上是为了从全球的范围来解决国家工业资源问题,而中国东接世界最富有活力的新兴东亚市场,西接世界的工业资源聚集在印度洋,东面的财源和西面的能源离我国很近。既如此,我们就没必要建立美国那样的漫长岛屿链。这就大大减轻了我们海军的负担。海军是用于为国家争资源的。如果资源就在我们家门口,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建立西方那样的长线海上作战力量。
印度洋从而中亚是历史上所有帝国坟墓,英帝国覆灭于此,美帝国也衰落于此,苏联更是没过阿富汗就解体了。所以,胜者在短地,谁离资源近,谁就拥有可持续的战力。而印度洋恰恰就在我们家门口,因此,中国不需要帝国式的扩张。由此看,与英美国家相比,中国推进海权事业比西方海权国家更有地缘政治优势。
航空母舰是国家体现其制海能力的重要标志,在这方面西方国家长期占据优势,这也是我们一些学者在海权问题上不自信的原因之一。但我们也要看到,航空母舰的只有在远海作战才能显示其海上作战优势,在导弹可以饱和覆盖的大陆近海,航母优势就会大打折扣,因为大陆本身就是个超大的“航空母舰”。这些发现有利于我们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打破了对西方海权迷信,建立起我们实现祖国统一的信心。
至于地缘政治,在这方面,中国也有西方国家不可比拟的优势。
欧洲地缘政治的特点是从中间小、四周大,这种地缘政治结构最不利于欧洲的稳定;中国这边正好相反,是中间大、四周小,这种地缘政治结构有利于亚洲稳定。
欧洲的地缘政治结构有利于英国的长期控制,而亚洲的地缘政治结构却不利于日本右翼的野心,那他们最希望的就是中国大陆出现欧洲式的破碎——正是欧洲大陆的破碎才确立了英国的霸主地位。所以,如果日本不放弃它的“大东亚”旧梦的话,它与中国的矛盾就是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的矛盾。相反,在雅尔塔体系框架国,中国和美国是有许多可以合作的领域。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国情和地缘政治特点,我对中国未来外交布局提出五条建议,这就是:国内保政权,国家保主权,周边保格局,全球稳利益,世界保和平。
国内保政权。我们要走向世界,这没有问题,但不管走多远,但是切记我们的人民军队第一要义是保卫党中央。唐玄宗时高仙芝打得很远,打到了帕米尔。这可以理解,当时西面有“黑衣大食”,北面有突厥两种力量压唐朝。当时有作战力的军事力量都拉得很远。与此同时,长安的卫戍力量就薄弱了。中枢空虚,唐玄宗只能尽力安抚安禄山,可安禄山不买账,发动了“安史之乱”,把唐玄宗从长安赶到四川。这时朝廷有战斗力的部队都拉得太远,无力回救。
“安史之乱”后,唐朝开始衰落。这个教训我们今天也要牢记:我们不能得鱼忘筌,不管走得多远,保卫党中央保卫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政权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国家保主权,周边保格局。当前保主权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祖国统一。在此前提下,我们要经营好中国的周边。其中的关键是维护以中国为重心的亚洲特有的中间大、周边小的地缘政治格局。这种格局对亚洲和平是有利。与此相反,欧洲中间小四周大的格局就容易爆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爆发源头就是欧洲。
全球护利益。国家的力量永远是有限的,在我们力量极限之外的远方,就应当用政治和友谊的方式来维护。这就是《尚书》所说的“柔远能迩”,意思是用怀柔远方可以使其亲近。毛泽东时期我们修的“坦赞铁路”就使非洲人民记住了中国人民的友谊,并在中国最需要的时候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迎入联合国。
最后是世界保和平。今天的美帝国统治权从昨天的金融垄断资本集团转到军工垄断资本集团手里。特朗普上任后,军工订单飙升,而军工生产的出路只能是战争。如果说昨天世界动荡是美国金融资本集团的需要,那么今天的美国军工资本集团需要的就不是一般的动荡,而是大规模的世界战争——只有战争才能使军工产品迅速形成利润。
与此相反,我们中国是为民生服务的实体经济生产,这种经济生产的利润形成周期较长,因而它需要的是和平环境。这样,世界和平就成了今天美国的“敌人”;同理,世界和平就成了我们必须高举的大旗。保卫和平,就是保卫中国的发展,当然也是保卫世界的发展。和平对中国和世界来说日益珍贵,而对美帝国来说则成了利润增长的障碍。
总之,服务于“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是我理论的明确指向。这就是,在第一个百年中我们必须解决台湾问题。台湾问题解决以后,沿中国东部的海域南北连贯了起来,到那时原有的“北海”“东海”“南海”中涉及中国主权海域就会连贯为“西太平洋中国海”的概念。在这一区域,中国沿海还会出现第二次改革开放热潮。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拉动了中国内地的发展,那么,下次则会拉动西太平洋的东亚国家的整体发展;这一地区的国家和人民将会率先体验到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带来的有别了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新文明。2019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文表示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区,此举意义非常深远。
1935年10月,毛泽东在《昆仑》一词中对未来世界有过“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设想。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批注中说:“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
显然,两岸统一后,包括东亚国家将会更多地分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年即2049年,东亚的共享经验就可以进一步西移至印度洋。
今天,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我希望未来的中国人民牢牢建立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中国强大起来后,不要再重复帝国主义的扩张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保证我们的中国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