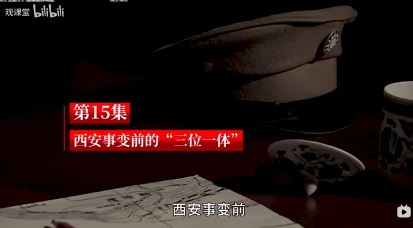主流经济学不为中国的发展买单
上一篇《主流经济学不懂中国》里面,我们谈了公有制主导的基建体系如何挤出超额利润代表的无效率,通过活跃要素流通向全社会输送巨大的经济效益。今天我们继续来分析公有制主导的另一大生产领域,也是长期被主流理论忽视的生产过程:劳动力的再生产。
理性人需要吃饭吗?
人想要健康地活着,就必须吃喝、休息、睡觉、治疗;人想要提升知识技能,就必须上学、读书、接受培训;人想要生育下一代,就必须孕育并承担孩子的养与教——这些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常识,却不是主流经济学的常识。
相比对商品生产的详尽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劳动力生产的刻画非常幼稚苍白。在主流宏观模型里,个人在工作带来的消费效用和不工作带来的休闲效用之间进行权衡,从而决定自己花多少时间工作,也就是供给多少劳动力。吃饭休息变成了锦上添花的效用来源,而不是不可或缺的生理过程,劳动力的供给者做到了字面意义上的“不食人间烟火”。
主流经济学类比物质资本的概念,创造了“人力资本”,在学习、医疗、技能培训等领域投入的金钱计为人力资本,认为这能让劳动者创造更多产品、分得更多收入。相关文献大多集中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不甚在意折旧;少数讨论折旧的论文也主要考虑年龄增长和技能落伍,饥饿、疲劳等最日常的劳动力消耗反而很少讨论,换句话说,人力资本的重点还在“资本”不在“人”,饿了三天的搬砖工和天天吃饱的搬砖工的人力资本在主流经济学眼里没什么区别。
物质决定意识,黑死病造成农奴短缺的记忆属于封建地主,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大吃低人权红利从来就没断过顿。美洲原住民奴工、黑奴、契约工、殖民地劳工、第三世界新城镇化人口、难民移民,只要西方人肯付出暴力或者金钱的代价,就会有精壮廉价的劳动力像韭菜一样冒出来,挤掉病弱多事的劳动力。
因此主流经济学对基础生理需求的天真漠视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只需考虑“人工成本”,也就是企业主购买工人劳动力的支出,而不是工人作为一个人恢复和生产劳动力的成本。
还好马克思把工人当成人看,劳动力的再生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劳动力是消耗性的,人只有满足了吃住用度和休闲学习的需求,才能恢复在生产中消耗的体力或脑力,满足这些需求的费用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
模型的好坏不在于使用高大上的数学工具,而在于能否与经济现实相吻合。主流经济学用无数的模型和实证计量探讨为什么人工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而不可逆地上升、出生率则不可逆地下降,但只要现实中的工人还需要吃饭睡觉,他们的解释就永远不可能比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理论更有力。
根据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资本家压低工资,工人就减少工作时间(劳动力供给),在家躺着享受休闲的效用,从而迫使资本家重新提高工资,由此还衍生了很多“自愿签合同不能叫剥削”的谬论。何不食肉糜,食利者把自己躺着看进账的爽感嫁接到打工人身上,手停口停的打工人何来主动压缩劳动力供给还能悠闲愉快不怕饿死的底气?
马克思指出,资本家压低工资的理论下限面临工人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约束,即使资本家可以对个体工人说“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如果不付出补偿该岗位劳动力消耗的最低价格,劳动力群体也会因不可维生被迫停止供给——饿死或转行。
从时间轴纵向看,社会总产品发展丰富的成果理应由全社会成员共享,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水涨船高。封建经济下,农民只需口粮、蔽体衣物和简陋住房就能完成再生产,工业革命开始后,产业工人的再生产需要摄入一定的蛋白、接受基础教育、购买工业品,以及对抗城市疾病的医疗服务等等。到了今天,恢复脑力消耗和愉悦身心的物质精神消费也变成了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当然组成。
纳入阶级因素,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更加复杂。中产阶级会把“小资轻奢”的景观符号算作自己的再生产成本,必须为吃穿住行附加更高的“装逼价值”。这在劳动力的代际再生产中体现更加明显,无论中产还是上流都大量投资后代的教育和符号塑造,保证下一代劳动力的生产也是本阶级的再生产。
上面描述了劳动力再生产需要的社会产品和服务,资本主义通过价格机制把它们纳入市场交易,然后劳动力再生产撞上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自由劳动力制度要求劳动者与资本家签订“自愿且平等的契约”,自己承担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激励”工人为了生活的重担不停奔走劳作。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通过研究南北战争前奴隶庄园的账本资料,发现南方黑奴的饮食、居住环境等部分生活质量指标优于北方工人,北方的低人权优势甚至强到了奴隶主闻之自愧的地步。
他估算的具体数值在学术上尚存争议,但资本主义的黑色逻辑展现无遗:被剥夺财产权的黑奴是属于奴隶主的“生物性资本”,奴隶主愿意付钱抵消私人资本折旧;而资本家对自由人的劳动力不享有产权,自然他们对这种“非消耗性”经济要素的再生产不负任何责任。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工人必须到其他社会生产者手中付费实现劳动力再生产,利润这个私有制市场的魔鬼开始发挥主要矛盾作用。
衣食住行等均属生活必需品,劳动力再生产“原料”的价格弹性很低,商家很容易强迫消费者吃下抬价。房东抬高出租屋的利润,工人的再生产成本变高,于是要求厂主支付更高的工资,厂主为了维持利润上调工业品价格,使用工业品生产的农业主推高农产品价格,房东再次提高房租以购买等量的工农业产品……沿着劳动力再生产的链条,利润发动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生产成本高,产量就降低,这是任何经济理论都承认的铁律。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不可逆提高,必然导致劳动力供给和出生率的不可逆降低。为了维持政治稳定、经济运转和社会延续,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采取手段把部分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分摊到社会,发展到今天的主要分摊手段有两种:一是政府补贴服务供给者,再向低收入者提供相关服务,二是工会集体议价,掌握更多货币工资支付再生产成本。
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前者本质上是用纳税人的钱为企业利润买单,最后羊毛出在羊身上,比如奥巴马医改搜刮中产养肥保险公司和医院。后者只能让工人更高效地加入到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公共交通、医院等关键基础设施的罢工更是加剧了底层互害的烈度。
体制与廉价社会再生产
铺垫这么久,终于要说到正题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的“体制”掌握着大多数劳动力再生产的生产资料,既降低了再生产的货币成本,又把这些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分摊到社会承担,让劳动者能以低廉的价格实现相对高质量的劳动力再生产。
“体制”是计划经济时代下城市福利系统的产物。城市阻断农民的自然生产,充斥着饥饿、工伤、恶劣的居住条件和传染病,从中世纪巴黎到圈地运动后的伦敦,再到当代马尼拉贫民窟,没有福利兜底的城市永远是穷人的地狱,资本低人权优势的狩猎场。前三十年,新中国采取有保障、有控制的城镇化策略,把新城镇化人口编入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等“单位”,捆绑工作和福利保障,避免进城农民成为贫民窟中用完即扔的干电池。
国企改制后,企业办社会成为历史,政府和事业单位成为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形成了我们今天认知的“体制”。体制覆盖了相当广泛的劳动力再生产需求,包括治安、必需品价格管理、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医疗、养老乃至部分文化体育活动,是世界上最庞大最复杂的社会福利体系。
凭借国企主导的基本商品产销和发达的基层管理,我国劳动力再生产基础保障的缜密程度独步全球。面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引发民众恐慌的“天赐良机”,中盐非但没有借机涨价,还发文抑制自己产品的需求,每一个举动都写满了“违反市场规律”。而某前自由派媒体人饿死在发达国家的新闻,对于适应了高人权最低保障的我们来说过于不可思议,以至于第一时间愿意善意地相信她死于厌食症的折磨。
治安是一切人身财产权利的基石,教育是提高未来收入的必需,医疗服务买卖双方具有极强的信息不对称,这三大服务业特别容易占据垄断地位牟取暴利。在《主流经济学不懂中国》里我们详细论证过,公有制厂商不追求利润,挤干了价格中的利润水分,使劳动力再生产体系“寓福利于价”。
三大基本服务要么不收费(治安),要么几乎完全处于价格管制之下(教育医疗),至少单位整体账面上保持负利润,依赖财政补贴运行,让劳动者只需付出接近甚至低于成本的货币就能实现再生产,从而达成再生产资源的高效配置。
笔者在海外学习期间,一位研究劳动经济学的诺奖得主曾在讲座上提出疑惑:研发是一个人才密集的行业,中国大学研发支出中人员费用占比远低于国际平均,为什么还能取得如此快速的科技进步?
如果让笔者来回答这个问题,答案会是低廉的学费,聊胜于无的宿舍租金,财政补贴的食堂,这些费用投入压制了大学劳动力的成本,也没有计入人员经费科目。而外国大学雇佣博士生,至少要在工资中支付商业化的食宿价格,往往还得涵盖动辄10%以上的学生贷款利息,显然吃睡收租的高额支出是高质量科研产出的不充分不必要条件。
体制不仅在自身内部拧干水分,还能背靠14亿人的统一大市场改变外部供应商的垄断盈利逻辑。这几年医保局“灵魂砍价”的新闻屡上热搜,供药商以往的定价策略是依托专利形成的垄断地位和患者对健康的迫切需求,认为制造稀缺赚取暴利,医保谈判则要求他们将供给扩大到社会最优数量,薄利多销取得合理利润,不必像奥巴马一样反其道而行之,让国家支付垄断卖方的吸血账单。
由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逻辑不同,用GDP、财政支出等“过程”统计量比较各国人权优势毫无合理性。有太多专家或自媒体拿我国医疗、教育、社会救济等支出占GDP或者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很低当论据,攻击我国民生保障差、福利待遇差。但他们没发现按自己的逻辑,阿富汗的福利待遇全球领先,一定是比法、德、比、日等发达国家更高级的润人归宿吧。
实物工作量是检验经济绩效的唯一标准,我们既不嘲笑发展坎坷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不继续鞭尸某些臭名昭著的低人权优势发达国家,比好不比烂。西欧北欧福利国家的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基本维持在10%-12%,人均预期寿命则维持在83岁左右的人类科技极限,疫情期间略有下降。
我国疫情前医疗支出占比为5.4%,21年防疫期间升到6.5%,人均预期寿命升至78.2岁。到了高龄区间,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我国正在用不约一半的社会总资源占用稳步追赶福利国家的上限。也正是因为以挤出利润的少量货币投入完成同等甚至更多的实物工作量,在使用购买力评价法计算GDP时,我国的经济表现都会较增加值法(利润)计算时出现大幅度提升。
还有些事情完全超越了GDP的衡量。相比商品的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涉及更为广泛的社会道德因素,只有排除了盈利追求,再生产的提供者才有“闲心”实现背后的社会价值。教培讲师可以教会学生做题应试,但学校老师育人育德的责任意识绝不可替代;西方乃至香港的私立医院医护在疫情最严重时大量辞职或罢工,我国的医护人员却逆行而上。
2012年前,警察、老师、医生曾因行业的混乱寻租被百姓称为“三大黑”,假设社会只把他们当做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市场化服务卖方,也不会对这些职业产生如此之高的道德期许。
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员本身也需要再生产劳动力,如果他们再生产的成本本身已经很高,仅仅挤出利润还不足以保证公共服务的廉价。英国NHS健保体系虽然由政府运营并免费提供,医护人员的培养和日常再生产都在含利润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动辄罢工要求提高货币工资,医疗服务的“起步价”越来越高,最终政府不堪重负。
我国体制内人员往往享有一定特权,可以在餐饮、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优先接入体制,比如单位廉价食堂,教师子女上学照顾等,代价是货币工资低于与自己同等学历能力的市场就业者,获取市场供给产品的能力比较低。这是计划时代高福利低工资的孑遗,客观上把他们的再生产过程留在低成本的体制内循环,压低了他们对体制支付货币工资的要求,从而使其对外部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进一步降低。
体制搭台,个人和企业唱戏
我们普通人从这套再生产体系中获取的益处不仅是价格性的,还有机会性的。这里又要插入一些枯燥的名词解释:经济学定义中的“需求”,和我们日常的语义大有不同。我们饿了渴了,就会产生吃饭喝水的需求,孩子到了上学年纪,就会产生受教育的需求。但在经济学中,只有在某一价格下获得市场承认(简单说就是付得起钱)的索取欲望才是“需求”。所以食品价格上升食品需求下降,不是人们摄入营养的需求被“调节”了,而是穷人的吃饭权被“调节”了。
诺奖经济学家的异类、新自由主义的鲜明反对者斯蒂格雷茨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很多短缺现象本质上来源于价格被控制在较低区间,无法消灭“理应被消灭”的需求,导致在资本主义国家被掩盖的真实需求被表达了出来。苏联末期家庭主妇排队买面包的场景不会出现在美国,因为饿着肚子的美国穷人知道,排队也买不起面包。
回到国内,公共服务质量终究有高有低,但不能用支付能力抹杀人民对于高质量再生产的需求。治安消防等最最基本的公共服务还能均匀分布在城市内,其他类型的公共服务则需要依照非货币标准进行排序分配,包括户籍、考试成绩、排队等等。
家境一般的笔者读书期间,小升初、中考、高考成绩还是分配下一阶段教育资源的唯一标准,保障了笔者这个小镇做题家还有干部子弟、书香门第竞争一下的权利。而排上队、挂上号就能看三甲的医疗模式,相较分级转诊的免费医疗或按价分诊的美式医疗,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群众迫切的看病需求。
非货币标准筛选当然不可能做到绝对公平,但在较长时期、较大范围内相对公平普惠地分配公共服务资源,也确实没有比“体制”做得更好的答案。何况公家出钱的再生产成本社会分摊模式,本身也要求使用与私人财富脱钩的分配方式,否则必然陷入成本社会化、收益私人化的丑陋境地。
和廉价的公有制基建系统一样,体制主导的劳动力再生产持续向商品生产领域输出利好。仅仅人口基数的庞大决不足以构成“人口红利”(虽然笔者非常非常反感这个词),改开初期,中国人均GDP只有印度的75%,但成立三十年的新中国就已经战胜了血吸虫等公卫顽疾,普及了赤脚医生,推广了乡村教育,人均预期寿命比印度高11岁,成年识字率比印度高25个百分点,婴儿夭折率是印度的一半还低。这支用30年培养的年轻健康、男女参与、有基础文化和纪律意识的劳动大军,成为了我们国家工业化城镇化腾飞的最强动力。
另外简要提一句,总有人试图把“体制”代表的再生产体系描述为城市工人和干部建立在剪刀差剥削农民之上的特权。实际上,前三十年工业向农业人口再生产的反哺是相当积极高流动性的,包括拖拉机、水泥等工业品的平价下乡,赤脚医生代表的现代技术向农村的渗入,知情下乡客观上实现的“能上能下”福利流动等等。
而“工贵”印象的产生,恰恰来自于80-00年代再生产体系的激进私有化,把工业和服务业成果越来越多固定在货币支付能力更强的城市,转而通过掏空六个钱包的新型剪刀差,要求农民购买有保障城镇化的机会。
40多年来,劳动力再生产体系整体保持了公有制,压低了居民货币工资需求的下限,甚至部分遮蔽了经济成果分配、劳动权利保护的缺陷,民企可以以很低的价格雇佣到高质量的劳动力,是中国制造最主要的竞争优势来源之一。这是又一个“体制打牢基础、民企锦上添花”的基本模型,大量输入中国制成品的发达国家当然也是中国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没资格对我们的公有制模式指手画脚。
中国的新城镇化人口如此充沛,廉价再生产体制覆盖如此广泛,以至于国内外很多方面产生了优质廉价劳动力供给无限的错觉。他们像习惯空气一样无视了高性价比劳动力背后的生产机制,还试图逐步蚕食公有制的再生产体系,转化为口袋中的利润和GDP,反过来长吁短叹大呼小叫“中国正在逐步丧失人口红利!”“人工成本太高企业就要跑了!”仿佛劳动者对美好生活的愿望是一种经济犯罪。
于是他们润去到低关税或低人力成本的洼地,才发现素质扎实、勤劳服从还价格低廉的劳动力供给不是理所当然。曹德旺到美国建厂,给工人开出6万美元的年薪,还要用“激励管理”好生关照工人情绪(在国内他们连社保都不情愿交),可美国工人还是会在午饭时间一哄而散,没人在乎资本家的商品生产。
而搬到东南亚的工厂不仅面临熟练工比例低、生产效率和良品率不高的难题,光是严肃工作纪律和鼓舞内卷精神头就够老板们头疼的了。比中国劳动力质量高的国家再生产成本“起步价”高,比中国“起步价”低的国家劳动力质量不行,只有公有制再生产的中国拥有最高性价比的劳动力要素供给。
笔者承认,全文的论述略偏相对理想化,还是那句话,任何体系都不能避免摩擦。无须讳言,当前体制中行政权力分配公共服务资源的过程不够透明、监管困难,滋生了巨额的资源浪费。周公子们肆意绕过前门钻进体制内低价体系,但他们的劳动力可没有用于提供公共服务。还有同时来自体制内外的、将再生产资源寻租变现的冲动,产生了大量灰色的、没有被统计数据捕捉到的再生产成本。
多少有些讽刺意味的是,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即使存在如此大量的摩擦,我国的劳动力再生产体系仍然拥有全世界最高的性价比。但如同海浪冲击礁石,从房地产的大块切割,到医疗、教育等行业的缓步溶蚀,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中注入了越来越多的牟利水分,公有制再生产模式的礁石被搬走一块,压在群众身上的大山就多一座。到了近几年,新三座大山已经开始在经济中造成质变。
而这些,正是主流经济学和企业利益辩护士始终大力驱动的,从鼓吹医疗教育私有化到频繁攻击社保制度、要求取消企业缴费负担,本质上都是要把社会买单的劳动力再生产转嫁到个人的钱包。
再生产成本在上升,而我国在劳动权利保护等方面的诸多不足毋需为讳,劳动者很难通过议价等手段提高手握的购买力(哪怕只是暂时的、终将互相伤害的),不遏止这种对公有制再生产模式的侵蚀,社会就会越来越难以支付再生产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