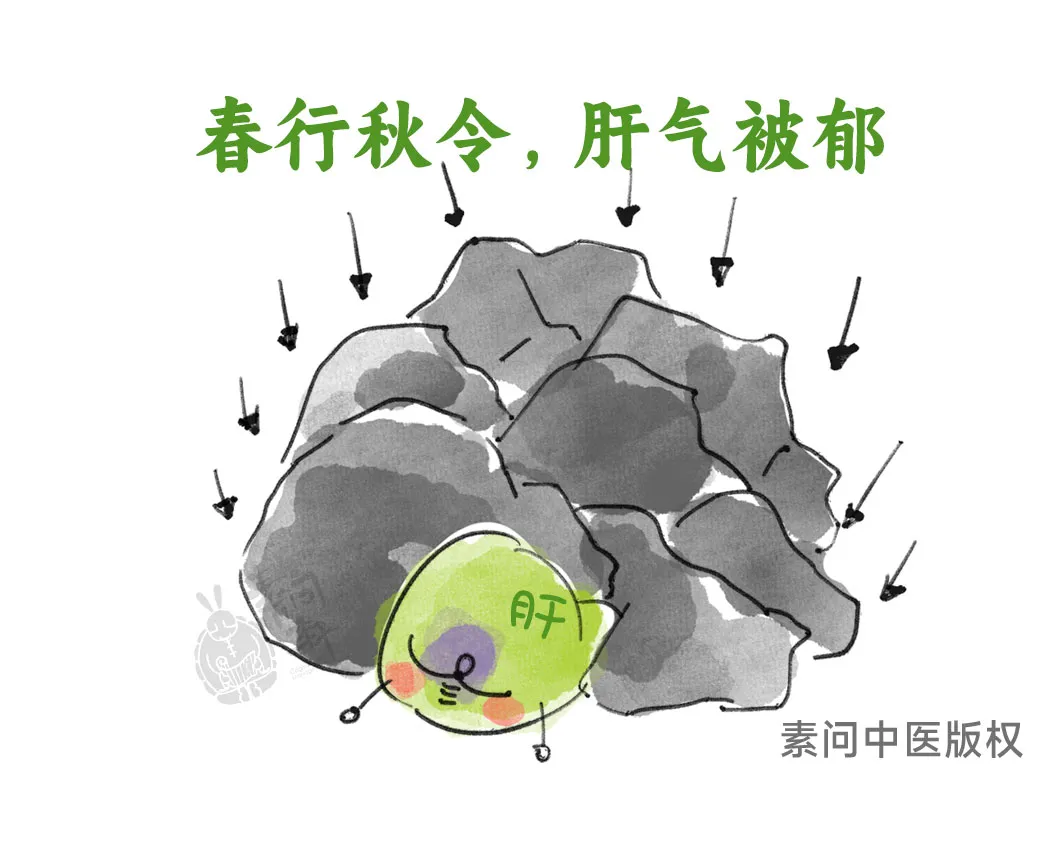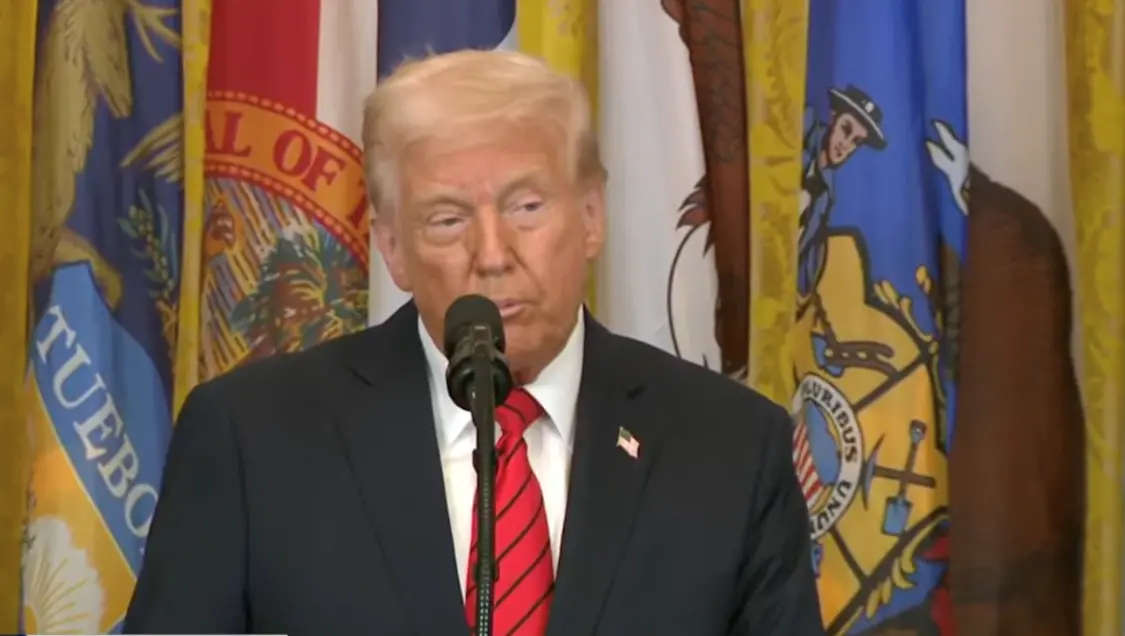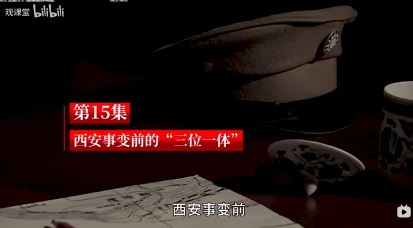《资本论》的“形式分析”与马克思“政治哲学”
1
形式分析与阶级分析
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中,阶级是一个基础性的概念。但随着社会现实条件的变化,阶级问题日益在理论话题中“隐退”。这种“隐退”一方面源于对 “阶级”议题本身的认识局限,另一方面源于诸多社会理论对于“阶级”概念的消解。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对“阶级”议题的经验化分析密切相关。但就马克思本人对“阶级”议题的讨论而言,并不是一种纯粹经验化的社会分析,而是有着更深的社会形式和结构化的思考。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阶级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结构性存在也是独特的社会形式的结果。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分析,首先必须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形式分析之上。马克思本打算在《资本论》中有所解释,但可惜在开了个头之后便戛然而止。就《资本论》的整体结构和“阶级”小节中马克思的论述而言,我们可以尝试对“阶级”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在此,马克思要表达的意思是,虽然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已经完成,但阶级结构并没有实现纯粹的形式化存在。但他认为这无关紧要,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趋势和规律将逐渐使其形式化,原因在于生产资料和劳动的分离。马克思认为对“是什么形成阶级”的回答,不能着眼于对阶级的收入及其收入源泉的同一性的分析。这意味着阶级的内涵不能从其内部的 “同一性”开始,而是要回到具有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普遍性”的“社会形式”中来展开讨论。因为这种“社会形式”塑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的“结构性”存在。
就马克思关于“阶级”的几段铺垫性论述而言,这种“结构性”源于生产资料和劳动的分离,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表面上看,“劳资分离”使得资本家成为资本家、工人成为工人,但实质上更为重要的效应是自然经济基础的消亡、发达商品经济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型。因此,对“劳资分离”的分析,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构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形式分析内容之一。而“劳资分离”之于自然经济的消解与发达商品经济学的出现,恰恰也构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品经济讨论的基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一开始从使用价值、价值和价值形式的角度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分析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从而聚焦于对抽象劳动及其交换价值的讨论。正是在“抽象劳动”的基础上,商品的交换价值才得以可能,而这个表达了不同具体劳动所蕴含的共同性的抽象劳动,使得思考阶级成为可能。
从马克思关于价值、抽象劳动与交换价值所作的“形式分析”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这些社会形式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与属性也都来源于此,并在此基础上得到合理的理解。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这种社会属性本质上都来源于社会规定,而马克思所做的“形式 分析”就是要展示这种社会规定性。
2
形式分析与意识形态批判
作为阶级内涵的塑造形式,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不仅能够说明阶级的形成机制,同时也成为分析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重要切入点。因为阶级统治不仅是一个现实的过程,也是一个观念的过程。阶级统治必然带来观念的统治,而这是意识形态操作的对象。《资本论》“商品”章中对生产和价值的形式分析,其实就暗含了意识形态批判的指向。“形式分析”是我们寻找意识形态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二者关联的重要环节,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分析,一方面可以在宏观的维度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历史性特征,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微观的维度上揭示古典政治经济学概念体系的特殊性。
就《资本论》“形式分析”的意识形态批判内涵而言,主要是围绕着“商品拜物教”展开。社会形式塑造了阶级,阶级也需要社会形式来实现统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借助于对抽象化的分析和批判开始的。马克思首先认为,商品所具有的价值形式标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特征。具体而言,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以抽象劳动和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商品价值形式才发展起来并占有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家根本不作形式分析,以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开始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形式分析,最终目的是要指向其特殊性和历史性。而古典经济学不仅 “无视”这种特殊性和历史性,还致力于意识形态的建构。这个建构的过程不 是一个外在的过程,而是内在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规范中,从而 形成阿尔都塞所说的“理论总问题”。
阿尔都塞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特殊性和历史性是由其“理论总问题”决定的。在这种总问题的形式中,这是必然“看不见的”,是必然的结果。通过阿尔都塞的论述,我们可以从这种必然关系的结构中真实地揭示 “看不见的东西”的存在。这种在现实中存在、又在认识中或者观念中不予揭示甚至采取掩盖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的操作对象。由阿尔都塞的论述可见,所谓“看不见”的东西并不是真实不存在的东西,而是在这种“结构”视域中被遮蔽的东西。因此,对“看不见”的东西的认识,就必须从反思总问题的结构开始。对总问题的反思,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在对“总问题”本身进行形式分析。在这种操作中,“看得见的东西”则成了社会的外观,是最真实的唯一的 东西。而斯威齐认为,马克思的工作就在于指认出这种“外观”并扩大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性分析。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直接引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和秘密,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性的揭示,也是在一般意义上展示现代社会中观念意识和现实的关系。正如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所指出的:“形式” “范畴”作为“客观的思维形式”本身是具有社会效力的。对观念范畴所具有的社会效力的分析,不能仅仅立足于一般的纯粹理论分析,而是要还原为阶级关系的分析。换言之,通过价值形式分析所揭示的阶级关系,必然要求观念意识即范畴的统治。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观念范畴具有社会效力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观念必然成为社会的总体观念,所以马克思说这些“形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这一过程的核心在于形式分析,一方面体现为对范畴及其历史性的揭示,另一方面体现为对意识形态及其抽象统治的揭示。所有这些内容,都可以构成我们分析构建社会共同体的一般内容。
3
形式分析与社会共同体的重建
在对商品、生产的形式分析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资本论》“商品拜物教的性质与秘密”中特意提到了四种“共同体”形式,这为我们思考社会共同体的基本原则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政治哲学的讨论。
虽然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没有直接使用“社会共同体”概念,但就马克思在此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而言,我们可以将此问题的讨论纳入到 “社会共同体”的范畴中。在马克思为数不多的关于“社会共同体”的讨论中,可以窥探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一些基本原则。其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讨论,从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形式即商品生产形式开始,最后衍生出对建立在这种生产形式之上的共同体话题的讨论,并且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不同社会共同体形式的比较。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共同体的内涵就必定与劳动的社会关系与形式密切相关。私人劳动通过“等同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社会共同体生活的内在机制就是物的抽象关系。在这种模式中,人的存在、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并没有出场。当这种原则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的支配性原则之后,这种社会共同体则被一个外在的间接物所规定。
当一个社会共同体的目的在物而不在人时,马克思称之为“虚假的”社会共同体。私人劳动在这种模式中之所以具有社会的性质,并不是因为其自身的原因,而是因为“物”的原因。一切劳动及其社会关系围绕“物”展开,所以马克思要对这个“物”及其之上的社会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以揭示这种“虚假性”。这种“物”的关系不仅规定劳动者,同时也规定资本家。在这种模式中,整个社会的一切要素都围绕着“物”在运动,由“物”所主导而建构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是第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共同体。此“完整”是指“物”对所有社会要素的吸纳,从而使得所有人、所有物都处在同一种关系中,只是这种关系最终采取了一种间接的形式。
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思想原则,在对这种社会形式的形式分析和批判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在“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其出发点就是从生产领域开始。首先,马克思指明了“自由人联合体”生产的基础是对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而不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及其与生产者的分离。其次,他认为劳动直接作为社会劳动得到体现,劳动产品作为社会产品由联合体成员共同占有。最后,马克思倒转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由物支配生产过程的逻辑,代之以“自由联合的人”支配 “物质生产过程”,从而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抽象性质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神秘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