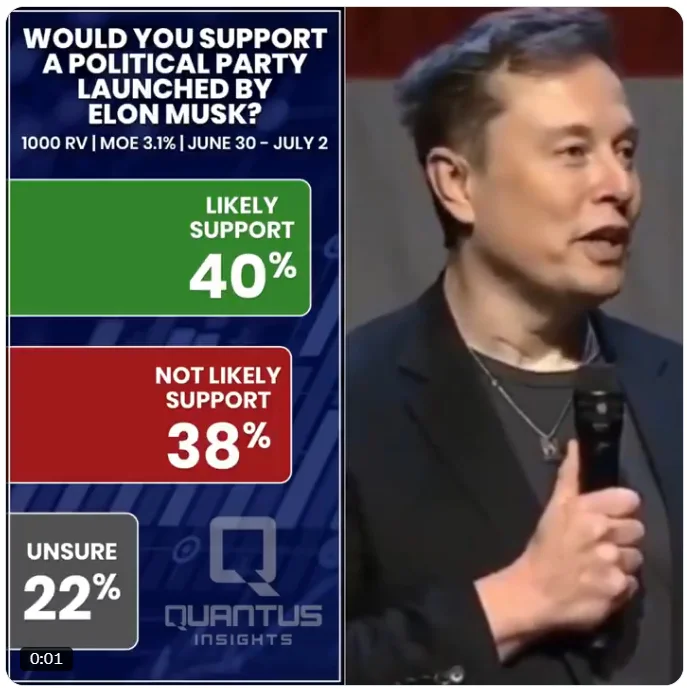立冬时节,娘走了——谨以此文缅怀仙逝20周年的母亲
又过了寒风冷雨的秋末,又是雪花飘落的立冬时节,置身于三尺书斋里,隔窗遥望两千里开外的故乡,心情沉痛,思绪绵绵……今天,我要用那不尽的哀思,缅怀德高望重的慈祥可敬的母亲。20年了,她的音容笑貌依然在我脑海里浮现,挥之不去,难以忘怀……
齐鲁呜咽,荆楚哭泣。
2001年11月6日,对于阔别故乡34载,迁居异地他乡的我,确确实实是一个黑色的日子。晚7点25分,当我和爱妻坐在客厅里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时,突然接到娘逝世的噩耗。顿时,我像遭到了电击,木然地愣在电话机旁,半晌说不出话来。心痛如绞,悲从中来,那泪水宛如天河决堤似的流淌着,流淌着……
娘啊!您怎么就这样走了,儿还有许多话儿要跟您说呢,您那争气的、想您的、孝敬您的孙子在他的日程里,还打算要带您到大洋彼岸风光风光哩!
那晚,我侧夜未眠,泪水打湿了枕巾。
翌日,履行公事,向组织请了假,因发往故乡唯一的那趟列车是上午8时,我只有次日踏上奔丧的路程了。晚9点30分在枣庄西站下了车,10点钟赶到了家。每次省亲,迎来送去、和蔼可亲的娘,如今已与我阴阳两隔,只见她静静地躺在客厅中间的灵箔上,身上覆盖着洁白的绫缎,四周安放着鲜花和花圈,花圈上的挽联墨淡情浓。此景此情,我心头一阵触电似的震颤,迅速向周身辐射,鼻子一酸,无声的泪水涌满眼眶,从脸颊冰冷地滚落下来,接连不断地滚落下来,我终于撕心裂肺地痛哭起来。稍顷,一脸悲伤的哥哥、姐姐、妹妹含着泪对我说,娘那晚上本已咽了气,5分钟后竟奇迹般地又苏醒过来了,气愤地掀开蒙脸的纸,大声说:“俺还没有死,俺要等俺三儿和孙子回来呢!”接着哭喊,不断地重复着那句话。
尽管哥哥、姐姐、妹妹再三解释,说路程太远,怕赶不回来了。可娘仍不相信,她转过脸,盯着墙上的挂钟,哭着说:“不,他们已经到薛城了!”娘的哭喊声时断时续,忽高忽低,一直持续到7日凌晨零点25分,声音戛然而止。
5个小时的哭喊,5个小时的盼望啊!
就这样,88岁的娘走完了她一生的最后旅程,离开了她用毕生精力养育的至亲挚爱的儿女子孙们,驾乘仙鹤,飞向另一个世界去了。
正是立冬时节,天空布满星辰,无一丝风,娘带着满腹遗憾,永远永远地与我们永别了。但愿天堂没有病痛。
纵观娘的一生,可用五个字来形容:平凡而高尚。
娘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劳动妇女,她生于1914年农历7月12日,属虎的。18岁时嫁给父亲。也许遗传基因渗透了姥娘那勤劳善良,宽厚坚强的美德,娘来到我家就挑起了沉重的家务担子。爷爷兄弟四个,均已成家立业,另开炉灶。爷爷排行老二,他有三子二女,父亲是长子。大爷爷是晚清落第秀才。他学富五车,博古通今,满腹经纶。老天爷对大爷爷太不公平了,他有妻无后,按习俗,由我父亲赡养。年迈体弱的大爷爷和嗜好说长道短、喜怒无常的大奶奶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全落在娘的身上。那时,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相继出生,娘既要关心小的,又要侍奉老的,她没有一声怨言。我那两个叔叔也都娶妻生子,两个姑姑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婆媳、姑嫂及妯娌们之间,厚往薄来,偷寒送暖,和睦相处,娘从来没有跟她们红过一次脸,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一直到了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上冉冉升起,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年,大爷爷和大奶奶一前一后寿终正寝。这双重责任,三代义务,让娘尝够了艰辛。
我的故乡南庄位于微山湖东岸,在抗日战争时期被称誉为“小延安”、“小莫斯科”,是一个三面环湖,一面靠陆地,且风景秀丽而又十分富饶的狭长的小渔村。父亲有一套下湖捕鱼捉虾的绝活。生活所迫,他经常驾船奔波在浩瀚无垠的微山湖上,风里来,雨里去,终年披星戴月,辛勤劳作。在城里长大的娘很快就学会了撑船划桨、下网捕鱼等活计。有一年夏天,姥娘带着舅舅和姨来看望娘,当时父亲上城里卖鱼还没回来,姥娘提出要找人划船带她们到湖里去摘莲蓬、采荷花,潇洒走一回。娘底气十足地说:“不用找了,俺带你们去。”说完,领着姥娘、舅舅和姨来到湖边上了小船。望着娘那娴熟的撑船划桨的技术,姥娘会心地笑了,诙谐地说:“俺那城里的闺女真的成了湖猫子了!”
娘心灵手巧,这在村子里是公认的。她用左手干活,绣花呀,描云呀,十分在行,且很有立体感。我们兄弟姐妹七人,孩提时穿的鞋和戴的帽子上的装饰品无疑都是娘的大作。她还会裁剪,左邻右舍的大姐二妹、大哥二弟们每年换季要添置新衣裳,都不约而同,三三两两地前来找娘帮忙量体裁衣。娘不管手头的活再多,也从不推辞。
别看娘斗大的字不识一个,讲起大道理来可是一套一套的。她常说:“要与人为善,要积德行好,要舍己救人。”
1947年秋末,蒋介石反动派大肆向山东解放区进攻,我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以教书作掩护,在微山县夏镇做地下工作的表舅刘金鼎,因叛徒出卖,暴露了身份。多亏党组织提前通知他安全转移了,可他的家人却一概不知厄运即将降临。我县还乡团长、杀人魔王张西玲扑了空后,恼羞成怒,扬言要将刘金鼎全家斩尽杀绝。人们深知张西玲的淫威和残暴:前不久,我党一位地下工作者的亲属老少四口,连同一位送信的被他们这帮畜生活埋了。此时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挺身而出,去通知刘金鼎的家人赶快躲难。刘金鼎是我姥爷家的至亲,母亲出嫁那些年,因两个舅舅太小,接娘回娘家,送婆家的事全由表舅负责,自然是我家的常客,姐弟俩感情很深。娘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俺去!”说完,她化妆成要饭的,掂着三寸金莲,一口气跑了10里多路,向居住在部城里的刘金鼎家人报告了那个可怕的消息,他们这才免遭毒手。事后,有人对娘说:“你真是个傻大胆,你们前脚刚走,张西玲带着一帮子还乡团后脚就赶来了,好险呀!”娘听后没有惊慌,她语气缓缓地说:“刘金鼎是俺亲表弟,又是八路,为了他全家人的安全,就是俺死了也值得。”
1980年国庆前夕,我去北京中国科学院度量衡分院采访在该院任党委书记的原微山湖游击队政委孙新民,并带着创作的描写这支活跃在湖区的抗日武装,配合主力老三团和铁道游击队,维护湖上交通线,打击敌伪顽的长篇小说《晓星欲出》初稿征求意见,巧遇来京城开会的表舅刘金鼎。舅甥喜相逢,格外激动和兴奋。他开门见山地说:“外甥呀,我全家的命是你娘冒着砍头掉脑袋的危险换来的,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啊!”
接着,他又说:“你姥爷在夏镇北面一个叫花园的庄子,也称北茶庵,说是靠开茶馆为生,其实,那是我党的地下秘密联络站。他可是功臣啊!你姥娘也功不可没。当然啰,军功章里也有你娘的一份啊!罗荣桓元帅处理湖西边区‘肃托’事件,后来他和陈毅元帅多次来往延安,去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都在这里歇脚、喝茶、打打牙祭。对了,罗元帅还赠送你姥爷一副水晶老花镜,以作纪念哩!”
顿了顿,他回忆说:“当年我接你娘回娘家,并不完全像那支《回娘家》歌儿唱的那样,‘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后背着个胖娃娃’,而是我挑着俩圆子,里面装有干鱼干虾和菱角、莲子什么的,全是微山湖里的特产,一颤一颤地在前面走,你娘挎着花包袱紧跟在后面,沿着古运河边上的青石板路直奔花园,可惬意了。还有,1944年我执行公务回家,想把你小姨带走参加革命,你姥爷姥娘是封建脑袋瓜一百个不同意。1948年山东全境解放,我不死心,又回来一趟,动员你大舅和大哥跟我走,又碰了钉子。如果他们跟我走了,凭着他们的能力,现在都是县团级或厅局级干部了。”
解放后,在上海市担任要职的刘金鼎不忘旧情,时常给娘来信问长问短。1982年7月,应中共微山县委的邀请,刘金鼎来微山审定微山县党史文献,特意把娘、舅舅和姨接到县委招待所,设宴款待,合影留念。
娘一生养育了三男四女七个孩子,全是她用奶水汗水和泪水养育大的。按顺序,男孩我排行老三,姊妹我排行老六,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都是在旧社会出生的。那年头兵荒马乱,微山湖每年洪水成灾,庄稼颗粒无收。幸亏湖里物产丰富,再凭着娘一手操家理财的本领,精打细算,粗粮细做,布衣蔬食,细水长流,一家人一个不少地安安全全地挺到了全国解放。
新中国诞生,百业待兴,乡下人的生活与城里人一样不太富裕。尤其是适逢三年自然灾害,逃荒要饭的人在微山湖畔也不是什么新闻。为了养家糊口,度过难关,娘在分的近一亩的自留地里搞起了科学种田,小麦杨花时,套种玉米,小麦收割时,套栽地瓜,玉米成熟了,套种白菜、萝卜,反正不让一寸地闲着。加上生产队分的口粮、从湖里捞来鱼虾、鸡头米、菱角等湖产品,我家干的,稀的从未断顿,逐渐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她还经常接济断炊断粮的街坊邻居们。娘的这些善举,至今仍是家乡人民茶余饭后谈论的主题词和新闻导语。
最使我动容、终生难忘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文革”飓风未停,升学无望,就业无门的我只有选择走当兵这条路了。我报名参军,综合素质在全县一千多名体检合格的适龄青年中属皎皎者之一,二炮部队接兵的连长对我大为赏识,暗示一定要把我带走。可是,本村有个妒忌心强的“二半吊子”口吐恶言,说我在文革中是逍遥派。无疑,我的政审受阻了。那年大雪飘飘,天寒地冻,娘踩着没膝深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一次又一次地领着我到十里开外的县人武部、征兵办公室找人说情,终于感动了“上帝”。虽然我没能去二炮部队,工程兵部队却收留了我。到了部队,我发奋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地干,赢得了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新兵训练一结束,我就被选调到了机关,当年还被评上五好战士,并入了党,立了功,随后提了干。
在旧社会含辛茹苦疲于奔命大半辈子、曾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支前模范、解放后一心为集体披肝沥胆的父亲,刚享受一点我做儿子的孝敬,便因积劳成疾,于1973年农历6月20日晚7时40分与世长辞了。打那以后,我把对父母的爱心全都奉献到娘的身上。每年大小节日,我都要给娘寄去两、三张“大团结”。后来每月都要寄去20块,总觉得这样做还不够,我又先后多次把娘接到部队。尤其是在部队成了家,有了儿子后,娘又多次来到军营,一住就是数月。我那贤妻总是想方设法给娘加强营养,把膳食调剂的一日三餐不重样。娘高兴地说:“俺在这里天天就像过年啊!”那些日子里,经常从我家的窗户里飞出笑声。娘看见她的孙子活泼天真、聪明漂亮,我们小两口相敬如宾,脸上经常堆满了菊花瓣似的笑容。来时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的娘,走时竟然容光焕发,健步如飞了。娘自己都觉得就像又找回了当年抗战时期,她带领妇救会的姐妹们参加识字班、推磨压碾、摊煎饼、送军鞋的精气神啦!
1985年3月上旬,已72岁的娘一是太想孙子了,二是想逾越73岁的坎,她只身一人从故乡乘车摸到了襄樊。当时我正拟调到南方一家报社工作,只在家与娘团聚了一周时间。娘在襄樊同她儿媳妇、孙子住了一段时间后,她又挂心老家的几只老母鸡,因此执意要回老家,无奈,爱妻和儿子只好送她上了火车,她噙着眼泪对他们说:“俺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们了!”懂事的儿子马上说:“奶奶,您不要难过,您一定能活到100岁。”
有一年秋天,我又一次到上海电影译制厂制作几部广播连续剧,途中回故乡看望娘。闲谈时,娘说:“还是俺孙子金口玉言呀!73岁这一关俺闯过来了。”
1987年7月,娘又一次到了襄樊,一进门就说:“真不由人呀!俺想你们啦!”爱妻说:“您来的正巧,咱们一块到北京玩玩去吧!”娘高兴地点了点头。在北京,我们全家老少三代,一块参观了天安门、故宫、中山公园等名胜古迹,还去了商业繁华的王府井。去天安门那天,娘提出要瞻仰一下毛主席的遗容。但是,那天在毛主席纪念堂前排起了长长队伍,一眼望不到头。儿子打岔道:“奶奶,排队看毛主席的人太多了,别挤坏了您的身子啊!”
2001年9月13日,我请假回故乡看望病重的娘,娘指着儿子从美国寄来的一大盒西洋参,旧事重提:“俺那孙子已经长大了,懂事了,那年俺想去看看毛主席的纪念堂,没能如愿。现在,俺还想让孙子租个小包车带俺去呢!”语气中流露出一丝惋惜。
娘共有5个孙子和两个孙女,加上三个重孙,两个重孙女,已是十里八乡令人羡慕的四代同堂。他们个个都很优秀。娘心中有着满满的自豪感和荣耀感。
然而,我那儿子是她最大的自豪和荣耀。1996年7月,16岁的儿子高考成绩斐然,理科在湖北省第二名,在襄樊市第一名,被清华大学录取。消息传到娘的耳朵里,她高兴得嘴都合不上,逢人就说:“俺孙子考上了清华大学,按过去的说法是中了状元呀!”娘打发外甥打来电话,传达她的指示:“俺手脚不灵了,不能再去襄樊送孙子上北京的大学堂,一定让他回老家一趟啊!见一面是一面呀!见一面少一面呀!”
为了却娘的心愿,第二年3月,借儿子寒假返校之际,我带着他回到了故乡。我蓦然发现,娘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背,已经变驼了……虽然是小住几天,看得出,娘那几天很开心,她一会儿看看长得很帅的孙子,一会儿又看看我,但更多的目光都聚焦在她孙子身上。
2000年8月,儿子在清华大学读完本科后,因成绩优秀,获得了美国某大学读研的全额奖学金。送儿子赴美留学启程那天,我们一家三口特意绕路回到了故乡。平常有说有笑的娘见我们来了,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很少说话,不停地做家务。真是“此时无言胜有言”啊!
娘后来患了萎缩性胃炎,这是我在病历上看到的。我和千里赶来看望娘的战友卢焕喜轮番对娘安慰说,不要听别人瞎咧咧,是胃里出现了炎症,吃些消炎药就会好了。果然,娘那几天食欲大增,精神尚好。
然而,转瞬间,这一切都成了过去,娘没能走出病魔的阴影。
欲归未得怅空囊,儿女相思泪千行。
严父早逝恩未报,慈母别世恨衷肠。
良操美德千秋在,亮节高风万古存。
晚萱音容犹再现,寸草春晖慰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