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资本论》,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其中繁杂的理论阐释与晦涩的概念输出,其实,从《资本论》中,诞生了非常多的名句,不少人都是耳熟能详的,比如“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在我看来,《资本论》不仅是一部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大成的著作,其中很多语言的使用都直接我们细细品味,特别是第一卷作为马克思亲自“润色”修改的,是经过他长时间的“产痛”以后所“舐净”的“孩子”。
据不完全统计,三卷的《资本论》共有比喻、典故共近千个,尤其是第一卷,占相当高的比例。据《列宁全集》第55卷记载,列宁曾说,马克思虽然没有像黑格尔那样写一部《逻辑学》,但写了《资本论》,《资本论》就是逻辑学。今天我们同样可以说,《资本论》何尝不是一部典故学、比喻学。
老实说,《资本论》里面有不少比喻和典故不好理解,特别是书上没有给出详细的解释,比如出现过“美杜莎”“柏修斯”“普路托”等等,至于比喻就更多了,比如第一卷出现过的“巴黎确实值一次弥撒”“货币贮藏的蓄水池,对于流通中的货币来说,既是排水渠,又是引水渠。”在原理总结的系列推文中,无法对这些东西作解释,所以我单独开辟一个系列,专门更新这种比喻与典故,希望能帮助到正在读《资本论》的你。
一、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
出自第一卷第10页,“紫衣”指天主教的红衣主教穿的袍子,黑袍就是耶稣教的黑袍子,原文提到的“在奴隶制废除后,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会提到日程上来!”意思就是说,劳资关系的变革无论用什么也是掩盖不了的。
二、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尼克派
出自第一卷第104页,“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尼克派,它随时准备不仅用自己的灵魂而且用自己的肉体去换取任何别的商品,哪怕这个商品生得比马立托奈斯还丑。”这里的“平等派”指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激进派,代表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昔尼克派”即犬儒学派,是古希腊一个哲学学派,该学派否定社会与文明,提倡回归自然,清心寡欲。至于“马立托奈斯”是《堂吉诃德》中的一个女佣,长相极丑。马克思的这个比喻意思就是只要商品存在一定的价值,无论多丑,都会有人拿对等价值的商品来交换。
三、巴黎很值得一个弥撒
出自第一卷第67页,这是亨利四世所说的一句话。16世纪60年代初,法国的大封建主明显地分成两个对立的宗教政治集团:一部分封建主支持加特力教,另一部分封建主支持胡格诺一喀尔文教。这两个政治教派进行着残酷的斗争。当时巴黎的王国政府控制在加特力教联盟手中。亨利三世死后,华洛亚王朝告终,亨利四世即位。他是新的波旁王朝的始祖,属于喀尔文教,而巴黎人不承认“异教徒国王”。当时亨利四世的处境非常困难,但他精通商人哲学。为了改善自己的政治处境,亨利四世决定改变信仰,加入加特力教。这样,便引起支持他的人的责难,亨利四世向他们作了一个巧妙的解释:“巴黎很值得一个弥撒!”意思是说,我用一个弥撒,交换了一个巴黎。麻布等于上衣,巴黎等于弥撒。如果说麻布=上衣,这个等式表明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那么,巴黎=弥撒,这个等式则表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与联系。主祭人司铎将人们的愿望和希望,通过弥撒仪式向神(上帝)表明。马克思在讲价值的表现时,使用了“巴黎很值得一个弥撒”这个典据。弥撒作为祭祀,表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作为市集,则表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商品交换关系。麻布等于上衣,巴黎等于弥撒,这只能放到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去理解。商品的二重性在文字上也得到反映。国王用弥撒去交换巴黎,并不是真诚的宗教信仰,而是一种商品交换关系的特殊表现。
四、瓷器和桌子就舞蹈起来了
出自第一卷第88页,“我们想起了,当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静止的时候,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舞来,以激励别人。”有的人解释,桌子上放着瓷器,桌子动起来,瓷器也动起来。这只是一个错误的推论。在1862年7月7日“泼来塞报”上,马克思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事件”的论文,文中第一句话便是:“在桌子开始跳舞以前不久,在中国,在这块活的顽石上,开始了革命酝酿。”马克思在这里谈到“桌子跳舞”和中国的革命酝酿。
1848年欧洲一系列的国家都发生了革命运动,不久后便出现了贵族反动。欧洲的土地贵族请神扶乩,使“桌子跳舞”的把戏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初。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在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金田起义(1851年)。桌子从来也不会自己动起来,现在居然不可思议地跳起舞来了。在欧洲某些人的心目中,古老的中国停滞不前,现在也发生了革命,当其余的世界像是平静不动的时候(在欧洲一系列的国家中,革命运动都被镇压下去),“中国和桌子就舞蹈起来了"。
“中国舞蹈”——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桌子舞蹈”——指欧洲贵族反动。
这是两回事情,但这两个“舞蹈”都同样带着宗教色彩。马克思使用它们来说明商品的拜物教性质,“中国和桌子舞蹈起来”,那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生产物之商品形态的神秘性,就和那些“舞蹈”的难于理解一样。
五、笃格伯勒和希考尔
出自第一卷第102页,笃格伯勒和希考尔是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烦恼》中的人物。在第三幕第三场有这样的一段对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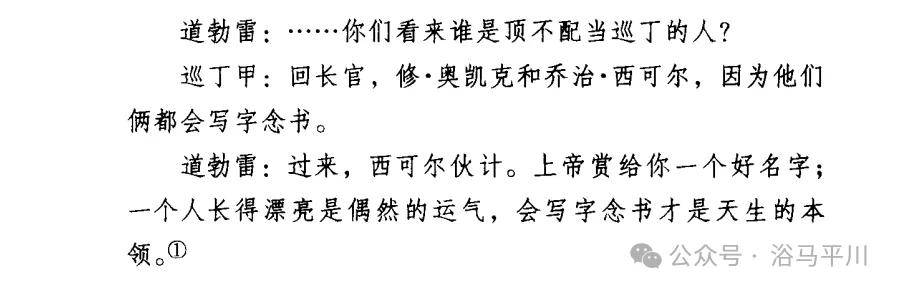
这个老好人,他把事情说颠倒了,一个人是否长得好看,那是天生的,读与写的功夫,却是后天造就的。马克思利用这段形象化的对白,讽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让我们听听经济学者是怎样由商品精神出发来说吧:“价值(交换价值)是物的属性,富(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在这意义上,价值必然包含交换,富则不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事情恰恰说颠倒了,使用价值不是人的特性,而是物的特性,价值不是物的特性,而是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人的特性。在这场合,那些政治经济学领城的蠢才,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道勃雷一样。

 188金宝搏体育官网 SZHGH.COM
188金宝搏体育官网 SZHG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