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耽美?
下面是第三组文本,来自网文中特定文类:耽美小说。大家又开始笑了。笑得有会心有暧昧(笑)。这说明耽美文正从特殊的、封闭的女性网络社群的分众文化开始成为某种低调的、世界性的流行文化元素。中外文学书写中古老而回肠荡气的桥段:义薄情天的兄弟情义——三剑客或桃园三结义,经此坠落肉身(笑)。英国文化工业“卖腐”卖得有声有色,这一次好莱坞尽管有些迟钝,但已略显笨拙地奋起直追(笑)。异性恋女性网络社群对男性间同性恋情或情色的想象(应该说歪歪/YY?)、书写,演变为主流文化工业的新卖点,逻辑而又怪诞。言其逻辑,是因为战后欧美的消费主义经济与文化自身便是“欲望的经济学”,任何有新意的欲望表达都意味着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怪诞则在于这一流行的形成无疑震荡了现代历史500年、脱化于基督教世界的资本主义的两大禁忌。一是同性恋,准确地说,是男性间的情欲关系。依照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的酷儿理论的权威著作《男人之间》(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Gender and Culture Series) Paperback – Deluxe Edition, November 24, 2015。Foreword by Wayne Koestenbaum ),这曾始终是异性恋父权制资本主义最为内在而秘而不宣的禁忌与威胁。一是女性的欲望/观看主体的张扬登场。这同样是欧美基督教会镇压千余年的妖孽。因为,一如劳拉·穆尔维所言:男人看/女人被看、男人行动/女人被动是好莱坞(及绝大多数欧洲主流叙事)的铁定模式。然而,也正是“腐文化”的悄然流行,表明现代资本主义的激变、危机或重构。如果你不是一个纯洁的、历史目的论或进步论者,那么,你也许会同意,对男性间情欲及女性欲望主体这两块基石的撼动,其本身间或是一个思考、图绘现代世界问题的入口之一。但这不是我这次讨论的重点。
在正式进入对中国网络耽美小说的讨论之前,我想补充一些前提——我个人对中国的不同的文化历史脉络的思考和勾勒。这些也是我一再提醒从事性别研究、女性文学研究(包括耽美研究)的青年学者和学生的中国文化特征;此前我更多地是为了强调对文化差异的自觉,而今天我尝试的是勾勒寄托怪影的铠甲。
1.题内的题外话
首先,在前现代中国文化中,我们并没有某种与欧洲基督教文化相类似的、判然两别的性别观念。在我们这里,与男/女相对应的是阴/阳,但阴阳所指称的却远不只男女这一对差异性所在,阴阳观最突出的符号表达,当然是太极图。太极图自身形象地表达了其中差异性的存在处于两仪——相生相克、相互转化之中,这某种非本质的、相对的差异性存在。
事实上,在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的创世神话中,上帝——意味携带着绝对创造力与毁灭力的男神在第七日“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之父亚当,而后抽取他的一根肋骨制作了夏娃——人类之母。不言自明地,女性在这人类故事之处,便被钉死在次生的、从属的“第二性”的位置上。且不论正是夏娃接受了魔鬼/蛇的诱惑,吃下了智慧果,令人类堕入“失乐园”。因此,所谓人类的“原罪”便是女人的原罪。而尽人皆知的是,在中国的创世神话中,是多神的民间信仰中的女娲——一位女神“抟土造人,造男造女”。即使在中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各种伏羲、女娲创世造人的神话变体中,男人和女人间也从无等级排列,只有相对差异。或许还可以提到的是,在圣经故事中,上帝之于人类重大行动的“第二章”是惩戒:大洪水、毁灭与诺亚方舟;而中国创世神话中,女娲的“第二章”,则是救助:补天。(余下的石头生出了无数中国神话、传说、文学、幻想——笑)。
其次,或许更重要的是,阴阳/太极图原本是外在于权力等级意识的表述,但毕竟为后者所渗透或污染。在尊卑贵贱的差序表达中,阳为尊、为主、为贵,阴为卑、为次、为贱;以此类推,便是男尊女卑。然而,这一关于男女之间的权力阶序,在欧洲的基督教的文化中,是一种特异性的、本质的、不可更动、僭越的等级分布,而在前现代中国文化中,男女间的权力关系与其他等级阶序的序列相关,而且可能依据其相关性发生互换。因此,前现代中国的社会权力秩序或文化的核心表达: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固然构成了自上而下的权力阶序——一如新中国建国初年的《妇女解放歌》所言:“旧社会好比那黑咕隆咚的枯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受苦人,妇女是最底层”。然而,换一个角度,三纲之君臣、父子、夫妻又是某种同构的权力、等级排列,君之于臣,相当于父之于子,夫之于妻。(在此,我不想去讨论为某些海外汉学家“坐实”了的、关于这一以男女喻君臣的文学传统的创造者屈原与楚襄王之间的同性恋人关系;因为,即便的确如此,也不能改变或完全阐释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事实:香草美人自比,是一种负载着特定的权力逻辑与文化心理结构的中国男性文人的书写惯例与文学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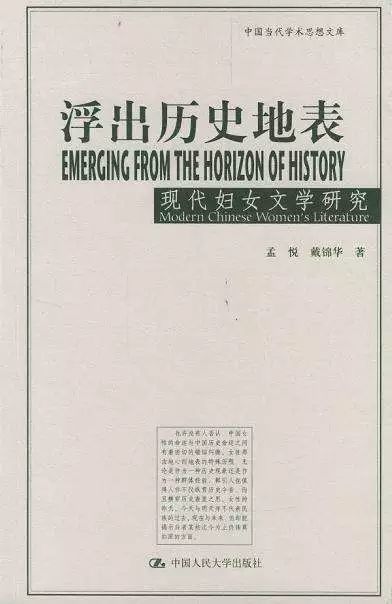
《浮出历史地表》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变体,则是与尊/卑、贵/贱的等级并置或内置的长/幼等级——尊长、尊老,长幼有序。因此,在前现代的权力表达中,存在一种奇特的“母权”(绝非女权)。事实上,20年前,我们曾在《浮出历史地表》一书中将其称为“代行父权之母”——母亲作为肉身之父缺席之际的、年长的、父权功能的执行者。至少古代文学中两则最著名的爱情悲剧故事:《孔雀东南飞》、《钗头凤》中,代表压抑与毁灭性权力的都是代行父职之母亲。而种种历史与传说故事中的“垂帘听政”的“太后们”,无非是作为父亲 “缺席之在场”的“母权”的变奏形式。其极端形态和例证,便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著名女帝,武瞾/武则天。
再一个变体,则是相对的权力、等级差序结构所形成种种错位和裂隙,令前现代中国文化中存在着“代父”、“代夫”的女英雄、女将军,存在着无需借助如上名目的女侠,存在一个特定戏曲行当角色:刀马旦;一句话,存在着女性的行动者和诸多限定之下的女性主体位置。
与我将要讨论的文本组密切相关的是:正是由于关于性别的权力规定是一个可以与其他权力阶序相关,因而出现变体的结构,因此不同于基督教文化将同性恋情——准确地说,是男性同性间的情感与情欲关系视为绝对禁忌与跗骨之蛆;相反,一般说来,男性间的情欲关系(当然绝非自主的性向选择)从来不是前现代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禁忌,也不曾被视为洪水猛兽式的威胁;尽管始终“不登大雅之堂”,可依据其不同的情境和参数,成为 “丑闻”、或“趣谈”。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前现代中国,始终存在着某种名曰“龙阳”、“断袖”的亚文化传统。其前提无疑是不容冒犯、僭越、妨害父子相继的主体秩序,尽管在一对一的现代爱情观念之外、在事实上的多妻制的前现代,类似同性恋情亦难以构成对中国或曰东方式的父权制的威胁。因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从一而终”等等仅仅是针对着女性的威压和规定。然而,在类似不无含混、暧昧意味的“容忍”空间中,最为基本和重要的,是不容在任何意义上冒犯或僭越了尊卑、贵贱、长幼的等级秩序。因此类似的亚文化更近似于某种特权阶层、某些特权位置的专利欲望和满足。一个近便的例子便是《红楼梦》第四十七回《呆霸王调情遭毒打,冷郎君避祸走他乡》,其主部故事是一向欺男霸女的薛蟠因公然调戏柳湘莲而遭到后者一顿胖揍。但参照小说文本便不难发现,除却薛蟠这一角色惯常的粗鄙不堪,他对柳湘莲的冒犯并非在于他公然赤裸地表达了对他的身体欲望,而在于类似行为背后昭然的身份错认:薛蟠将柳湘莲错认为一个“戏子”——“下九流”或“下等人”,而非他的真正身份:一位“公子”,玩票只是一份“雅趣”。换言之,如果他是一个真戏子,那么纵有不甘,也绝非愤怒,更无从反抗(事实上,民初的著名流行文本之一正是《秋海棠》——一个“乾旦”的悲惨命运)。
2.僭越或规训?
回到对当下中国耽美文本的讨论中来。尽管已阅读了相当数量的网络耽美小说,但我无意也无法“化妆”成同人女或腐女(笑)。代沟是原因之一,认同与否是另一个。因此,尽管我的阅读量足够大,但我观察仍是外部的,而非内部的;是对文本和文化的观察,而非对这一特定的亚文化网络社群的立体观察。再次,我也不拟全面地考查这一亚文化的国际旅行线路,不拟深究这一在时间上最早发生在欧美的女性(网络)社群特定的同人文化到以日本动漫(/少女漫画?)产业为主要依托的BL(Boys’ Love)漫游到中国的路径。我想明确,这类无疑是舶来的文学与情色书写的样式或主题,以日文汉字“耽美”——唯美(aesthtic)的日译——为名,但事实上却是相当本土化或曰“原创”性的。其与欧美和日本相关文化的最大区别,是其主要的表现形态,是数量极为可观的、“原创”(打引号是为了暂且搁置对风波不断的网络抄袭、剽窃事件的讨论以及相关的诸如数据库写作一类的理论与实践议题。在此,原创一词用以区别“同人”写作)网络小说写作。在广泛涉猎中国耽美小说之前,我对类似文化的了解止于欧美女性同人文化,准确地说,是兴起于20世纪70-80 年代的、以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为主体的、美国电视连续剧《星际迷航》俱乐部。在我认知视野中,是她们最先开启了这种亚文化,依托大众文化文本将其中的主要男性角色重写为同性恋人。我关注是逆推式的,开启这一视野的,是美国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康斯坦丁·潘莉对这一文化社群及其写作和想象的研究。补充一句,也是这一研究,标志着电影理论由文本中心向受众中心的转移,加盟后现代、主体性讨论的理论取向。当然,关于这一美国的同人文化(slash),更著名的研究出自亨利·詹金斯的《文本盗猎者》。詹金斯在类似写作是“女性的性幻想”的基本界定之下,讨论了其中的性别/性爱的乌托邦特征:社会性别与性身份的流动,自我与他人之间障碍的突破,平等,感受性的突显,脆弱的坦然裸露……

或许正是类似的指认,令我带着“错误”的或曰“谬之千里”的期待视野进入了中国耽美小说的文本世界。当我经由“资深腐女”导航进入这一世界,并渐次深入之时,我阅读体验是震惊。我极度讶异、几乎带痛感地发现,耽美社群对类似写作的共识性规定,是其中的主动者与被动者、上位者与下位者,即她们笔下所谓的“攻”与“受”,是清晰明确、判然有别的角色设定。一经确定,绝无更改。其中的被动者与劣势或弱势者的挣扎或逆转角色的尝试,因其注定无果或失败,被视作喜剧性段落或常规性调味剂。据说,作为一种有力的接受惯例,“反攻不成是情趣,反攻成了是雷点”;偶然的、一次性的角色反转并非不可,但决不可能是“反攻”得手,而“应该”出自强势一方的施舍。类似接受心理与需求无疑强有力地、在网络写作的作者/读者的密切互动加固了这一叙事成规。(在此,我亦不拟引入真实世界中同性恋社群及其文化作为参照。 世纪之初,出现在晋江网上的耽美社群与同性恋社群冲突间,耽美社群的自我界说:“珍爱,耽美,远离同志”,尽管此后有社群内部的反省、分梳,仍清晰地表明了她们将自己明确区别于同性恋者、同性恋社群、文化的自觉。但也正是为此,此间的文化与书写成规便具有了更为清晰的社会症候意味)。进一步构成了我的阅读震惊体验的是,这一不容更动的主动与被动、强势与弱势(即使在所谓“双强”设定的人物关系中亦然)的角色位置鲜有例外地与角色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全然高度吻合;甚至绝少背离新旧主流文化的各种规范,诸如身高与权力,诸如在欧洲殖民历史中形成的伪人种学(金发碧眼优于浅黑型);诸如拯救者/施恩者vs.获救者/受恩者。也就是说,在更换了爱情故事或情欲关系的性别身份之后,这一亚文化中的小说创作不是剥离了,而是凸显甚至强化了的权力和等级阶序。于是,皇帝vs.将军便成为一对黄金CP。当然可以十分结构主义地(笑)替换为皇帝(皇储、王爷、盟主、贵人、CEO、演艺明星……)vs.臣子(伴读、质子、侍卫、戏子、公司下属、助理……),或广义的胜利者/成功者vs.失败者。于是,一种逻辑的、在我的感知中颇为怪诞的文本事实,便是亡国之君、败军之将、敌国质子成了类似文本中盈溢着特定性感的欲望客体。
无需赘言,耽美这一概念在中文指称的是对角色性别身份的规定:男/男,而不是一种叙事类型;其最单纯的叙事形态是言情,但它毫无疑问可以,也事实上叠加在任何叙事类型之上:武侠、玄幻、科幻之赛博朋克、蒸汽朋克、太空歌剧……侦探、历史之历史小说、架空、穿越、演义……。其共享部分,是女性写作者及其社群的某种性文化或曰情欲想象(所谓“歪歪”),后者似乎正是这一亚文化形成的内在动力之一。然而,类似性幻想并非以柔情蜜意开启或充满,相反,大都以公然、赤裸的强暴为端,包括持续的强暴、囚禁、施暴、羞辱。不是S/M的游戏、不是“虐心”——苦情或悲情,而是连篇累牍的直接凌虐。令我颇感匪夷所思的是,这类故事却大都最终以真爱作为结局。在此,或许不是文本细读,而是叙事序列演示,是更恰当的分析方法。耽美读者知道,在类似成规中,故事以强暴为开端;若以“攻”为A,以“受”为B(尽管其这类文本内聚焦/读者带入于“受”,也就是说后者才是男一号/A),故事前半部是A虐B,“虐身”——施暴、施虐,后半段是B虐A,虐心。故事的转折点是施暴者A陡然意识到自己对B的欲望发自真爱,因而陷于迷惘、彷徨以致于无助——“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在类似文本中引用率高到“令人发指”的是徐再思的《折桂令·春情》——笑)。因此,即使在故事的后半部中,B亦非主动者或主导者,相反因无以领悟A的变化或曰真爱表露而陷于更深的绝望和无所适从之中;所谓虐心,更多的是A所体认到的自虐。B最终被A的无限深情所感动,真爱/相爱的结局由此达成。事实上,这不仅是耽美,也是相当数量的网络古言(古风言情)的叙述范式,“不同”之处在于,在异性恋/男人和女人的故事中,尤其是当历史或架空“历史”的叙述设定在前现代/多妻制之中时,出自男性的强暴便意味着(只要他愿意)占有——“主人”对其“所有物”的处置,便依据社会惯例而不论侵害或囚禁。这也正是我所体认到的、耽美文本自觉或不期然的意义所在:角色的性别身份置换,令在历史上和依旧现实中的女性生命的创伤经验和司空见惯的悲剧再度获得了可见、可感的质地。然而,无论在耽美或言情中,当类似故事的“标准”结局是真爱/相爱时,在我看来,文本便显影出迫近且狰狞的后革命时代的幽灵:故事更近似于权力的肉身形象征服,准确地说,是驯服他的猎物的过程;“真爱”的结局成就了彻底的屈服或臣属(在所谓君臣文中,也许该叫臣属者的臣服——不是对民、对社稷或江山、天下,而是完全对王者);或许可以说,文本自身成了受虐者/弱势者/臣属者最终心悦诚服地与强势和权力签署了一纸鲜血淋漓、血肉模糊的契约。如果说皇帝vs.将军是耽美写作的某种“标配”,那么更典型或极致的,便是皇帝(/王爷/盟主……)vs.侍卫。为类似写作所偏爱的创造之一,是“影卫”——某种类似死士、忍者与家奴间的角色。如果说前者显影的是奴隶的养成,后者则更近似奴才的逻辑。于是,耽美——这女性网络社群的性别僭越性文化,便如此清晰地显影出社会规训的意味。
3.惯例与反例
类似文本的数量如此众多,以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所谓“虐文”在数量上大大超出了“甜、宠文”,也令这类文本于我显现出鲜明的症候意味。反驳者一定可以提出反例。我也读到过不少反例——可以说,寻找和发现反例,是我持续阅读的动力之一。但事实上,就大众文化工业产品和流行文化文本而言,佳作大都是其中的反例。因为所谓佳作,始终意味着其形式元素或曰媒介语言的独特令其凸显于大多数作品形成的底景,意味着制作者某些个性风格的清晰印痕,意味着对主流之成规惯例的僭越或改写。体认或思考这一现象之初,我首先考虑确认/排除这一书写惯例是否来自其直接出处:日本文化工业及其(我始终无法接受的、不时极为扭曲的——笑)日本性文化:诸如其中的“圈禁”与“养成”,在中国网文中,流行词是“束缚”与“调教”。我求教和考查获得的答案是肯定的。然而,这并未构成对我自己问题的有效解答。因为在其日本“出处”中,除了各种舶来与本土的差异,中国耽美写作无疑在自觉或懵懂间,更多接续了前现代中国的亚文化传统,而非欧美的新创“酷儿”或Slash;然而,这一接续同时召唤或释放出前现代中国文化中的权力与等级的鬼魂或魅影。因此,在种种差异间,最突出的是,双重或多重的幽灵与鬼魂——后革命的幽灵或前现代的鬼魅。在日本的类似文本中,显然没有如此浓重的,可谓浓墨重彩的、多重后革命幽灵的萦绕——或者说,革命,原本是非革命造就的国家和地区文化中的极为陌生的所在;相反,对我们,不论是否愿意,是否自觉,革命,仍是某种极为内在的构成,尽管此时已多为幽灵怪影。

耽美作品《凤于九天》
所谓后革命幽灵显影的形态之一,便是我们前面已然提到的对权力机制、对当权者的内在、细腻的体认。不是简单的直接臣服/认同,而是委婉、深刻的体察。或许为我的一贯立场或我的视野所囿,类似阅读带给我的、颇具新鲜感的获知和体验,正是这份不是极为精当、细腻的表述:将当权者(包括其极致形式:皇权的拥有者)体察、指认为一具沉重、硕大的权力机器的功能位置。其中甚至包含某些颇具历史唯物主义特色的洞察:即使是立于权力之巅的皇帝,也从不是、从不能独自统治;皇权统治始终是皇帝、皇族与贵族、地主阶级或阶层的、充满争斗、阴谋、博弈的联合统治。因此,诸如所谓后宫,并不是男性个体的“所罗门王之梦”的对应物,而是一种作为皇权补充物的制度,作为皇权与宦官、外戚、文臣与武将、中央皇室与藩王或封疆大吏间的交叉点与连接点,是借以平衡、控制统治阶级/阶层的利益分配与利益冲突,也是反制、限定皇权的制衡装置之一。当权者拥有权力,也为巨大的权力所控制甚至“囚禁”、反噬。因此,我们尽管身处低端和弱势,我们也可能对权力巅峰付出一鞠同情和悲悯。或需赘言,正是类似叙事视点与策略,在不言自明的非政治化的社会语境中,相当有效地令故事中的强势者、权力的肉身形象得以伦理化与情感化,得以获得结构性的理解、原宥和体认;这当然也是剧情得以实现其先设结局/真爱所必须的绝地逆转的内在依据。相较于21世纪之初,类似《英雄》的叙事逻辑:认知自己的局限和弱小,因而捐弃反抗,将曾经自认的使命与诉求托付给强(权)者,耽美、古言或诸多历史小说的写作,也正是为这份体察,赋予了强(权)者伦理与情感的含量和血肉与肌理的充盈。换言之,革命时代击毁了权力机构曾高度自然化的合法性伪装,令我们得以近察细观权力机器自身;但后革命的现实却令我们反转或倒置曾经的、间或是悲情动员性的对权力、统治的控诉,代之以对其自身逻辑,包括对暴行的必要性(——“不得已而为之”)的理解。其中,颇为有趣、有时堪称精妙的,是古风耽美、古言、历史小说,包括种种拟古之作中的“历史”、“史书”的运用。其中成为某种特定“桥段”和炫技的,是在情节段落之间插入或可乱真的拟古、史传体段落;或者将权力暴力干预史官书写作为情节附线……。这里有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赋予的对“历史是胜利者的清单”之洞察的分享,有后现代主义游戏、戏仿,有“数码原住民的”、象征着朝向想象界的无尽坍塌之后的扁平历史,有后革命的虚妄与犬儒。
在多数的耽美文本中,尤其是所谓虐文中,其内聚焦是安放在被动者/受的被述位置之上的,这便结构性地(尽管在其更新过程中时常因与读者间的互动而微调)决定了读者的认同/带入选择。换言之,我们的认同大都是建立在“权力的轮下”的(八十年代文化、文本中引用率颇高的、泰戈尔的诗句:感谢上帝,我不是权力的轮子,我只是压在轮子底下的活人之一)。事实上,在我的“古老”的阅读中,我在诸多的网络古言和古风耽美中读到了此前我不曾在虚构类作品中读到的、对父权下“女性”/弱势者极为悲惨的生命、身体经验的书写,间或充溢着真切、密集的痛感。然而,考虑到虐文的极盛出现在资本介入网文写作、收费阅读制度成了专业网站的运营方式之后,那么似乎显而易见的是,类似书写惯例的形成与流行的“缘由”,正在于它作为一种情色想象的类型,生产并满足了阅读、幻想、歪歪的快感需求。我不止一次读到了类似的更文后的“作者有话说”:“强上了!你们爽到了吧?”回应是一片读者打赏的“手榴弹”、“地雷”、“火箭炮”炸响。我的确在“无言以对”的同时感到“晕眩”(笑):如果你的认同建立在被动者/弱势者一边,那么你如何会在“他”遭到强暴或凌虐时获得如此心理满足?当然,如果在性心理学或S/M幻想的层面上,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实”;其中快感始终在M/受虐者一端。然而,我仍然感到疑虑的是,耽美不仅是作为大众之小众的流行文化,而且正在逸出特定的网络社群,入侵主流大众文化。在一般意义上,女性主义关于女性的情色想象基本是被虐幻想(代表文本《O娘的故事》)的回答是,只有自我安置被动、被虐的位置,被(父权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禁止的女性欲望才可以在安全阀之下获得有限的表达。于是,问题成了:当耽美社群已然获得性别身份的换装出演,何以受虐想象仍是必须的和主导的?性别的“换装”出演只是增加了性爱想象的强度?与台大张小虹教授讨论到这一问题时,她的答案是:在中国、东亚,现代100年,还是太紧促而短暂的时间,“女性还来不及形成自己的模板”,“但变化已然并正在发生。”而在另一层面上,作为女性性幻想的受虐乃至(被)强暴幻想之所有可以称为怪异而充裕的快感来源,正在于它与现实中的暴力结构与行为无涉,而为幻想主体/女性自身所掌控。这当然也是对中国耽美虐文的有效脚注之一。因为为网络的媒介特质所改变的写作,除却已为相关讨论的所命名的“同人”、“数据库”等特征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不同,正是读者与作者共同分享着一份心明肚知的游戏的自觉,一份文本作为可选择、可调节的娱乐品与白日梦的属性。于是,有“亲妈”(大团圆结局,有情人终成眷属)、“后妈”(悲剧结局,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之说、读者有抗议、索求角色“戏份”、坚持结局走向的权利;有作者与读者真诚地或表演性地讨论作品的设定及情节的走向。因此,读者对文本中价值表述或角色位置、命运的认同,也无疑有别此前的“严肃”文学阅读和社会认同(/身份/同一性)体验。换言之,读者可以如同作者,充分享有对其中的性幻想的主控自觉。与其说,网文的读者如影院中的观众,是同时置身多重的梦幻主体,不如说,她/他更像是游戏的玩家,可以在每次游戏重启时选择或更换角色和阵营。因此,尽管耽美社群中所谓“攻控”是绝少数,可以说,所有的“受控”都是“攻控”,她无需认同“攻”,她参与掌控至少是分享创造角色和“世界”的规则。但上述反馈表明,此间的认同如果不是不断逆转,至少是含混漂移;是施动(/虐)、掌控与受动(/虐)、被控、征服与臣属,共同构成了某种不无怪诞(对我说来)的阅读/幻想快感。如果考虑到耽美——这一特定的女性欲望或情色写作,事实上翻转了主流文化的既定;因此,欲望舞台上的双主角原本可以轮替成为观看、欲望客体和认同的主体位置。然而,也正是在此,幽灵或鬼魂再度出没为某种政治潜意识的诡计:认同的漂移或轮替,内在地抹除了对抗性关系的可能,相反,在不期然间完成的正是对权力机器或机制,包括其暴力的认同,乃至背书。
4.题内的题外:心理学的角色
在开始讨论这一文本组之时,获得来自腐女社群的反馈之一,是一个简洁而断然的专有名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是对我所描述和探究的叙事惯例的命名(据说,这是社群内部“求文”时的有效标签),也带着某种肯定及辩护的意味。但类似“客观”、“科学”的表述与齐泽克所谓“幻想的瘟疫”相遇,令我有兴趣去追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心理学术语的由来,进而在想象、幻想、幻象的意义上追问或反思冷战-后冷战-后冷战之后的世界及其中心理学的角色意义。
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出自1973年8月23日发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桩真实罪案:一名叫让·埃里克·奥尔森(Jan Erik Olsson)男人在试图抢劫信托银行未果后,挟持了四名银行职员(三女一男)为质,据金库与警方对峙了六天之后,警方打穿金库墙壁,以催泪瓦斯将劫匪逼出。这则近乎笨贼故事的寻常罪案在这里出现了奇异的变奏:人质在前来解救的警察面前以身回护绑匪,以防警方射杀绑匪,而后拒绝出庭作证指认绑匪,且筹集资金为绑匪开脱。报道称,获救后,人质之一与绑匪间建立了极为亲密的、近乎爱情的关系。这起抢劫绑架案的尾声令其成为更轰动的新闻。若干年后,精神病学家受FBI和苏格兰场的委托,将类似人质对绑架者发生了强烈的、正面情感的例子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然而,为我们的国内中文网站上广泛转载、显然同源的词条、定义不曾说明的是,这则心理学症候新条目甚至令其命名者踌躇:因为这几乎如同孤证一枚。而同样为国内门户网站的相关条目省略的,是这一研究和命名的金主/订购者:英美警察机构。但即使是后者,也在迅速将这一成果纳入了警方的反恐与人质事件谈判的培训课程后,开始遭到了持续的怀疑和诟病。质疑集中在:鲜有发生,仅有的例证几无共性,而通常发生在遭绑架期间的、人质与绑架者的“正面关系”显然是理性选择,而非情感或病态的因素——或则是策略性选择:配合绑架者以求存,或则是真切的判断:在人质境况下,来自营救者/警方的威胁如果不大于至少不小于绑架者。因为例证稀少、歧义横生,这一著名的心理学命名长期为其学科的权威名录拒收。即使这一命名的最热情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极小概率事件。然而,这一为心理学质疑的命名,却在90年代中后期(也是后冷战年代)经由流行文化:电影、电视、通俗小说,作为一种新的叙事路径与策略而传播;出现在国内网站上同源复制的词条或解释,将其表达为某种刺激—反应,设定条件—必然结果式的科学—心理学事实,然而,那与其说出自相关案例,不如说更像是对类似叙事惯例的总结,而非普遍存在的心理/病理事实。但也正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作为一个新的开始。

在此,我想稍作延伸的是,尽管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命名自身是一个特例,但它在中国的(以讹传讹的)流行却提示着二战后尤其是越战后,心理学与精神分析所出演的独特的社会功能角色。类似命名的意义,以科学,即普世性的名义,向上阻断了去追问个案背后的真切具体的历史成因,向下阻断了探寻其他选择的现实可能性。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例中,命名先在地否定,至少是搁置了对绑架者动机及目的的探究,因此悬置了人质对其产生认同的任何合法性理由;而一旦泛化为一般性、普世性结论,也必然阻断了在“人质”陷入了他人生杀予夺、自我孤立无援、无路可逃的处境后,除了屈服、“爱上”自己的掌控者之外,还可能宁折不弯、宁死不辱、铤而走险……。而斯德哥尔摩人质事件——这一不无喜剧色彩的笨贼故事,在人质危机频发的20世纪70年代,确乎是一个特例:因为这一十年,是恐怖主义——这一专有名词问世的十年。一边是慕尼黑奥运会上人质危机及悲剧,标识着围绕巴以冲突、西亚北非地区因种族之名的悲剧冲突拉开序幕;一边则是德国“红军”、意大利“红色旅”、日本“赤军”所代表的、发达国家激进左翼青年主导的城市游击战”,频频制造着各种人质危机。后者,无疑是在1967年10月9日切·格瓦拉就义于玻利维亚荒原,第三世界游击战退潮后;而1973年美国从越南撤军之后,围绕着反战而集结起来的欧美左翼青年的反文化、反制运动随之解体而继起的极端主义行动,无疑是在绝望与不甘间的铤而走险,或者说走火入魔。他们举起切·格瓦拉,却几乎完全背离了格瓦拉主义;他们自称“革命者”,其“革命”中,却完全没有了人民,没有了阶级的维度,没有了社会动员与组织,只有暴力与个人/小团体的极端行动。这也正是詹明信定义“恐怖主义”的年代和背景。在他的定义中,所谓恐怖主义不仅Made in Hollywood,而且正是没有革命可能性的年代,人们想象革命的方式。这里,詹明信所谓的“人们”,包括那些的确狂热的、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者,包括主流社会的人群。
回到我们讨论的问题与文本上来,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颇具“文学色彩”的心理学“术语”的确准确地对位于网络耽美社群(也是部分古言)某种盛极一时的写作惯例与快感机制,复制着也印证着中国网络上颇为流行的、由“以讹传讹”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定义和描述“逻辑”引申出的断语:“人,是可以驯化的”。似乎是对“造反有理”的逻辑及文化的逆转或代偿,是对由于20世纪这个中国的革命世纪所动摇、开裂的秩序与服从的加固,类似身体与心理快感便在社会学意义上成就了某种十足的受虐快感。一如在某些时刻,人们“内在需要魔鬼”,这一次,我们内在召唤着“强势征服”。这无疑是后革命时代的精神症候之一。
5.爱,爱情的意味
然而,同样作为惯例和反例,在那些耽美或言情的“虐文”中,“完满”的结局(/HE/happy ending)之一,是弱势者最终因“真爱”而皈依了强势(/强暴)者,最终接受了类似后宫-上书房之间的、传统后妃、宫娥之类的传统女性地位,自此夫唱夫随,尊卑有序(在古言中,类似的结局则是遣散后宫,确立、确保一对一的爱情盟誓,女人依旧皇后,变化只是成了唯一女人)。然而,即使在这类故事中,爱情/真爱的意觉时刻,仍被表达为某种始料未及、充满震撼、携带着破坏力、威胁的时刻,令上位者震惊、恐惧的时刻。因此,在故事中,上位施暴者自觉到爱情的时刻,往往并不是其行为模式发生逆转的时刻,相反可能是更狂暴地施虐,希望藉此对自己否认爱情的存在。因为在他的感知中,爱情正是权力铠甲上的裂痕,是可能亲手交付施暴对象的利器。
事实上,爱、爱情正是后革命、后冷战时代的一股暗潮汹涌的暗流。有趣的是,它却更多是在昔日理论的领地上暗涌;而惯以爱情故事为主打产品的好莱坞及各类流行文化工业,却祭起亲情的旗帜,前所未有地“不谈爱情”。或许,在这轮关于爱情的理论话语中,最为突出而鲜明的,是阿兰·巴迪欧的对话录《爱的多重奏》。其中,这位《共产主义构想》的作者大声疾呼:必须保卫爱情!(笑)因为,在他看来,爱情是纯粹的偶然。而爱情的宣言,即“从偶然到命运的过渡”。在我看来,巴迪欧的《爱的多重奏》或许应以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为参正文本。是在《恋人絮语》中,巴特把爱情展示为一份全然的脱轨、一份微型或巨型的疯狂。爱情由此成为现代文明或秩序中防不胜防的危险品。这份“偶然”的爱情正像是巴迪欧所定义的“事件(/event)”——一个令你摔出或滑脱秩序轨道的时刻。然而,这并非“爱情”这一能指固有的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爱情是欧美最著名,也是最庞杂的神话之一。从圆桌骑士或神殿骑士的禁欲之恋,到“不死的爱情战胜死亡”的欧洲浪漫,或爱情作为个人主义的最佳践行,都并非在处理“二”(“二人世界”、爱情/欲望、身/心),而是“三”——最终在某种“关系”或曰“间性”中安置“大他者”将权威、秩序、绝对权力内在化。一如孙柏在谈到诺兰的好莱坞巨制科幻《星际穿越》时的洞察:《星际穿越》的确涉及政治哲学的问题。或者说,也是一个数学的问题。这一点用范伟小品里一句经典台词来表达最准确不过:“二啊,不是说山(/三)嘛!”爱的主题并不像表面上看那么无聊,尤其考虑到它完全是现代文学的贡献就更是如此。因为它所体现的是失去上帝这个第三项或任何外在的意识形态规约之后,人只能通过另一个自己镜像般的他人来指认和确证他/她自己。这就是“2”的维度,及其意识形态的起源。然而“3”并没有就此消失,尤其在黑格尔发现承认的政治内在的现代性危机后就转向了“绝对”(哈贝马斯等人包括福山就是要在冷战结束前后的历史语境中提倡重新回到交往或承认的政治上去),于是,在接下来的二百年里,范伟那句著名台词就一直回响在西方哲学界了。那个“3”当然不必然指向上帝,因为它所体现的其实是人类主体性所面临的茫茫无际的未知领域,也就是区别于小写他人的大写“他者”的领域(齐泽克称拉康和他自己是黑格尔主义者,道理就在这儿)。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科幻是触及相关哲学议题的首选题材了吧。科幻的政治哲学都是在“3”和“2”之间的调停,即在大写“他者”和小写“他人”之间可能实现的过渡、容纳、转化,等等(引文完——笑)。当然,不止是科幻,也是一切幻想类文本(诸如……某些耽美文本)。事实上,爱情故事的经典收束当然是婚姻/或者任何一对一的情感关系的固化;然而,婚姻或任何形式的关系固化却显然与爱情话语或爱情故事有着社会与文化逻辑的巨大裂痕和差异——如果不说是天差地别至少也是天南海北。所以, “主角的婚礼”是与“主角登基”、“主角葬礼”并称叙事的古典结局,“……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之后,大幕落下,再不开启。婚姻(/关系固化)故事只能存在于另一本书、另一个故事中。因此,爱情故事自身更“完美”的古典结局是死亡/悲剧。可以说,在现代性反思的维度中,爱情是最具建构性的话语,也始终携带着内在的破坏性和颠覆力。此番巴迪欧不仅重提爱情,而重在在爱情盟誓及其恪守中,凸显着“二”;用他的说法,便是“我们如何由单纯的相遇,过渡到一个充满悖论的共同世界,在这个共同世界中我们成为‘二’?”参考着他鲜明的欧洲左派立场,这便成为耐人寻味的“新”个案。无独有偶的是,临床精神病学家霍夫曼则在接受澎拜新闻访问时,称“爱能够创造社会联结。”对照上下文,不难领悟到,霍夫曼所谓的“爱”(/移情)相对的是自恋——泛滥全球的时代病,也就是爱的能力的丧失;而巴迪欧所谓的爱,爱情宣言和爱情盟誓则指涉着将“爱”——某种偶然,间或是疯狂,我的“翻译”是激进/激情,转变为常态的寓言。所谓“偶然应该被固定”。一如晚年德里达始终在尝试将一些日常的,间或是诗意的语词转变为新的哲学概念,爱,似乎成为与革命、与理想有关的、尝试为理论所回收的关键词之一。
回到我们讨论的作为中国网络耽美写作的惯例之一中来,其中,真爱的到来固然是类似叙述中必须的、充满政治无意识的装置,或称叙事必须的“机械降神”,但这也间或成为某种文本逻辑的裂隙,成为其中近乎绝对的权力游戏的对立项。就“单纯”的女性性幻想而言,耽美虐文中快感强度,首先来自于男性间的“虐身”部分展示(/幻想)着对男性所谓自足、封闭的身体的侵害与被迫打开;但“虐心”部分,更大的侵害与威胁(阅读/想象快感?)则来自爱情的自觉,那意味着封闭的权力主体之边界的开裂乃至消融。在情节层面上,与那些最终甘居后宫、夫唱夫随的故事相并列的,是真爱战胜权力欲望:禅位、弃权,相携“泛舟五湖”而去的结局选项。换言之,此间的爱情,无法也无意颠覆权力秩序,但却多少撬动了这庞然大物,或留下了擦痕,乃至裂隙。而在意义层面或曰快感机制上,真爱的降临,可以意味着弱者的臣服,也可能意味着强者的归顺。

当然,一如我自己坚持的观点,在既存的秩序之下,主体性意义上的另类选择始终存在,有效,但也有限。在我们所讨论的耽美文类中,类似的“爱的逃离”,意味着对权力的放弃或拒绝,但这逃离,通常是在福柯所谓圆形监狱或监狱群岛的基本设定之下发生。于是,逃离者可以选择离开原型监狱的中心/权力中心,逃亡之路却只能通往牢房的深处。因为在这类似想象世界的方法之中,江湖本是王土的地下层,而非王权外的荒原或净土。所以,作为惯例之反例之一,公子欢喜故事中典型的“岁月静好”、相爱相守的结局,同时意味接受放逐,接受一份贫贱、卑微的地位与宿命;放弃权力,同时意味臣服于权力并以献上必须的供奉为代价。因此,类似的“大团圆结局”同时弥散着一份荒芜、颓败、自甘而无助的氛围。阅读类似文本时,我体认到了某种心有戚戚焉的痛感,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是一个老旧、几乎带荒诞感的语词:“旧社会”(笑)。正是在这里,我再次辨析出重重叠叠的后革命的幽灵。那是在革命年代曾在、革命年代已远,在深刻、内在地经历颠倒之颠倒之后,人们可能获得的历史感悟和体认。也许更具症候意味的,是近期大热的、作者Priest的耽美长篇《默读》——现代都市警匪故事;同样作为反例,这部可谓恢弘的故事设定了警方的双重敌手:一是资本与欲望造就的凶残怪兽(大资本、黑社会与警局高官的利益共同体),一则是无权势者因社会正义缺席而法外执法的疯狂(真凶在逃之罪行受害者家属同盟);相对于作为大他者的绝对秩序,故事之意味的双刃性便跃然纸上。这都市警匪/黑幕故事结局处,爱情盟誓的表达是:“没有了……怪物都清理干净了,我是最后一个,你可不可以把我关在你家?”爱情故事的完满收束,关起了什么?或释放了什么?究竟是镇压了“怪物”,或封印了后革命时代的幽灵?或者,爱情是权力的钢铁城堡上的一道裂痕,幽灵间或由此逸出?
在这三组文本的对应参照中,我尝试触摸、捕捉并与大家分享我们置身其间的社会文化症候。我们观察到了某种似乎陡然耸立、不可撼动的权力逻辑和绝对秩序,我们看到了某种无力和无助。但换一个角度,我们也看到了某种对历史与现实的社会命运的清醒;看到了鬼魂西行之时的多种幽灵的出没。事实上,后革命时代的全球文化的另一个突出症候,正是历史的坍塌与历史纵深的消失;与此同时,最急迫的任务,也正是我们——我们和你们对自己身为历史遗嘱执行人的自觉,清理20世纪历史债务,不是为了加入审判失败者的大合唱或改宗式,而是为了终有一天重启革命的历史遗产。同样,当我们置身于中国崛起的时代,开始意识到启动中国文化历史遗产的必需,不能忽略的是,我们仍必须继续充当历史债务的清算人。说到底,我们都是“五四”的儿女们,中国革命的后裔。在对权力秩序的警醒与梦魇之间,在性别与解放的迷思之间,在肉身与赛博格之间,在弃民与中产之间,新的可能性或新的另类选择究竟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别样的方式去想象和认知世界?我想,新的可能性也许正徘徊、游荡在众多的幽灵之间。幽灵是用以放逐的,但是幽灵却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予以放逐。因为幽灵的特征正是它终将返归。
推荐阅读:戴锦华:后革命的幽灵(上)

 188金宝搏体育官网 SZHGH.COM
188金宝搏体育官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