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是人的基本需求,在居住上的开支是不能避免的。老百姓在生活必需品上支付的超过正常水平的部分,我把它视作类税性支出。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推高了房价,高房价让老百姓在支付“超级地租”,这其实相当于国家把收税的权力部分让渡给了地产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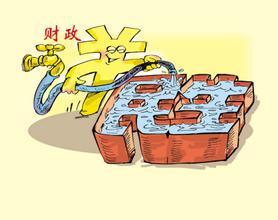
文∣本刊记者 李北方
说到中国的财政问题,人们关注得较多的是财政收入连年增长,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了经济发展等正面的议题。但财政体制有哪些深层的隐忧,财政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与经济社会中的其他问题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呢?就此,本刊专访了卢麒元先生。
卢麒元,1963年生人,早年曾供职于财政部,现居香港,长期研究财政问题,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内地和香港财经问题的报告。
创业创新要靠财政政策激发
《南风窗》:你研究财政问题多年,就这个问题写过很多有真知灼见的文章。财政问题非常重要,但由于它的专业性,一般人理解起来门槛比较高。你可否用易懂的方式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财政,财政为什么重要?
卢麒元:财政是一个国家维持秩序所必须的那部分钱,通常维持一个国家的秩序,需要一支军队,一支公务员队伍,一个扶危济困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我们可以把财政理解为一个国家的制度成本。财政收入由各种税和费构成。
但财政职能不止于维持制度的正常运行,还有平衡社会收入的职能,就是抽肥补瘦,进行社会再平衡。
在现代文明国家,财政的两大职能同等重要,特别是第二个职能的存在和完善表明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社会收入再平衡意味着劳动者的劳动被确认,意味着国家创业和创新的能力。怎么样才能激发国民的创业和创新能力?不是政府放权,而是通过财政的再平衡和收入的再平衡奖励那些真实劳动和创业创新的人,使劳动的收益超过食利的收益。
具体到我们国家,政府的有效性还是很高的。1949年建立的政府全世界效率最高,成本也是最低的,所以中国在1949年以后的工业化在发展速度上是史无前例的。不能使用美国麦迪逊公司的数据,他们做了一个中国2000年的GDP统计,那个数据是错的。有些国内学者使用了麦迪逊数据,所以得出了错的结论。
《南风窗》:那个数据流传很广,影响力也很大,把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那段时间的GDP数据弄得很低。
卢麒元:衡量经济的根本性指标不是GDP,不是当年的营业额做得多大,而是ROE,也就是股东权益,即全体国民拥有资产的增加速度。西方大部分国家在计算国民财富的时候是使用ROE的。我们当年修的8万个水库大部分没有进入GDP统计,但它是国有资产的增加,这种劳动及其成果当时没有商业化和资本化,要是加上去的话,前28年的GDP增速应该乘以2或3,一定是两位数以上。
财政实际上是ROE的处置方案,多少拿来养军队,多少拿来照顾需要照顾的人,多少用来安排国家的长远发展。总体来说,中国的财政安排形式是非常好的,无论是前28年还是后34年,这才有中国的经济奇迹的发生。但后面这30多年,尤其2000年以后,我们的财政的转移支付能力急剧衰落,去工业化进程逐渐开始了,因为允许食利阶层出现,允许资本利得远超过劳动收入。一个人如果在北京有两套房子,出租收入肯定好过去当一个白领,如果有3套豪宅出租,基本上相当于办一个工厂了。
《南风窗》:这种现象对社会风气有非常不好的影响,做实业不如炒地皮,愿意干实事的就少了,政府现在大力简政放权,鼓励创业创新,也许是对这种现象的回应吧。
卢麒元:创业创新能力急剧衰退的原因是食利的出现,跟政府权力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商鞅变法提出来的是削减秦王的权力,而不是废井田、开阡陌、奖励军工,秦必亡。今天的思路仍然是要在财政上做功课,增加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的税负,平抑食利阶层的利益,增加劳动者的福利—不是救济,而是让劳动者获得他们的价值。只要把食利打下去,创业和创新就会迸发出来。
《南风窗》:不过你说中国在经历去工业化进程,这个说法恐怕很多人没办法同意,制造业看起来发展得很好。
卢麒元:创业和创新需要制度环境。我有一个做焦炭生意的朋友,企业一年的营业额300亿。企业要发展,每年得拿出10到20亿做科研,不然没法创新。这个行业的利润率也就在5%左右,可是融资成本超过15%,因为银行不贷款给他,企业需要流动资金,他只好借高利贷。没办法只能把科研砍掉,而且开始卖房子、卖地、卖企业了。
基准利率并不高,但银行不愿意贷给企业,因为利率只能收到比如5个点,贷给中石油、中石化可以收到8个点,中石油、中石化可以再加到15个点往外贷。或者银行做产品,这样的话除了收利息还收产品的费用。在金融领域,这叫金融创新,他们赚钱了,死的是做实业的。国家的创新能力全部被金融吃光喝尽了,去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就迅速展开了。
想让最需要资金的人得到资金,只有通过财政才能解决。为什么利率能抬到15个点?因为有人的利润太高了,资本利得太高了,通过超额累进税把它砸得跟工业一样,或者比工业还低的时候,钱就回工业了,这才叫定向放贷。
现在我们整个金融体系完全不支持中低端工业化,中低端工业在迅速消失。很多企业在考虑搬去河内或者西贡,去越南还有活下来的可能,那有优惠政策,有年轻劳动力。可全搬过去了,我们国家怎么办?
财政是道德的风向标
《南风窗》:你对当前税收的失衡多有批评,对劳动课税过重,对资本持有和资本利得课税太少。能否用量化的方式讲一下这种失衡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或者跟财政体系比较健康的国家相比,情况有多糟糕?
卢麒元:德国的情况是,对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的课税和对劳动的课税大体上是一半一半。英国这样的国家,对资本好一点,资本课税也至少占整体税赋的三成以上。在香港,对资本课税趋近于零,在内地基本上是没有。这是不可以理解的,这和现代文明是相逆的。
《南风窗》:这个比例是基于什么样的计算口径得出的?
卢麒元:无论是增值类税费还是所得类税费,都与劳动有关的。与财产相关的税费,遗产税我们有吗?赠与税有吗?对财产离境转移的征税,有吗?在股市赚钱了,股权溢价了,相应的税有吗?关于资产类的,一个税种都没有。也难怪,到今天连财产登记都没做,怎么征税呢?一个税种的准备时间是3年,如果2017年开始准备的话,也得2020年再征。
《南风窗》:公司的净利润分配,也就是股东的分红是要征税的,这不算针对资本的税收吗?
卢麒元:公司利润也是劳动创造的一部分,只不过是归老板,归股东而已,对这部分的课税也是基于劳动的税。对劳动创造,不管是公司行为、个人行为,我都是主张低税率。
我强调的是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为什么不把该对地租收的税收回来呢?像德国这样比较极端的国家,对豪宅的税收,相当于5年就把房子收走了,所以德国富人不住豪宅。正常的像美国,对资本已经够宽容了,对豪宅也是12年左右的税收就相当于房价。而我们国家,持有豪宅的成本与持有一个小房子是一样的。
《南风窗》:如果劳动创造是一部分税基,资本利得和资本持有是一部分税基,后者要是比例相对小的话,不收税对财政整体上影响还不大。这两部分税基你认为是什么样的比例关系?
卢麒元:我觉得如果对资本持有和资本利得征税,占到总税赋的30%一点问题都没有。这30%不要用来去做其他的,就用来水平转移支付,社会财富因此会平衡。
这个过程的含义是多重的,首先是社会收入再平衡,其次是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中国有钱人人均居住面积至少超过1000平方米,他们在所有好地方都买楼,有几十套很正常,大部分是豪宅,很多不住也不租,就放在那,全世界没有这样的情况。财政要平衡收入,让劳动者有尊严,还要平衡资源,让资源有效地利用起来。
房子的事情本质上表达的是中国的财政问题。财政是道德的风向标,我一再强调,观察政治不能去看报告,有两把尺子,一个在吏部,一个在户部,户部就是财政部,吏部就是组织部。国家鼓励什么反对什么,全都在税收里面,如果鼓励劳动就会把劳动的税降得低低的,让劳动的人有尊严,如果鼓励资本,就会把劳动者收死。还有人事,如果选拔的是社会贤达,社会想坏也坏不了,有好人就有希望,如果还用坏人,那就不用讨论的。
《南风窗》:现在不是开始搞不动产登记了么,相当于你一直呼吁要搞的“鱼鳞册”(古代的土地登记簿册,是征收赋税的基础),对这个工作你怎么评价?
卢麒元:这在大数据时代就不是一个难事,关键看决心。之前政府是想推到2020年再说的,在各方呼吁下提前了3年,提到了2017年。
看看历史,做错的人太多了,做对的人太少。商鞅做对了,秦国就崛起了;美国人做对了,美国就起来了;德国人做对了,德国就起来。过去每一个王朝完蛋都是因为在财政上做错了,最经典的是崇祯,17岁登基,豪情壮志,做了很多事,就是没有重建财政体系。崇祯下过六道罪己诏,没有一道说对,不知道政治就在户部和吏部,把这两个部分放出去,抓其他都不管用。崇祯最后吊死在歪脖树上了,死前说诸臣误我,诸臣怎么误你了?说你不听啊。
财政问题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一听就明白。更严重的是金融问题,金融问题不过是财政问题的延伸,我们现在做的金融方面决定不少是因为财政出了状况,用金融手段来应付。
中国经济的负债率过高了
《南风窗》:民间金融跟财政没有直接关系,你谈的金融是指那个各级政府发债弥补财政的这一块吧。
卢麒元:总体上我们还在增加杠杆,我们现在的杠杆率可能已经超过我之前测算的322%的水平了,已经过了最后的风险线。322%的杠杆率是什么概念?60万亿的GDP,相当于做了60万亿生意,但负债差不多200万亿。60万亿的生意能赚10万亿不少了吧,可是200万亿的利息是多少,5%的利息就是10万亿。赚的钱连利息都覆盖不了,已经赔定了,那么我们是在给谁打工?
经济学讲边际,杠杆有一定的极限。美国、德国这些国家,都把这个写进法律,像美国,必须修宪才能再增加借贷,负债超过GDP的100%,政府要关门。我们这没有人算这个账。
《南风窗》:关于负债率,有没有官方公布的相关统计?
卢麒元:没有。国家预算里面只有一部分中央政府债,地方债谁都不知道有多少,企业债和个人债更不知道了。
《南风窗》:官方一直强调债务风险在可控的范围内。
卢麒元:官方说的债就是中央政府发的债,才占GDP的40%,日本都200%了,我们40%还不可控吗?有人甚至认为40%太少了,增加一倍还追不上美国、希腊,但总负债我们比他们都高了。地方政府做担保的债务在中国是不统计在地方债里的,其实不光是地方政府直接借的,地方政府为企业和项目做融资担保也全部要算,你提供的是信用,是要负责任的。
消除腐败要靠财政制度
《南风窗》:你提出了“三色财政”说,把财政划分为“白色财政”、“灰色财政”和“黑色财政”,从广义的角度看待财政和税赋问题,提供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视角。这个概念体系的版权是属于您本人的吗?
卢麒元:对。通常西方的财政学里面,它只描述狭义的财政,不从广义角度看。我们国家是共和国,财政不可能不管国家财产和财产附着物上的利益,所以中国的财政天然具有广义的性质。
我把所有因公职、公务而产生的所有交易都看作财政行为。被预算法和税法管着的部分是“白色”的。不被预算法和税法约束但没有违反其他法律的,属于“灰色”的。
“灰色”部分可能有合理性,比如说土地财政就是“灰色”的。建国初对地方财政是有明确限定的,地方不能拥有太高的独立财政权,因为地方一旦拥有相对独立财权的时候,可能会出问题,但土地财政突破了这个不可言表的政治逻辑。
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推高了房价,居住是人的基本需求,在居住上的开支是不能避免的。老百姓在生活必需品上支付的超过正常水平的部分,我把它视作类税性支出。高房价让老百姓在支付“超级地租”,其实这也是一种财政行为,相当于国家把收税的权力部分让渡给了地产商,房价中很大一部分应该视为价内税。
《南风窗》: “超级地租”是一个非常犀利的概念,它可以揭示某些被掩盖的秘密,你是怎么提出来的?
卢麒元:基于我对香港的观察。香港政府是典型的小政府,预算也透明,从表面上看香港的税率非常低,可是这么低的税收,老百姓怎么那么辛苦呢?一定有税收以外的东西压在他身上。那我们就看老百姓的负担,主要是供楼或房租。全世界的正常情况是,一个人支付居住的支出不应超过全部收入的30%,越文明的国家或地区越低。
《南风窗》:30%是一个经验性的数字吗?
卢麒元:是的,也是教科书数据。香港呢?快到60%了。老百姓的不合理支出到谁那去了?香港弹丸之地出现了一大批世界级富豪,他们不是在做生意,是在收房租。这个钱老百姓一定要付的话,应该是交给政府,由政府搞建设满足居住需求。香港应该像德国一样,是一个高税负地区,比如说50%的税率,然后生老病死、读书、居住政府全包了,但在香港各方面全不包,钱全给了几个地产商,地产商僭越了政府的土地权。不光是香港,内地也搞这一套,老百姓都在承受超级地租。
《南风窗》:为什么把腐败贪污也视作(黑色)财政行为呢?
卢麒元:徐才厚如果是一个乡野村夫,有人送给他1000亿跟财政也没有关系。所有依据公职的经济行为都类似于收税,徐才厚真的是在收税,最后一并交公了,这真是最经典的财政行为。
我估算,现在“三色财政”的比重大概是1∶1∶1。如果财政中“白色”的部分过小,“灰色”和“黑色”的部分过大,就很危险了。我研究了很多国家的财政问题,这是很多国家失败的原因。
《南风窗》:你还经常谈财政体制建设对反腐的作用。
卢麒元:完善财政体制,建立起对资产征税的机制的最大好处就是纪委不用那么忙了,因为一旦“鱼鳞册”有了,税收就开始有根据了。徐才厚的错误在“鱼鳞册”里面有充分的表达,你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完税了吗?大数据时代的“鱼鳞册”可以覆盖任何一个死角,没有人可以例外。按理说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会不怕税务局,他每一个行为动作都在记录之中,腐败问题也就一次性解决了。所以我特别能理解“鱼鳞册”出不来的原因,我也特别的痛恨这些原因。
本文来自《南风窗》2015年第10期(2015年5月6日出版)

 188金宝搏体育官网 SZHGH.COM
188金宝搏体育官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