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的瓦格纳事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借着各路自媒体的分析科普,也让更多人了解了俄罗斯政治生态中所谓希拉维克集团,皇俄,自由派之类的“派别”概念。由于国内不少人代入俄或乌的立场入戏过深,或者习惯性的拿中国历史和政治思维逻辑套入瓦格纳事件,也闹出了不少笑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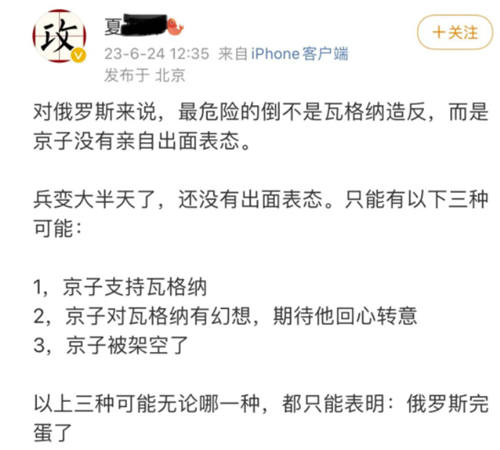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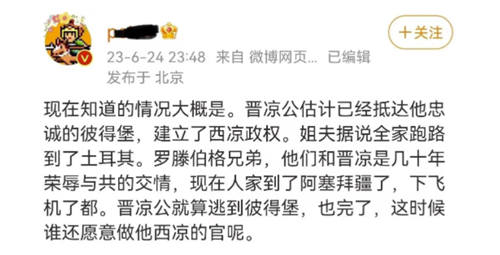
当然,就算是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闹剧式兵变也有很多,更不用说在广大存在部落形态的边疆辐射地区。只不过中国人确实过早的开启了中央集权模式,唐宋至明清中央皇权的不断加强以及历代史书中的法统意识塑造让很多简化过的历史思维深入人心并延续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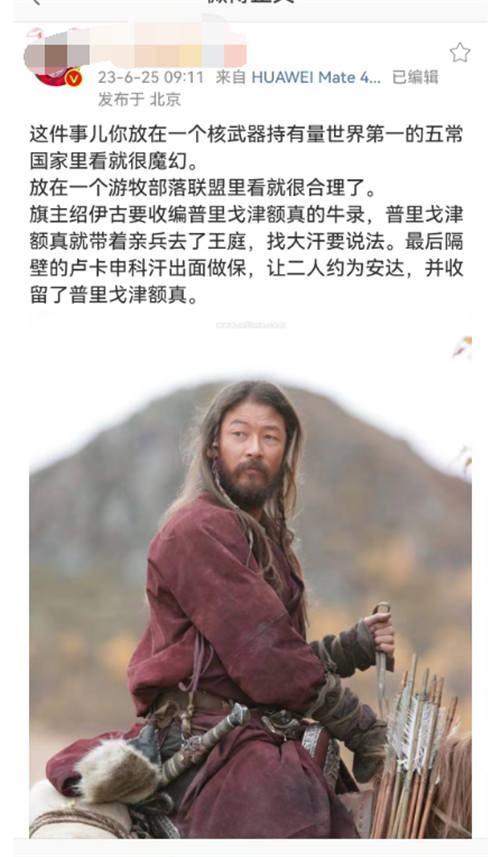

很多时候,套历史玩梗或者搞历史影射学,确实是属于一种键政娱乐行为,历史总有相似之处和延续性,但影响历史事件具体走向的因素往往又都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我们既不能去用古代历史逻辑来硬套现代的时事政治,同时也不能有现代性和近代/古代截然不同的机械思维,认为现代国家就一定不会/不应该存在某种情况。现实中的每一种存在本质上来说都是历史的结果。
与其急着天天脑补谁谁要马上输马上赢,不如寻找一些对于中国人有用的历史启示。借着瓦格纳事件来和大家聊聊,俄国这种处于东西方夹缝的历史悲剧性命运是如何形成,并一直延续至今的?
就如同这两天很多人在解释俄罗斯政治生态问题时说到的“普京已经是能上台的最亲西方的利益集团了”。先不讨论几种简单的政治生态划分是否准确,从苏联后期先是知识分子和民众心态上不断靠近欧洲,到地图头主动奔向欧美,叶利钦时代全面倒向欧美,普京的执政生涯也是不断试图融入欧美秩序而不得,被逼至今天的地步,亲西方心态一直在俄国上层人士中徘徊不去。而在俄国历史中,对西方(欧洲)的狂热迷恋与敌视两种极端情绪的共存可以说是一条历史主线。
理解这一现象的历史成因,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俄国与西方的关系,中国与俄国的关系,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民族主义概念等很多问题。
(警告,本文一万字出头,推荐读者们看完,如果你现在没什么时间可以收藏一下有空了再看)
俄罗斯大地的政治与文化特质
无可否认,整个世界的近现代化过程都始于对西欧诸国制度的模仿学习。然而与中国这种异质原生文明,在学习西方之后最终能找到属于自身道路者不同,斯拉夫文明本身并非欧洲文明圈的原生文明,并且在融入过程中长期处于文明圈边缘地带,最终在各种尝试失败都后陷入了如今的彷徨局面。
在早期斯拉夫人分化为东西南三支后,由于地理位置原因,东斯拉夫人融入欧洲文明圈的进程最晚,由原为维京人的罗斯人与东斯拉夫人融合成的早期封建国家基辅罗斯,直到公元988年才在弗拉基米尔大公的推动下受洗,成为东正基督教国家,此时对应欧洲神罗早期,中国宋太宗年间。在那之前,东斯拉夫各部族信仰的是原始多神崇拜。
公元13世纪蒙古人建立金帐汗国,统治罗斯诸地二百多年,“鞑靼桎梏”对俄罗斯造成诸多影响,一方面,蒙古的统治过程促使俄罗斯民族意识觉醒,让莫斯科公国得以壮大,成为后来沙俄的前身,另一方面,本就融入欧洲文化圈较晚的俄罗斯在经过蒙古人二百多年统治后,在很多方面进一步与欧洲文明脱节,公元1480年伊凡三世战胜蒙古人,罗斯各地获得独立,此时欧洲已经开启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了。政治上,蒙古的军事独裁制度也成为了后来俄罗斯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文化上,蒙古人的萨满信仰与东正基督教中的苦修传统融合,形成了俄罗斯民族文化中最重要的宗教形象“圣愚”。圣愚是这样一种形象,秉持苦修传统,拥有为侍奉基督而疯癫痴愚,自我贬抑的宗教觉悟。他们通常浑身污垢,衣不蔽体,疯疯癲癫,不能言语。要成为圣愚,必须要不顾自己,不计名利,受苦受难,全心全意侍奉上帝同时怜悯人民。这样的人在俄国会被封圣。
圣愚文化的另外一层特质是与俄罗斯底层的社会和文化生态高度相关,圣愚文化中来自萨满文化中粗俗下贱淫荡的部分并不符合一心向往西欧基督文明圈的俄罗斯上层精英们的追求,但在俄罗底层却长期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圣愚对俄国人文精神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形象也出现在很多俄国文学作品中,即使到了否定宗教的苏联时期,其影响仍然是深刻的,保尔就是一个圣愚和共产主义战士形象的结合。葛里高利和日瓦戈医生等等形象也具有这种性质。
理解圣愚文化的长期影响是理解俄罗斯问题的重要一环,另一环则是如何理解俄罗斯的政治生态特点。
伊凡三世战胜大帐汗国(金帐汗国分裂后)之前,拜占庭灭亡,公元1469年,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菲娅·帕列奥罗格在罗马教皇安排下下嫁伊凡三世,从此伊凡三世开始以东罗马继承者自居。
从地理上说,莫斯科公国始终是处于欧洲,从血缘上说,斯拉夫人本来就是古罗马时期的欧洲蛮族,且西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等早已成为欧洲文明圈的成员,从文化上说,自罗斯受洗到赶跑蒙古人也过了快五百年,随着拜占庭的灭亡,莫斯科公国逐渐成为东正教盟主。所以从蒙古人统治中获得独立后,俄罗斯上层精英的欧洲身份意识就快速膨胀。
公元1547年,伊凡四世称沙皇后,开始将莫斯科公国改为沙皇俄国,号称“第三罗马”,俄国开始不断通过扩张领土和介入欧洲事务寻找自身在欧洲的存在感。然而,比起欧洲各国,当时的俄罗斯在发展程度上确实落后很多。此时的欧洲文明仍然视罗斯诸地为野蛮人,甚至波兰这种在公元996年也才受洗的西斯拉夫亲戚,也因为罗斯诸地长期被蒙古统治而看不起他们。
在我们以前文章《解体三十年,成败苏维埃》一文中曾经提到,古罗斯各城邦拥有长久的自治传统。一方面,封建分封制导致不断产生新的小公国,另一方面,古罗斯政治生态中长期存在各种形式的自治/协商组织,如市民大会(维契),波雅尔贵族议会(杜马),全国实力派联盟(缙绅大会),以及属于最底层社会结构的,最广泛的自治组织苏维埃(СОВЕТ)。
苏维埃这种政治形态属于欧洲诸多民族中原始公社组织的遗留,早在6世纪~10世纪中叶,西斯拉夫的原始公社就开始逐步解体,而属于东斯拉夫的俄国则一直将这一形态保留至了近现代。
沙皇的产生开启了俄罗斯向集权国家迈进的步伐,蒙古军事独裁制度的深远影响也为沙皇专制提供了历史背书。然而这时的俄罗斯仍然是半身不遂的,本身政治形态上有长久的自治传统和原始公社遗留,在16世纪向西伯利亚方向扩张的过程中,又吞并了许多部落形态的游牧民族,这导致沙俄成立后政治生态在很长时间仍然松散不堪。
17世纪初,俄国进入“混乱年代”,沙皇空缺,波兰入侵,各种自治组织和地方势力频繁登场。在赶走波兰人入侵后,不得不通过选皇大会尽快选出新的沙皇,各方势力争斗,最后选出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对于当时的俄罗斯来说,时代的变化不允许国内再保持以前的各地自治一盘散沙状态,所以对沙皇这种专制独裁政治结构的需求非常迫切。
当然,即使又选出了新沙皇,在中央之外的各地仍然保持着各种自治组织形态。罗曼诺夫王朝继续艰难的朝着集权迈进,直到大北方战争俄国胜出后,彼得一世加冕皇帝,才有了快速推进改革,全面学习欧洲的政治基础。
对欧洲的疯狂迷恋与脑臀分离
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林娜二世,加强集权与学习西方一直在推进,但俄国上层和底层之间的脑臀分离也越发严重。
从彼得大帝时期开始,俄国上层社会对欧洲的学习和迷恋步入近乎疯狂的程度。这有几重原因。
一是当时俄国与欧洲先进国家发展水平差距很大,此时欧洲已经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以第三罗马自居的俄国如果想真正成为欧洲强国,通过学习先进国家改革势在必行。
二是随着俄国心态越靠近西方,就越想根除蒙古统治对俄罗斯各方面造成的深远影响,认为如金帐汗国的八思哈制等造成的历史遗留是导致俄国落后的重要原因。从18世纪到19世纪的西化改革中,清除蒙古文化基因也是一个重要旗号。
三是欧洲此时已经进入启蒙运动,对天主教文化的反思,对理性精神的推崇成为时代主流。东正教传入俄国之后经过漫长发展,和原版东正教也已有所不同,并且俄国上层精英和知识分子与底层农民对东正教的理解差异也很大。
对上层精英和知识分子来说,俄国的东正教文化更加充满弥赛亚精神和救世情结,导致知识分子们普遍有在俄国建立地上天国的热忱。而此时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中的欧洲,在他们看来到处都是“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正是他们心目中追求的地上天国。
而对底层农民来说,东正教融合了很多以前罗斯的多神教和蒙古时期的萨满传统,充满神秘主义,热爱上帝在地上的代言人沙皇,并且极端迷信崇拜圣愚形象,一个极端例子就是拉斯普京。
上层精英们一心要在俄国建立地上天国,对比欧洲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回头再看看俄国的宗教文化,发现越往底层就越是愚昧无知,就更加迷信全面学习欧洲才是出路。在俄国上层,对欧洲诸国语言比母语更精通的人比比皆是,尤其法德两国,对俄国改革进程中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极大。法国大革命也影响到了俄国,如十二月党人起义。
这导致俄国上层社会和底层的隔阂越来越大,在底层民众看来,上层老爷们并不像俄罗斯人,更像外国人。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中写道:
“俄国从18世纪开始明显受到西欧的影响,在以后的140年不断地接受西欧文明,社会上层接受西欧模式的培养,所有国家机关的建立都仿效西欧模式,法律也模仿西欧制定,但这一切仅限于社会上层,西方文明并未深入俄国下层,他们的道德规范、风俗习惯、家庭生活、公社生活、土地所有制和耕作方式根本没受外来文化和法律的影响,甚至不受政府的干涉,俄国社会上层和下层的文化差别,使得自由文化等级根本不理解农村的民间事物。”
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的命运》中写道:“同是在一个国家里,贵族和农民之间的鸿沟具有600年的差距,俄国与欧洲文化的差异甚至还没有贵族文化和农民文化的差异大。”
与上层对欧洲的迷恋相对,是底层社会对欧洲文化的排斥和敌对情绪。除了底层群众对欧洲生活方式和文化的抵制,还有对欧洲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与批判。俄国作为民粹主义最主要的发源地,就源于对欧洲当时资本主义下工人悲惨处境的恐惧,结合俄国底层长期的自治和公社传统,形成了一种空想社会主义。
也就是从这种上层和底层的两极分化开始,俄罗斯直到今日也摆脱不了处于文明夹缝中的命运。
陀斯妥耶夫斯基,疯癫先知的预言
要理解这种命运,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很重要的入手点。
年轻时的陀氏和其他俄国知识分子一样,也致力于改造俄国,建立地上天国,他加入了由进步知识分子组成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结果由于在小组会上朗读反农奴制题材的信而被逮捕判死刑,后改为流放西伯利亚十年。
在流放期间通过对各种问题的思考与形形色色俄国底层人的接触,让他深刻感受到宗教加诸于底层人民之上所带来的那些不同于欧洲,属于俄国底层人民特有的质朴精神,美好品格和虔诚信仰,他给兄长的信中写道:“即使是在服苦役的强盗犯中间,我在四年里也特别注意到一些人。你信吗,真有一些深沉、坚强、美好的性格,而在那粗糙的外貌下发现了宝贝,又是多么高兴。”
陀氏在这期间成为了信徒,并且开始思考在学习欧洲文化之外如何找寻俄国自身的道路。他创办的《时代》杂志发刊词宣称::“我们的任务是为自己建立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那种我们自己的、本民族的,来自我国根基的,来自人民精神和人民基础的新方式。”
19世纪60年代,陀氏去欧洲进行了广泛游历考察,最终让他从俄国知识分子对欧洲地上天国的迷梦中彻底挣脱出来。在见识了英法德等国的繁荣文明的同时,他敏锐地捕捉到这文明背后的黑暗。人民依然穷困,金钱物欲盛行。在资本社会没有什么是不能用金钱去衡量和交易的。陀氏在《冬日里的夏天印象》中写道:“巴黎是地球上最讲道德,最有德行的城市。多么有秩序!何等有理智,何等明确有稳定的关系,都竭力自信自己一切称心如意,非常幸福;而且……而且……也就到此止步,再往前可就无路可走了”
种种见闻与思考在这期间让陀氏确立了俄国的道路需要通过坚持自身宗教文化获得救赎的思想。然而,如果只是止于宗教救世这一步的话,那陀氏无非是另一个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在其长期创作生涯中也坚信着宗教最终能拯救俄国大地。
大概是因为陀氏患有极其符合圣愚形象物质的疾病癫痫,让他真的以极其敏感的心态接受到了上帝的启示。那个启示是一件如此巨大的事情,在19世纪只有陀斯妥耶夫斯基和荷尔德林两人最先发觉,即后来经由尼采之口说出的,上帝已死。
关于上帝已死这个话题很复杂,对于没有欧洲两千年一神宗教体验的中国人来说可能不太好理解,这里不展开太多。简单说,它代表着自启蒙运动开始,资本主义与科学理性思维迅猛发展两百多年后,欧洲思想文化中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和信仰危机。可以说欧洲哲学文化思想整个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转向都建立在对这个危机的探讨和解决上。
海德格尔曾说:“‘上帝死了‘这句话意味着超感性世界没有作用了。它没有生命力了。”尼采在道出上帝死了这句话时,同时默认了一切形而上的终极价值的解体。终极价值缺场,取而代之的是虚无。然而大多数人无法认识到虚无。多数人忙碌于扮演在他别人眼中,在社会中的角色,这构成了一种自我存在的欺骗。
就像陀氏代表作小说《白痴》中,代表欧洲青年形象的加尼亚的看法那样:“人要活,要吃,要喝。这是普遍的需要,而缺乏普遍的合作和利益的兼顾是不可能满足于这种需要的,这是人类社会的支点。”
作者又借另一个角色列别科夫发问:“你们有什么办法拯救世界﹖你们包括从事科学、办实业、开公司,拿工资以及其他等等的人们,你们为世界找到了正常发展的道路没有?”
陀氏自己终究也是找不到出路,陀氏在借文学创作探索宗教救赎和被癫痫折磨经常陷入非理性状态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整个欧洲信仰在崩塌,传统价值在崩塌,在理性主义发展到极致,上帝死亡后,世界将陷入非理性,虚无与荒谬之中。陀氏虽然有宗教救世的信念,实际上他的内容心处可能更接近一个无神论者。
这种矛盾在《白痴》中深刻体现。《白痴》的主人公梅诗金公爵是一个圣愚形象,不过与传统的圣愚形象稍有不同,他并不脏腑丑陋,反而穿着得体,能言善道,旅居国外,回到俄国后一腔赤诚想要拯救俄国人的精神信仰,建立人间天国。然而这一切是徒劳的,在这个时代,即使一个进行过现代包装的圣愚形象,对于时代来说仍是格格不入的,是不被人理解的。青年加尼亚的形象在俄国资本主义获得进一步发展之后,实际上也会逐渐成为俄国青年的形象,就像小说中列别科夫的外甥,道德水平更为恶劣。小说最后公爵因理想破灭变为白痴,宣告灵魂死亡。
之后的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圣愚形象又回归传统,丽萨维塔是一名看似疯癫又被人奸污的女圣愚,这位上帝的使者是一面镜子,众多人物的癫狂虚伪都在这面镜子中一览无余。在这里没有人得到拯救,只有癫狂导致的悲剧。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俄国在几百年中狂热的学习和靠向欧洲,然而最先发现整个西方文明症结的又是俄国一个抱有宗教热忱的癫痫之人,欧洲现代哲学,文学,精神分析等思潮都从陀氏的作品中受到启发。
到这一步,俄国之前的探索就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东斯拉夫作为欧洲文明圈的次生文明,在头部努力靠向地上天国几百年之后,愕然发现上帝在欧洲已经死了,欧洲自身也将遭遇重大精神危机,欧洲的知识分子们反过来还要从陀氏这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自己的身体还是在靠着宗教,公社,民粹这些已经跟不上时代的东西维持。作为次生文明的俄国该怎么寻找自己的道路?不光是陀氏,托尔斯泰在晚年也认识到了宗教无法建立天国拯救俄国,只能救他自己。
说个题外话,中国前几十年的很多知识分子之所以对西方过于迷恋,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根本没有认识到西方的精神危机是怎样发生的,对于西方的理解还停留在前现代,即启蒙时代甚至文艺复兴时代的水平上。
比如出身北大的著名叛徒余杰,他对托尔斯泰的宗教救赎理念非常推崇,并且拿苏联解体后宗教的回归和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的“进步”当作自己的论据。然而只要对陀氏以来的现代性思潮演化,以及对俄国社会有些了解,就会知道这种推崇是非常搞笑的。
苏联的失败,俄罗斯的宿命悲剧
总之,俄国上层的知识分子们仍在继续寻找道路自救的努力,一个有趣又尴尬的现象产生了。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之后,一些精英开始提出所谓要唤醒俄国的“东方人意识”。俄国在历史上和血缘上都与东方有着亲近关系(因为蒙古的统治,俄国人有一些钦察血统,但不多,俄语中有大量的蒙古语词汇,由于长年扩张境内又有了不少亚洲民族),既然全面融入西方处处碰壁,那么俄国应该重寻东方传统,将东西方文化融合起来,互通有无,才是俄国的新使命。这种观点的代表有“东方人派”,“欧亚主义派”等。
这就更尴尬了,俄国有的那点全部的东方基因,其实就是蒙古文化基因。然而东方文化真正的基因在哪里谁都知道。但俄国直到十八世纪,对中国的了解都还赶不上欧洲。在欧洲碰壁之后想到东方寻根,但游牧民族文化的根对解决俄国的问题没有任何作用。
终于,俄国人在知识分子的努力下又赢来了自己最重要的一次建立地上天国的机会,然而因为它自身的历史和文化特殊性,在某种程度上也为这次努力的最终失败种下了因由。
这次机会就是我们熟知的十月革命。如果我们抛开马克思主义经典框架中关于社会形态演进和革命发生规律的一般构想,而是从俄国这个国家的特殊性考察的话,马克思思想在俄国的传播,以及十月革命的发生都非常有俄国特色。根本上说,俄国革命的发生同之前那些想在俄国建立地上天国的知识分子一样,本质上还是一群知识分子引入外来先进理论,对落后的俄国社会形态进行强力灌输的结果。
俄国自发产生的革命思想是民粹主义那样的东西,但在遇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们之后在理论上已经完败。俄国的工人组织和运动在进入二十世纪后也远没有欧洲那样成熟。就像布哈林说的那样:
“俄国是一个落后国家。但是,它为无产阶级输送了一大批第一流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件事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文化较高的一些民族,首先是德国人创造了许多思想,我们不必用自己的智慧再去创造它们。在这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输入的”。
在俄国这样的大国搞革命,必须建立最严密的政党组织,需要职业性的革命家,俄国传统的自治传统和公社形态完全不适应这种要求。历史又一次呼唤着强力领导人的出现。首先就是列宁,在后来的研究者中,如齐泽克那里,就非常重视列宁本人的“决断勇气”对十月革命成功的关键性影响。列宁认为严密的革命家组织是极重要的,反而“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在当时,大批党内人物都反对列宁这一观点,不过事实证明列宁是对的。
在《解体三十年,成败苏维埃》中我们提到,由于当时俄国种种复杂现实情况,布党必然承担起那个俄国历史上的一元决策与执行单位的角色,导致布党必须“说最民主的话,做最独裁的事”。
因为先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们对俄国的革命灌输太快太猛,实际上广大基层很多时候也并没有理解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等的真正含义,只能套用传统宗教中的救世与地上天国等概念来理解。就出现了在违反列宁本人意愿的情况下,将其无限神化,乃至打造成了新的“神”的情况。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神化,有些地方甚至是把列宁画像当做东正教圣像代替品来对待的,还有沙俄将军投奔布党后,见到列宁嚎啕大哭跪下亲吻他的手指。
另一个致命问题也像历史宿命一样展现,就像当年拜占庭灭亡,俄国成为东正教盟主那样,源于欧洲的共产主义在俄国首先开花结果,苏联成立后,自然也就接过了共产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大旗。然而,对于俄国底层人民来说,实际上在当时也搞不清这些概念。1936上映播放的苏联电影《夏伯阳》,被认为是“高大全艺术形象”的起源,但是在这部电影里,也表现出普通老百姓和士兵分不清什么是布尔什维克什么是共产国际,作为主人公的夏伯阳也不太分的清,只好说我跟着列宁走,列宁在哪一方我就支持谁。
世人都说苏联后来变成了红色沙文主义国家,背弃了国际主义理想。这是一个现实结论,但问题是这个现实怎么来的?首先要问,国际主义精神到底是什么?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考察,实际上会得到一个不少左翼不太愿意接受的答案。
19世纪的欧洲其实就有了不少“国际主义者”,但这种国际主义者,实际上是欧洲文明共同体主义者,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到19世纪,是欧洲民族主义国家开始形成的时期。到19世纪经过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欧洲中产以上阶层统一的文明生活方式。各国的交流与长年战争,让很多人厌倦了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回望罗马,认为欧洲文明应该是一个整体,逐渐产生了”欧洲人”的身份共同体意识。
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的国际主义最早又是怎么来的呢?实际上是欧洲煤钢和纺织等资本主义早期产业工人共同体。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基本上等于欧洲,主要工业国之间经济文化隔阂较弱,社会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前夕,工业模式和产业链条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此时的产业工人成分比较单一,以煤钢和纺织等工人为主,复杂分工和脑力劳动者都未大量出现。这才有了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实践的现实条件。
无视一切现实物质条件的国际主义理想确实美好,但唯物主义者不应当单纯沉迷于崇高道德幻想。
所以,也只有在一二战期间西方大动荡的时刻,苏联才有能力扛住国际主义这面大旗,而西方内部完成利益重新分配,抱团发展对扛社会主义阵营后,苏联就没法再保有国际主义大旗就是一个现实问题了。工业上,苏联没有能力给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一致的生产力水平和工业分配。文化上,除了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点之外,苏联和阵营其他国家的文化差异极大。
西方反而轻松很多,欧洲在战后弄出共同体,进一步发展成欧盟,美国又借着对小弟们的工业再分配,在剥削第三世界的基础上拉着小弟们共同构建起了打着普世自由大旗的霸权秩序。所以当代西方,以及皈依西方的人中才会产生那么多口称自己是“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动辄将民族主义打成万恶之源,但实际上屁股却坐在帝国主义那边的虚伪之人。
还有一个最致命的问题,就是苏联虽然强大,在期间创造了辉煌的社会主义文化,但根本上还是没有解决掉自己缺乏独立文化根基的问题。对上,从苏联成立开始,就一直没有解决大批知识分子和精英仍然倾慕西方的现象。对下,红色文化也没有替换掉俄国底层的宗教基因。
这不光是苏联一个国家的问题。从现实上来看,已经出现过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哪个能真正不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结合,完全凭空创造出社会主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本土化改造实践才是最有现实操作性的路径。
从斯大林执政生涯前后对东正教的政策转变就可以看出,东正教文化在俄国的底层是十分强大的,即使强大如苏联,也不得不与之妥协。勋宗时期,苏联宗教政策进一步宽松,不过程度还是控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底限内。然后戈秃上台之后,同其他政策一样,宗教政策也彻底放飞了,这也是压垮苏联的稻草之一。
俄罗斯历史上比“混乱年代”还悲惨的时代开始了。我们不用再说叶利钦上台后那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事情,两个简单的问题:这一次彻底倒向西方的俄国,实现地上天国的梦想了吗?没有。苏联倒台之后全面复兴的东正教拯救俄国了吗?也没有。
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进入后现代了,陀氏在癫狂中早已预见了这一切,一神教的世俗权威早已瓦解,在后现代社会中,宗教起到的是一种裱糊作用,以更庸俗滑稽的方式影响我们的世界。
由于现代文明生活的威力,苏联后期普通人就已经在文化上倾向西方了,在我们以前文章《狂欢过后,圣诞解体》中有过讲述。从苏联第一家麦当,解体前的摇滚演唱会,解体后迈克尔杰克逊访俄到如今,俄国的流行文化和欧美已经没有太多区别。在俄国的抗蒙神片《怒战狂心》中,处处都是《斯巴达三百勇士》的影子,甚至俄国和东欧地区还成了高质量色情片产地。
从陀氏到现在,西方在上帝之死后的精神危机解决了吗?从哲学和社会形态发展上看好像没有,而且还想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可能也越来越少了。欧美,尤其是美国,现在仍然有所谓的昭昭天命在我的情结,然而这已经和上帝没什么关系了,完全是二战和冷战红利以及新自由主义秩序带来的富裕和霸权,让人们不得不承认其天命所归。齐泽克们是在重新呼唤共产主义,期待再有一场列宁式的革命,然而本质上仍然囿于欧洲中心主义之中。
更多西方知识分子的眼光,则是放在如何在后现代社会改善西方内部的秩序冲突与公平问题,以及多元化和平权,仿佛只要西方内部和谐了,世界就可以永远美好下去。
所以如今的俄国,甚至比几百年前更为彷徨。彻底融入西方?现在确实仍然还有很多精英在幻想着西方能打开大门。但是还要怎么融呢,再下去只能把自己完全拆了。回到苏联?根本不可能了。回到沙俄?在当代国际现实中这就是个笑话。没有哪一条老路能走通。
无论如何,俄罗斯终究要直面这样的历史宿命悲剧,当前的世界秩序摇摇欲坠,俄罗斯必须真正地想清楚自己与西方究竟该形成什么样的关系,与东方又该形成什么样的关系,以及自身在东西方之间该走出怎样的道路。历史已经给了俄罗斯多次机会,如今还剩下的时间可能不多了。时不我待,必须尽快抉择了。如果俄罗斯再一次遭遇苏联解体式的悲剧,那能给这个民族再重来一次的希望可能就更渺茫了。
纵然以后通过与某东方大国的合作重新强大,摆脱西方的威胁,俄罗斯仍要面临寻找自身文化根基的问题。当然,毕竟已经是21世纪了,可以以现代生活重新塑造传统,但这一切也要首先从摆脱西方迷梦与边缘人身份开始。
俄国宿命悲剧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今天的内容,我们梳理了俄国自古至今面临的问题,一个处于东西文明圈夹缝中的次生文明,在一次次向外寻求文明升级方案的尝试中不断面临本国上层与底层两种相反力量的拉扯,最终在外部文明方案也出现根本性问题后,陷入了彷徨尴尬的境地。
读者们看到俄国精英对欧洲的迷恋和西化努力,可能会想到近代的中国,会想到高层大员很多私下都说英语的国民党,会想到一心脱亚入欧的日本。就像前面说的,整个世界的近现代化过程都始于对西欧诸国制度的模仿学习。然而,中国人始终应该记住,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原生文明,即使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学习西方,中国的选择和操作也不能和次生文明一样。就像中国革命的成功,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成功本土化。
从人类社会早期开始,先发文明就天然的会对后发文明产生吸引力。西周四百年奠定的礼法制度基础,让后来的中原诸国成为“诸夏”,“冠带之邦”,并开始对周边族群一轮轮的同化。楚国曾是蛮夷,但后来楚国的漆器帛画,屈原辞赋,楚简儒经冠绝七国,及至“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虽然最终汉朝一统天下,但楚人也早完全成为了华夏人,并不会有心理上的隔阂。
从文明的处境上看,俄国在这一点和楚有些相似之处,上层半吊子的西化,境内遍布部落诸侯,文化冠绝欧洲。但秦汉奠定了大一统,罗马却早亡了,俄国只能自称第三罗马而不被世人承认。
次生文明想通过模仿原生文明进行改造升级没有问题,但结果并不总是理想。历史上如北魏,辽等等,汉化程度过头反而最终导致自己的国家消失。这从历史上民族融合的角度看固然没问题,但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和文字传播技术的扩散,越到近现代,次生文明的民族意识就越是强烈。
当代内外对中国设下的民族主义话术陷阱正在这里。但凡中国有一些“反抗西方”的举动,就会被内外各种人指责为“极端民族主义”。又有很多人拿着所谓“民族国家是近代才形象的概念”,“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之类只言片语试图解构中国人心中的共同体意识。
然而这些人嘴里的“民族主义”的对立面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的国际主义吗?显然不是。所谓的近代构建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式的民族主义的对立面是国际主义吗?也不是。
欧洲民族主义国家的诞生,本质上是一大批有着不同语言和宗教传统的次生文明共同体,面对以欧洲原生文明自居的大国们,是选择被彻底征服同化,变成罗马的一部分,还是独立抱团的结果。而原有的宣称继承了欧洲原生文明的大国,则是把对罗马宝座的竞争动机换了一套更符合时代潮流的理由。
由于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文明层之间再没有农耕还是有游牧之类的差异,所以就得文化上构建共同体差异。由于次生文明很多祖上的历史源流都非常混乱,所以在构建民族意识的时候出现现实需求,就会出现所谓“想象“的情况。
比如在我们之前文章《乌克兰是怎么产生的?》中提到,在波兰和立陶宛联邦时期,往往一个立陶宛人在政治上是波兰人(波兰国家)、血统上是立陶宛人(立陶宛血缘)、宗教信仰上是希腊人(信东正教)而同时可以说教会斯拉夫语、波兰语、拉丁语。更典型的“想象”就是土耳其埃苏丹式的乱认祖宗。
欧洲小型民族国家之所以要构建民族意识,不是什么没有国际主义精神,而是不愿意配合欧洲大国的罗马梦,查理曼梦。至于20世纪后亚非拉民族主义的兴起,更是为了反抗西方的殖民统治。欧洲小国们的民族主义国家构建,和融入欧洲秩序的进程相对都是成功的,俄国融入欧洲的失败,因为历史,也因为俄国的体量对欧洲威胁太大。
所以中国是不是民族主义,是不是想象的共同体?我的看法是西方民族主义概念并不适合我们,我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原生文明,共同体的存在并非靠想象。虽然不提倡文明特殊论,但也要明白原生文明在面对现代化进程中选择的道路和方式不可能跟次生文明一样,小型次生文明拥有的周旋空间和余地我们往往没有。连俄国融入欧洲几百年都未成功,一个体量庞大的原生文明抛弃自己的根本去完全投入另一个异质文明的怀抱,这是真正的愚蠢之极。
那些拿民族主义指责中国,屁股的本质却坐在霸权秩序那国的人,口中的国际主义,世界主义本质上还是“罗马主义”,告诉后发国家们不要搞什么民族国家,大家都接受当代罗马的统治就好了。
国际主义的未来道路在哪?我们还是要以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态度来直面这个问题。苏联没有实现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的同化,当代中国能对第三世界输出的是工业品和生产力,但在产业分工和文化隔阂上,目前也无法超越现实抹平一切差距。自我感动式的口号并没有用,现实只能是在推倒当前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基础上,让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真正有可能朝着平等公平的秩序努力迈进。
不论如何,国际主义的未来显然不是罗马。

 188金宝搏体育官网 SZHGH.COM
188金宝搏体育官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