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麦克·布洛维,译者:周潇 / 张跃然
1971年至1972年,匈牙利诗人和社会学家米克洛什·哈拉兹蒂在布达佩斯郊区的红星拖拉机厂工作。他在《计件工资》(Piece Rates)一书中讲述了他的经历,该书的英文版名称为《一个工人在工人的国家里》(A Worker in a Worker’s State)。哈拉兹蒂被匈牙利政府审判,罪名是其著作扭曲事实,将迷惑性的场景泛化,因而刺激了民众对国家的仇恨。毫无疑问,红星拖拉机厂当时正处于危机之中,因此劳资关系一直在恶化。在50年代,红星拖拉机厂因为农业机械化而获得补贴,然而到60年代,它失去了这些补贴,在1971年,受到新经济机制的压力,它不得不为生存而奋斗。“情况严重,需要重度救济”。事实上,对任何熟悉英美机械工厂的人来说,救济是不可思议的。尽管哈拉兹蒂对红星拖拉机厂所处的环境鲜有说明,但是我将重构它的特殊情境,以阐释在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存在于工作中的一般力量。
哈拉兹蒂在红星厂的经历与通常的认识相背:国家社会主义的劳动强度要远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根据哈拉兹蒂的叙述,他在机械车间的操作工岗位上工作,这与我在南芝加哥的车间和岗位类似,我估计他的工作量是我的两倍。在一次接受《东欧劳动聚焦》(Labour Focus on Eastern Europe)的访谈中,哈拉兹蒂认识到但并未解决这一矛盾:
我并没有打算将之与其他工厂比较。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快的节奏。但我现在确信,在社会主义国家,节奏一般比西方国家慢,这不仅仅是因为发展不足。它是“完全国家垄断系统”的一个特征:工人被限制了他们的权利,但具有一定的工作保障。简单说来,就业保障是导致工作节奏较慢的一个基本因素,尽管人们可以对隐性失业进行经济学分析。就工作节奏较慢这一点而言,技术官僚为将工人阶级纳入超级垄断工厂系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所在的工厂实行的是计件系统……这些工人的工作节奏是最高节奏之一。半自动化工人可能面临更高的节奏,但是一般来说计件工人比计时工人具有更高的节奏。计件制在斯大林时期非常普遍,如今它再次被引入。
考虑到我们所知的东欧就业情况,同时操作两台机器这样紧张的工作节奏,如何可能?其次,哈拉兹蒂的经验是否具有典型性?在这一节中,我尝试用我在联合公司的经验作为比较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在下一节中,我们将尝试回答第二个问题。

劳动过程和标准专权
红星厂实施计件制的机器车间在许多方面非常类似于联合公司。同样的机器——磨机、钻机、车床等,由一名男性工人按照计件工资率操作。他们受到各种辅助工人如设定员、检验员、库房保管员、计时员、卡车司机和工头等的帮助或阻碍(红星厂的辅助工人更多)。在两个车间,辅助工人都按计时制工作。
然而,就纯粹的努力而言,哈拉兹蒂描述的标准似乎令人难以置信。试用期满后,哈拉兹蒂被介绍到“双机系统”。资率设定员决定,操作工应尽可能地一次运行两台机器。哈拉兹蒂最初认为这是一种更能赚钱的方法,直到他发现这些工作中(他的机器上主要的工作是碾磨),单件的时间被减半,但有可能得到额外的20%作为补偿:
同时在两台机器上工作非常困难:危险且让人筋疲力尽;你必须全神贯注。当我在一台机器上工作时,我觉得无聊和疲惫,当然,当它自动运转的时候,还是有些满足感的。看起来我在支配机器:我给它加料,我的手放在它的外壳上,然后它就开始工作。只有当我从操作两台机器转换到一台时,我才能感受到些许温柔的情感,即便如此,这种情感也很快就消失了。而当我在两台机器上工作时,这种感受是完全不可能有的。你不是控制两台机器,而是它们控制你。我变成一个毫无意义、无意识的机器。
我在联合公司确实经常操作两台机器。但条件和后果非常不同。其中一台机器是自动锯,不需要持续关注,因此我可以投入精力在另一项工作上。这不仅意味着我总是能够存储一堆零件以便随时可以上交,而且意味着如果自动锯不能保障一个可接受的产量,我就可以拒绝运行两台机器。换言之,同时做两项工作油水丰厚,正如哈拉兹蒂最初以为的那样。
但是哈拉兹蒂是如何被迫像疯子一样工作的?部分答案必定在于计件系统的性质。在红星厂,该系统以与马克思的描述非常相似的方式运行。有一个基本工资,但它纯粹是个形式,并不保证最低额度。然而,这种小时工资在其他方面是重要的。第一,它可能决定一个工人跳转到另一个企业时能够获得的工资。工头尽可能地压低小时工资,这为工厂节约了支出,但更重要的是阻止工人跳槽。第二,小时工资决定了月中工人收到的津贴,以及假期和病休期间的薪水,“否则凭着微薄的小时工资,你看不起病”。第三,小时工资或对应的工人类别被工头用来决定向操作工的任务分配。更轻松的资率通常被分配给更高级别的工人,也就是享受更高小时工资的工人。第四,前三个月,工头有权利保障工人的小时工资,即使他们的产量无法保证。此后,操作工就得靠自己了。当计件工资率不可能达到的时候,工人无法把他们的收入提高到时薪水平。他们只能先愤怒,后抓狂。在联合公司和吉尔公司,情况非常不同。工人被保证有一个最低工资,所以如果资率不可能达到,他们会休息、偷懒,甚至期待资率被放松。
由于红星厂没有最低工资,工人的收入直接取决于所生产的产品数量。每一件都有一个根据资率确定的价格,以使操作工能够获得其小时工资,小时工资则是按照产出的100%设定的。通过遵循图纸的指导,规定的速度、进料和切割深度,哈拉兹蒂发现,他不可能以获得小时工资所需要的速度去生产零件。此外,计件系统不允许任何时间花费在设定(如在联合公司中所做的)、检查或其他意外情况上。为了获得小时工资(更不用说最低生活工资),操作工必须通过增加速度和进料以及采取危险的“抄近道”的方式来打破规则和安全规章。只有这样,操作工才能生产100%。这种“标准欺骗”,被称为“抢劫”,主宰了操作工的整个车间体验。它消耗了他的注意力,成功时则提供了一些成就感。因此,概念和执行的统一部分得以恢复,但却是为了老板的利益。
由抢劫的必要性所带来的“神经紧张”不能由战利品本身之外的东西缓解。我们必须利用我们所有的创造性、知识、想象力、主动性和勇气去获得它。当获得战利品之时,它带来一定的胜利感。这就是为什么计件制工人经常觉得他们打败了系统,好像他们占了上风。
虽然负责“保障规则得到遵守”的工头、检查员和资率设定员就在现场,“他们却视而不见……只要你不迫使他们注意到你的‘抢劫’”。事实上,工头的奖金和声望依赖于冒着失去生命和肢体的危险追逐战利品的操作工。
但是,在超过标准以获得最低生活工资之时,操作工向资率设定员提供了加速弹药。追求最大化经济收益迫使单件价格下降。
为了生计,我们被迫向资率设定员提供修正标准的无可辩驳的论据,进而单件的时间以及单件的收入降低到更不现实的水平。这使我们进一步加快速度,尝试达到更高的生产水平。因此,毫无疑问,我们慢慢地为另一个增加的标准准备证据。
标准修订不仅一个工作接一个工作地进行,更重要的是它建立在集体的基础上。工人被劝告为了共同利益增加他们的产出,并且他们得到惠及所有人的“标准修订”作为“酬赏”。
重要的是,红星厂操作工称为“抢劫”的,联合公司的操作工称为“赶工”。在联合公司,他们期望超过100%的生产水平,管理者和其他工人也如此期待他们。事实上,“预期比率”为125%,每个操作工设定了自己赶工的目标(在125%和140%之间)。只要操作工的产出不超过140%,他们的资率不会被“方法部门”削减。限制生产以便上交额度不超过140%,是为了他们的利益。红星厂的操作工却没有这样的“配额限制”,只要他们欺骗标准,他们就会遭受任意的资率削减;标准的修订与实际产出水平无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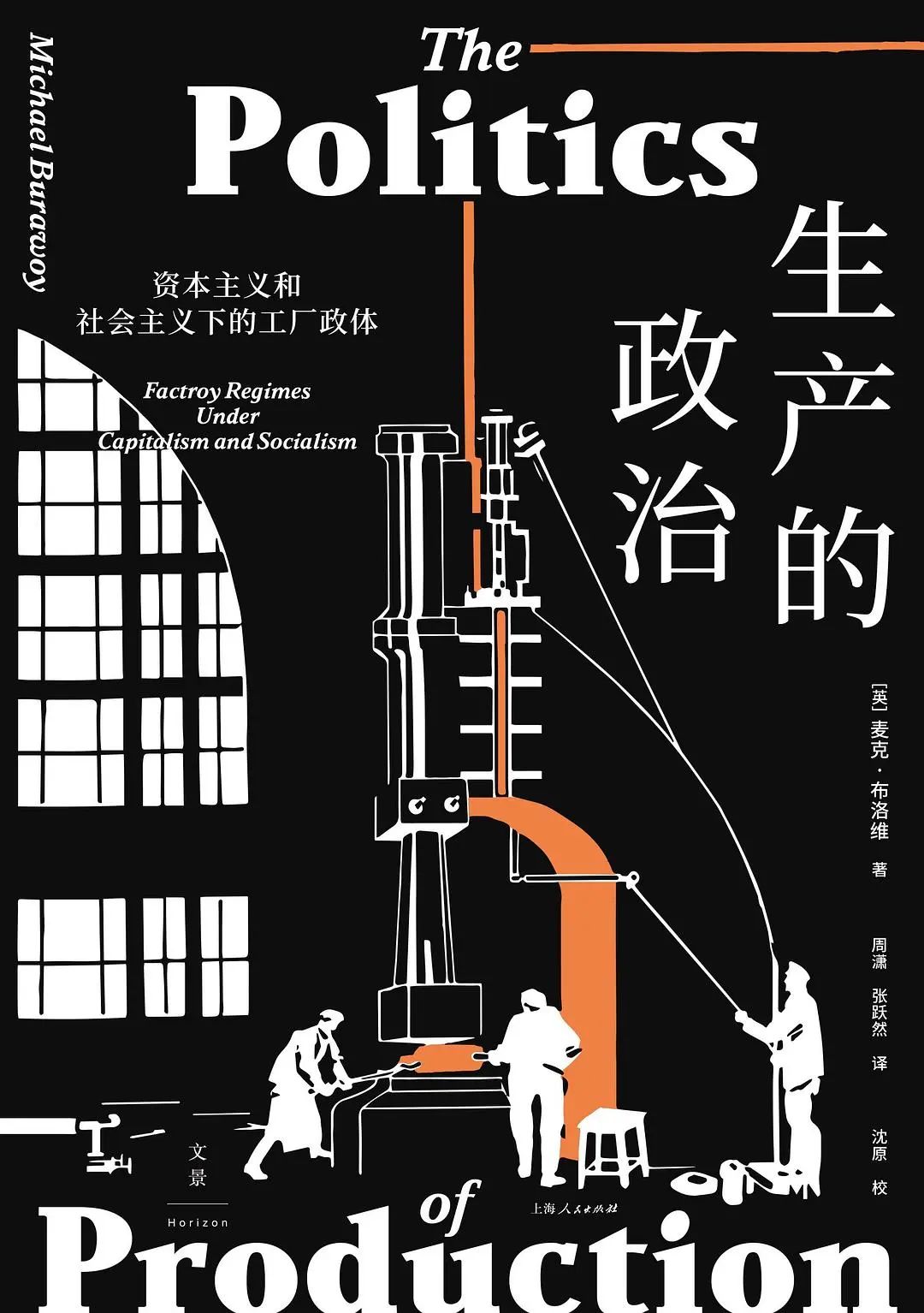
受权刊发,选自《生产的政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下的工厂政体》,[英]麦克·布洛维 著,周潇 / 张跃然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世纪文景2023年6月。
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两个机械车间劳动强度存在差异的原因。在红星厂,“就业保障”与“工资无保障”相结合,而在联合公司,“就业无保障”(尽管工人很少被解雇,但冗员总是可能的)与“工资保障”相结合。红星厂工人的工作得到保障,但最低生活工资必须通过加强努力才能赚取。因此,在1971年,工业工程部门的平均小时收入为11.2福林。按照哈拉兹蒂所从事的工作类型,这意味着平均生产水平为147%。2][但是,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红星厂的工人不能挑战标准的专权,或者进行讨价还价以获得对付出的更大酬赏?为此,我们首先需要考察劳动过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效果,以及工厂的政治机构。

劳动过程的意识形态效果
工人如何在野蛮的从属关系中保持合作?生存的需要以及管理者因此拥有的权力显然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有一些劳动过程的要素,导致了工人自身在其从属地位上的某种共谋。将工人卷入到“非人性化”境遇中的机制,是结果的不确定性。“无保障是所有根据结果付酬的制度的主要驱动力……计时工资显而易见的强制性和依赖性转变为计件工资伪装的独立性……不确定性是计件制的伟大魔术师。”同时,太多的不确定性使得工人对产出漠不关心。如果资率设定者将他们的运气推远,或者标准的修订过于剧烈,操作工就会离开。
因此,在联合公司和红星厂,劳动过程与计件工资系统的意识形态效果非常相似。一旦工人认为他们能够在计件系统下生存,他们就会运用智力、意志和忍耐力应对挑战,并将失败归咎于自己。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工人参与到对自身的残酷剥夺中。
当然,(工人)清楚地知道他被欺骗了,但他积极参与对自身的反对使得他不可能看到这种欺骗;他们也不能将之与其生活条件相关联,而计时工资的工人却能够如此。
相反,他对于小小的歧视、不公或者操纵非常敏锐,并且为反对这些而斗争,确信斗争的胜利能够被用来反对欺骗。他趋向于用收入判断所有事,当他某月收入不错的时候,他从心底里确信,他不是上当者而是胜利者。
一旦被迫投入“抢劫”,使得“抢劫”成为必要的条件就退回到背景之中,成为不可改变的既定事实:“不仅双机系统,而且工作性质本身,似乎都是不可改变的。”
标准系统在束缚想象力上比在刺激生产方面更为有效。计件制工人最甜蜜的梦想就是获得公正和充足的小时工资:换句话说,是从标准下得释放。如果一个生产中的关系的乌托邦——在那里他们能够共同确定其目标——可能冒头,他们就会立刻将之扑灭。
工人不是构想组织生产的替代性方式,而是被每天面对的各种变数所充斥:好工作而不是坏工作,一台机器而不是两台,获得补充工资和奖金的可能性等等。这种明显无关紧要的差异压倒了车间工人的所有其他体验。
我们就像土著,在殖民早期,上交所有的东西,财宝,土地,以及他们自身,为的是换取不值钱的小玩意儿。只有在我们没有获得通常作为回馈的垃圾之物时,我们才会开始意识到自己被掠夺了。
而收入的真正相对性又进一步神秘化了工资劳动的基础。
人们可能认为双机系统如此残酷粗暴,它会打破那种“我们被实实在在地按劳付酬”的错觉,进而打破关于有偿工作的一般性错觉。事实却是,它增强了幻觉的力量。当双机系统与旧系统或小时工资相比并没有改善我们的工资时,对我们而言,这并非那著名的生产关系的残酷表现,我们感到受骗了,真的受骗了。
再一次,我在联合公司发现了同样的情况,当我们不能得到所提供的必要条件,如可接受的计件工资率、足够的工具和固定装置、辅助工人的快捷服务等,以便完成赶工时,我们就对管理者义愤填膺。
无论一个人将多少知识带到车间,无论一个人读了多少次《资本论》,经验都是一样的。一个偏执狂将其所有的精力和创造力都用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如果“抢劫”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如果赶工是为了补偿工作的无聊,一旦开始,它们的意识形态效果便在于掩盖其根源并自主地产生意识形态条件以完成自身的再生产。

劳动过程的政治效果
物品生产的同时是关系的生产——竞争和相互依存的关系。1][在计件工资系统下,竞争围绕着好工作和坏工作的分配,从一个岗位到另一个岗位的转换和升职,以及补贴的分配(补贴是对操作工遭遇的一些意外事故进行补偿,这在计算计件工资率时不包括在内)。当这些竞争在所有的机械车间发生时,其特定的组织方式反映和塑造了从属关系的不同形式。因此,在联合公司,竞争通常通过规则的运用来解决,在吉尔公司,它更有可能通过非正式协商解决。而在红星工厂,则通常是通过工头独断的意志来解决。
所以每个工人都依赖于工头,工头设定了工人的工资水平:这是计件工资的悖论。一个工人对其他工人的唯一关注是嫉妒性的猜疑。其他人是不是多赚了几菲勒?他们的小时工资是否上涨更快?他们是否会获得更多“最好”的工作?这种竞争在由工头决定的所有其他事项上同样激烈:假日、加班、奖金、奖励。”[
还有其他方面的竞争。在“抢劫”是生存的秘密武器且其可能性受限的情况下,操作工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们积累的经验。当新操作工进入车间,接受高级操作工的训练时,就会面临这种情况。如果新手预备好通过上交许多零件来增加师傅的收入,他就会学到一些东西。但是“抢劫”不能凭空而降,坏工作也不能自动变为好工作。新操作工必须通过密切观察他人来学习,或者通过一些好处来交换。
(师父)不让我同时操作两台机器,尽管我最终必须这样做。他很快设定了一台机器,速度之快使得我根本不能看清他做了什么。然后他让我进行余下的操作。同时,他自己在另一台机器上碾磨,直到我结束为止他一言不发。他的行事方式有一个勒索的暗示:如果我同意参与,他可能就会同意偶尔跟我解释那些古怪的事情。有时,他提前下班,就叫我为他打卡。作为交换,他会花半小时教我事情是怎么回事。
一名操作工只有在其受训期结束并开始投入战斗的时候,才开始明白抢劫的艺术。他不仅要设定和操作机器,与其他操作工为了同样的稀缺资源竞争,而且要为了获得辅助工人的合作而战斗。他依赖于这些辅助工人,但同时又跟他们存在对立关系。对于获得计件工资的操作工来说,浪费时间等于浪费金钱。对于按时间付酬的辅助工人而言,浪费时间等于省了力气。哈拉兹蒂在面对设定员时很快明白了这层含义,设定员有各种理由对操作工逞威风,让他为了无用而不必要的差事跑来跑去。“我所失去的就是设定员所得到的:他按照小时得工资。我开始恨他。”他的一个邻工解释说,“看,他们在这里不是为了让你更轻省些。……他们为什么应该更友好些呢?如果你想继续下去,你最好是靠你自己。你必须学会这些,如果你想维持生计的话。”
检查员的情况类似,但有一个区别:你不能没有他。只有获得了他的认可,你才能继续你的工作并尝试赚得一些收入。哈拉兹蒂的师傅如此告诉他有关检查员的情况:
他的特别策略是绝不会立即批准一批产品。你给他看你的第一个产品,他总是要求你修改一点。但不用管它。继续做你的事,下一次他来了,给他看另一件。通常,他会立刻在你的工作表上盖章,因为他感到羞愧。
检查员明显是多余的,是工资劳动系统的一种明显表现,以至于他们把自己塑造为“质量男人”(men of quality)。他们以此角色直接与操作工——“数量男人”(man of quantity)——相对抗。
车间的小官员既非工人也非老板,他们作为企业代理人、规则的执行者和强制实施者、档案管理者,以及老板和工人之间的沟通者出现。虽然他们自己没有什么权力,但却仍然处在一个羞辱车间工人的位置上。
这些都不会导致任何团结的感觉:计件工资工人不能将所受的侮辱传递给其他任何人,当被原则上并非自己上司的人粗暴轻率地对待时,他们遭受巨大的痛苦。
此外,任何团结的希望被简单的日常经验所破除:白领工人做更轻松的工作,完成的任务更少;他们的工作更容易,劳动强度更低;他们无需黎明即打卡上班,不用在工作时间吃饭;在其办公室里熬煮的咖啡象征着他们的权力,尽管权力有限。
在联合公司,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机器操作工和辅助工之间的合作,在吉尔公司合作更为普遍。可以肯定的是,工作的组织将两组工人之间的对抗结构化了,管理者增加机器操作工产量的压力通常被转化为操作工和辅助工之间的横向冲突(后者对增大工作强度没有兴趣)。然而,辅助工没有试图让操作工从属于自己。相反,他们经常从事禁止的活动以方便操作工赶工,唐纳德·罗伊称之为“修复”(fix)。联合公司的辅助工人和机器操作工在一起工作,两组之间有很大的流动性。在红星厂发现的辅助工人以煮咖啡、闲聊和开玩笑而表现出的优越地位,在联合公司是不存在的。这种较高地位的基础是什么?分化是如何产生和再生产的?为什么检查员、安装员、文秘与老板而不是与车间工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等级制的政治组织
我们已经看到,在联合公司,操作工和辅助工如何成为通过投标和挤兑规则来管理的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空缺职位由投标的工人填补,资历是通常的决定因素。公司内部未填补的空缺对外部劳动力市场开放。面临下岗的工人,如果可以完成其他资历尚浅工人的工作,也可以“挤兑”他们。简而言之,为了“提升”和“转岗”而进行的竞争是由规则而不是工头个人决定的。虽然存在工作的等级结构并因而存在相应的基本工资的差异,但这种等级制不会导致任何结果,也不会根据权力或对管理层的忠诚来区别对待工人。
在红星厂,辅助工的收入与机器操作工的收入大致相同,但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等级关系。辅助工毫不怀疑他们的利益取决于老板。党的角色似乎在保障对管理者的忠诚方面非常关键。对那些寻求职业发展的人来说,晋升到辅助工是必要的(即便不是充分的)一步。但是,要突破操作工的等级实现这种跃升,需要通过党员身份和党的活动。哈拉兹蒂的邻工告诉他:
他们都是老板的朋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安装员。他们在晋升的路上。(那个年长的安装员)曾是地方法院的主席。全薪,当然还有所有的补助。其他人也一样。那个年轻的,去年才成为安装员,你会看到明年他将成为工会代表或党组书记。工程经理曾经也是一个安装员。
检查员,跟安装员和工头一样,都处于特权地位,并通过党的恩惠获得了工作。
但是,即使检查员(meós)竭力帮助我们,老板也会阻止他们。他们非常珍惜检查员的声誉,认为他们的工作应该受到羡慕和尊重。这些独立的“陪审团”成员在工会或党组织中站在老板一边,这不是矛盾的。晋升为检查员被视为工人的特权之一,正如足球运动员和其他运动员经常被提高到“质量男人”的级别。
通过在生产中创建等级结构,党被用于满足管理利益。管理者实施控制的代理人,其忠诚不是通过财务利益(至少表面如此),而是通过政治机会上的特权来加以保障的。从最低级别提拔上来的辅助工人,在其职业生涯道路上,目光关注的是提拔他们的人,而不是试图安抚那些灰心沮丧的昔日队友。联合公司的辅助工人没有这样的利益和机会,他们的效忠与操作工牢固地联系在一起。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工会在联合公司发挥的均平效应,在红星厂并不存在。(注释略去)

 188金宝搏体育官网 SZHGH.COM
188金宝搏体育官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