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着一种缅怀的情绪追忆青春岁月,于漫长的历史跨度中全景扫描乡村与城市,在文学潮流的季节轮换中“以旧为新”,思考中国乡村向何处去,并以此清理和反省我们的知识以及所谓的知识界,为在历史大势之中重建一个世界的愿景作准备,这是刘继明的长篇小说《人境》的题中之义。在此,小说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创业史》等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当代再现。这也就像评论者所指出的,“《人境》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对社会主义立场的坚持,而且在于它充分写出了坚持这种思考、选择的复杂与困难之处,让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在今天的承续与新变。”[1]这种文学传统的赓续有力地体现在对于重建乌托邦的执着想像,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我们时代的流行知识的全面反省、批判乃至决裂。
《人境》的理念性特别清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伴随当代史而来的各种人物前后相继的理想主义情怀与乌托邦想像。具体依据时间为序,小说展现了三种乌托邦的想象方式,这也可以见出当代中国人不断求索的心路历程。小说通过马垃,以及他的两个精神导师哥哥马坷与老师逯永嘉的实践与求索,体现出当代精神史中对于理想主义的不懈追求。正是借助这样的方式,小说基于现实,执着地重新想象一种乌托邦,一种桃花源式的理想,或者更确切地说,想象一个更好的世界,从中亦可看出刘继明的勇气、抱负与诚意。
小说之中,主人公马垃的哥哥马坷是一位成长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新人”,他就像十七年文学中的梁生宝和萧长春那样,拥有一切“社会主义新人”的所有美德:大公无私、勤劳坚韧、坚定沉着而富有智慧。他身上所寄寓的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精神深深地烙在马垃的心中。然而可惜的是,正值韶华的马坷因为抢救集体财产而不幸牺牲在火海之中。在此,马坷之死所在的年份——1976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作者也似乎是为了竭力避免马坷的理想主义,去颓然面对那个“不合时宜”的“新时代”,便“不失时机”地让革命的烈焰以其极致的方式吞噬它的孩子。马坷之死无疑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革命理想主义的终结。
在紧接着的新时代中,新的英雄成了逯永嘉这样蕴含启蒙主义与个性解放的“风云人物”。“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人们在破除旧的政治偶像的同时,也在不断制造扑面而来的文化偶像。”[2]而马垃的这位老师所代表的正是这样一种启蒙与自由主义的人生理想。作为新时代个性主义的先驱,逯永嘉被视为某种意义上的离经叛道的天才。他信奉西方的启蒙主义思想和“酒神精神”,放荡不羁、崇尚自我、追求自由,希望在现实社会中建立一个“理想国”,其卓尔不群的性格和狂放不拘的做派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甚至连生活作风问题也是他个人魅力的一部分。他具有敢想敢干的人格魅力,与之相伴随的是蓬勃的生命力,这也是资本主义上升期所具有的活力。他的理想是成为企业家,买下一座小岛,在世界招募一千名男女青年,建立一个理想国,在这个平等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前提是不能妨碍别人的生活。这种自由主义的理想随着逯永嘉的因病逝世而宣告终结。在此,逯永嘉的人格魅力,他的迅速暴富,又因投机而破产,最后患艾滋病而英年早逝的命运,都具有非常强烈的象征意义。这种放纵的疾病正好呈现出自由主义的反讽所在,在此,启蒙的理想主义,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在马垃这里,两位精神导师的理想主义及其结局,分别代表了当代中国的革命年代与资本年代各自不同的象征性命运。马垃的身上凝聚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历程,他和大部分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人一样,少年时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而到了青年时代则转而信奉强人哲学与自由主义。在他的脑中,这两种思想,即哥哥马坷与老师逯永嘉的争辩,成为时时困扰的问题。然而这两种理想都有终结的一天。如果说此前马垃始终是按照哥哥马坷和逯老师指引的方向前行,那么现在,他必须独自对后半辈子的生活做出选择了。面对两种理想主义失败的遗产和债务,马垃这位“精神孤儿”试图在兄长与老师的精神废墟上重新展开一种新的理想主义。他必须在一种痛苦的煎熬中走出一条新路。
“孤独是一种可怕的销蚀剂,在其中浸淫久了,心灵会渐渐生锈,变得颓废起来。所以,人总得找个伴儿,比如书本,比如朋友。有了这两样,他就可能重新振作,将自己的生命与更多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那样,他就算真正摆脱孤独了。”[3]如小说所描述,在经历了人生的大挫折之后,马垃于列文式的孤独玄想中顿悟,他终于决定回到乡村,寻找新的人生道路与理想价值。这位“陷入迷途的幽灵”,开始“沉思”,读更多的书。“他关心的不止是三农问题,包括当代中国的一切矛盾、困境和希望,都不乏真知灼见”。他在哥哥的日记与当年那本《青春之歌》的激励下,向自己的理想迈进。在此,历史的幽灵被重新召回,过往的历史被重新连缀。他把自己变成了真正的农民,与土地融为一体。他选择在河滩上建房独居,种植果园,创办“同心合作社”,投身农业市场,甚至对神皇洲村未来的发展都有自己的设想和规划。如评论者所说的,“回到神皇洲是回到土地的激情,回到一种被历史和叙事淘汰已久的道德和理想,重新回到合作社,萃取新的活力和精气。在马垃的世界中,乡村不是整个社会的赘疣,而是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生长点。”[4]对于多数人来说,马垃是个奇怪的人,奇怪得仿佛不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小说也显示出他对于那个年代的由衷赞美。“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对自己的外表总是那样草率和随便。但正因为如此,他们身上才具有一种朴实、刚健和坚定的品质。他们内心的健康胜过任何巧于修饰的华美。”[5]在此,马垃像一棵树那样,将双脚牢牢扎进土地,直到长成一片繁茂的树林,这是当代文学中一个不曾有过的新形象:“此刻,马垃赤脚站在江堤上,一只手拎着被露水打湿的鞋子,一只手握着铁锨,整个身体浸染在色彩斑斓的霞光里,远远望去,像一棵燃烧的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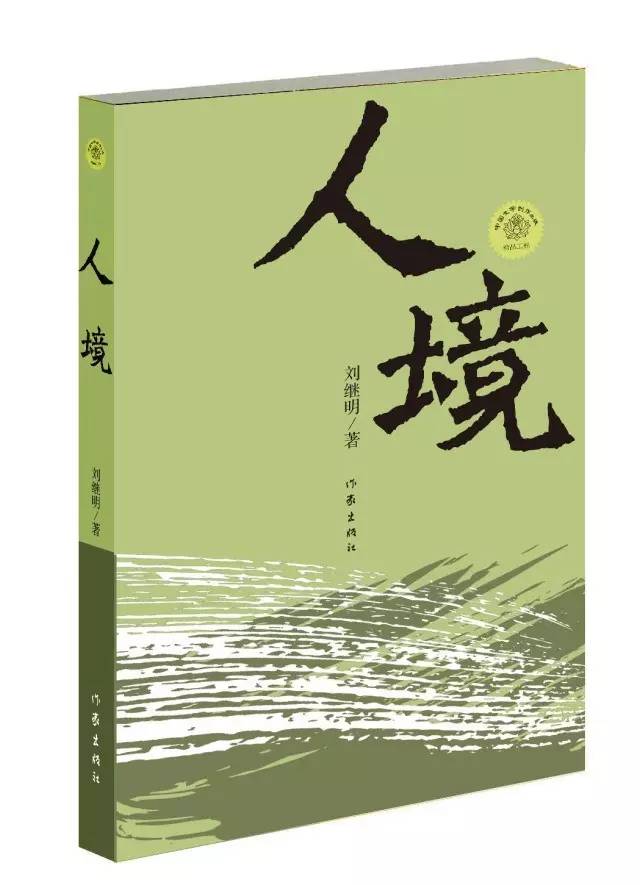
马垃的农村专业合作社,无疑是一种新的乌托邦实践。当然,它与传统合作社的不同在于是从一种经济角度切入的,而非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它面对的是WTO之后,国家取消农业税,以及“资本下乡”成为热潮,这样一个迅速变动的社会现实。借助专业合作社这种方式,马垃得以在乡村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共同体的文化。这个共同体非常温情地容纳了那些社会边缘的人群,它们包括残疾人谷雨,吸毒者唐草儿和乞讨无家可归的小拐儿,甚至还有大林和小林这样的小刺猬。这既是一个经济共同体,最初的目的是将农民的散兵游勇组织起来,以此抵御资本与科技的联手绞杀,“合作社是经济组织,和以前的不一样,根本不改变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制,只不过农户们自觉自愿联合起来,搞一些种植和经营活动。”与此同时,它又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其与社会主义时代的农业合作社相似之处在于,每一个个体都能在其中获得成长和救赎。马垃的理想国最后被资本和权力的合谋所扼杀,这使得他看上去更像是堂·吉诃德式的人物。然而,在这种乌托邦实践的失败中,我们获得一种文化的反思,关于现实与历史,社会总体与权力结构,以及知识与未来多重关系的思考。
小说取名《人境》,书中主要人物马垃也的确有陶渊明的理想,他希望把神皇洲变成桃花源。可是就像陶渊明的理想终不能实现,马垃也是如此。一场洪灾加上楚风集团出手,他的家园就面临灭顶之灾,而乡村迷雾般的前景则让人揪心。不过好在,马垃最后的梦境给了人们一丝希望与安慰。在他的梦中,大雾散尽后的旷野上走来的一个人,这就是下部的主人公慕容秋。小说借此将叙事的焦点从马垃的乡村转向慕容秋的城市。由此也竭力证明这并不是一部单纯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而是试图全景式表现近三十年来中国“城乡生活史”,所以对城市和知识分子生活的描写就显得十分必要。从乡村到城市,从历史到现实,从诗意的情感与追忆,到新的现实剖析与批判式介入,一种完美的变奏,是具有历史容量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当然选择。
在一种整体性的视野之中思考中国农村的历史出路,当它借助自身无法完成时,必须求助于城市知识分子,依赖一种知识的决裂与转型而获得启示。在这个过程中,当下城市的知识状况,及其与权力的关系问题便自然呈现了出来。其中,知识的阶层化及其与利益集团的高度同谋已然成为突出的问题。鉴于这种知识的本质,与它的决裂便显得至关重要。
在此,小说的预设读者看上去似乎就是知识分子,它总体指向的是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的问题。如果说小说上部中马垃的乌托邦实践意味着改造世界,那么下部慕容秋的思想转变则意味着重新认识世界。在此,改造世界的失败,某种程度上是源于我们认识世界的不够充分。这其实也暗含着作者对于慕容秋所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的期待,不敢说这种期待就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新结合,但至少是对知识界的分化,通过知识的决裂来获得一种新的可能的热烈冀望。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上下部分被人批评的所谓分裂感与脱节感,就变得可以理解,因为它正好呈现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这种将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以及资本新贵、官员都囊括进来的总体性,则生动体现出《人境》不局限于一隅,而是对整个历史大势深入思考,“把对一个世界的重建作为愿景”的艺术野心。
作为一个旧家族的女儿和当年的知识青年,慕容秋有着独特的生活经历,而回城之后,她从学生到教师,一直在高校与知识界生活。置身于学界各种问题的讨论之中,慕容秋越来越感受到知识背后立场与情感的重要性。一方面,她对脱离现实、理论空转、丧失人文关怀的社会学研究深感不满;另一方面,她对僵化的学术体制以及学术官僚化、庸俗化也十分反感。她不仅在思考学术研究的突破,也在思考知识分子的意义所系。小说之中,慕容秋一直在思考中国农村如何摆脱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模式和近些年来方兴未艾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因此她也无时无刻不面临着知识的利益与立场的问题。是站在资本与权力一边,还是站在她永远也没法忘记的民众一边,这都是与自己的道德、良心以及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大问题。而要彻底走出这一切,不仅需要一种自我批判的雄心,更要有一种知识决裂的勇气。小说借《何家庄的变迁》作者何为的批评道出了作者对于当下知识界的态度,“中国的某些新自由主义者和主流社会学研究,差不多成了市场经济理论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诠释工具乃至附庸,完全放弃了批判立场和对人的关怀,而一种缺乏人道主义情怀和现代民主精神的社会学研究,除了谄媚一般向国家意识形态提交一份份冷漠琐碎、充斥着各种数据的评估报告,其内在的贫乏和残缺,已经根本无法支撑这一学科应具有的道义力量。”而小说也将更多的反思与批判指向了整个知识界,“社会学研究是否存在某种缺陷或误区。我们是不是被动地将自己捆绑在经济学甚至政治学这辆大车上,而在忽略甚至放弃自己立场的同时,又自动斩断了对其他精神资源给予接纳的努力?总是习惯用经济学、市场社会学等思维方式分析和观察社会,却对哲学、宗教、人文学科等等,持一种冷漠的态度,其结果使我们眼中的中国社会只剩下体制和市场,唯独看不到人在其中的位置了。”[6]
面对这样的时代知识状况,慕容秋的思想觉醒,就必须体现在与知识界的决裂之上,这甚至包括与自己的老师庄定贤的分道扬镳。疲惫不堪的她终于决定从这看不见的网络中挣脱出去,摆脱学术圈的无聊游戏。“不能再在散发着腐朽气息的学术圈里待下去”,她要“回到那座曾经生活和劳动过的村庄,做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这不仅是治学方式的改变,更是精神世界的一次蜕变。于是在那个大雾弥漫的清晨,她向着心中的田野,向着马垃的神皇洲走来。她要与他,与更多的中国人一道,走一条与过去不同的路。
如果说马垃在新时期对乡村“合作化”的坚持与创新的实践,体现出乌托邦重建的历史冲动;那么慕容秋在知识界自由主义泛滥之时对社会主义思想的重新认识与思考,体现的则是对流行知识体系的反省与决裂。这两个方面在小说中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关联,成为有机的思想整体。小说在此其实隐含了对于像慕容秋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期待,他们应该以一种决裂的方式告别那种肮脏的知识界,重走知识分子与工农联盟的新路。小说之中,马垃最初的农村改造失败以后,他定然不会气馁,在他后续新的乌托邦实践当中一定有着慕容秋的位置,而且这一位置将会越来越重要。因此,小说对于慕容秋的期待,其实也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期待,小说期待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与知识清理,以及与流行的知识体系的勇敢决裂,这才是这部小说的最大价值。
(原载《南方文坛》2017年第3期)

 188金宝搏体育官网 SZHGH.COM
188金宝搏体育官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